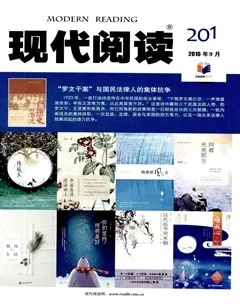一个西方政治领袖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分析
2016-12-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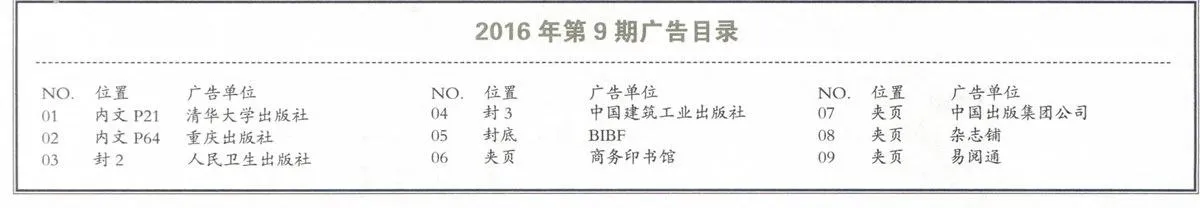

作者施密特为德国前总理,在西方被认为是在经济政策上卓有建树的“伟人”,政治、军事上“杰出的战略思想家”。与许多西方政治家不同,他关注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客观地思考中国问题。
20世纪下半叶,中国为其在世界上的地位打造了一个崭新的基础,使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毛泽东成功地结束了中国长达一个半世纪饱受欧洲人、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凌辱及统治的历史。而与此同时,他也使中国几乎与世隔绝。毛泽东谢世后,邓小平做出了经济上的双重决策: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邓小平是一个务实而理智的政治家,他不受固定的意识形态束缚,没有使用革命的手段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而是采取了许多小步子,但目标明确地朝着一个方向前进。谁要是熟悉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如今再去北京、上海或广州,他将不得不为中国在最近几十年中所取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和技术进步感到惊讶。
过去30多年里,我多次访问过中国,目睹了中国经济的渐进演变。将近20多年来,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年均增长率高达8%,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我也经历了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相应变化。1975年,中国在日本面前,经济上还有明显的自卑感,现在代之而起的是在数十年内赶上然后超过日本的自信心。20世纪70年代,每个中国人被迫学习和背诵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语录,如今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真空。一个由大银行、大公司和证券交易所通过信贷及资本扶持经济的国家,一个由众多大大小小的私人企业家推动经济发展而同时也使自己变得富有的社会,自然不会奉行源自苏联的集体主义思想。
大约在10年前(本书写于10多年前——编者注),中国经济的新活力就使美国人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中国是未来战略上甚至是军事上的竞争对手。对未来军事强国的担心以及对拥有核武器的中国会滥用其力量的担心是否有理呢?目前,我确信可以对这个问题做否定的回答。因为,至少在今后几十年里,这个幅员广袤的国家将面临巨大的国内问题和任务,任何中国领导人都会避开任何可以避免的战略风险。中国必须把国内问题放在首位,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再过几十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占世界第二位。但讲到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在长时间内仍将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有些大城市的生活水平比农村高出几倍至十倍,但是,对于老人和失业者来说,没有一个地方有充分的国家保障体系。每年还有1500万~1600万年轻人进入劳动市场。银行体系因不得不为所有新老企业提供贷款而呆账累累。不仅仅只有这些结构性的问题。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指望,每年8%的经济增长率会延续数十年之久。中国也将面临经济危机,包括能源和水资源供应不足。
除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外,中国还面临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大城市的年轻人,比如在黄河、长江和珠江3个三角洲地区,人们热衷于西方消费标准和新的经济自由,而旧的共产主义观念已经无法适应这些新的现象。当今25岁的年轻人再过10年后,将面临一个用什么准则去教育自己子女的问题。完全可以想象,他们会重新拾起孔子的伦理学说,使之得到补充并适应现实情况。事实上,儒家观念在中国人相互交往中起的作用要比公开承认的大得多。家庭和睦,尊重老人,教育后代,勤劳节俭,乃至当权者对人民负有义务和责任,所有这些都是中国从千百年前传承下来的价值观念。
今天,中国共产党试图在儒家思想、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找到平衡。对于生活在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平衡术玩弄得太长了。特别是那些曾经留学欧美的人士,他们更希望儒教与民主交汇融合。在我看来,中国由于从未有过一个统一的宗教,现代的儒教很可能作为一种世界观,填补当今意识形态的真空。毕竟我们欧洲人不仅信仰基督教和保罗教皇,而且也崇拜希腊和罗马的古典哲学。
有些美国人和一些欧洲知识分子(在德国是一些绿党分子)自以为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有道义上的权力批评乃至激烈指责中国。这些人对于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发展起来的不同文化缺乏尊重。他们也没有意识到,在西方文化的艰难发展进程中以及在他们自己的历史上,也同样有过可怕的阴影。那些批评中国的人,应该想想不过几代人之前发生的对印第安人的灭绝,想想奴隶制,想想美国的南北战争,想想越南战争及纳粹时期。
认为自己的宗教、自己的道义、自己的文化或者自己的生活方式拥有绝对优势,这种信念曾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多次导致流血冲突。伊斯兰的远征军,或者右手拿着战刀、左手拿着十字架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以武力推行基督教的人,就是最突出的例子。南亚部分地区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或者是以色列人与穆斯林之间持续不断的战斗,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例子。伊斯兰激进组织的恐怖主义则是最新的例子。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几乎所有这些冲突都是为了争权夺势,为了使别人的权势和财产消失,而自己的权势则要扩大。几乎所有大的帝国都是按这一模式行事的。在近代,欧洲各国的殖民帝国也是按照这个模式建立起来的。
而中国,这个汉民族的伟大国家,3000多年来似乎是一个例外。也许这正是这个国家能够延续如此长久的一个原因。在我看来,正是由于没有一个统率整个民族的宗教或国教,才没有提出对邻国进行传教的要求。无论如何,在其悠久的历史上,中国这个大国的对外扩张倾向比之历史上所有其他大国都要小得多。
当然,人们会回忆起毛泽东支持朝鲜和越南共产党的统治以及共产党对其他亚洲国家的渗透。毛认为苏联进攻中国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指望中国在人数上占有优势。而面对中国众多的人口,勃列日涅夫的确既尊重也害怕。今天,这样的考虑都已成为历史。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已经不再害怕人口众多的中国。
但是,面对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优势和中国的劳动力会替代本国的劳动力,人们还是害怕的。近几年来中国涌向亚洲市场的工业产品大幅增加,这种害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也应看到,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国家普遍发生金融危机时,北京顶住了为有利于自己的出口而让人民币贬值的诱惑。与此同时,中国增加了从日本、韩国和整个东南亚地区的进口。
然而,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深刻忧虑深深影响着日本。许多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在中国面前有一种隐蔽的、很大程度上是下意识的自卑心理。他们知道,日本的文字、大部分的文化和艺术,包括日本的儒学都要感谢中国人。很多东西是很久以前直接从中国传到日本的,有些则是通过朝鲜传到了日本。除此之外,由于占领过中国的满洲和大部分地方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犯下的残酷行径,日本人潜意识中也有一种负罪感的心理。有些日本人的负罪感可以追溯到1895年对台湾省的占领。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面失败以后,成功地在经济上实现了令人惊异的重新崛起,由此产生了可以理解的经济优势感,从而使文化上的自卑感以及那种负罪心态得到了平衡。最近几十年中,日本的经济发展明显放缓,自信日本优越于世界其他工业国家的心态又消失了。日本人甚至认识到,中国将取代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最近日本又流行一种看法,认为与中国相比较,日本成了一个日渐衰老和不断萎缩的国家。日本面对中国这个邻国,复杂心态依然如故。
日本在世界上的朋友甚寡。部分归因于日本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长达数百年之久的自我孤立,更多是因为日本后来奉行帝国主义政策,给所有邻国带来了灾难,邻国对此铭心刻骨。但关键还是日本人对过去的征服行径和犯下的罪行不愿意承认和表示歉意。在日本,战争时期那一代人活着的已为数不多,并且早已退休。但是,日本政治阶层的多数仍旧还在示威性地崇拜昔日的战争英雄及一些军事领导人,而对战争受害者几乎只字不提,更不提及遭到日本侵略的那些国家的死难者。虽然有一些例外,例如当政时间短暂的村山首相,然而,日本的所有邻国都确信,日本人不愿意进行道歉。韩国在这方面反应最强烈,中国也一样。反日情绪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普遍存在。
对中国人来说,日本与美国缔结军事同盟,更是雪上加霜。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领导人一直谋求同日本关系正常化,尤其是在经济方面,但内心深处对美国借助日本包围中国的感觉并未消失。美国在日本、韩国、巴基斯坦、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驻军和军事基地,以及太平洋第三舰队再加上夏威夷和关岛,所有这一切给中国领导人造成一种中国被美国军事力量包围的印象。作为由此得出的结论之一,中国和俄罗斯于2000年缔结了友好合作条约,这在毛泽东和勃列日涅夫时期是不可想象的。中日之间,不能指望双方关系会有实质性的接近。
20世纪90年代,我与日本一位政治家就日本战略地位进行交谈时指出,日美当时对两国军事合作所做出的附加定义远远超出了日本安全利益的需要。我的那位朋友反对这一看法,声称这确实是为了日本的防御考虑。我问道,谁有可能会进攻你们呢?他对我向他提出这个显得很天真的问题感到不悦,并回答说:当然是中国!接着我又带着一点挑衅的口吻问道:中国皇帝最后一次在什么时候派兵攻打过日本?我的朋友再没有作答。那次谈话在我的记忆中是很具有征兆性的。理论上,日本出现摆脱对美国单方面依附的进程是可能的;但实际上日本没有作这个抉择,因为日本政治阶层的思维方式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对美战争的彻底失败,使日本特别是其政治家在心理上高度依赖美国。邻国对日本的持续仇恨促进了这种依赖性。
中国将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强国,之后还会成为军事强国,这一信念不仅使日本也使其他国家产生了某些忧虑。因此,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早就指出,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美国是最不令人疑心的世界强国。在中国,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低调而谨慎的。而在美国,这种讨论完全是公开的。华盛顿的一些战略思想家相当公开地声称,美国必须尽快建立对整个“亚欧大陆”的控制。“基地”组织的恐怖袭击和国际反恐的共同利益导致了美中关系的暂时平静。但从长远来看,必须估计到,既成的超级大国美国和正在崛起的世界强国中国之间将进行公开的竞争。
中美两国的文化、传统和特点如此不同,而双方彼此的了解和对对方历史的认识又如此缺乏。两国的精英和政治阶层对对方的认识也是十分残缺不全的。双方的相互了解很少,偏见占主导地位。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一旦有个由头,传媒很容易制造敌对情绪。
两个大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具体导因将是多种多样的,居首位的是围绕台湾地区的利益冲突。这个岛屿几百年来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经过半个世纪的日本占领之后,1945年又归还给中国。它很快成了被毛泽东赶走的蒋介石的逃生之地。美国极力支持台湾同中国大陆的实际分裂,而且在军事上给予这个岛屿支持,但对台湾当局要求承认其主权的愿望未予满足。1971年,华盛顿同意将中国的否决权归还给人口为台湾50倍之多的大陆。从美国的角度看,台湾是其在东亚政治势力范围内的一个重要基地。因此,人们认为,必要时美国会以军事手段阻止中国大陆使用武力迫使台湾回归中国。北京则认为,台湾的回归是中国天经地义的权利,而且是至高无上的民族目标。而台湾本身,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则是不一致的。一些人主张谋求主权;另一些人认为,只有在中国大陆达到了与岛上同样的自由和生活水平之后,才可以考虑回归:而许多商人相信统一会到来,因而他们把一部分资本拿到大陆去投资,并且在那里把生意做得很好。
在过去数十年中,中美之间由于台湾问题而不断发生冲突和危机,但也有过缓和时期。今后也还会是这样。任何中国领导人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继续耐心地依靠自己生活水平和实力的加强,同时强烈地坚持统一的权利并警告台湾当局不要提出主权要求。事实上,特别是鉴于中国广泛存在的爱国主义自豪感,美国如果承认台湾拥有主权,可能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从理论上讲,作为一种选择,美国可以逐步减少对台湾的军事和经济支持。但只有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才可能敢于迈出这一步。只有中美关系出现根本性的变化,这样一个步骤才会被认为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在我看来,在未来几十年里,这是不大可能的,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在这期间,预计中国将与韩国和东南亚国家保持睦邻友好关系,并将靠近东盟组织。在东亚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经济成就使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非同寻常的经济活力。最初是日本,然后是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最后是20多年来一直预示要发生的中国的崛起。与此同时,亚洲国家也开始关注欧盟的机构及其统一市场的经验。可以设想,欧盟的榜样将促使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类似拉美那样建立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区。由于这种发展尚面临相当大的顾虑和心理障碍,使之实现估计还要好几十年的时间。
无论如何,今后数十年里,中国有兴趣维持多边组织存在,特别是维护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功能。在这一点上,与欧洲国家、俄罗斯、日本以及几乎全世界的利益明显一致。而这些国家又希望拴住中国。因此,像迄今已邀请俄罗斯那样,邀请中国参加七国/八国集团是明智的,并且要让这两个国家均成为正式成员。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已远远超过加拿大或巴西,以及意大利、英国和法国,2007年以后超过了德国。由于中国是最重要的进出口国家之一,并鉴于其巨大的石油进口需求(仅次于美国占第二位)以及巨大的外汇储备(2003年底时达到4000亿美元,几乎和日本一样多),世界经济希望中国参与制定共同避免危机的战略和参与共同的危机管理。中国也迫切希望全球经济发展良好。
最后,还需要指出,防止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国肯定担心完全被孤立的直接邻国朝鲜可能拥有核武器,至少也同样担心美国和朝鲜围绕这一问题的冲突会激化。因此,中国为缓和局势而继续发挥影响是可能的;而为了世界和平的利益,中国发挥影响也是可取的。
(摘自海南出版社《施密特:未来强国》作者:[德]赫尔穆特·施密特译者:梅兆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