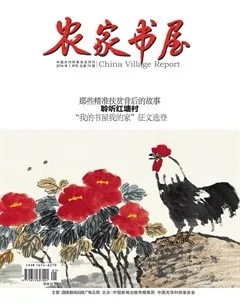回忆吃地瓜叶的苦日子
2016-12-29陶诗秀
日前读到一篇报道,称地瓜叶将成为美国下一个超级市场中极受欢迎的青菜。
刚看标题时,还不知其何所指,因为地瓜在中国北方是指红薯,可是在南方,也指红薯和凉薯。我在农村长大,对二者在地里生长和收获时的长相等情况很清楚,能够区别开来。所以,后来看到文中所谓地瓜叶的插图,立即得悉,这篇新闻报道是指红薯叶,在南方,就是常作烤红薯的那种薯类叶子。
当我弄清楚地瓜叶是啥玩意儿后,不觉蹙起眉来,“美国人真是吃饱了撑的,超市那么多蔬菜不吃,偏要吃红薯叶?”
这一篇新闻报道勾起了55年前我在中国成餐成顿吃红薯叶的一段苦日子。
1960年冬季,我从学校被抽调到基建部的挑土队,填一块大洼地,为将来兴建教学大楼做准备。
每天上午8时到午间12时、下午2时到5时,到学院校园中心挑土。从各个科室来劳动的人数大概五六十个,筋骨磨损和内容枯燥固然不好受,倒不是主要的问题。最难熬的是劳动时间不到规定的一半,就开始感到肚子饿。大家都不吱声而默默忍受着。但是,看得出来,挑土的人流逐渐慢下来,队伍也变得稀疏起来。下班的广播乐曲一响,大家都把箩筐丢下,朝家中或食堂奔去。
我是单身,无家可奔,就直奔职工食堂。按规定,一天有一斤粮票。本来也不算太少,可是,由于菜蔬和副食愈来愈单调和稀少,肉食和油脂绝迹,中晚餐能买到的钵子饭大概不到半斤,在挑土劳动以后,吃下去和不吃实在是差不多。但是,从工地到食堂的多数人,例如我,一定是跑步去用餐。
这时,“上面”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城市居民和机关干部开展“饥饿自救”运动,过好“苦日子”。把“苦日子”的牌子公开打出来,不再高唱日子过得如何幸福,大概可以让口粮不足的群众心理上反感和抗力少些吧!具体如何自救呢?“上面”煞有介事地提出了三个办法。
一、培养小球藻:
意思是指运用一切可以利用阳光的空间,小者脸盆、脚盆,大者在室外开塘,在屋顶筑池,培养“上面”供应的小球藻样品。
据说在阳光快速的光合作用下,小球藻可以把空气中的氮和氧,再加水中的氢合成为蛋白质。又据说这种蛋白质可以养活整个水生物,说明小球藻潜在的营养价值多么大。
等到几个星期以后,小球藻培养到一定的地步,捞出水来,经过一定的风干手续,然后碎化成粉粒,掺和到面粉中,提高其热卡和蛋白质含量。
听说医学院有些大的科室,办起了这种作坊,并且在某一日宣布取得了成果,准备向大家献艺,在食堂展示他们制作的这种小球藻馒头,欢迎大家品尝(当然要交相应的粮票)。
我也去凑了一角,买了这种馒头一试。它外观倒显得饱满,颜色成浅浅的墨绿色,看起来比平时二两大的馒头稍微大一点,据说其热卡能当二两半的粮票。
我拿到手立刻咬了一口,馒头的香味可以说吃不出来,倒是能够下咽,但是有一股明显难以形容、似霉样的味道而不敢恭维。总之,印象不特别好。除非你相信它所含有的热卡,真的值二两粮票,否则没有人愿意买它来代替真正二两粮票的传统馒头。
不过,“上面”有一个说法,声称由于其中所含的蛋白质比平常多,因而比较耐饱,所以有些人还是认为小球藻掺杂的馒头值得吃。
但是我不大相信,所以没有再买。大概出于同样的考虑,喧腾了一阵子,小球藻的热潮很快就过去了。
二、制作稻草蛋白质馒头:
先从去掉稻穗后的干枯稻草中,把其中所含有的蛋白质提炼出来,加到面粉或杂粮粉(如玉米粉)中,做成馒头。
我们没有看到“上面”对群众交代如何提炼的方法,也许有所宣传,我却已忘记,反正只知道有所谓稻草蛋白质馒头在食堂出卖。外观颜色略黄,比粮票相同的货色预计的要稍微大一点,可是并没有大很多,闻起来味道还算正常,香喷喷的,可是吃起来却不敢恭维。因为在口中咀嚼时感觉到一口一口沙沙作响,颇似躺在刚刚用新鲜干稻草为床垫、铺好薄床单的床上,转动身体时听到的沙沙声。可是,用舌尖在口腔内探寻砂子或别的什么东西可以解释声音的来源时,却毫无所获。
口中吃东西时发现砂子,不管吃什么,一般是会立即吐掉的,可是,那时正当饥饿当道,也就饥不择食地把整个“带砂”的馒头慢慢咀嚼一番后吞下去了。这种馒头又不是免粮票的,下次我就从未再买过。
三、吃地瓜叶:
相较于上面两种旁门左道的充饥法,地瓜叶吃起来,倒真算是一种吃法。还是那句话,饥不择食嘛!
我在渝东乡下度过童年,每到夏秋季节,漫山遍野布满了茂密深绿的红薯藤,上面结满了巴掌大的叶子,阳光闪闪。进入秋末以后,阳光闪烁的程度减低,也间或看到一些枯黄的枝叶在其中忽隐忽现。
人们知道收获的季节到了。首先是割红薯藤,然后是挖红薯本身。一些农村妇女背着背篓,弯腰把红薯藤上留下的较完整而色泽健绿的叶子,连茎带藤用镰刀割了下来,抓在手上。又割第二把、第三把……直到一手抓不住了,才把镰刀插到背篓上,站直身子,两只手把手上所有的藤、枝、叶卷成紧紧的一把,往背篓里一甩,然后开始第二轮红薯叶的切割。
她们把这些枝叶和嫩软的藤子割回家,洗都不洗,切碎以后,放到一个大煮锅里,加上足够的水,再或者加上家里的残渣剩饭和泔水余汤,用柴灶的文火慢慢煮。大概大半天或大半夜以后,趁温热的时候,大勺大勺地舀到猪栏的食槽里喂猪。
所以,地瓜叶是猪食的主要成分。我虽然没有吃过,但却是闻着它在煮锅中长大的。它是一种极具特色的“猪食味”。60%发酸的泔水,加上40%若隐若现的红薯味,就很接近个中真情了。
不过,以前农民单干户养猪时,家中餐桌上,多少还有点荤菜,大小地主家养猪时,就更加不用说了。彭德怀元帅批评公社食堂给社员开出来的饭,“连地主家的猪食都不如”,大概就是指这一点。
到了1960年冬季,我们职工食堂公告周知,从某月某日起,职工食堂开始供应炒红薯叶为菜给就餐的成员,不限量。这时,我才知道,食堂当局与经营菜园的后勤部门约定,菜园向食堂免费供应新鲜红薯叶,改善伙食。
原来学院校园内外大量的山坡空地,由后勤部门经营红薯种植,原意是为了养猪。早两年,靠这些红薯养了多少猪,学生和职工打了多少牙祭,我还没有来,所以不清楚。当时是不是还在养猪?我也不清楚,好像很少打过牙祭。
人们面临的饥饿问题可大了。为制备调理猪食而从地里切割下锅的红薯叶,煮熟以后现在改为人食,行得通吗?这就要看人们的口舌如何反应了。
我初步试了几筷子,嗯!还吃得下去。于是,又是几筷子。把上面提到的“猪食味”减去60%的“发酸的泔水味”,剩下40%的红薯叶本味,就不是什么难以忍受的化外之物了。
虽然谈不上好吃,可是如果加点盐和辣椒,那想必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不知为什么没有人想到?不过,事实是,我每餐都对它敞开了肚皮,吃得“饱饱的”。从理论上来讲,总算还是吃进了一些热卡和维生素吧!
这次看报道才得悉,地瓜叶的维他命B6比地瓜多3倍,维他命C多5倍,核黄素多几乎10倍。从营养成分看来,这种组合类似菠菜,但是地瓜叶所含的草酸较少……
唉!如果那时就知道它的营养价值这么高,真该多吃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