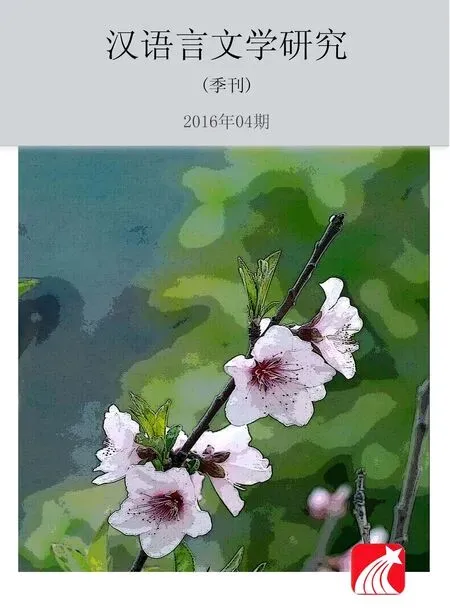视界调整与学术生长
2016-12-29宋声泉
宋声泉
视界调整与学术生长
宋声泉
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渐由对新方法的追求转向新材料的挖掘。人们越发认识到方法应随问题走,否则不是扦格不入,误解丛生,就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然而,对“史料热”本身也该有所警惕。一方面,正如严耕望所言,“能有机会运用新的史料,自然能得出新的结论,创造新的成绩,这是人人所能做得到的,不是本事,不算高明。真正高明的研究者,是要能从人人能看得到、人人已阅读过的旧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这就不是人人所能做得到了”,亦即“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①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另一方面,过度热衷新材料,易流于边角罅隙讨话题,琐碎细小,反而使文学发展的主潮湮没无闻;殊不知遗珠之憾固然常有,然而被过滤淘洗的,除去前人走眼之外,或其本就不那么重要。其实,学术生长自然离不开新方法、新材料,但于今而言,更为迫切的是建立新的视野。而新视野倘若只是在前人的认知窠臼中亟亟增加新角度,则如此看似是看前人所未看,实则萧规曹随,原地踏步。一种新视野的形成需要重新调整研究的焦点与焦距,打开新的视界,提供不断深入探讨的新可能。青年学者李松睿的新著《书写“我乡我土”——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恰可在这个方面有所启迪。
平心而论,“书写‘我乡我土’”并非是一个炫目的论题,“地方性”话语也是老生常谈的字面;但好的研究者恰能于平常中见神奇,层层追问,抽丝剥茧,从丰富复杂的文学史中发现反映时代特征和本质意义的典型现象。在李松睿的研究中,“地方性”即是理解20世纪40年代文学转型的关键词。他敏锐地注意到,被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分割在不同地域和政权之下的作家、批评家,在差异性极大的政治情景和言说环境中,都不约而同地对五四新文学感到不满,开始自觉地构想某种更能为中国普通读者所接受的,并与战争环境相适应的文学表达方式。由此出发,他指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作家,例如赵树理、周立波、丁玲、贺敬之、沙汀、老舍、师陀以及梁山丁等,都特别强调以地域风光、地方风俗以及方言土语等形式出现的地方性特征的重要性,并纷纷选择以这一特征来塑造文学作品的感性外观。在李松睿看来,“地方性特征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作品最重要的风格来源”。他希望解答的是:“为什么20世纪40年代的作家、批评家会对书写‘我乡我土’如此念兹在兹,并在文学表达中将其放置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他们在加强其作品的地方性特征时,究竟想要表达些什么?地方性特征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到底发挥着怎样的功能?”①李松睿:《书写“我乡我土”——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第12页。从这一系列逼问中可以见出,在兵燹摧残、国土撕裂、国人被迫卷入全民战争的20世纪40年代,“地方性”不只是探究文学世界的一个视角,而且成为引领时代洪流的核心命题。
引起笔者思考的是,以往对20世纪40年代文学创作中的地方性的研究,可谓相当丰富,但何以提不出李松睿式的问题?这便涉及如何在研究中调整视界的方法论层面。具体来说,《书写“我乡我土”》至少有两点可资借鉴。
首先,要能跳出惯性思维,避免先入为主,摒弃后设眼光,打破认识“装置”。目前,关于文学的地方性的研究,业已形成两种常见的研究套路。一是区域文化的视角。基本操作方法是把对“区域文化”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划分为书写者与书写对象两部分:在对书写者的研究中,研究者通常会详细分析独特的地域文化对于作家的性格特征、精神气质等方面的影响;而在对文学书写对象的研究中,研究者则往往从文学作品中抽绎出某些对特定的地方风景、乡土民俗的描写,并以此证明所谓“区域文化”对文学风貌的塑造作用。二是乡土文学的视域。在这类研究中,研究者的分析重点,往往放置在乡土小说如何表现具有地方性特色的乡土生活,总是在题材或内容的意义上来理解小说作品中对地方风光、地域风俗以及方言土语等地方性事物的描绘和表现,因此,在具体的分析中往往会着力于呈现不同的小说作品为读者描绘了怎样不同的地域性特征。毋庸置疑,这两种学术思路自有其价值。然而,此亦往往将某种具有整体性的文学史现象割裂开来,然后分别纳入相对成熟的研究框架里,于是很难为读者提供一幅整体性的文学史图景。故而,数量众多的有关地方性的作家作品论,给人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憾,难以构建行之有效的宏大论域。
有鉴于此,李松睿尝试跳出已有的研究范式和框架,以全新的方式深入到具体的文学史现象中去。他力避主题学、意象或母题探究等形式分析的路数,着意将20世纪40年代文学的“地方性”问题,放置在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这三个不同历史语境中予以考察,思考其在怎样的脉络下得以提出、以怎样的方式进入到作家的创作过程中,以及它在作品中发挥着怎样的功能。《书写“我乡我土”》第三章以老舍的小说为中心,勾连了地方书写与国族叙述的关系;第四章对比赵树理与周立波的创作,揭示出解放区文学关于地方性的认识“装置”;第五、六章分别以梁山丁、师陀为个案,先描绘多重关系中的地方风物,后勾勒作为心灵投影的地方,由此说明,沦陷区文学的地方性特征既可以用来帮助作家表达那些不便明言的思考,也可能在那些因苦闷贫病变得意志消沉的作家那里成为心灵世界的镜像。
该书在论述地方性特征成为20世纪40年代小说创作中的总体趋势的同时,也让读者看到,不同区域的作家们是在不同的价值尺度下,或者说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理解和书写文学的地方性特征,而且他们在作品中纳入地方性特征的方式也都不尽相同。李松睿指出:“正是由于文学的地方性特征可以在多种价值尺度下予以理解,使其成为一个意义相对含混的场域。战争年代身处不同政治环境下的作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问题意识、成长环境、知识结构以及气质禀赋等,在不同的脉络中将地方性特征吸纳入自己的作品,并改变其小说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地方性特征成了20世纪40年代最能激发作家创作潜力的艺术元素,也在事实上主导了这一时期小说的创作风格。”换句话说,地方性特征在文学作品所具有的潜力,为不同区域的小说家在不同路径上的写作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可能性。而作家们在创作实践中所进行的多重尝试,也让地方性特征对于文学的意义变得丰富多彩。如此操作,显得别具一格。这便与惯于归纳、满足于大而化之地离析共性的一般研究者拉开了距离,也由此解开了以往加诸“地方性”之上的阐释枷锁,激活出十分广阔的话语空间。
其次,在文学史视野的整体观照下,兼顾文学批评与创作实践,使三者相关联,从而搭起书写20世纪40年代文学思想史的新架构。“地方性”首先是一个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理论范畴和重要概念,但是它的产生与演变始终与一定时期的创作风貌、文学思想潮流有关。《书写“我乡我土”》大体上可以划分为理论探讨与小说文本分析这两个部分。在理论探讨的部分,李松睿以共时性的研究为主,集中分析为何地方性特征对20世纪40年代小说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以及文艺理论家究竟出于何种目的倡导作家在写作中加强作品的地方性特征等问题。在文本分析方面,他放弃了对这一时期小说创作进行全盘讨论的尝试,而是选择以个案研究的方式,从解放区、国统区以及沦陷区选取几位有代表性的作家,对他们的小说创作在这一时期所经历的种种变化,特别是对地域风光、地方风俗以及方言土语等地方性因素的呈现进行考察,探究这些作家在怎样的价值尺度中理解文学的地方性特征,他们为什么在创作中努力加强作品的地方性特征,他们的这种尝试又对小说的形式产生了什么影响。而该书无论是对文学批评的梳理辨析,还是对小说创作的深入解读,都让人产生信服的感觉。这要归功于作者把握文本时的整体感和概括力,从容不迫、娓娓道来又能在关键处力透纸背、拨云见日。
一方面,《书写“我乡我土”》勾勒了文学批评与创作实践在“地方性”问题上的互动与共生。作者辩证地指出,这一时期的小说家的确受到文艺理论界的巨大影响,但其作品对地方性特征的呈现却并没有完全按照理论家的指导进行,而是呈现出异常复杂的面貌。另一方面,又将文学批评与创作实践的勾连放到了文学史的宏观脉络中去把握,由此来具体回答20世纪40年代的作家、批评家心目中理想的文学形式究竟是什么样子。或者说,这样一种能够成功实现文艺大众化理想的文学究竟应该具备怎样的感性外观呢?为什么20世纪40年代的批评家、作家会特别重视文学作品中的地方性特征?这种在一个问题上将文学史、文学批评、创作实践三维进行有机整合的尝试,令人耳目一新。
《书写“我乡我土”》为探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地方性”问题提供了新的支点,也打开了观察20世纪40年代文学的新窗口。然而,掩卷长思,仍有意犹未尽之感。该书以“书写‘我乡我土’”为名,可谓运思巧妙。“我乡我土”出自上官筝(关永吉)的文章。其所谓“乡土”,“并非单纯的‘农村’之谓,乃是说的‘我乡我土’,指生长教养我们的作家的整个社会而言,所以也就是要求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忠实于他的生活,而如此达于并完成现实主义”①上官筝:《再补充一点意见》,《中国公论》第9卷第3期,1943年8月。。这个词汇的借用恰可作为扩容“地方性”概念的纽带,由此辨析地方性与区域文化、乡村的界限,放大“乡土”的内涵。但书中标举费孝通的判断“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并具体解释道:“中国农民因流动范围有限,长期生活在某一个地方,即所谓‘粘着在土地上’,于是形成了各地独特的民间风俗、地域文化以及方言土语等地方性特征。”由此可见,作者潜在预设的“地方性”仍是偏重在“农村”,可是在个案选择中,老舍笔下的地方风物、方言土语却是北京城的特征。“京味”自身确实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可其实如果深入到城市文化的内部特别是市民文化或底层文化来打量20世纪40年代的天津、西安、成都、广州等其他城市,各地的乡土味道也未尝不浓厚。延展来看,该书如果能在剖解“我乡我土”内蕴的基础上,厘清“地方性”与地域、农村、乡土、城市等多个方面的重重幽深相接之处,则会更加自足饱满。
此外,就文学批评与创作实践的关联来看,本书在作家心态方面的深描有失简单;而其代表性作家的选取依据,也未能充分交代。不过,《书写“我乡我土”》毕竟已经打开了新的视界,贡献了方法论上的启迪和重新思考“地方性”的新框架,同时也提供了不断深入探讨的新可能。
【责任编辑 穆海亮】
宋声泉,北京邮电大学民族教育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