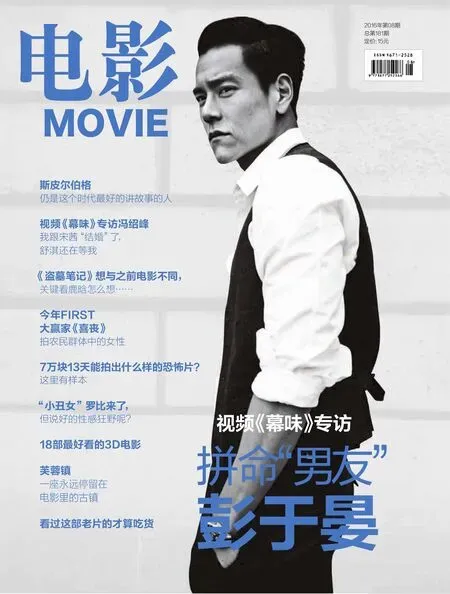当年的女神
2016-12-26王樽
文/王樽
当年的女神
文/王樽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银幕女神,或者说,所有的女神都是时代的产物。在风云际会间,泥沙俱下里,她们于不经意中被锻造而成,或妖冶,或清新,或英姿飒爽,或百媚千娇,总之姿色各异——不关乎阶级阶层、政治信仰,黑白高矮、环肥燕瘦都有可能。而具体到各个女神炼成的机缘,则因人而异,有意栽花的当不在少,更典型的似乎多是无心插柳。新中国早期的银幕上,最光彩照人的女神,当然应属赵一曼、江姐、林道静、金环与银环,或来自苏联的乡村女教师、卓娅等革命女英雄。但在这些女神的光环背后,却有不少观众,尤其是男性观众另有私爱。就像金屋藏娇,别有所属,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他们潜意识里会与主流倡导的女神拉开距离,而心仪那些“灯火阑珊处”、秘而不宣的“女神经”——像王晓棠扮演的国军女秘书,师伟或叶琳琅扮演的女特务;她们或在神秘的“寂静山林”或在险恶的“龙潭虎穴”,一个个丰姿绰约、风骚入骨,虽戏份不多,却以夸张的程式、逼人的性感,点燃了被压抑的微暗欲火,成为无数男人暗恋的“女神”。
不管时代如何倡导,人们会将更性感或更感性的女人视为心中的女神。那个时代的神秘女神,那些被鄙薄被批判的对象,往往以一种隐蔽却不容置疑的决绝,温火攻心,韧性渗透。开始可能没有留意,一旦入眼入心,便再难抵御。
当年的女神,总与匮乏的渴望有关。她们从某个暗地或别处而来,陪伴、沐浴,甚至滋养着我们,驻留成青春的记忆,影响我们一生的审美。有位资深媒体官员曾讲过他的亲身经历,在“样板戏”一花独放的年代,他看过一百多遍《红灯记》,他的偶像就是电影里的李铁梅。当时情窦初开,他将印有女主人公的剧照、海报贴了四壁,常常关窗闭户,独自对着那双眼圆睁、高举红灯的革命“后来人”想入非非。
几天前,我途经深圳一家大超市,竟意外看到电视里正播放电影《龙江颂》,周围衣着光鲜的时尚男女来来往往,更有金发碧眼的鬼佬好奇地观赏。我定定地站着,恍如时光倒流,那“莺歌燕舞”时代正扑面而来。当年的女神出现了——李炳淑扮演的村支书江水英,眉目开朗的单身熟女,如此鲜明,如此强烈,用那个时代常用的词语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那时的我尚在学龄前,还隐约记得一个小胖妞。有天晚上跟父亲去开会,会后放映京剧电影《智取威虎山》,几乎对全剧都耳熟能详的父亲硬着头皮陪我看,我能感受到他的不耐烦。放到“深山问苦”时,片子突然断了,等接好片子再放,那场戏整个给跳了过去。胖妞“小常宝”无端没了踪影,本来无精打采的父亲,忽然来了精神,他不安地左顾右盼,并警觉地自语:“这恐怕是政治问题?”跟下来,剧场变成了另一场“戏”——先是鼓倒掌,接着有人呼口号,质问为何在控诉土匪时断片?为何粗暴篡改样板戏?在纷乱的上纲上线中,电影只好再次中断回放。后来,市委将此断片事件定性为反革命阴谋。小小的技术故障升华成政治闹剧,今天的人也许会匪夷所思,当时的人却觉得十分正常。

新中国早期银幕女神江姐

《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

《红灯记》中的李铁梅

《春苗》中的李秀明

《龙江颂》中的江水英
当时的我坐在剧场,对父亲敏锐的觉悟和政治敏感不仅佩服,简直是崇拜和骄傲。直到很多年后,父亲对改革开放的一切都心存警惕,他带着“阶级斗争”不放松的弦,动辄义愤填膺地诅咒江山变色。这时的我已经长大,曾多次劝导他,但没有什么效果。从父亲身上,我看到了置身畸形时代,一个淳朴正直的人会自觉地变成敏感政治的人。
即使是禁欲的岁月,仍有特定时代的情色想象,虽然那时的电影都不谈爱情。
很多人都记得风靡一时的电影《春苗》,李秀明扮演的赤脚医生痛斥右派或阶级敌人,她挽起库管裸露的小腿,让很多男人心猿意马。顺便一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即《春苗》热映近二十年后,我受某报社总编之托曾在海口的夜市上陪同李秀明夫妇购物。当年的春苗已然是烟火小妇人,她穿梭在各种摊档前,颇有兴致地买了很多特产和服装,她的企业家丈夫几乎一言不发,只是站在一旁随时从大荷包里负责掏钱买单。看着少年时光焰万丈的大明星走在湿热嘈杂的小巷,犹如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女神”飘然走进凡间。
还有文革后期的银幕“女神”杨春霞——京剧电影《杜鹃山》柯湘的扮演者。她是那么秀美,又是那么冷峻,那么亲近,又那么遥远。与几乎所有样板戏中的女主角一样,她在剧中也是“女光棍”——没有家庭,似乎也不屑家庭;单枪匹马,坚贞不屈;永远都与“高”有关——高屋建瓴,高瞻远瞩。她奉旨前来改造湘赣边界的农民自卫军,用毛委员的建军思想改造部队。总能在关键时刻,识破敌人险恶阴谋,成功救出迷途战友,最后消灭匪首“毒蛇胆”,带领部队开赴井冈山。那是属于样板戏的最后绝唱,大导演谢铁骊将其搬上银幕,当时的杨春霞是无数观众的偶像,她英武的眼神、干练的发型风靡一时。在消灭“性感”的时代,她成了无数人心中的性感偶像。
重温这些时代的“样板”,这些近乎没有性别的“女神”。想到她们的不食人间烟火,或太食人间烟火——在台上或镜头前正襟危坐,煞有介事。我常常忍俊不禁。就想,如果把这些“红色经典”当成像《等待戈多》、《秃头歌女》一样的荒诞派作品去看,倒是颇有意味,那剧里剧外的一本正经,构成某种绝对的黑色幽默和反讽。义正词严的滑稽,郑重其事的做作,既充实又空虚,既熟悉又陌生,既严肃又搞笑——比荒诞派更荒诞,比现代派更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