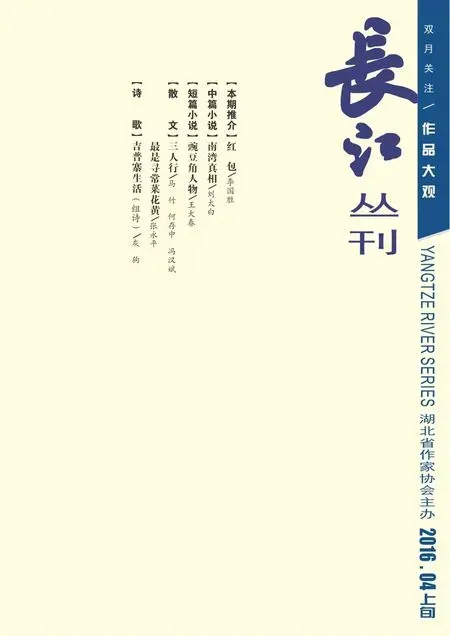灯前谈笑人依旧(外一篇)
2016-12-24伊汉波
伊汉波
灯前谈笑人依旧(外一篇)
伊汉波
伊汉波,笔名伊人。现任黄冈日报《周末》主任、编辑、主任记者。1962年随父母从城里下放农村,经历过农民、军人、学生、工人及商人生活。九十年代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中间搁笔十来年,总计发表作品约八十万字左右。

何大垸,蕲春县漕河镇所属的一个自然村。北依蕲河,南越一个垸村就是漕河县城。该村何姓居多,杂夹张、徐、周、吕、王姓等,伊姓只我一家,且属外来户。
我在何大垸生活了十五年,经历了童年、少年与青年初期,其中许多人和事让人感慨——
1962年,我举家从县城下放何大垸,借居在仅有三家住户的小土墩上的一户人家。住所后面有一片茂密的竹林,穿过竹林,是一条小河港,河水清澈见底。初来乍到,村里小孩不和我玩。为此,家中养了几只小白免。没事时,我就独自带着小白免在林中玩耍。聆听风吹竹叶响,惯看河水静静流。林中曲径,景致幽深,让我也有了喜好独处的一面。
高中时节,我体弱多病,但喜好看书。有两本书对我影响很大。一是线装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手抄本;那发黄的纸,浸着墨香,那凄美的诗句,让人心灵受到震撼;另一是线装枕中记、石头记,同样七字一句,尽管有很多看不懂,但读了就让人欲罢不能。其章法结构与语句措辞,对我后来的写作爱好,起到了一定的导向作用。
为看书,我多次借病逃避上工,因而母亲常被生产队长训斥。我也屡出笑谈,故而常被村人讥讽。
有年腊月间,几个上高中的学生,利用星期天挑堤(现称吹沙),目的是疏通河道,稳固堤基。河中那浮起的一层层水泡沫,天未亮时,我以为是沙子,便纵身跳了下去。冷冰冰的水,很刺骨。我的衣服全被浸透。队长见了,冷冰冰也只一句:“把书带上烤火去!”
高中毕业,队长要我去学用牛犁地。我也觉新鲜。谁知,一鞭挥去,牛缓缓调转头,用眼瞪我,让我有些胆怯。再挥鞭,那牛竟180度大转身,猛地向前一冲,我猝不及防,铁犁片生生地从我脚背划了过去。血流了满地,队长用眼鄙弃我:“看你将来真的吃书去?”
如今这队长还健在,每每见到我,就友好地笑着说:“还见我的怪吗?”我回以淡淡一笑。
1974年,见有很多同学进厂当了亦工亦农的“农民工”,心里既羡慕又复杂,为求平衡,便写了一篇题为“没有大粪臭,哪有五谷香”的广播稿,县广播站播了。这在大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称我还真是一个读书的人。与我同名不同姓的团支书建议我任团支部副书记。期间,我看到一“五类份子”的子弟,也是我一小伙伴,表现不错,但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我心怀恻隐,就介绍他加入团组织。有人说我不讲阶级立场。我说:“都是年轻人,表现好凭么事不能入团!?”这伙伴入团后,为乡亲们做了很多好事,人们都念他的好。他对我,至今还心存感激。
1975年,我在公社水利建设指挥部担任广播宣传员。一边写稿一边用土洋结合的普通话广播,引起很多人笑话,说这是:“河南的骡子做马叫。”公社书记听了,却大加赞赏,说带有乡音的普通话好,亲切。也由此,我的汉语拼音到现在还咬不准。书记姓余,我常念他的好。前几年还听说他在漕河县城挑担卖甘蔗。健在的话,也快90多岁了吧。
次年7月间,在蕲州牛皮坳大闸附近山上炸石时,我经历了人生第一次差点要了命的险情。那天,我兴致好,便跑到工地帮一伙伴扶钢钎。谁知,一哑炮突然炸响。我抬头望去,一块约40来斤重的石头正朝我头顶飞来。我不知所措。危急时刻,舞铁锤的伙伴下意思用手臂挡了一下。我没事,他的手臂却血流如注,肘骨外露。为感激他的救命之恩,我倾其所有送了他2块4角钱。多年后,一帮儿时朋友感叹:“不是人家挡一下,你恐怕命都没了。”一晃40多年了,我始终记得,救我的伙伴名叫何细友。
1976年底,一年一度的征兵活动开始了。村里第一批符合条件的十几个青年参加体检,被了剃光头,一个都不合格。得知这一情况,我和父亲,苦苦恳求大队干部让我参加体检,碰碰运气。
没想到,身体合格了!但大队干部们却一万个理由不让我去。说上年我哥被保送上学,下年我又要参军,在农村没这好的事。就我家情况,两个男孩,外出一个可以,但另一个必须留在队里干活。并说我家走后门,他们告到公社与县武装部,想把我撤下来。村里一些年长者也说,他不能去,去了就不会再回何大垸了。好在公社武装部挑担子,在全大队只一个指标的情况下,追加到四个指标,终于让我穿上了军装。
大队见实在拦不住,又提出了一个非常苛刻的条件:“每年扣除你家90个工分。”这在当时,可是一个成人的全年劳动收入。我的老父亲二话未说:“扣吧,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让他去当兵!”看到我穿上了军装,村里不少人又说:“是城里人的命,谁能拦得住!”民兵连长也提出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要求,要我送一个用子弹壳焊接的台灯座给他。这种台灯座在当时很流行。
没想到,我回地方工作多年后,原大队几个负责人为土地纠纷找到我,我通过关系较好地作了协调,达到几方都满意的效果。事后,他们都说:“以后村里有人能外出的,还是让外出为好。”前嫌冰释。可以说,任何人都是念旧的。
刚到部队不久,村团支书就帮我介绍对象。人情不能却。我便和女方有了书信往来。女方条件不错,人漂亮,其母是党员、大队干部,对此,我很满意。但不知什么原因,本可成就一段美好姻缘,却戛然而止。待十几年后,她请我吃饭时才获知,我每次去的信都被其母藏于墙壁缝隙之中,以致双方误会,各听天命了。再见时,物是人非。而今的她,已是县市人大代表,家产近亿万。说什么姻缘天定,但有时也是人为的。
何大垸的风水并不好。多少年来,全村没出一个处级官员,也没产生一个博士或者教授。我母亲去世时,我的一个县级领导朋友前去吊唁,乡亲们惊诧:何大垸第一次来了这么大一个官!但生活在这里的人,天生的不卑不亢。既不追名,也不逐官,我在媒体工作近三十年,也没一个人找我为其发表一篇文章或写一篇颂扬之作。受其影响,我多次回老家,也没去拜访过父母官。乡亲们恪守:你当你的官,我打我的砖。天广地大,世事轮回,该我有的自然有,不该我有的也不去强求,更不去计较那些恩怨情仇。一切都是那么淡然平和。
现在的何大垸,有很多好田好地被开发被利用,也建起了不少的别墅,商品意识也很浓厚。我家原居住的小土墩早已不知去向,小河港填平后建起了楼房。对此,有人担心,有人叹息。但大多数何大垸人想:田地减退,人员外流,物价飞涨……这也是一种新的自然现象。读了一些古书的何大垸人生就了这样一种自然现象观:“改变现有的面貌叫创新,再将创新后的面貌加以改变,亦叫创新。人类不就是在这种改变中前行的吗?”生活在这里的人一切都顺从自然,随遇而安。
何大垸的人淳朴厚道讲情义。我回地方工作的第一年,去看望原大队书记。此时他已闲赋在家。看到我们,他一声长叹:“你们兄弟不错啊!”后来,在我父母先后去世时,他忙前跑后,不遗余力帮我家做事。我很有些过意不去,不说年纪那么大,他可毕竟曾是大队书记呀!他来黄州时,我简简单单地招待了一次,陪他喝了一点酒。他回到何大垸后,见人就说我的好。我很感动。后来我就想,人是会变的,人也不能太过计较过去的一切恩恩怨怨。遗憾的是,他因病去世时,我未能前去送他一程。每念及此,我便惆怅不已。
何大垸有名声,其中有两次叫得响。一是“文革”期间,当有人要进垸武斗时,村里百姓将四周的篱笆都通上电,将那些想冲进村武斗的人拦在村外。此举轰动全县,后来再也没人敢到何大垸惹事生非了。二是近年在此建造了一座庙宇。听说此庙香火旺、签卦灵。十里八村的乡邻多来此处烧纸求神,祈福还愿。甚至还有不少国家公职人员也前来求签问前程。其主持多年前还是小人物一个,据说在名山古刹修行了几天,领悟了禅意,回乡后就修造了这一庙宇。我疑惑的是,何大垸前因“文革”有名,后因神灵叫响,是人力所为,还是风水轮到了呢?
何大垸,还有我的几分自留地。我要留着,那儿给了我太多太多的记忆。
中秋思故人
明月似镜,往事如昨。中秋到了,更让我想起三十年前在大西北结识的陈道瑞大姐及其一家人。
陈大姐原本南京人,因支边来到甘肃张掖地区西关农业机械厂,时任技术科科长。
1979年,全国风行军地两用人材培训。我所在部队的处长与大姐的老公赵工是同学,赵工时任该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我在该厂先后学过焊工、车工、刨工、钣金工。该厂见我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与写作爱好,便借我进技术科学习新疆双铧犁设计、描图、绘图。就这样我被安排在陈大姐手下。
技术科原有四人,二男二女,加我五人。我作为一名战士进去干事,规规矩矩,眼不斜看,话不多说,又因性格温和,陈大姐及技术科所有同志对我都格外关照。
那时北方的生活十分艰苦,大多以粗杂粮为主,面粉极少,大米更是稀罕,让我这来自南方的人生活很不习惯。为此,每当陈大姐家吃大米饭,必要我去。尤其吃拉条子(类似现在的炸酱面),一定要我去打打牙祭。她家五口人,一个月面粉指标也很少。每逢我去,她总是让赵工单独为我做“拉条子”吃。而她总要炒上几道小菜,诸如山东大葱炒鸡蛋、肉沫、面酱,烩在一起作为炸酱面臊子。每当我吃时,她都让自己的三个孩子离开。老大叫赵静,女孩,老二叫赵虎,男孩,最小的女孩叫赵璇,十来岁。菜一炒好,赵静便翕动着鼻子对赵虎说:“斧子(即虎子),你看爸妈又拉拉条子伊福福吃。”北方把“叔叔”叫成“福福”,把“一毛钱”叫成“日毛钱”。这时小璇璇就上前去问她妈妈,能不能让她尝一下菜。回答是肯定不行的。那拉条子味道真是好,让我一生难忘,以致现在我还喜欢那种又粗又有嚼劲的拉面条。久而久之,小静与小虎常对爸妈提抗议,说爸妈老偏向伊叔叔。有时我也住在大姐家,一次,她发高烧,我摸了一下她的额头,滚烫,就这样,她还坚持下地为我做饭。
技术科有位年纪与我相仿的女同事,名叫马兰,其父是该地区行署专员,其母是兰州市一家银行行长,均为抗美援朝战斗英雄。大姐见我尚无对象,便有意试探马兰对我印象如何。得知马兰对我非常有意时,便全力撮合。她与赵工及其他几位厂长商量,想将我留在该厂,并与部队首长及马兰之父商定,欲将我转往地方工作。后因家里执意要我回去,我结束了在大西北的工作及那段即将成熟的感情。
我本是从城里下放到农村,又从农村到部队,那时的确想找一个吃商品粮的工作。陈大姐获知我的想法后,竭力从三方面为我想办法。一是让我留在该厂;二是让我参与西北食品罐头厂筹建工作;三是让她在江苏老家的弟弟想法,将我调往南京。由于在该厂断断续续呆了近四年,以致不少战友到现在还说我,根本没在部队呆几天。
西北气候,极为干燥,而我那时的身体又极为羸弱,尤其易患口腔溃疡,吃不能吃,喝不能喝,连说话都十分困难。陈大姐看了,心里十分难受。她家没大米时,便向人借,用上好的大米,再将红枣剥皮去核熬粥让我吃,以补身体。那份细心,一般人是做不出来的。很多战友看后,都感慨我怎么就碰上了这么好的人。并经常借故来看我,有的甚至还借机与我住在大姐家。
1983年,我赴兰州军区防化教导大队及西北师范学院学习。期间,我上呼吸道上火,严重溃疡。在军区门诊部涂抹几次碘甘油,不但不见好转,反而愈严重。最后被送到兰州军区总医院检查,被诊断是恶性肉芽肿,即咽喉癌。同病房四人,一人白血病,一人胃癌,一人鼻窦癌,我是“咽喉癌”。进院才三天,患白血病的病友就死在手术台上,年仅十八岁。而按部队有关规定,特殊病人院方要留二个与外界的联系方式,一是所在部队,一是至亲的人。我二话没说,留下了陈大姐的联系方式。而家里,我一直没有谈及这件事。
住院一个多月,病情不见好转,医院也准备放弃治疗。不料会诊时,一小护士随口说了一句,用四环素试试吧,反正死马当作活马医。谁知,就是这四环素,竟让我的病情疾速好转。刚有起色,陈大姐便委托在兰州工作的朋友前来探望,并为我熬了一罐稀饭。那是我病情好转后,第一次能咽的稀饭。下病危通知期间,我总在想,陈大姐一家对我这么好,我还没来得及报答,就一命呜呼,实有不甘。后来陈大姐说,你好就行了,不用说什么报答不报答。
1985年,我从野战部队调回黄冈军分区。离别时,陈大姐亲手为我做拉条子。全家人没一个动筷子,全家人就那么看着我吃。大姐说:“多吃点,以后就很难做拉条你吃了。”赵工说:“回去后多联系啊。”几个孩子左一个“福福”,右一个“福福”,叫得我的眼泪不自觉流了出来。我不知道,此去经年,多少年后才能见面。
我回黄冈后的一段时间,我们之间还保持着书信往来。不过,陈大姐一家对我调回黄冈一直不看好,认为我留在西北作为可能更大些。尤其得知当时我所处的环境不是很理想时,更是希望我能回到张掖,与他们在一起工作,并作好了各方面的准备。事后从西北来看我的战友也多次证实了这一点。虽然如此,她还是在信中对我说,把日子过好就行了。万一有难处,可以去西北,也可以去南京工作。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写了一些文章在全国各地报刊杂志发表,大姐得知后,很高兴。经常在不同的报刊杂志里找我的文章,向工友们推介,说我写的文章很好看。
几年后,全国厂矿企业实行体制改革,陈大姐所在的张掖西关农机厂也在其中。不知是因为改制,抑或其他原因,陈大姐给我写了最后一封信,说是社会形势有些变了,你要多保重之类的话,就再没消息。这封信我一直保留着,想她及她家人时,我就时不时拿出来看看,一看心里就有种被撞击的感觉。
前几年,有陕西的战友来看我,说很多战友想找陈大姐。战友们以为我一定有陈大姐的联系方式。其实,很多年了,我一直没得到她任何信息,心里很难受。我的一位连首长调回陕西,后任省军区副司令,我向其打听陈大姐,他只是听说在延安,后我又从延安媒体打听,也无消息。如今已有三十年了,我与陈大姐不曾再谋面。
现在,我也快退休了。每逢闲暇,就无端地想起这一家人,想起陈大姐。家人曾多次劝我,实在不行,就去央视《等着我》栏目求助。想来陈大姐现在也七十有五了,身体怎么样?儿女怎么样?三十年来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一直让我牵挂不已。做人讲良心,处事重情义。月满中秋,我再一次对家人说,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再见一次陈大姐。不为其他,只为这三十年的念想,从未停息。
窗外,月明如洗。陈大姐,您知道我在想念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