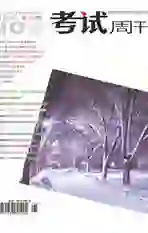从电影到话剧的《风声》
2016-12-21杨文华
杨文华
摘 要: 由同名电影改编的话剧《风声》,在电影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导演经过加工处理,把剧情集中在以甄别“老鬼”为出发点,意在塑造众多的舞台形象,从而体现出一种精神、一种信仰。
关键词: 话剧《风声》 信仰 人物形象
格里菲斯说:“电影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娱乐形式,成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精神力量。”[1]安德烈·马尔罗说:“电影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是世界第一艺术。它能依靠画面消除语言不同所造成的隔阂。”[2]贝拉·巴拉兹说:“电影艺术的魅力就在于:它将把人类从巴别摩天塔的咒语中解救出来。现在第一个国际语言正在世界所有银幕上形成,这就是表情和手势的语言。”[3]因此,作为“第七艺术”的电影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观众的喜爱。然而,从世界电影的发展史不难看出,电影的诞生却是以戏剧为基础的,正像安德烈·巴赞所说:“我们至今仍然把戏剧奉为一种美学的极致,认为电影也许能够以令人满意的方式接近它,不过,充其量也只是戏剧的谦卑的仆从。”因为“戏剧给我们留下的愉悦比起看完一部好影片获得的满足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更令人振奋、更高雅的东西,也许,还应该说,更有道德教益”[4]。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现在观看戏剧的机会越来越少,但有幸的是笔者曾欣赏到由云南艺术学院戏剧学院2013级戏剧导演专业的学生表演的话剧版的《风声》,在观看话剧《风声》之前,对于这部戏的整个印象还只定格在电影版的《风声》,然而通过观看话剧《风声》后,笔者感触最深的却是导演在艺术风格和主题的表现和人物的刻画上都有很大的差异。
一、话剧注重刻画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从电影与戏剧的表现形式看,它们属于一种表演艺术、视觉艺术及听觉艺术,不同的是,电影可以跨越时空的限制,是自由和开放的,而戏剧因为受地点、时间、场景等因素的限制,所以在表现手法上,戏剧冲突更集中,就如话剧《风声》来说,它在通过对人物细腻感受的处理,心理活动的铺排比电影更胜一筹。
首先是反派人物肥原,他是整部剧中的一个核心人物。他开始是以上帝视觉观望着五个嫌疑人,下好一个个圈套,让他们去跳,看着他们痛苦、挣扎,甚至自相残杀,作为一名日本军人,却是让人感觉他的残忍、可恨,那么他真的是至恶之人吗?人们都说人性本善,而能让一个人由善变恶应该是有根源的,我们追溯小说原著,不难发现在小说的故事背景中交代过,肥原曾是个记者,对中国文化十分了解,多年前与新婚妻子一起来到西湖边上小住,不料夜里被中国人袭杀,由此看来,他后来的一系列行动就可看做是复仇。在电影中,肥原的祖父因自杀而被同僚看不起,因为他不想以代罪之身回国,最终选择最极端的道路证明自己。但是,不管是这两个故事中的任何一个,这种人情都是情有可原的。我们并不能说这种“情”是不好的,以至于肥原所作所为是有道理的。再者身为日本军人的肥原,揪出“鬼”是他的职责所在。侵华这件事本身是绝对错误的,但从个人看,处于这样的大环境下的肥原或许一切都是符合逻辑的。
其次是两个女性人物:一个是作为母亲的李宁玉,也是整个故事最终的“真相”,她是话很少的人,在外人眼里是个浑身是壳的女人,冰冷,坚硬,又优雅。她把自己感性的一面留给家庭,也留给顾晓梦。只身身处敌营,充满危险的未知数,同为女人的顾晓梦给李宁玉带来些许安慰。毕竟是女人,心里总有一方柔软,两个女人相互取暖。但实际上,所有的一切都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纯真。裘庄里的每一个人都在伪装自己,把自己藏在纯良的人皮之下。钩心斗角,静观其变。而另一个女性人物顾晓梦,她展现给大家的是大大咧咧娇气的富家千金,但真相往往是出人意料的,她也是个“鬼”,是藏匿于人群之中,隐蔽的在老鬼更深处的“鬼”。军统出身的顾晓梦确实有一定的胆识,甚至有些巾帼的意味。两只鬼相互依偎着、伪装着、猜测着、撕咬着,这种暧昧不明的情感是耐人寻味的。褪去身上的那层皮,如果不是站在两个不同的阵营,那么或许,她们真的为彼此付出了真感情。所以,正如评论家李敬泽称《风声》为“人类意志的悲歌”,《人民文学》则评价“它探索人的高度,它塑造超凡脱俗的英雄,它以对人类意志的热烈肯定和丰沛的想象,为当代小说开辟了独特的精神向度”。
最后是剧中的另外三个男性人物。对于剧中白小年的死,笔者认为是意料之中的。笔者猜测,或许白小年对张司令的“感情”并不纯正,或许是白小年这种遭人唾弃的伶人在惨痛之际被张司令收留,为了生存,八面玲珑地讨好张司令。或许他对张司令确实有些知遇之恩,但更多的是为了依附权势而活。而金生火和吴志国与白小年比较而言就简单许多,吴志国一心为党国,在他看来自己是正义的,如果不是投错了政府,那么也许他会成为英雄式的人物。金生火是个胆小的人,靠着裙带关系混的一官半职活得狗模狗样。这样的人不存在忠诚,于他而言,命和钱是最重要的。
二、情调独特的话剧风格
德国美学家康德说:“美是一个对象合目的性的形式。”[5]《风声》这部话剧展现了一种极致的风情,这种风情是一种氛围,个人的情调和整部戏的情调。这就要求从人物出发,从性格中散发人物的独特性。多层面多侧面地表现人、物、事,然后再统一到这部戏的主旨和意念上来。每个人物都不能单从概念出发,在大环境背景下,所处的立场,迫使人物必须做出的行动,他们各自的人情是塑造人物最好的调味剂。国家、家庭、自我、如何调和他们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这部戏的人物性格更甚人物关系。众多方面,进行多棱角的折射,综合起来就构成整部戏的风情,在笔者看来这部戏有着二三十年代上海女人的风情,有着昭和时代日本的状态,也有着红色年代中国人的反抗与逃避。这部戏充斥着危险、迷离、煎熬,无奈、冰冷、残酷、猜疑,也掺杂了些许美丽、柔情,这种谜一样的意味不言而喻。
三、话剧的主题强调个体的塑造
电影《风声》虽然是一部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主题也是小说作者麦家所言的昂扬“信念”主题,但在今天这个时代却俘获了众多影迷的心,这足以说明这部电影绝不是仅仅关乎历史那么简单。正如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童刚所言:“影片《风声》在谍战片类型的包装下,正面的内核价值被成熟的类型模式所包裹,获得了观众的普遍好评。”电影《风声》的导演在电影中对于整个故事的注解就如同顾晓梦所说:“民族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我不怕死,怕的是爱我者不知我为何而死。我的肉体即将陨灭,灵魂却将与你们同在。老鬼老枪不是个人,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对于电影中的故事,导演把主题定义到一个超乎自我价值的精神层面,完美地塑造大义凌然、视死如归的英雄式人物形象,从这些人物身上折射出社会大环境下的社会价值所体现出的个人价值,这是种令人敬佩的奉献精神。而笔者所观看的话剧《风声》的导演并没有把这种英雄主义精神主题带到话剧中,而是把主题定义为个人。话剧《风声》通过对硬汉十足的剿匪队长吴志国,娇娇富家千金顾晓梦,高雅清冽的破译科科长李宁玉,胆小如鼠的处长金生火,依靠他人而活身份最低劣的伶人白小年,金风使舵的汉奸特务处处长王田香的塑造,反映了他们所代表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立场,在伪装的面具之下所被做出的种种选择。
总之,话剧《风声》的改编及演出还是成功的,整个故事的脉络清晰紧凑,悬念层峦迭起迷雾重重,它告诉我们,《风声》不仅是一场话剧,还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正如卡努杜所说:“视觉戏剧的奥妙和伟大就在于它运用光的无限变化来表现整个生活,包括人的各种思想感情、意愿冲突和胜利,它只把人和物体当做光的具体形态来理解并且根据剧情的主导思想来和谐地安排它们。”[6]
参考文献:
[1]格里菲斯谈电影[A].电影文化丛刊[C].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2).
[2][美]刘易斯·雅各布斯.美国电影的兴起[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7).
[3][匈]贝拉·巴拉兹.可见的人电影精神[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16).
[4][法]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185).
[5]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6][意]卡努杜.电影不是戏剧[A].李恒基,杨远婴.外国电影理论文选[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4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