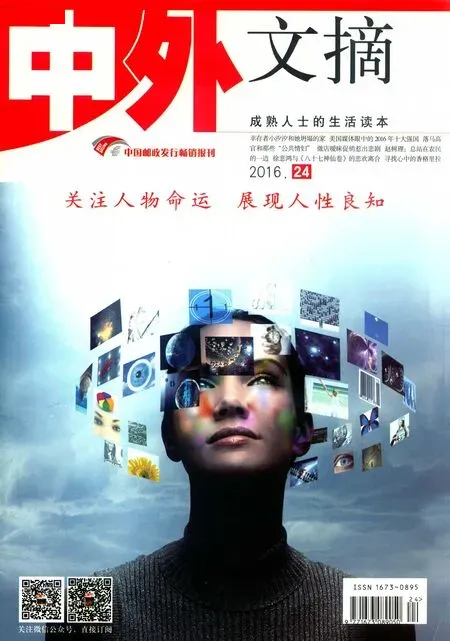赵树理:总站在农民的一边
2016-12-14李少林
□ 李少林
赵树理:总站在农民的一边
□ 李少林

1970年秋,“文革”进入了第五个年头。从“文革”开始以来,著名作家赵树理就受到了山西各地造反派连续的粗暴批斗和迫害。这种“革命行动”绝不仅仅是触及灵魂,而且实实在在触及肉体。
1967年太原五一广场,赵树理被造反派打断2根肋骨,之后一直得不到正式治疗,自然愈合后骨骼变形,带来了长期的痛苦;1969年晋城,造反派特意把3张桌子摞起来,让他站在上面接受批斗,摔伤后造成髋骨骨折,64岁的衰躯雪上加霜。生命的最后几年,赵树理连平卧睡觉都已不可能,晚上常常只能以坐姿靠在桌子边休息。
这种度日如年的日子,使得这位农家出身的老人,已近油尽灯枯。但江青不会放过他。赵树理的名气太大,彻底批倒这一黑典型,可以为其造反业绩添加重重一笔。1970年6月,山西省委秉承旨意成立了赵树理专案组,对这个几近衰竭的老人继续施压。3个月后,一代文学巨匠、曾被毛泽东称誉为“人民作家”的赵树理,默默含冤死去。8年后,他的案子被平反昭雪。
流浪的萍草生涯
赵树理生于山西沁水县尉迟村,母亲是民间宗教清茶教的虔诚信徒,所以他小时候不吃肉,性格自制,功课一直是村中的翘楚。在成名之前,赵树理的经历非常坎坷,比之于其他这个级别的著名中国作家,可谓最为不幸的一个。
1928年,赵树理由于秘密参加中共和闹学潮,被长治第四师范借故开除,其后8年一直没有稳定的生活。他做过多种短期的工作,奔走于城乡之间,成为那个时代文化边缘群体中的一员。
赵树理坐过监牢。由于被人举报为漏网共产党,他被关进自新院一年多的时间。那里有图书馆让犯人读书自新,因国民党特务不学无术,其中居然有不少名字上不显眼的左翼书籍。赵树理在自新院读到了不少红书,受了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洗礼,为今后投身革命做了铺垫。
8年中,赵树理断断续续地做过几回乡间小学校的教师,但都没有做长久。在教学上他是把好手,他教过的学生在多年以后,仍对他的作文课赞不绝口。但他倔强的个性、反封建的态度,常会得罪地方的封建势力,使得他做不成一名冬烘先生。期间,他还打过各种零工,写作卖文,给省政府当录事,给中学教师抄写讲义,给文具店糊信封……挣的一点钱也仅够在外的吃住。
甚至,一度赵树理还演过电影。1936年,在西北影业公司的演员训练班中短期培训了一段时间后,他得以在两部电影中跑过龙套。虽然后来没有做成演员,但多年后,他的小说《小二黑结婚》《登记》《三里湾》等,多部被拍成了电影。
在最落魄时,赵树理曾自杀过。1934年经人荐举,他去河南一家文具店当店员,到达时发现在城市改造中店铺已经拆除。怀揣4个大洋返回的路上,被一群专业打劫的盗匪盯上……因此后来患上了“迫害狂”。由于总感到被人跟踪和逼迫,5月的一个早晨,他在太原中山公园欲投湖自杀。此事当时被报纸报道过,还被另一位文人写成短篇小说《水警》,发表于民国时期国内影响力很大的“百年老刊”《东方杂志》上。
1928年至1937年,赵树理几乎一直在漂泊、流浪,属于社会的边缘群体。事后,他把这段漂泊时光称为“萍草生涯”。现在常有把民国浪漫化的倾向,其实那时战乱频仍,底层人民极端贫困,没有成名知识分子的生活,比之现在的北漂要狼狈得多。文化边缘人的群体为数相当可观,许多后来著名的文化名人,都曾有过落魄的失业、漂泊的经历,如丁玲、杨沫、沈从文、郁达夫等。但即使在边缘文化人的群体中,赵树理都属于那最边缘的一类。
别人多是在北平、上海等大城市,处在一个较好的文化环境中,而赵树理8年多的漂泊生涯,基本是在山西的乡村地区,他断断续续的几次教师经历也都是在乡镇小学校,能接触到的文化资源很少——这一点事后来看,对于形成他独特的源于农民、为了农民的写作风格,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如果他像湘西的沈从文那样是在大城市闯荡,在文化环境的影响下,也许他的文字也会形成民国那种文艺腔,绝不会成为解放区文艺的方向。
赵树理的失业、流浪时间之长,也超过大多数同时代的主要文化人。困苦的经历给他带来对底层人民的同情,他的作品都是写农民,也是有意识地为农民写。长篇《三里湾》完稿后,他不是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这样的国家一流大社,而是选择了通俗读物出版社来出版,因为这家出版社面对普通读者,发行量大,印刷成本相对低一些,定价也就低,农民能买得起。
赵树理成为著名作家后,曾经说过,他不想上“文坛”,只想上“文摊”,流露出他的草根情怀:“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小唱本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就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这是我的志愿。”
“赵树理方向”
直到抗战爆发,赵树理参加了牺盟会,他才真正结束了多年的失业和漂泊生涯。之后,他被分配到党的宣传部门,编辑过《中国人》《黄河日报》等报纸的副刊,他干得很不错,战争年代组稿不易,版面上二三十篇文章常出自他一人之手。他写小说、诗歌、快板、民谣、笑话,所编副刊贴近民众,非常受欢迎,常常是每期副刊一出版,贴在城门洞处,周围挤满了观看或者“听读”的老百姓。他的写作风格正在逐步形成。同时,他的工作有一半时间要深入基层采访报道,与农民深入接触。对农民的生活更加熟悉,在这样的积累中,一个属于他的时代正在到来。
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提出革命文艺需要更多地展现农村、农民的生活。1943年成为文坛的赵树理年。一年内,他的两部后来被编入中学教科书的经典之作诞生:《小二黑结婚》上半年完成,仅仅几个月后,《李有才板话》也脱稿了。这个多年的文化界的边缘人,几乎是旋风般地成了文坛的风流人物。
提到赵树理,不能不提《小二黑结婚》。这本书的出版最初其实并不顺利。出版界的人对这种充满乡土气的作品很不认同。由于赵的上级杨献珍(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做过中央党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向彭德怀极力推荐,这才有了彭总那段著名题词的出现:“像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在一位哲学家和一位军事家的鼎力帮助下,才催生了这部里程碑式的不朽名作,在这个过程中,来自文学界的认同力量反而是最小的。
当时,一部小说在边区的销量顶多二三千本,而《小二黑结婚》仅仅在太行区就销行了三四万册——而当时太行区的人口还不到500万!数以百计的剧团用不同的地方戏将《小二黑结婚》搬上舞台,受群众欢迎的程度达到火爆,对边区的移风易俗产生了巨大影响。有人指出:从五四运动以来,还没有任何一本新小说能在农村引起如此大的轰动。
而就在《小二黑结婚》在边区传遍千家万户的同时,赵树理又完成了他的另一部经典之作《李有才板话》。又是一个出版奇迹!此书前后被北京、上海、香港等地的多家出版社转载再版达38次之多!此书是他和真实的“李有才”在一个炕上睡了半年写成的。其原型人物官名就叫李有才,后来一直活到了20世纪90年代。赵树理的很多作品都有明确的原型,如岳冬至(小二黑的原型,真实生活中被村干部害死)、李有才、孟祥英、潘永福等。
赵树理开创了新文学的一个时代。之前,“新文学的圈子狭小得可怜,真正喜欢看这些东西的人,大部分是学这种东西的人”;“新文学只在极少数人中间转来转去,根本打不进农民中去”。而赵改变了这种面貌。有人这样看赵树理的贡献:他“突破了此前一直很难解决的文学大众化的难关”。——这是他的同行,荷花淀派主将孙犁的评价。
赵的热心读者并不仅仅是农民。上至毛泽东、邓小平,军事家如彭德怀,文坛大家如郭沫若,都读过他的作品并做出过很高的评价。民国才女林徽因是出身名门的“娇小姐”,但她就向朋友热烈推荐读赵树理!
之后的几年,《孟祥英翻身》《李家庄的变迁》……赵树理的佳作不断涌现。由于其作品的巨大影响力,自发形成了近代文学上的一个重要流派——山药蛋派。鼻祖是赵树理,重要成员还包括马烽、西戎等。其与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一起,成为写农村最大的两个文学流派。以一人之力而推动形成重要的文学流派,这在近代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
他的创作被官方认为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1947年,《人民日报》发表了陈荒煤的文章《向赵树理方向迈进》。自从毛泽东提出“鲁迅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后,能够享有“方向”这种极高肯定的人,除了赵树理几乎再无旁人,“郭老茅公”都没有获得这样的“待遇”。这个曾经多年流浪、找不到稳定工作的人,就此走入了中国近代文学的殿堂。赵树理有3个公认的头衔:毛泽东亲自定的“人民作家”;作协大会上众人提出的写农民的“铁笔圣手”以及胡耀邦等领导人说过的与“郭茅巴老曹”都是“语言艺术大师”。
赵在解放区的名气之大,当时在现场的美国记者贝尔登也有亲身体会。在其名作《中国震撼世界》中,他记录了当时的情况:赵树理“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
大作家进京:并不顺遂的16年
1949年来到北京的赵树理,已是名满天下的大作家,不久又获得了文坛的一系列头衔和职务。有意思的是,他本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作家,却被指定为工人出版社的首任社长。赵树理踌躇满志,对改造和发展新文艺有着很多自己的想法计划。但直到1965年初他举家迁回山西,北京的十几年过得并不平顺。
第一个打击来自《说说唱唱》。赵非常重视满足底层人民对艺术的需求。他看到北京天桥的传统艺术非常繁荣,但内容充满封建色彩,提出“打入天桥去”的口号,组织成立了北京市通俗文艺研究会,创办了《说说唱唱》杂志,获得极大的成功,发行量激增,很短时间内,这本新刊物就在国内文艺领域发行量居第一。
但赵只注重了“好看”,却对内容上要突出政治考虑不足。结果不久,一篇《金锁》被认为看不到劳动人民的反抗,赵受到了批评,他不得不两次做出公开检查,在《文艺报》《人民日报》《说说唱唱》上刊载。1952年登了一篇介绍种棉发家的文章,也受到了批评,他不得不检讨说,“文章用纯经济观点宣传种棉,没有给农民更高的政治教育,没有宣传无产阶级在国家中的领导作用”。不久,他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评,被免去几个主要的职务,改任中宣部文艺干事。他到底还是不擅于做官的。
在此期间,他曾和老舍共事,关系处得很好。老舍夫人胡絜青就指出过,二人在很多方面都很像,最明显的,都是在语言的运用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程度。也许,这种相像也似后来命运的谶语:一个为捍卫尊严而自杀,一个受尽痛苦含冤而逝。
1955年,赵树理写出了文学界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进程的小说《三里湾》,又一次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他甚至红到了国外:1956年,仅仅在苏联,他的作品就用6种文字出版了14次,印数近百万册!如果就此满足,偶尔赞颂一下社会的新变化,也许会一切顺遂;但赵树理对农民、对家乡的感情太深,终于因言贾祸。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在经济上的挫折主要来自农业方面。赵树理对农村时时关注,有时一年在山西农村生活的时间不短于在京的时间,耿直的他难以对看到的实际情况三缄其口。1956年,他向长治地委写信,提出了下列农村真实存在的尖锐问题:粮食供应不足;缺钱缺草料;买煤难;命令生硬死板;基建任务不顾实际情形……
到了“大跃进”时期,赵树理挂职阳城县委书记处书记,对公共食堂、大炼钢铁等的危害有了非常清楚的认识,坚决反对不顾农民死活的高指标。为此,他写了篇很长的专题文章向中央反映农村的问题——就是那篇交给《红旗》杂志的《公社应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我见》被直接转给作协党组批判,被认为是“反映落后农民观点的一套复辟资本主义的意见”,与彭德怀的上书同类,“一文一武”反对总路线。在作协内部,批判会持续了3个月之久,后由于中央政策变化而不了了之。
第三次大的冲击围绕所谓“写中间人物论”展开。赵树理对作品有自己独特的理念。“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的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像《李有才板话》,就是感于“有些很热心的青年同事,不了解农村中的实际情况,为表面上的工作成绩所迷惑,便写《李有才板话》”。

1958年,赵树理的女儿赵广建(左一)回家参加农业生产,赵树理(右一)也回来故乡工作。这是赵树理一家人在一起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不断有人指责赵树理没有热情歌颂社会主义新农村大好风貌,写的形象多是存在毛病的、思想落后的中间人物——这能代表新农村的面貌和主流吗?作品中不写阶级斗争,如《三里湾》里不写地主破坏——这是忽略敌我矛盾。对赵树理的争议一直存在。
20世纪60年代初,一度出现了一个小阳春的文化时期。1962年8月,中国作协在大连开会,邵荃麟明确肯定了写中间人物,因为“矛盾往往集中在这些人身上”;周扬则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中国作家中真正熟悉农民、熟悉农村的,没有一个能超过赵树理。”
但两年后,情况又变了,文艺界开始批“写中间人物论”,赵树理受到了点名批评。随着政治压力不断加大,赵于1965年初举家迁回山西,工作关系转到山西省文联。
不脱农民本色
生活中的赵树理,经常让人感到就是一个勤劳而淳朴的农民。他下乡,不报销车旅费,都花自己的钱。20世纪50年代,中央曾经号召作家自己买房,赵树理用自己的稿费买下香炉营15号的一座四合院,18间房子,家具一应俱全,非常舒服;之后因为上班远,怕影响工作,换到了东单煤渣胡同,仅仅五六间房,中间的差价几千元都不要了。1965年一家迁回山西时,他又把这套住宅无偿捐给了作协。因为稿费高,又加上国外出版机构常汇来外汇,赵树理不安了,最终决定不再拿国家的工资,成了新中国不领取国家工资的第一人,也是作家中极少几个不领工资的人。
赵的待人之道,从与朋友和论敌的关系也可看出来。他的朋友兼同事王春在1952年英年早逝,他看到其家属生活困难,从此每月资助她们30元,给了十几年,直到他自己落难为止。这笔钱在当时是不小的数目。
在赵进北京后,他主持的工人出版社多是“土包子”,与丁玲主持的作协那些“喝洋墨水的”,在观点和立场上形成了一些对立,关系有些紧张,当时被内部称为“东西总布胡同之争”,以致需要周扬出面加以摆平。但丁玲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后,虽然许多人纷纷检举上纲上线,赵却并未落井下石,只是写了一篇应景的官样文章,泛泛地表了个态,之后便回山西老家去了。其与人相处,确有古人忠恕之风。
一个人在子女亲情上是不会作伪的。而他是最早送子女下乡务农的高级干部之一。女儿赵广建从小受他疼爱,新中国成立后就跟在他身边。她北京高中毕业,想让身为大作家的父亲给她在宣传、文艺系统找份工作,而赵树理则响应中央的号召,动员女儿回乡务农。女儿只好暂时躲去哥哥那里。期间,平时很少写长信的赵树理专门写了封长信对她进行劝说。这封信被女儿做《山西日报》记者的一个同学看到后,经得同意,在1957年11月11日的《山西日报》以《愿你做一个劳动者》为题发表。不久,《人民日报》加以转载,其后又被《北京日报》《文汇报》等多家大报转载,赵树理成为干部送子女下乡最早的典型。
赵树理对女儿的这个安排,产生了很长久的影响。女儿赵广建1957年回家乡,在农村务农20年之久。除此之外,赵的其他子女也没有因为他而占什么便宜,都是普通的劳动者,有的还随着时代的变迁,下岗、做小买卖……
曾任过山西省委书记的王谦,对山药蛋派的两大作家有一个极为准确的概括和评价:“马烽和赵树理不一样。马烽是为党而写农民;赵树理是为农民而写农民。所以当党和农民利益一致的时候,他们两人似乎没什么差别。而当党和农民的利益不一致时,马烽是站在党的一边,而赵树理是站在农民的一边。”
茅盾曾说,“文革”时期文艺园地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这一个作家指的是写农村题材的浩然。虽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全国学人民解放军”,但工业题材小说、军旅小说都少有大作,反而是写农村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红遍整个中国。可见在当时农民作家是有很大舞台的。
比起赵树理来,浩然只是小字辈,“文革”时所获的定位也赶不上“赵树理方向”。可以设想,如果赵树理“政治觉悟”更高些,“阶级斗争这根弦”再强些,以他在解放区就已享有的崇高声誉,紧跟形势写一些反映农村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作品,塑造一些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可以预想其地位将远远超过浩然。即使如果他在“大跃进”时保持沉默,而不是写那些“问题小说”、中间人物,也许他可以平静地过着城市高干的生活。他太贴近农民,骨子里太多农民的淳朴与正直,才会在“浩然走在金光大道上”时,凄然离世。好在今日的文学史已给他们各自做出了公正地记载。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