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子的两面
2016-12-10黄昱宁
黄昱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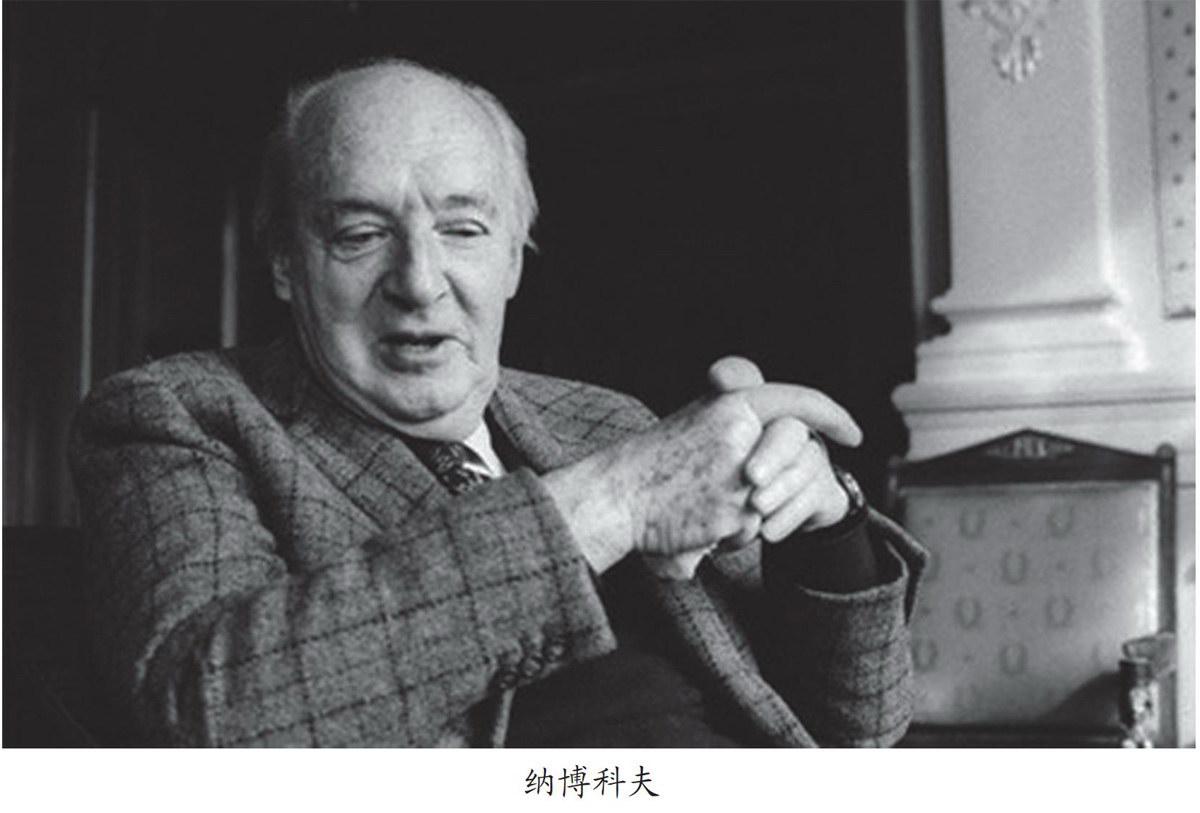
“现在大家的翻译观不同,有人希望尽可能地流畅,和读者距离更近一点。我坚持注释,实际上有很多外国小说,你光看字面意思是看不懂的,尤其是一些‘抗译性很强的东西——修辞的、双关语,如果不加注解,就什么都没有了。如果译者不去解释,读者根本不能得其要领。译者都要承认,两种语言是无法完全传达对方的,一定是有消弱的,如何让信息消弱到最少……注解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办法,是一个笨办法,看上去像一个补丁,但它确实是能让希望得到更多信息的读者满足的一个方法。”
1
正式讲翻译与写作这个问题之前,好像很多媒体记者和读者都会特别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客观评价当下文学翻译的质量?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厘清这个问题可能会让我后面的论点更有说服力。
为什么说当下的翻译质量会成为一个普遍的话题呢?因为我们在很多报纸上都会看到大家挑翻译的错,比如把蒋介石翻译成常凯申的笑话等等,这些问题会让媒体记者得出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就是现在的翻译质量每况愈下。前一届的鲁迅文学奖只有翻译奖这一个奖项空缺。于是很多记者就问,现在的翻译家是不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因为老一代的翻译家我们可以举出很多,比如傅雷、梁宗岱等。
对此我可以斩钉截铁地说,尽管问题很多,质量还谈不上尽如人意,但是如果单纯做纵向比较的话,在综合考量的基础上我不认为总体质量比以前有明显下降。甚至在某些单项上还有提升,那么为什么我们会给读者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呢?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简单地说一下。
首先,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作品的数量也是急速增加,我们现在每天接触到的新出版的翻译作品和解放前接触到的数量是完全不成正比的。因此总的基数大,质量不尽人意的作品也会增加。你随便举几个例子,就非常容易击倒一大批其实还不错的文本。
此外,现在学习外语的人数增加很多,而且程度也很高。豆瓣上可以看到很多民间高手,字幕组也是遍地开花。在这种情况下被挑错的几率太大了。而且一个人挑出错很快就能在网络上传得到处都是。传播给人造成的印象比几十年前大大增加了。但从我的从业经验来说,我并不觉得劣等译作的比例较几十年前有多么明显的增加。
其次,考量译作好坏的标准不能离开它诞生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语境,桑塔格说过,一个个译本就像一座座建筑物,如果它们有任何出色之处,时间的光泽会让他们更出色,像大浪淘沙一样,留下的经典例子和译家都是经过时间淘洗的,劣质的都被剔除掉了。所以我们觉得耳熟能详的精品译作,反复说的其实还是那几个。
另外呢,翻译作品对母语文学构成的新鲜的刺激,起初会让读者有一点点轻微不适的感觉,这需要历经时间的流逝才能被读者渐渐接受。译作和母语本来就是不同的,肯定是有点异化的东西,而这些东西经过几十年的积淀后,就会被接受,甚至被广泛使用,而开始时的那种轻微不适感早就被人遗忘了。这可能说得会比较专业,但是我相信桑塔格的意思就是这样。
她还说过更专业点的一段话,“如今对原文忠诚的标准,肯定要比二三十年前高得多,更不用说比一个世纪前,近年来至少就翻译成英语而言,一直是更看重字面意义的,也就是更严谨的标准衡量,尽管大部分译作未尽如人意,一部分原因就是翻译本身已经变成学术思考的对象,而译本都有可能受到学者的检视,翻译者的任务似乎已经被学术标准同化。”她考量译作的标准,她说的“现在”比她说的“过去”要更严格,更为学术标准。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明清时代,林纾在翻译史上也是被认为非常重要的阶段,他译过大量的作品,比如《块肉余生记》等作品。但是他对原文篡改非常多,他本人并不懂外语,需要别人把语言的意思告诉他。这在当时是被普遍接受的,甚至对翻译史是有推动的。但是现在你还能接受这种方式吗?
世界文学潮流是在变化的,对好译本,甚至对好读者的要求也会产生变化,现在的读者在评论译作的时候,常常提到译者的中文造诣远不如过去,译本读来常有生涩之感。一定程度上可能是这样。因为当年从业者少,真正能达到这个门槛的,本身就是大学者、大作家,个人本身的烙印就留下很多,所以你会觉得他们文采斐然。
但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原文和傅雷时代的原文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现当代文学本身就是更跳跃,更抽象,更重视文字所携带的意象和信息。而有意避开已经成为定势的美文。你去看现代文学的原文,跟我们当年看狄更斯、雨果都太不一样了,那种写法在现在往往是被刻意回避的,他会觉得那样写既无新鲜感并且与现在的生活是并不合拍的,所以它本身的变化是需要读者适应的。读者并不是很适应,而把这种原因归咎于译文。
福克纳的文字是以晦涩出名的,虽然他也生活在二十世纪比较靠前的年代。可是他的意象还是会让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读者有不适应之感,我们每年都会接到投诉,说为什么你们的印刷是有错误的?为什么连着几页都没有标点?我们解释说这是作者的特殊表达方式。读者还是不甘心:他这么写,你们可以改过来,否则编辑和译者是干嘛用的?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我觉得并不是译者或编辑需要做调整,而是怎么普及现当代文学的问题。当然这是个比较极端的例子。还有很多针对译文的问题,我们查过之后发现译者是忠实于原文的,但很难被读者理解,最终很多人把问题归咎于现在的翻译水平越来越差。
我认为现在有一个不太好的导向,就是最终被大家所接受的译文,往往是离原文非常远的。比如有一阵子《乔布斯传》里乔布斯的情书有各种版本的译文出来,有乐府诗,唐诗,诗经体的等等,最后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中文最好。英语哪有这样的表达方式?你完全可以认为这是开玩笑,可是当你发现大部分评论都是这样的时候,就不得不严肃地面对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到底欣赏什么样的翻译?
翻译文学到底对我们思维的演进,对我们创作的刺激,它的作用在哪里?如果我们的导向是这样的话,如果我们都普遍认为骈四俪六就是文学至高境界的话,那么语言和文学实在太容易不思进取,就是说它的发展和活性难免就会缓慢就会迟滞,只要关上门来自己观赏自己的文字就可以了。我们翻译理论中常提到的两个标准,一个是归化,一个是异化,这是个长期斗争的一对矛盾。通俗点,“归化”就是把异国的语言文字变成完全中国式的,就是不需要你去怎么理解的,让你把国外一些知名的东西对应成中国自己知名的东西。比如把国外的喜剧演员直接对应成赵本山,这个在好多电影的翻译里已经看到了,这个现象有很多人很反感,但也有人觉得这样挺好的,我不需要动脑筋去理解,也不需要去记住国外的名字,我为什么要理解国外的文化呢,那么反过来呢,我觉得你为什么还看翻译作品呢?
举个例子,俄国作家纳博科夫后来是用英语写作的,他同时也是个翻译家。他就有很多非常偏执的翻译观念,可能比当年鲁迅主张的硬译还要硬,他当时就闹出一个公案,在译《叶甫盖尼-奥涅金》时,他强调直译到了一个非常偏执的地步,哪怕是把译文变成很生硬的英语他也在所不惜,他说我的目的是为了吸引你去看俄语原文。当然这个是比较极端的译法,可以说是我看到过的翻译理论中最极端的例子。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在异化这个理论上有那么多作家那么坚持,因为他们知道很大程度上翻译的意义在于对母语的冲击,这就牵涉到我们后面讲到的翻译和写作的关系。
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文学翻译的实践者来说,就像桑塔格那句中肯的说法: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才是大多数翻译者的用功之处。就是说呢,每一次翻译实践都是在异化和归化之间平衡的结果,而每个人的平衡点位置是不同的,每个时代所有译者平衡点的平均值也不一样。这个平均值大概就是我们大部分人觉得认可的一个地方,这个平衡点是和时代有关的。好的译者就要揣摩这个平衡点大概在哪里。我个人感觉在我们国家,随着时代的演进,这个平均值还是在缓慢地向着异化这端挪的。相对比起以前来,我们对于原文的很多意象、用法、结构、语法的特点,容忍度会越来越大。就是因为很多人本身是在学外语,对外语这种表达方式通过那么多代的译者,已经越来越接受了。这也可能跟语言的强势弱势有关系。比如对英语的接受度啊,对国外的了解程度等。
2
在厘清上述问题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审视下翻译与写作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可能就会有个比较豁然开朗的感觉。就我国的历史和现状而言,完全可以说翻译文学是近代以来,深入改变中国文学走向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而这种影响今时今日也在向深处发展。出于种种原因,这种影响往往被低估曲解,或者流于表面,更多被提及的可能还是语言上的演变,没有更深入地观察到它在思维上的变化,程式上的借鉴,文学视野及思维方式上的渗透和对话,这些东西往往被人所忽视,实际上它们的影响作用是非常大的。我前面已经讲过,现在中文对世界文化潮流的吸收和接纳,反过来对翻译文学的价值和标准,就不管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其实能够提出一些新要求的。我们现在的读者尽管主观上不一定有这个意识了,可是实际上跟原来的要求已是大不一样了。如果现在让我选择看一部外国电影,我会更多倾向于看原版片,直接看它的字幕,这其实就是一个变化,广大读者也是这样。我也经常思考,翻译实践中的很多东西是否也需要有些变化。比如以前规范的中文当中是绝对不可以出现原文的,但是现在就像CT、NBA,是不是很有必要说它们的中文全称,或者是不是在每种语境中都必须这样,这个就是可以讨论的。还有像在互联网轻易就能提供简单检索的今天,我们有没有必要削减一些非常简单的说明性注解,扩大阐释性注解,这些阐述性注解就像链接一样提供一些背景资料来丰富原文的表述,毕竟是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思维方式。相反说明性注解可以减少,如果现在提莎士比亚这个人就没必要再注解了,可是如果里面提到莎士比亚的某个引文时,中国的读者是感觉不到的,这种情况你就要加注解了。
还有一些标点的问题,其实中文的规范和西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分号和冒号用法。有双语基础的朋友可以观察下,其实它们的用法是不同的。比如外文在直接引用时,是用逗号代替冒号,这按照我们的规范都应该改的,可是如果改,你可能把它的整个结构就给破坏了。如果不把这点作为重要因素来考虑,而仅仅让维护汉语纯洁性这样的理论作为指导的话,我觉得我们的翻译及编辑标准就是落后时代要求的。
长期以来,我觉得像翻译体也好,翻译腔也好,其实在很多场合都是作为一个贬义词而存在的。但实际上,翻译文学与原创中文作品客观上确实在“体”“腔”“格”上面都不同,而这种“不同”我认为本身不仅应该是中性的,而且甚至也是十分必要的。我不觉得翻译体就完全是一个贬义词,就看你怎么掌握这个分寸。既然事关文体的沿革,那么译文既要兼顾每个特定时代读者接受度的平均值,也始终应该保持着比原创文学“快半拍”的节奏。我是觉得半拍,不多不少,半拍正好。保留一定程度上的陌生感,而不是说完全迁就于母语,这样否则它就无法对本国文学的创作,以及思维方式上的交流产生任何刺激作用,一点陌生感还是相当重要。当然这个陌生感不能陌生到一个你不知所云的地步。
说到这里,我想我这个题目的意思就是比较明确了。我认为翻译和写作之间,就是存在这种建议“快半拍”的节奏。你不能认为是完全把它变为中文,甚至是越古越好的中文。前几年倒是相对比较承认有异化有归化。可是,现在在网上反而有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论调:我们中文有多么的博大精深,我们的语言文字有多美,比任何国家的语言文字有多美。这种其实是一种挺无知的想法。你看到过多少国家的语言文字?那只是你不了解他们的语言文字,不知道他们也有古诗,而你们看不懂而已。我觉得这种无知的论调是不应该占据主流。
本文选摘自微信公众号梁宗岱译坛,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