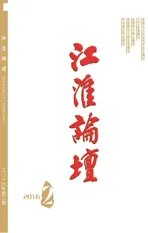虚拟社会认同建构机制与引导策略研究*
2016-12-08李彪
李彪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北京100872)
虚拟社会认同建构机制与引导策略研究*
李彪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北京100872)
互联网作为一种虚拟社会场域,存在着不同群体之间建构的虚拟社会认同,结合传统社会认同过程,文章重点研究了虚拟社会认同的五阶段建构过程:社会事件发生、集体记忆“投射”、社会意义建构与社会意义赋予、社会情绪启动和小范围内的群体认同、社会情绪渲染及社会态度形成和行动仪式与社会认同,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虚拟社会认同与现实社会认同的差异,最后从社会管理创新的角度提出了虚拟社会认同提升、引导和管理的相关对策。
社会认同;集体行为;集体记忆;行动仪式;亚政治
随着社会化媒体的发展,“两微一端”成为社会话语场域中的重要子话语场域,并日益扮演着第一社会信息源和意见“发酵池”的重要角色,尤其是热点事件中,微信和微博通过其传播特性为热点事件的传播提供情绪渲染、社会意义赋予和社会认同建构,很多研究者对微信、微博在热点事件中的信息传播进行了研究,但对于“两微”在其中对用户社会心理的型塑机制的研究较少。
社会认同是社会心理学中的特定用语,解释的是个体在社会中获得一定的归属和情感依赖,使社会个体所在的群体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和信仰,进而又作用于社会个体,影响其社会判断、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认同的功能在于向社会成员灌输行动逻辑、塑造特定结构以及营造相应的群体文化。社会认同是社会情绪传导和线上线下群体性行为的认知基础,在很多舆情事件中,信息流动和认同建构就好比油和水的关系,信息流动好比是水面上的油,具有流动性和随机性,而认同建构后的社会情绪传导好比油面下的水,具有稳固性,因此研究社会认同对社会舆情研判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价值。
一、虚拟社会认同建构的五阶段
社会认同一般是由社会分类(Social-Categorization)、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和积极区分原则(Positive Distinctiveness)建构的。[1]通过对社会热点事件中“两微”对社会心理的塑造过程的影响,可以将虚拟社会认同建构分为以下六个阶段。
(一)热点事件的发生
热点事件的发生是虚拟社会话语场中的导火索。在虚拟社会中,群体一般呈松散化、随意性的存在,很多群体是基于趣缘和线下社会关系网而形成的,只有在社会事件发生以后,大范围的社会认同才开始启动,因此事件发生是社会认同建构的第一步。
(二)集体记忆“投射”
20世纪2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所谓集体记忆是关于一个集体过去全部认识(实践的、知识的、情感的等)的总和。[2]集体记忆具有选择性,并不是“有闻必录”,民众头脑中的固有认知框架会对进入的互联网信息进行选择,强化与自身认知框架相近的信息,选择性遗忘与自身认知框架相左的信息,遴选后的部分信息才有可能进入人们大脑内部成为集体记忆,作为一种诠释的认知框架而存在。社会现实会不断“投射”到集体记忆中被诠释和解构,从而不断重复激活着社会成员的共享情感,因此集体记忆对社会认同的形成具有重要认知框架价值。如网络中不时充斥着官员腐败、炫富、强拆等事件,在整个网络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消极性集体记忆与情感。再加上在一些社会不公事件发生后,部分政府部门所表现出来的“不作为”也使得民众形成了“既有的社会权威与制度体系可能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刻板印象。
基于这种消极性集体记忆,不难解释一旦虚拟社会中出现公共事件,社会民众便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这些事件,抱着“这其中一定有内幕”、“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扫视,这也为造谣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三)社会意义建构与社会地位赋予
克兰德尔曼斯指出:“社会问题本身并不必然引起社会行动,只有当社会问题被人们感知并赋予其意义时才会成为问题,许多原本可以被看作严重的社会问题的客观状况从来没有能够成为公众讨论的话题,甚至没有被人们所察觉”[3]。因此,任何一个事件一旦脱离了自身的事实表述,而成为一种价值判断和意义符号,那么这个事件会很快成为社会性事件,意义建构和社会地位赋予就是为事件贴标签、“上纲上线”。
需要强调的是,虚拟社会个体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受众”,对信息缺乏互动性,相反,处于对事件真相的关注,个体会通过自身的二次创作和“全民狂欢”的形式积极地参与到社会意义建构中,根据自己的“文化地图”和“集体记忆”对各种外界因素作出适当的话语诠释和社会意义建构。如会理悬浮门事件中,网民脑洞大开,争相PS搞笑,对整个事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社会意义的建构也是“概念化”和“标签化”的过程,“概念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再造了、深化了甚至是夸大了人们的怨恨、剥夺感或压迫感”[4],如爱戴手表的官员杨达才被网友称为“表哥”。斯梅尔塞(Neil J.Semelser)的“价值累加理论”(Value-Added Theory)认为“某种因素孤立出现的时候也许并不足以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但当它们按照一定的顺序出现时,其价值就会被放大,群体性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就大”[5]。对往年社会舆情事件的盘点中可以看出,任何一个事件的出现首先必须具备以下几个因素:一是事件本身具有民众关注的元素,二是能够引起“二次创作”的全民狂欢,三是关键人物的介入,以上三个因素缺一不可,并且顺序必须有先有后,通过这种同波共振的机制,事件的价值被无限放大,激活了民众自身的认知框架,进而造成社会民意的啸聚和事件的酝酿发展。
(四)社会情绪启动和小范围的社会认同形成
在事件获得其社会意义的建构和社会地位的赋予之后,借助“双微”的“嵌套”传播结构,其传播速度会呈几何级增长,经过意义建构,事件在作为一种事实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也伴随着社会意义符号传播,从本质上讲,社会意义是一种价值判断,背后是社会情绪及社会情感。相同的地域空间、相似的生活经验使得网络上早已形成的“地域-身份-命运-道义”组合共同体,一旦这个组合共同体被激活,民众的社会情绪被唤醒,社会个体自动选择不同的群体进行集聚,进而引起社会态度形成,因此,社会情绪启动是社会认同进程正式开始的第一步。随着社会情绪在小范围的群体获得认同和接受,小范围的社会认同得以形成。
(五)社会情绪渲染、演化和社会态度形成
这一阶段主要是由传播来完成的。虚拟社会网络关系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与现实关系网相重叠的,基于社会信任的人际传播是一种成本最低、阻力最小、效率最高的传播形式,因此社会情绪会随着事实信息进一步大范围传播,在大范围内被自媒体用户所接受,并进一步同化,进而内化到自身,形成自己的社会态度和社会意见,对整个社会热点事件具有一致的看法、一致的行为倾向,社会态度达到最大的“合意”,即“最大公约数”。
(六)社会认同与行动仪式
在社会态度形成后,集体认同得以建构,进而付诸社会行为,产生了社会集体行为。需要说明的是在集体行为最终出现前,还有个别社会事件存在所谓的“行动仪式”,如维权事件中经常出现的“集体散步”、“集体购物”等行为。卡茨(David I.Kertzer)指出,仪式的神奇效果之一即在于“缺乏共同信仰的情形下制造团结”[6]47-49。在“集体散步”等行动仪式中,行动不是目的,只是一种象征性符号表达,这种符号会使群体内部生成一种认同和情感归属,使得每个个体产生身份和群体图腾。如昆明反PX项目事件中,民众通过戴口罩聚集静坐来获得一种行动认同,在这种认同的基础上宣泄着自己的情绪,以达到一种“情境规范”和“行动仪式”,进而参与到社会集群行为中。
二、虚拟社会认同建构机制及特点
通过以上的社会认同建构过程可以看出,虚拟社会认同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虚拟社会认同主体的多元化、易变性和多层次性。虚拟社会认同主体具有多元性。认同主体多是基于趣缘、业缘等建立起来的社会群体圈子,在社会认同过程中扮演信息提供者、社会意义建构和仪式赋予功能的角色、信息传播和情绪传道者的角色等多元角色。而在这个过程中,主体之间又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即有些群体扮演着主导者角色,有些群体则扮演跟随者角色。
另外,由于网络个体往往具备多重身份,有时甚至可能出现认同重叠和多元认同的现象,如有些社会认同主体对社会不公平都深恶痛绝,但对于其他问题如同性恋、中性美等网络文化现象则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
2.社会认同由群体主导到意义建构和情绪渲染主导。以往现实社会的认同机制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是群体认同,群体认同被认为是社会认同的基础,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技术消弭了时间和空间的阻隔,传统社会的群体结构被最大限度地解构,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血缘、地缘为基础,“家国同构一体”的社会结构被不断解构,基于趣缘的虚拟网络族群崛起,这种群体形式更为松散和易变,群际联系更加复杂。虚拟社会认同主要是由情绪渲染为主导,情感同幅共振成为群际间的最新黏合剂,成为社会认同的原始动力和主要组织形式。
3.虚拟社会认同分为共情认同、对立认同和误同等形式。传统社会认同更多是基于群体认同基础上的态度认同,而虚拟社会认同有了进一步演化,概括起来主要分为以下几类类别。
一是共情认同。即事件发生后,认同是群体的认同,不是个体的认同,是一种边界性认同,因此,认同个体首先是对本群体或者与自己相近社会地位、境况的个体产生认同;其次是对社会中基本道德水准的认同,如同情弱者、痛恨施暴者等等。安徽芜湖跨年夜女生坠楼事件中,任何社会个体对该事件都表现出同情受害者的情感共鸣,很容易形成整个社会范围内认同合意,因此,共情认同是一种直接认同。二是对立认同,即主体产生社会认同是基于共同的对立方,即敌人的敌人即是朋友的逻辑假设,如社会民众对社会中的不公平、官员腐败等不满,虽然不同群体具有自己的群体利益诉求,当面对这些社会不公事件时表现出的一致性即为对立认同,对立认同是一种间接认同。三是误同。即认同主体错误地将别人的感受、遭遇境况和行为当作是自己的,进而产生“在场”的情境假设,进而对事件产生认同。在很多热点事件中,社会个体表现出异常的愤懑甚至付诸行动,主要是集体记忆认知框架的影响,很多社会个体认为自己就是社会事件中的被害者,感同身受。如群体性事件发生时,很多围观群众为什么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心”甚至演变为打砸抢烧等危害性活动,主要是错误的社会认同心理在作祟,误同是社会认同的一种延伸认同形式。
4.政治化社会认同是社会认同的高级形式,社会认同促进政治参与意识。根据认同目标和利益诉求,可以将社会认同划分为经济化认同、道德化社会认同和政治化认同等。经济化社会认同相对简单,主要是基于经济利益而形成的诉求,如各地爆发的PX项目事件中形成的社会认同,主体基于邻避效应而担心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而形成的认同;道德化社会认同是基于人类共有的道德价值底线而形成的认同。如佛山小悦悦事件中民众基于社会道德滑坡现实而产生的社会认同。
政治化认同是社会认同的高级形式,一般在社会不公事件发生后,主体间的共同愤怒意识进一步加强,明确了该为弱势群体处境负主要责任的外群体,认同个体的社会话语直指这一敌对群体,认同主体开始有意识寻求赢得政府等权威机构或大众等第三方的关注和支持,此时,社会认同将发展出它的高级形式——政治化社会认同。如于建嵘组织的随手拍解救流浪儿童事件、随手拍豪华军车事件等。
5.高度认同尤其是愤怒情感认同对社会集群行为具有直接促进作用。Van Zomeren[7]等(2008)对2007年6月之前的集体行动研究中的182个独立研究结果进行元分析,提出集体行动社会认同模型(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Collective Action,SIMCA)。模型证明了社会认同在集体行动前因变量中的中心地位,并确认不公和效能是集体行动的主要前因变量。同时,相关研究[8]表明,社会认同具有高认同度和低认同度之分,一般来说,高认同度的群体更容易直接付诸,集体行动,省去了群体讨论和共同态度形成的阶段;低认同度的群体则只有对未来预期乐观时才愿意参与到行动中,因此高认同度往往带来的是高行动力,在社会认同中有一种情绪特别能够引起群体形成高认同度,那就是群体愤怒情绪(Group-Based Anger),愤怒情绪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群体内部的认同,让群体感觉到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对群体的生存产生焦虑,希望通过集体行动改变这种现状,因此,愤怒情绪往往是认同的第一催化剂。如历次PX项目事件中,短时间内形成的集群行为很多程度上是由群体愤怒情绪来主导的。
6.虚拟社会认同的异化:内群体为外群体产生社会认同。在社会认同的研究中,内群体和外群体之分是形成社会认同的组织基础,恰恰有了基本的群体边界才产生了群体认同;而在虚拟社会中则出现了一种异化的社会认同,即地位高、形象良好的群体为外群体——弱势群体的权益而产生新的社会认同。
在现实社会认同中,群际间关系的显著特征是群体边界,甚至存在群际之间的误解乃至冲突,尤其一些事件侵犯到内群体的利益时,群体成员会下意识地借助自身的刻板印象对另一个群体进行指责和讨伐。而在虚拟空间中,与真实现实不同的是很多个体将自己置于“道德卫士”的制高点,形成了一种新的群际间关系,即社会同情和关心,优势群体可能为了弱势群体的利益而形成社会认同。如意见领袖作为优势群体成员,借助自己的影响力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鼓与呼。
三、虚拟社会认同的引导与管理策略分析
积极的社会认同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消极的社会认同会导致集体行为甚至是社会极端行为的发生,因此对虚拟社会认同进行有效引导和管理,趋利避害,是社会管理创新常议常新的话题。
(一)警惕群际歧视,构建不同社会群际间的对话平台机制
改革开放后,社会信任共同体和共同信仰土崩瓦解,政府没有及时有效地在全社会范围内构建出一个公共话语平台,社会阶层碎片化,使得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形成了一个个断裂的社会族群,由于缺乏公共话语沟通机制,这些断裂的社会族群之间是“不通约”的,“你唱你的,我说我的”,没有共同的话语体系,不是互相倾诉,而是戴着面具、先设性的刻板印象隔空喊话、互相质疑、互相辱骂乃至相互怨恨。
因此,需要在全社会构建公共话语平台和对话机制,微博其实某种程度上能够扮演着这种角色,各个社会利益群体在其上进行对话和争鸣,有利于展开对话和协商,虽然表面上看上去很闹腾,但由于政治管控等因素的影响,微博的公共话语平台属性被最大限度地消解,政府应该主动承担起社会话语平台的构建者,让社会各个利益族群能够合理发声,并被其他族群所听到,而不是一味地进行限制,因为真理越辩越明,一个理性的虚拟社会对现实社会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同时,政府必须正视网络在社会管理中扮演着重要的安全阀和社会黏合剂的作用,将网络打造成为社会不同群体对话的话语平台,不得将社会情绪宣泄口关掉;网络的社会代偿功能不能很好发挥出来,社会矛盾和社会戾气会进一步淤积,会影响到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二)发挥社会认同的黏合剂作用,有效解决网络群体偏见和社会族群分裂
在目前社会缺乏共同信仰、利益诉求的前提下,应该发挥社会化媒体在促进社会认同中的黏合剂作用,扩大社会认同的基础和范围,促进社会达成最大公约数,警惕网络中存在群体偏见和沟通隔阂,如仇官、仇富的偏见,在虚拟社会群体之上构建超越于所有族群的全新社会认同。“中国梦”的提出一定程度上符合这种趋势和现实,但泛政治化的解读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认同、黏合的效能。
(三)构建社会情感按摩机制,改变社会个体“集体记忆”的认知框架
社会情感的形成是社会认同进程中最为重要的认知基础,而社会个体的刻板印象和记忆则是促进社会情感和社会态度的重要认知框架,因此对管理部门来说必须通过法治实现社会的公平和谐,改变社会个体的认知框架,改变目前的刻板印象,建构社会个体全新的认知框架,进而促进积极的社会情感。对当下社会消极情绪主导的境况下,管理部门应该完善社会情感宣泄机制,变堵为疏,构建社会情感有效疏导和按摩机制。
(四)监控公共空间仪式表征,阻断集体行动者的情境定义与集体共意
要加强网络空间中具有仪式表征的监控,阻断集体行动者的情境定义,通过对事件传播的话语场景进行改变影响事件的演变趋势;通过对各个话语场域中的代表进行对话有利于消解族群之间的误解;通过对个别极端行动者的惩戒达到话语权分散等状态,使得社会话语讨论回归理性轨道。
(五)改革社会流动机制,增强网络群体边界的可渗透性
改变目前社会阶层板结化的境况,增强群体、阶层和族群之间的社会流动和社会竞争。首先要对社会失利阶层特别关注,维护该群体的自我激励和社会参与感,最大程度消解这一群体启动群体愤怒情绪的产生机制,提升其群体效能,从根本上切断其产生社会集群行为的链条。二是改变目前社会阶层的流动机制,建构多元的低层次阶层向上流通的通道,提升弱势群体和失利阶层的国家认同感和生活幸福感,从根本上阻断弱势群体内部悲情形象的认同感生成机制,改变目前“弱势心理”、“相对剥夺心理”盛行的社会现实。
(六)构建自下而上的“亚政治”环境
乌尔里希·贝克认为现代社会已经步入了一个风险社会。亚政治是风险社会背景下的一种社会行动,已经开始渗透进社会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8]。通俗地讲,亚政治是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中间力量,具有调和政治和市场关系的作用。随着社会风险加剧,亚政治空间的建设显得越来越重要,已经成为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社会主体政治体系必须持开放态度,打开自己的边界,吸纳社会中各种资源和力量包括这种亚政治所呈现出来的力量,从而解决转型社会中的一系列政治问题。
[1]Tajfel H.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1982.33:1~39.
[2][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8
[3]Klandermans,Bert&Dirk Oegema 1987,Potentials,Networks,Motivations and Barriers:Steps toward ParticipationinSocialMovement.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
[4]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49.
[5]Smelser,Neil J.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r,New York:Free Press,1962:132-134.
[6]何明修.工厂内的阶级团结——连接石化工人的工作现场与集体行动[J].台湾社会学,2003,(3):47-49。
[7]van Zomeren,M.,Spears,R.,&Leach,C.W.(2008b). Exploring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of collective action:Does relevance of group identity influence howpeoplecopewithcollectivedisadvantag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47,353-372.
[8]曾鹏,练伟.亚政治与网络集体非理性行动//“秩序与进步:浙江社会发展60年研究”理论研讨会暨2009浙江省社会学年会论文集,2009:235.
(责任编辑焦德武)
G206.3
A
1001-862X(2016)02-0138-005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www.jhlt.net.cn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与网络社会治理研究”(15CXW014)
李彪(1981—),江苏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网络舆情,新媒体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