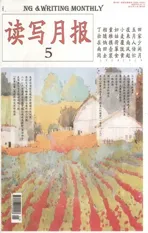生活在无隐私的世界里,不寒而栗
2016-12-05张定浩
●张定浩
生活在无隐私的世界里,不寒而栗
●张定浩

生活在一个完全透明的房子里,这是诗人安德烈·布勒东的愿望。
同时代的扎米亚京在《我们》里嘲讽过这个乌托邦的愿望。他设想了一种人人都住在玻璃房子里的生活,彼此完全没有隐私,一切行为都是可见的,这种乌托邦让我们现代人不寒而栗。
后来,建筑大师密斯曾经小范围实践过这个愿望。他应单身女医生范斯沃斯之邀所设计的别墅,坐落在森林之中,就像一个长方形的、洁白的玻璃盒子,除了内部卫生间略有遮挡外,四面完全透明,这就是建筑史上著名的范斯沃斯住宅。不过,这玻璃房子的种种不便 (除了无隐私之外,还要忍受曝晒),使得女医生最终愤怒地把大师告上法庭。当然,她或许只是没有勇气独自承受这种透明吧。
透明,在不同处境中引发不同态度。超现实主义的诗人看到透明的自由,热切于生活的小说家看到透明的不自由,建筑师设想透明的种种方便(利于采光、视野开阔等),而住户却感知透明的处处不方便。事实上,这种对于透明的矛盾态度,也贯穿于大多数人的生活。他们希望迅速看穿别人,又害怕被别人同样看穿;他们会在各种自媒体公开私人日志、自拍照、视频,又会间歇性地爆发隐藏和匿名的激情。进而,他们希望外部世界是透明的,清晰可辨的,而自己最好是可以有选择的透明;他们希望公众事务是透明的,而个人生活能保有某种私密性。但所谓事实,往往总意味着和愿望截然相反的那部分。
在政治理论中,透明性(transparency)是行话,指的是政治信息的公开性,西方学者梦想政府能成为“玻璃缸里的金鱼”,清澈透明。然而,米兰·昆德拉就不无讽刺地指出,最后成为“玻璃缸里的金鱼” 的,不是政府,而是个人。“官僚政治尽管声称是一种公共事务,却是匿名的、隐秘的、密码式的,像谜一样。在那里,个人,被迫说明他的健康状况,他的收入来源,他的家庭境况;而假如大众媒介再如此裁决,那么无论他是在恋爱,在生病,在死,都永远不会再有孤独的一己时刻了。”
无数的信息泄密事件,都在验证这种“个人透明”的恐怖。这种恐怖一方面源自某种比个人更强大的存在,另一方面,也正来自人性中对于“透明”的无尽欲求。无数的个体,躲在一台台电脑和手机筑就的玻璃缸内,貌似安全地力图看清一个貌似透明的世界,却不料,自己早已成为鱼缸外众多眼睛窥视的对象。英剧《黑镜子》要嘲讽的对象,正是那些 《黑镜子》的忠实观众。而在刘慈欣构造的“黑暗森林”中,那些倾向于隐藏自己而不是窥探他者的文明,才是相对更为高级的文明。
纳博科夫晚年曾写过一本名叫《透明》的小说,小说很短,却异常迷离,时间来回穿插,回忆、梦境、预言反复交织,简直就是“透明”的反讽。说起来很惭愧,我读了几遍尚未明白,但对于透明的欲求却正因为他的天才而逐渐消解。
(选自微信公众号“凤凰读书”2016.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