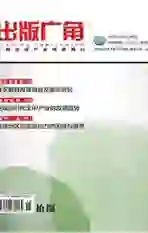明代拟话本小说编辑出版的“现代”萌芽
2016-12-03宁薇
【摘要】明朝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以模仿宋元话本小说体制编写的白话短篇小说——拟话本小说深受新兴市民阶层欢迎,涌现了冯梦龙、凌濛初等一批改编、辑录此类小说的编辑学者。明代拟话本小说编辑思想鲜明,选题明确,具有强烈的读者意识和市场意识,宣传方式和发行渠道多样,呈现了“现代”出版萌芽的特征。
【关键词】拟话本小说;编辑思想;读者意识;市场意识;图书宣传;图书发行
【作者单位】宁薇,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艺术与传媒学院。
明朝是我国古典文化的集大成时期,也是图书出版发展的黄金时期。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家到坊间,编书刻书蔚然成风,图书出版的种类和体例也极为丰富,不仅有朝廷主导编刻的制书、类书、史书,还出现了一些与民生密切相关的科技读物,如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
明朝中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江南新兴城市和市民 阶层日渐兴起,人们对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的兴趣不断增强,过去仅供艺人和书会先生说唱的底本开始变成专供阅读欣赏的文学作品。随着小说地位的提高和印刷手段的进步,当时出现了大批以编写和出版为目的的短篇小说,即拟话本小说。明代出版的拟话本小说数量很多,种类也很丰富,打破了以经史子集和八股文选本为主体的图书市场格局,涌现了冯梦龙、凌濛初等一批改编、辑录此类小说的编辑学者,在编辑思想和出版形式上出现了具有商业化气息的“现代”出版萌芽。
一、明代资本主义萌芽与拟话本小说的繁荣
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是明代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虽然当时的中央政府仍坚持“重农抑商”方针,但商品经济却在广度和深度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万历初期,宰相张居正去陈革新,采取了一系列改良措施,如丈清全国土地,实行“一条鞭法”的新税制,大规模兴修水利等,社会经济趋向繁荣[1]。此时,在东南地区的纺织业中出现了雇主与佣工的资本主义性质生产关系,并逐步从纺织业发展至整个手工业。“记日受值,各有常主”的手工业者们,脱离了生产资料,以出卖劳动力为生,具有了工人的特征。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明代中叶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苏杭一带新兴商业城市日渐兴起。根据《明书》卷八十一记载:“宣德中,令于顺天(北京)、苏、松、镇、常、扬、仪征、杭州、嘉兴、湖州、福州……计三十三处皆立署,曰钞关”,即立钞关征税,可见当时这些城市商业之繁荣。由于新经济因素的刺激,这些新兴商业城市出现了专门依靠手工业和商业生存的市民阶层。城市日渐繁荣,市民阶层也相应地扩大,形成一定的社会力量。因此,当他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一定的满足之后,其对文化生活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戏曲、小说等市民文学大量产生,为图书编写和出版提供了丰富的稿源和广阔的市场。
“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诗文才是正宗,而小说、话本、戏曲等一直被视为俗文学,不仅受到文学家本人的鄙薄,而且官方也制定了相关政策予以压制……但与向来被视为阳春白雪的诗文相比,小说戏剧等艺术形式娱乐性更强,更易为大众接受”[2]。明中叶,新兴市民对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的兴趣不断增强,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模仿宋元话本小说体制编写的白话短篇小说,即拟话本小说。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略史》中将其称为拟宋市人小说。明代拟话本小说集共有二十余种,如金木散人的《鼓掌绝尘》、周清源的《西湖二集》、佚名的《石点头》、于麟的《清夜钟》等。其中以冯梦龙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凌濛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流传最为久远,被鲁迅先生评为为市井细民写心的代表。
二、拟话本小说编辑出版的“现代”萌芽
虽然目前学界对我国出版历史的分期尚有争论,但一般认为,晚清至今的出版被视为现代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对出版的定义为:“将作品编辑加工后,经过复制向公众发行”,即要具备编辑、复制、发行三要素。“中国古代的出版概念,是两要素说。最早,宋代出版物上的新词如‘刊行‘印行‘板行‘梓行等,现在看来都是‘出版的意思。这些宋代时新出现的词语中,‘刊‘印‘板‘梓等,系指印刷,就是复制;‘行为行布,大致相当于发行。从历史上考察,各国古代最早的出版活动大都没有编辑这一环节。” [3]据此,纵观明代拟话本小说的出版,虽无现代的印刷手段和出版制度,但也开始萌发“现代出版”的特征。
1.鲜明的编辑思想和明确的选题目的
明朝中后期,一方面,城市工商业日渐繁荣,社会财富增长;另一方面,政治腐败,自明宪宗后皇帝大多不理朝政,宦官当道,加之苛捐杂税严重,整个社会矛盾锐化。空前繁盛的商业文化和巨大的贫富差距强烈刺激着人们对物质和金钱的追求,传统道德体系土崩瓦解。一些“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具有传统意识的传统文人”[4]开始尝试借助当时受众广泛且流行的拟话本小说来实现“济世”与“教化”之目的。
泰昌天启年间(1620—1632),冯梦龙的“三言”刊行于世,因其选题接地气、语言通俗易懂、故事内容情理皆真而吸引了大批的读者,极大地提升了拟话本小说的水平和地位,也带动了拟话本小说集的创作、编辑和刊行。“三言”集中体现了冯梦龙浅、俗、真的编辑思想。冯梦龙认为,“理着而世不皆切磋之彦,事述而世不皆博雅之儒”(《警世通言叙》)。对于村夫稚子、里妇估儿而言,其“以甲是乙非为喜怒,以前因后果为劝惩,以道听途说为学问”(《警世通言叙》),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情真理明的故事更容易打动他们,继而达到教化训诫之目的。而《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喻世明言叙》)冯梦龙编辑“三言”的目的也很明确,即劝谕、警诫、唤醒世人。“六经国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说也。而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此《醒世恒言》四十种,所以继《明言》《通言》而刻也。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崇儒之代,不废二教,亦谓导愚适俗,或有藉焉。以二教为儒之辅可也,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辅,不亦可乎?”(《醒世恒言叙》)“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顷从玄妙观听说《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夫能使里中儿顿有刮骨疗毒之勇,推此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导情情出。”(《警世通言叙》)
继冯梦龙之后,小说编辑家凌濛初也转而投入到拟话本小说的编辑中,撰辑了著名的“二拍”,作品充分地表达了凌氏讽时劝世的编辑意图。凌濛初出身刊刻世家,其父凌迪知“日校雠群书,雕版行世”,叔父凌稚隆也曾刊行大量史书,而他自己由于三个哥哥的早逝,在二十一岁时便成了凌氏的一家之主[5]。明嘉靖起,以拟话本小说为代表的通俗小说逐渐成为畅销书,这使得图书刊刻出身的凌濛初发现了商机。凌濛初对冯梦龙“三言”极为推崇和赞赏,“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着良规,一破今时陋习”,故其效仿冯氏,“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其事之真与饰,名之实与赝,各参半”(《拍案惊奇序》)。凌濛初编辑刊刻“二拍”,除希望“闻之者足以为戒”外,也有商业出版的目的。
明崇祯年间刊行的《型世言》(全称《峥霄馆评定通俗演义型世言》)也是当时流行的优秀拟话本小说集,作者陆人龙。《型世言》刊行时“三言”和“二拍”已经问世(另有专家认为《型世言》与《二刻拍案惊奇》同时刊印或时间相差无几),可供编纂选择的题材已极其有限。因此,陆人龙“将目光主要集中在明代当时的名人传记资料和野史笔记上” [6]。全书选取题材均为强调劝诫教化之功,编辑思路清晰,章法分明。
2.强烈的读者意识和市场意识
(1)读者意识。读者是出版工作的目标和服务对象。图书要走向市场,要被读者接受,就必须要有读者意识。具体而言,就是要明确读者定位,研究读者的阅读需求、阅读兴趣和接受能力,进而有针对性、有目的地进行出版工作。明代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商业城市的迅速发展,市民成为有别于传统封建社会地主阶层和农民阶层的新型阶层,活跃在新兴城市的各行各业。这一时期的市民阶层包含范围很广泛,如商人、作坊主、手工业者、艺人、妓女、隶役、平民、一般的文人士子、乞丐等皆属于这个阶层。拟话本小说的主要读者即是这些新兴的市民和“村夫、里妇”,而此类小说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已显露强烈的读者意识。
在小说人物选择上,相较于以往通俗小说中的皇亲贵胄、官宦巨贾、才子佳人,明代拟话本小说人物更多选择的是市民阶层——商人、妓女、小商小贩、村夫里妇等。如,《喻世明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里忠厚老实的小商人蒋兴哥,水性杨花、红杏出墙的蒋妇王三巧儿,明为掮客实为老鸨的薛婆;再如,《二刻拍案惊奇·青楼试探人踪 红花场假闹鬼》里贪图家产、“弄得身子冤死他乡”的张贡生。市民的文化阅读具有娱乐性、流行性、通俗性倾向,拟话本小说对这类小人物的选择,使作品更加贴近社会,真切地反映了市民阶层尤其是底层市民阶层的生活,更符合他们的审美意识和阅读口味。
拟话本小说的读者意识还体现在文学语言的表达上。语言表达的形式有两种,书面语和口语,即为文学作品中的文言和白话。活跃于商业市场的市民阶层有其独有的文学需求:一方面,他们的文化水平和阅读需求不同于官宦仕人,决定了“阳春白雪”的文字表达并不还合他们;另一方面,由于市民阶层不从事农业劳动,他们大多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身上或多或少承载了一些民族文化传统,因而又有别于目不识丁的农民。因此,拟话本小说的语言以通俗浅白的口语为主,同时将浅显易懂的诗词等韵文运用到通俗的语言中。“诗(词)文结合、韵散相间的文本框架达到了叙述、议论、戏谑三位一体的独特效果,呈现了中国古代市民阶层审美文化雅俗共赏的独特审美情趣”[7]。
(2)市场意识。拟话本的作者(编辑)除自身的文人属性外,还或多或少地与图书刊刻市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凌濛初自不必说,他出身刊刻世家,刊刻的图书涉及诗集、戏曲、佛教经典等,其中《〈西厢记〉五卷附解证》除亲自点评外,凌濛初还在书中附上精美插图,增添了图书的附加值,据此可见凌氏的商业意识极强。而其继冯梦龙后刊刻(撰写)“二拍”,除想借此讽时劝世外,也是看到了商机。冯氏的“三言”和凌氏的“二拍”带动了拟话本小说出版市场的繁荣,书商们见有利可图,竞相效仿,甚至出现仿造或剽窃的作品,如《觉世雅言》《醒世奇言》《警世奇观》等。虽然这些作品与现在市场上的“康师博”(康师傅)、“请风”(清风)一样都是“李鬼”,但从中也可以窥视当时图书出版市场意识的萌芽。
3.多样化的宣传方式和发行渠道
图书出版的最终目的是刊印发行,将书中内容传播出去。因此,在商业出版中,图书宣传和发行历来是出版商(社)十分注重的环节。明代的统治者注重图书的收集和典藏,加之活字印刷的推广和彩色印刷技术的出现,图书出版市场十分繁荣,并呈现商业化出版趋势。明中后期,传奇、话本、戏曲等通俗读物的流行,刺激了图书市场的商业化进程,一时间书坊林立,仅金陵(今南京)的书坊就有155家[8]。随着图书出版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急于成书射利”的书坊商采取各种手段,加大对所刊图书的宣传力度。
明代坊刊小说的宣传手段很多,其中广告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方式。除了在标题上增加新刊、新刻、精订等广告语,借助“名牌(名人)效应”也是图书宣传的重要手段。虽然当时市面上拟话本小说作品颇多,但质量良莠不齐,因此名家名作更受书商和读者的欢迎。例如,崇祯元年(1628年),尚友堂刊行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十分受欢迎。于是在尚友堂主人的极力邀请下,凌濛初撰写了《二刻拍案惊奇》,并为其撰序[9]。而《二刻拍案惊奇》能够在种类繁复的话本小说市场脱颖而出,与《初刻拍案惊奇》的热销和作者的名人效应有着密切关系。此外,书商们还通过加印插画增加可读性、刊行注释疏导本方便读者理解等方式,增加图书的销售量。
明代的图书发行渠道较之前代不断拓展。自宋以来,书肆是通俗文学最主要的销售场所。明代的很多书肆为书坊主所开,前面售书后面刊印,因此在书坊云集的地方,书肆林立,如南京的三山街、北京的大名门。由于有名的书肆都集中在经济文化发达的城市,无法满足全国旺盛的图书需求,于是湖州书商“购书于船,由至钱塘,东南抵松江,北达京口,走士大夫之门,出书目袖中,低昂其价,所至每以礼接之,客之未座,号为书客”(郑元庆《湖录》),用书船将书卖到全国各地。这种“流动书摊”增加了图书销售的流动性和灵活性。而明代永乐年间宁波帮商人首创的用以寄递信件、物品、经办汇兑的“民信局”,也为图书流通增加了渠道。
拟话本小说兴起于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逐步萌芽的明代中后期,日益发展壮大的市民阶层为小说的创作和出版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而独特的经济和文化背景又深刻地影响了小说的编辑出版活动。明代拟话本小说的编辑出版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并逐步呈现“现代”出版的特征。明朝末年,皇帝昏庸,官场腐败,农民起义和市民运动不断,初露头角的“资本主义经济”湮没在内忧外患的动荡时局中,拟话本小说的创作和出版随即没落。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中国文学史(下)[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788.
[2]曹鸿涛. 大明风物志[M].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8:189.
[3]刘光裕. 中国出版史的对象、范围与分期[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67-73.
[4]聂付生. 冯梦龙研究[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98.
[5]表野和江. 明末吴兴凌氏刻书活动考——凌濛初和出版[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3):57—67.
[6]陆人龙. 型世言:上册[M]. 覃君,点校,中华书局,1993.
[7]洪畅. 论中国古代市民阶层审美文化的发生、发展及特点[D]. 广西师范大学,2003.
[8]张献忠. 明代南京商业出版述略[A].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 明史研究论丛[C]. 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57-74.
[9]杜信孚. 明代版刻综录[M]. 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