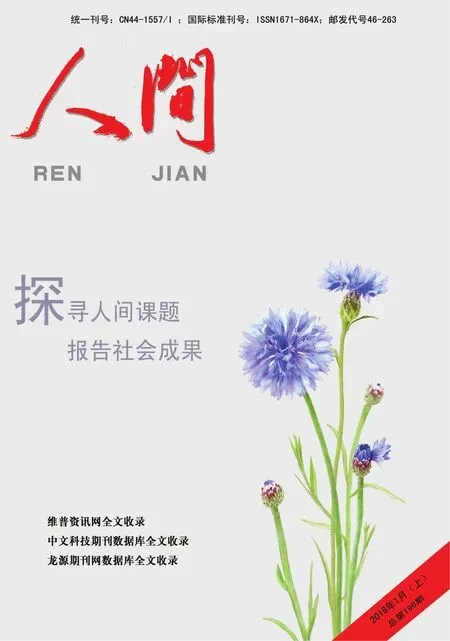老父与酒
2016-11-28吴文远
吴文远
老父与酒
吴文远
父亲这辈子就两个爱好,抽烟与喝酒。
抽了大半辈子年的烟,在他六十多岁的时候戒了。因为再不戒他连气都喘不上来。每天早上四五点钟他的咳嗽比鸡打鸣还准,妈妈被他吵得睡不着,关键是浓黑的痰到处吐,让妈妈厌烦得不得了。其实促使他下定决心戒烟的还不是这些,而是有一次去澡堂子泡澡因为胸闷一口气没上来,差点死在里面。这事之后痛定思痛,他终于把烟戒了。
其实早些年也戒过烟,只是决心没这么大。也停过几天,烟瘾上来就嗑瓜子吃花生,结果瓜子花生吃了一大堆,也没有戒掉。
不再抽烟之后,喝酒就成了他惟一的爱好。每天两顿酒,中午晚上,不喝吃饭不香,浑身没劲。在我当兵走的时候,我向想他表过孝心,只要他保重身体我会让他把全国各地的酒都喝个遍。说到做到,第一次探亲,我就把战友送的西凤酒背回了家,他高兴得不得了。我说您记着,这次是陕西的,下次还有别的省的。后来我就陆续给他背回了北京二锅头、山西汾酒、泸州老窖、衡水老白干等,还有什么扳倒井、闷倒驴的,几乎大半个中国的酒。酒不在名贵,也不一定对他的口味,但是花花绿绿各式各样的瓶子往那儿一摆,成了他在村里炫耀的资本。
后来我从部队里退伍,到大城市谋出路,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没忘记对他许下的诺言,每逢放假回家都要给他买酒。再后来工作稍稍稳定了,手头宽裕了,我也给他带过茅台、五粮液这样的高档酒。父亲这个人不抠门,不管好酒孬酒喜欢拿出来与人分享。记得有一次我给他带了两瓶五粮液,原本让他留着自己喝,结果家里修院墙时他二话不说拿出来跟瓦匠们一起喝了。这事我没埋怨他,我了解他的秉性,跟谁喝,喝什么,只要他开心就好。
父亲爱喝酒,家里自然少不了一些坛坛罐罐的,亲戚朋友都知道我家堂屋门后的墙角里常年墩着两个大酒坛子,而这两个大酒坛子里常年存着酒,泡着大枣和枸杞,不等喝完就续上,从不间断。我们兄妹了解父亲这点爱好,逢年过节不给他买吃买穿也要给他买酒,妹妹来得更加直接,每次回家就用十公斤的塑料壶从县城酒厂给他驮上两壶,父亲高兴得眼睛眯成一条线,说还是老闺女了解我,养闺女有酒喝,这话一点儿不假。
说到这儿别以为父亲是个酒鬼,他也有自己的事业。他做了三十年的赤脚医生,有自己的小诊所,只是他的“生意经”跟别人不同。别的医生给人看病药开得越多越好,用的越贵越好,而他不然,能吃药的就不给病人打针,能不输液的就不输液,而且药就用最便宜的,绝不多开。这样一来收入自然好不到哪里去,以至于多年过去,尽管他在村里起步最早,却是混得最差的一个,甚至拿不出多余的钱供我上学。所以高中毕业后我无奈选择了当兵。
后来他每每想起这件事总是愧疚得老泪纵横,说误了我的前程。我倒没有什么怨言,只是妈妈没少骂他死脑筋。他有他的坚守,在这个问题上不做丝毫让步,不愿昧着良心挣钱。他说你们别指望我发财,我能挣个酒钱就已足矣。
父亲挣的钱确实只够买酒喝,不过他那酒喝得安心踏实,理直气壮,从没让外人戳脊梁骨。
父亲爱喝两口,酒量也非同一般,在十里八村远近闻名。我很少看他喝醉过,唯一一次还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为了我的学籍请校领导和老师吃饭。父亲很少求人,他是很要面子的,但是那次他不得不低三下四央求别人。记得那天暴雨如注,就在我家破旧的茅草屋里,父亲喝得烂醉如泥。那一幕至今刻在我的脑海里。
父亲骨子里有些倔强和清高,但是为人非常忠厚,古道热肠。他读过几年书写一手好字,在村里也算是文化人,逢年过节给乡亲们写春联,红白喜事给人家记账派单,只要有事相求,他随叫随到从不拒绝。尤其遇到重要的事情宁肯关门歇业也要去帮忙,而且一忙就是好几天。妈妈说照这种干法你的诊所早晚要黄。果不其然,苦苦支撑了近三十年终于关张了。妈妈说黄了也好,赔钱搭精力,家里还闹得鸡飞狗跳的,这下子清静了。
其实诊所关张不能归咎于父亲经营不善,在我看来他原本就不会做生意,也没有把行医治病当成一种生意,而更像邻里之间的扶危济困。他至今还保留着一本账册,密密麻麻记录了很多赊欠账目,有几十的几块的,也有几毛的,有孤寡老人的,有家庭困难的,有的已去世多年。他从未主动要过,现在也很少提及。之所以不再行医,主要还是因为孩子们长大了,他不需要再为两顿酒发愁了。
父亲可以高枕无忧痛痛快快地喝酒了。他年轻时一斤八两不在话下,现在每顿也要三四两。他喜欢自斟自饮悠然自得,吃自己种的菜喝自己泡的酒,简单而舒心,这是他向往的生活。但是多数时候他无法享受这种清静,不得不隔三差五地忙于别人家的应酬。
农村里的应酬大多是婚丧嫁娶之类的事情。谁家要是遇到个红白喜事,邻里之间都要不请自来主动帮忙。这是祖上留下的不成文的规定。农村不同于城市,虽然处在新时代,办事依然沿用老规矩讲老理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既懂老理儿又有威望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父亲早年背着药箱行走于乡里,救死扶伤,帮了乡亲们不少忙,颇受大家的尊重和信任。又加上熟谙陪酒待客之道,懂得各种场合迎来送往的礼俗规矩,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自然成了乡亲们心目中德高望重之人。父亲也常常不负众望,尽己所能,把人家的事儿安排得井井有条,拿捏得极有分寸,绝对让东家满意。
人有人品,酒有酒品,酒桌之上的规矩实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浓缩。座怎么坐,杯怎么举,话怎么说,酒怎么喝,老幼尊卑,远近亲疏,复杂繁琐,一步做不到就会让客人挑理儿,搞不好就会不欢而散。父亲往往处理得恰到好处。
父亲爱酒但不贪杯,他有自己的原则。遇到谁家里老人去世,忙完之后,人家摆酒设宴极力相邀以示感谢,父亲多是婉言谢绝闭门不出,他说要理解人家的心情,这时候去喝酒不合适。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一辈子与酒打交道、爱酒如命、以酒为乐的人。
中图分类号:I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002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