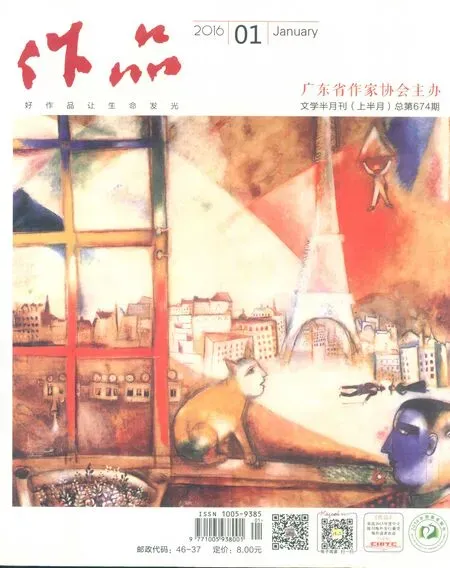如何描述我去过的海边
2016-11-26鲍尔吉原野
文/鲍尔吉·原野
如何描述我去过的海边
文/鲍尔吉·原野
鲍尔吉·原野蒙古族,辽宁省作协副主席。出版作品集多部,获全国少数民族骏马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内蒙古文艺突出贡献奖及金质奖章、第16届百花文学奖、人民文学散文奖等奖项。与画家朝戈、歌手腾格尔并称中国文艺界“草原三剑客”。
海 边
我们住在海岛的南边,叫东岙渔村。南风日夜驱赶着大海到岸上放牧,我从东窗上看到海浪的羊群钻进沙滩,不复出焉。后来的白浪钻进沙滩,寻找先前的浪,同样被陆地捕俘,不见踪影。由古至今,陆地究竟捉走了多少雪白的、蕾丝边的、裹挟小鱼小虾的海浪,算是算不过来的。
窗外是海,除了海就没什么可看。而海,它的每一样变化还没来得及看就已经消失,变化到新的变化之中。你说你看到了海浪,你说不清看到了哪一个浪,记不住它的模样。这个浪被它身后永不停歇的、性急的新浪碾碎。水还在,浪转瞬而逝。人类的视网膜的解码速度远不及浪的速度,想起金璧辉的干爹名谓川岛浪速有些道理。人看大海如文盲读一本篇幅浩大的书,认不出其中的任何一个字。我们虽然不认识海的字,但我们认识海鸥。海在光线和风里变出黄的,蓝的,灰的颜色,但海鸥始终是白色的,如一条会飞的刀鱼。我想象洞头岛真富庶啊,刀鱼满天飞。海鸥飞得低而慢,我们的视网膜大体上能看清它的仪态。它的翅膀似乎捋不直,如信天翁翅膀压不弯。它的翅膀(即刀鱼部分)上下翻,却让人觉得翅膀如V字。这个V字的长翅膀的两端下垂,俨然旧时代小瓦的瓦檐,却白。海鸥乱七八糟地飞来飞去,如潮水涨来涨去。海鸥的叫声大体上属于猫的音色却更凄厉。这一点,人类又有不解。以海鸥的优雅与轻佻,它的叫声似乎应该圆润些,如杜鹃鸟发出的双簧管的音色。人类有一种配套成龙的习惯,把东西放一块。好看的鸟儿叫声也要好,如不存在的凤凰。不好的东西也放一块,饿狼最好连腿都是跛的。但上帝不这样想,上帝创造万物的准则并不是人类眼里的完美模式,(完美这个词,上帝从来不去想)。上帝赋予每一种物种生的能力的同时赋予它们难以逾越的缺陷,让这一物种在缺陷中有序增减。追求完美即是人类的缺陷之一。
眼前的大海有黄色的波浪,他们说台风从南面快要赶到了。感觉不到风,但海浪越来越大。离岸很远的黑礁石围满了白色的浪花,这在头几天还看不到。浪头由西到东次第上岸,如同用鞭子在沙滩上抡了一下。由此,涛声由远及近或由近及远,传来长长的喧哗,海水一浪逐着一浪到岸边劈头摔下却没有水接着而发出的绝望呐喊。没随浪头转回反而钻进沙滩里的海水发出咝咝声,好像有人吃了辣椒之后的吸气。沙滩感叹浪头太大,不禁咝咝。
夜里,涛声越来越重,尽管台风并没有来。是夜无月,看不见海面的情形,只听涛声大如黄河决口,如同大山走动起来到海边集结。原来,一波与另一波的潮水拍岸之间尚有短暂的空寂,此刻空隙抹平,耳畔灌满涛声。我如作梦一般想起了学书法抄过的三位晚清诗人的诗:
千声檐铁百淋铃,
雨横风狂暂一停。
正望鸡鸣天下白,
又惊鹅击海东青。
沉阴噎噎何多日,
残月晖晖尚几星。
斗室苍茫吾独立,
万家酣睡几人醒。
——黄遵宪《夜起》
凄凉白马市中箫,
梦入西湖数六桥。
绝好江山谁看取?
涛声怒断浙江潮。
——康有为《闻意索三门湾以兵轮三艘迫浙江有感》
海天龙战血玄黄,
披发长歌览大荒。
易水萧萧人去也,
一天明月白如霜。
——苏曼殊《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
实话说,我不太明了这些诗的寓意,其意境混杂一体庶几可传达此夜涛声的氛围,但没那么悲观。人不明白的事情实在比明白的事情多的多,谁知道写书法抄过的诗篇竟能记住,竟能在海边的潮声中浮上心头呢?忆诗时手指要在腿上写,否则也记不起。可见这些诗记忆在我的手指上。我开始相信电影里的人物对着山峰、松林、花朵背诵诗篇可能是真的,他们原本都练过书法啊。这又提醒我以后写书法抄诗要抄一些着调的诗,蜀道难什么的干脆不要抄了,因为我根本去不了李白去的地方。
黄遵宪说“斗室苍茫吾独立”,吾乃“独卧”,立之事刚才站桩已经立过了。听海潮八荒涌来。你可以说潮声像什么事物,但没法说什么事物像潮。潮声把世上所有的声音都收纳了,如崩石、如裂岸、如马踏草原、如群狮怒吼。而被狂涛掩盖的细小声响,还如鸟鸣声,冲刷声,浪穿过空气的嘶声。更有巨浪打在岸上之后土地的震动声,浪打在船上,石上,浪上的不同的响声。众多声音一并响起,使人不知道这是什么声,曰涛声。黑暗里,我躺在床上想,假若这不是涛声会是什么声呢?竟想不起来。涛声之外,世上无此声。听来听去,禁不住几次起身趴窗台看海,偌大的海竟被夜色包裹得严严实实,一滴水也没看到,只有一阵紧似一阵的浪涛声。我想象浪头一浪高过一浪,在海上雪白地相互追逐。海水撞在礁石上,浪花伸出巨大的白爪。天上无星无月,乌云遮住了整个天空。遮住所有的天光。这需要许多云,数量要和大海一样多。我依稀记得陆地上没有太多云,如不下雨,云彩与天空基本是一半对一半。海边不一样,需要更多的云。为什么需要这么多云,我也不知道。在巨大的浪潮声里,我竟睡着了。我怨恨自己:这么大的声音,怎么能睡着呢?但还是睡着了,大自然的声音无论多么喧哗,都与人身体内部的节律合拍,大自然从来没发出过噪音。
夜里醒来,第一件事是听海浪还响吗?还响,不管有没有人听,它们都在响,我索性到了海边,找地方坐下听涛。天色黑得看不见海,看不见浪头打到岸边向前伸出的手。我如盲人一样瞪着前方,前方一无所有。听觉告诉我浪从左边打过来,从右边打过来,而眼前的漆黑即是大海。心里想海里的鱼在干什么,不知它们睡不睡觉。想“哗——”是什么,想“唰——”是什么,想我在想什么。起身走的时候,我看不见自己的脚和脚下的路。这个“我”慢慢地顺利地回到了房间,重新躺到床上。我方知人在海边并没有当下,一无所见亦一无所闻。我无法向别人转述“哗——”的内容,也不能转述我的所见。
第二天早上起来看海。大海来了,有远有近,风平浪静。最远处的海是灰的,接着蓝与黄的海水涌向昨夜我坐过的沙滩,海鸥在飞。昨夜的涛声与我的漫游都像假的,如同臆造。
岛 上
到了岛上,心想岛又怎么样呢?登陆时踩踩地面,挺结实,跟踩大陆没两样。汽车在岛上飞驰,没减速的意思,让我稀奇。岛挺大啊,汽车呜呜跑。坐车上,看岛上群山连绵,更稀奇。岛上还有山啊,同伴说你少见多怪,洞口群岛是一个县,设有中国共产党洞头县委员会,懂不懂?我闻此言,默默向洞头县委书记和县长致意,他们在岛上领导着一个县前进。
我到海边的机会少,上岛的机会更少,于是对岛上的连绵群山感到诧异,见到这里的人把零星小岛的山峰劈了一半填海更诧异。待到我开始环岛跑步,钻过一个又一个隧道就不觉得岛与大陆有什么区别了。岂止岛上有山?这座岛与每一座岛都是耸立于海面的高山,洞头人民在山顶修建公路,盖起了高楼大厦。假设某一天海水突然退掉,他们都成了在巍峨山顶上生活的高尚的人民,每人除身份证外,另外颁发一个神仙证。我们在陆地上或者在海底用望远镜仰望他们,那时候岛改为山——洞头山、灵昆山、霓屿山等等。海水固然不会退去,即使退去了,洞头早已修好连接温州与各岛屿的跨海大桥。坐车跨桥,在各个岛屿游走。洞头人真是了不起,该想到的都想到了。洞头人常说。我们与温州市区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他们想说的其实是他们已经去除疏离感,与大陆连接一体。
在岛上走,看到方石砌的民舍,比大陆的房子结实十倍。他们说,渔民修这样的房子抗台风。你仔仔细细看这个岛,不光房子抗台风,这里的每一株小草,每一棵树都在与台风的对抗中获得了大陆草木所没有的能量。你看岛上郁郁葱葱,草木在珍贵的、从远方吹来落在石缝里的土中扎下根。对岛上的草木来说,扎下根就永不搬家,台风或烈日都不会让它们死去,也不会让它们退缩。我在岛上的地面看小蚂蚁爬,它们在茂盛的植物下奔忙。我听说下周台风就来了,会把蚂蚁吹到海里吗?台风可以摧木毁屋,但不一定能吹走蚂蚁,大自然就这么安排的,我在心里对蚂蚁和池塘的白鸭默默地表达了敬意。
在洞头我们正赶上七夕节。这里的七夕与其它地方不同,是送给孩子的祈福节。家家户户蒸年糕,摆水果,烧纸上香,祝贺家里16岁的孩子长大成人,祈求上天保佑尚不到16岁的小孩子继续平安成长。我一想,其它地方好像没有这样的民间节日。这个节日好,凡是给小孩子的节日都是欢乐的节日。如果我是这里的孩子,看到大人为我大吃大喝,何其得意。父母为孩子祈福那么虔诚,孩子能不感动么?孩子在这一天会明白:中国的家长一切都是为了孩子,这是本能冲动,拦都拦不住。这个节过早了也不好,譬如孩子两、三岁时过这个节,他不感动。16岁刚刚好,此时他们刚要早恋,刚想叛逆,过完节,全正常了。洞头是温州市辖的一个县,最近改区了。这里的人却说闽南话,祖籍多是福建人。从地域性格说,温州人敢闯敢干,闽南人敢打敢拼,两股血脉在洞头汇合,真是得天独厚。洞头人劈山填海,见其勇猛,他们还有细腻的一面——渔民绘画。我们看画的同时看到了作者,他们中间有渔民,也有普通的岛民,女性居多。县文化馆为他们开辟了一间大画室,任其自由创作。他们的创作虽然“自由”,然而画面离不开船和大海。这些作画者没有技法与美术史的束缚,人物扁平,构图对衬,然而内容感人。他们把人画得像儿童一样跳舞唱歌,献出猪羊,祈求老天爷与海神娘娘保佑他们出海平安。画有画风,如果画出单纯与质朴,就感人,像这些画。
洞头岛商业发达。市中心商铺一家挨一家,游人川流不息,旅游经济带动渔家乐遍地开花。岛上公路好,这是就长跑而言。环岛柏油公路专门辟出一条彩道供自行车与跑步使用。我在岛上分别跑了五公里、十公里和十六公里。因为心里没底,没敢环岛跑。下回去洞头一定环岛跑一下,全程约23公里,对我来说刚刚好,再远就跑不下来了。
海上日出
我们和洞头县的摄影家刘海鸣约好,次日4:40起床,去看海上日出。
第二天早上4:30分,我们住的渔家小筑的楼梯“咚,咚”响了,我下楼与高伟一道上了刘海鸣的车。
车在极其曲折、上下坡度很大的路上行驶,岛上的路就是这样。外面漆黑,天上云层厚,一点光都透不下来。
刘海鸣是看日出的老油条,也是摄影老油条。他拍摄的洞头风光多次参加大展,他把我们带到看日出最好的地点。车开到宽阔地带,略微能分辨出天与海的连接。刘海鸣说:积云多,可能看不到日出。过五分钟,他又说:也可能看的到。但我们看云跟刚才一样,或许刘海鸣还有其它掐算日出的方法。
我们在浴场下车,径直下行。这是一处宽阔平坦的海滩,沙子好,无乱石兀立。马蹄形的沙滩被高崖环抱,高崖俱如黑黝黝的雕堡。抬眼看,天际有一隙暗红的光带,如烧红的铁条穿透了海平线。铁条分开了海和天上的云层。此刻仍黑暗,看不清海,也看不清云层,只是觉得那里应该是海天交接处。
太阳现在哪里隐匿?它要为盛大的演出而化妆、而换衣,而候场吗?在巨大的海与巨大的黑暗后面,会有一个金光四射的太阳吗?现在看不出来。平时谁都不怀疑太阳每天升起,但等在这里观日出的二十多个人都在心存疑虑。人们——一排排如黑树桩一般的剪影仰望天幕,日如不升,就成了一个负心人。我想的是:这根铁条横在那里,约等于说云层没有完全遮蔽我们观日出的通道,太阳升的时候会允许人们在这个窄条里看它一眼。这一条红线实在太窄了,类似百叶窗的缝隙。也许由于看日出的人少,太阳留给洞头海滨浴场的观赏视域就这么窄,约等于一根芹菜外加一根韭菜叶的宽度。我想,铁条上面平直的浓云会不会降下来?那我们什么都看不到了。
这些事写下来很啰嗦,当时只是一晃儿的时光。又一晃儿,云与海平线的间隙宽了。瞬间,彩光铺在沙滩上。温柔的潮水上岸转头走掉,沙滩便留下一个平坦的浸满水的镜子,里面嵌装彩光的倒影。在几乎还可以称为黑暗的海滩上,橙色加杂粉光的光影从沙滩的水渍反射出来,比天空更明亮。这些光并非彩云的光,也不是霞光,是太阳升起之前的金晖被乌云遮挡中喷发过来的光束,敏感的水捉住了这些光。然而,海面并没有粼粼的光斑。应该有,但没有。此时,人对面看不清五官,天还算黑着。
太阳要出来了,我觉得坐站皆不宜,应该蹦高。沙滩太软,蹦不起来。但奏乐显然是最适宜的事,我后悔昨晚没在手机下载几首乐曲此时播放。海滩上的人们开始照相,小孩子光着身子往浪里冲。没人用手机播放庄严的乐曲,他们像我一样无知,一样莽撞。俄而,金光铺满沙滩。这么说有点不真实,解释一下:海的尽头喷涌光芒,但海上见不到。海上的浪头骑着前方的浪头奔来,见不到反光。不知哪会儿,天空的云层瓦解了,可能是阳光太热,把它们烤散了。云的头顶出现青白色飘着红云的光,这些天光照在沙滩的水上,绚丽一时。但这时太阳还没出来,还没到出的时候。我上网查看,2015年8月20日洞头岛日出时间为05:21分,现在已是05:19分。众人欢喜,不再管太阳出不出来,不出也不算事。这些人照相,追逐浪潮,天边幻化以玫瑰色为主调的光幕,海浪把这些光如锦锻一般铺在沙滩上。刹那间,你不觉得这是水,也不是沙滩,而如真实的织锦,转而消失。下一拨的浪铺出一幅新的锦缎图,比刚才更美,当然又消失了。正在看,人高喊:太阳出来了!
太阳从海平线冒出头,边缘模糊,好像沾着水。它探出头来,似乎愣住不动了,原来世界竟是这个样子。少顷,日头猛地跃出海面,体积一下显小了。太阳在海上呆了三、五秒,钻进上面的云层,日出结束了,也可写成(完)。
日出这件事其实不可描述,宜目睹、宜惊呆,不宜转化为字。字跟日出的壮丽相比简直啥也不是。观日出后,总觉得一件事还没有完。人最爱用睡觉结束一件事,但现在是早上,怎么睡?我们坐刘海鸣的车回到东岙渔村,高伟回屋睡了一个回笼觉,我上公路跑了一个10公里。边跑边回味日出所见,想来想去不真实,这是真的吗?自己拿不准了。
(责编:张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