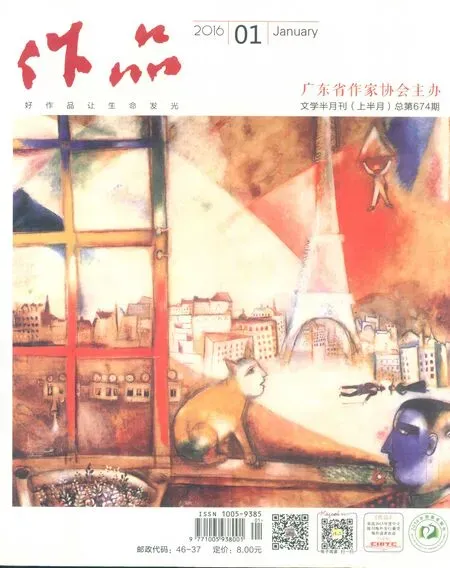夏天,冬天和金鱼
2016-11-26文/杨遥
文/杨 遥
夏天,冬天和金鱼
文/杨 遥
杨 遥原名杨全喜,中国作协会员。发表中短篇小说100余部,小说集《二弟的碉堡》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2009年卷”。并出版《硬起来的刀子》、《我们迅速老去》等短篇小说集和《脊梁上的行走》文化散文集。曾获“2007-2009年度赵树理”文学奖、第九届《十月》文学奖、第十届《上海文学》奖等奖项。
告示贴到镇上时,人们都凑去看热闹。
……
……
张超阳,男,出生日期1978年5月11日。因故意伤害他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人们看到这里,议论纷纷。都觉得张超阳不可能伤害他人。张超阳小时候学习好,听话,考上大学,当了老师,没几年相继被调到县里、市里。镇上每户人家教育孩子时,几乎都会拿张超阳来打比方。怎么会去故意伤害他人呢?
1
张超阳出生在普通农村家庭,在村里读完小学,上了县里的初中、高中,然后考了师范学校,毕业回到邻村当老师。
他28岁那年,母亲癌症去世,是他平凡的早年生活里唯一有些不寻常的事情,也算不上什么。
那时张超阳在五里之外的复式小学教二年级和四年级,平时住校,周末才回家。学校里除了他,只有另外一位女老师,也是自己开火,两人有些往来,无关情爱。
除了日子枯燥,工作也被人瞧不起。农村小学老师,能挣几毛钱?
有次,有人给张超阳介绍了村里的女孩。她问他每月挣多少钱?张超阳回答后,她追问道,除了工资还能打闹点吗?张超阳垂下头。女孩昂起头,骄傲的公鸡那样直接就走了。
张超阳有位当老师的同学,快要结婚时,未婚妻居然拿着他的毕业证来到张超阳家里问未婚夫是不是真的是大学生?毕业证是不是假的?让张超阳哭笑不得。
张超阳母亲患癌症以来,他们家就被沉重的债务压着,母亲去世后,债务落下来,像巨斧砍在张超阳和他父亲、弟弟三个人的脊梁上。
每次周末回家,张超阳骑着自行车老远处看见自家的房子孤单地耸立在村边,就有伤感涌上来。迎街墙上那道被邻居家汽车撞开的裂缝越裂越大,走到近前,从墙壁裂缝里望见院子里尺把高的野草四处肆虐,那些歪歪扭扭的黄瓜架子、西红柿架子、豆角架子和茄子、辣椒秧子似乎要被挤到外边去。进了门,满眼的灰尘。
开始,张超阳还拿起抹布,从门口的柜子擦起。以前,他母亲每天认真擦拭它们,它们干净得像羔羊。张超阳希望它们能恢复母亲在世时光泽,能看到岁月在它们上面留下的厚厚包浆。可是,母亲的去世仿佛带走了它们秘密贮藏在生命中的流光溢彩。他父亲和弟弟显然也没有打算让它们重新光亮起来,他们整天为了生计奔波,自己更先比屋里这些老家具苍老下去。
坚持几周之后,张超阳便没有耐心了,每周回了家,只是擦拭母亲牌位前的尘土,可是下周回来发现那块地方和没有擦过的其它地方基本一样,甚至因为那块地方擦了,反而显得突兀地难看。他便也放弃了这最后的挣扎。
三个男人像浑身长满刺的仙人球,相互之间只要说话,声音就高得让人害怕,再说上几句,就冒出火气来,顿不顿张超阳和弟弟出手打起来,已经明显衰老的父亲在旁边生气地跺着脚喊,你们还让不让我活了?
人们觉得张超阳家完蛋了。三个男人,两个大龄青年,还没有钱。
巨大的悲哀攫住了张超阳,他感觉到阻挡不住的东西在袭击他家,那就是人们常说的命运。他仿佛看到三十多年后的自己,已经退休,伛偻着腰,咳嗽、喘气,孤零零地被灰尘淹没。
暑假来临之后,从来没有感觉到的巨大的时间咣当放在张超阳的生活中,他不知所措。
为了挣钱,父亲在街面上的老屋开了个小铺子,张超阳顺理成章假期里当起了伙计。
每天吃完早饭,父亲和弟弟出去干活儿,张超阳打开铺子卖东西。镇上的铺子悠闲得很,上午偶尔有几个零星的顾客,到了下午,巨大的热浪把大家死死堵在屋子里,五点之后人们才荷着锄、拿着垫子、扇子等东西出门。张超阳通常大睡之后,带着汗津津的身子坐在门口钉鞋的金龙板凳上,边照看铺子,边听他神侃。
每天金龙的钉鞋摊子前,懒懒散散地总围着几个无所事事的光棍。他们喜欢聊女人,聊的时候总是赤裸裸地直接奔到性上面,脸上带着神秘而幸福的表情,仿佛身经百战。张超阳坐在他们旁边,一言不发,静静地听大家闲话春秋。张超阳的焦虑隐藏在闲适的后面,谁也不知道他每天闻鸡起舞,夜晚悬梁读书。
马路斜对面大约三百米地方,也就是紧邻水渠旁边,开着家卖毛线的铺子。炎热的夏天,没有人买毛线,店主无双尽管漂亮,但漂亮几乎总是闲着。闲着的无双喜欢吃零食。
“看看看,”金龙翘起眼睛不怀好意地笑着。
无双踩着高跟鞋走过来,倏地勾起旁边所有男人们的视线。他们的目光一接触无双身子,就像被蛇咬了,马上缩回来。无双一步一歪地走着,白色短裙子下的大腿比太阳都耀眼,胸脯挺得很高。那是张超阳看到过的最饱满的胸脯。她身后拖着短短的影子,在泛着白光的街道上,好像是唯一的影子,给人的感觉却不是清凉,而是燥热。无双赤脚穿着凉鞋进了张超阳家隔壁的铺子。过会儿,她嘴里咬着雪糕,手里拿着瓜子、辣条、薯条、鸭脖等东西走出来,屁股一扭一扭,男人们的目光随着她屁股的扭动在闷热的空气里挥舞,水泥路静得只能听见清脆的高跟鞋的声音。
走过大约三百米距离,无双在铺子前坐下,开始吃东西。
马路上安静了,灼热的白光波浪一样隔开这三百米的距离。男人们继续聊天,谈的还是女人。无双吃完雪糕,舔了舔嘴唇,上面雪白的奶油被她粉红色的舌头舔光之后,嘴唇变得更加湿润而诱人。她打开瓜子袋,瓜子皮从她鲜红的嘴唇里降落伞一样飞了出来。
“无双这个女人脑水有问题,”金龙说,“她去饭店当服务员,没干几天,就和修汽车的有了首尾,跟上跑了。家里到处找,急的。一个多月后她回来了,吵着要跟那个男的结婚。那个男的连自己还养活不了呢!”
“后来结了吗?”
“有肚了,只好结了。”
“好B都被狗操了,那男人现在干什么?”
“开出租车。”
金龙说这话的样子,满是不屑的样子。这时有女人过来钉鞋,金龙闭了嘴,拿起女人脱下的鞋,凑到脸前瞧。
金龙说了这话,张超阳耳朵又不聋,边为无双可惜,边更加仔细地注意起她来。出租车司机虽没名气,运气却好,张超阳却什么也没有。他只能望洋兴叹。
每个午后,看无双,成了张超阳的幸福时光。
无双很白,张超阳发现皮肤像涂着奶酪,看她时,他鼻子里总有丝丝缕缕的香气。她的鼻子、眼睛、嘴巴都雕刻出来似的非常醒目,双腿修长,从上到下都让人心跳。张超阳从来不敢正面瞧她,也不敢和她主动打招呼,每次当她走过来时,只是用目光远远地迎接她膝盖以下的地方,然后等她走过去背对他时,目光才慢慢上移,先到腰部,再从腰部转到肩膀、头,然后跟着她的背影进了邻居铺子,再用目光迎接她出来,目送着她走到自己的铺子前,坐下吃东西。
无双成了张超阳努力的动力。他常常想,这么漂亮的姑娘,为什么就早早结婚了呢?他渴望见到那个司机。
暑假快结束的时候,已经立秋,早晚凉爽起来。
张超阳夜读《霍乱时期的爱情》。窗外蟋蟀在黑暗中高一声、低一声鸣叫,云层透明,星星一闪一现。张超阳幻想八十多岁时有个费洛伦蒂洛·阿里萨那样的河运公司,忽然遇上无双。
这时,斜对面铺子里忽然传来尖叫。张超阳霍地坐起来,声音消失了……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重又躺下,侧着耳朵听,尖叫声确实没有了,但好像有另种混沌而愤怒的声音,听不清。张超阳在想那是不是无双的声音呢?但说实话,他们虽然离得这么近,他每天仔细观察她,但从来没有听到过她的声音。在犹豫中,张超阳听到摔门,汽车发动。他想出去看看,但始终没有出去。原因是他不能判断这到底是不是无双铺子里发生的声音。说到底,他是个怯懦的人,还有读书人那种可笑的谨慎。那晚,张超阳没有睡踏实。
第二天,张超阳早早起床,站到街上时,扫大街的人正好扫过无双的铺子。他装作散步走了过去。无双铺子的门关着,和平时并没有什么两样。他看看周围没人注意,走到台阶上听了听,里面没有声音。他想自己可能太多心,昨天晚上应该是别的夫妻在吵架,无双的铺子晚上大概根本就没有看门的人,谁会去偷毛线呢?
半上午时候,金龙摊子前人忽然多起来。人们议论昨晚事情。他们说无双和另一个男人有楂儿,昨晚被她丈夫捉了。她丈夫天黑之前就躲到床下,无双毫不知觉。半夜里只顾和野男人在床上做什么,丈夫忽然钻了出来。
张超阳紧着心里的不自在,问后来呢?人们说,那个男人是个武大郎,捉了奸却被无双和野男人打一顿,跑了。
张超阳想象着昨天晚上的事情,不由自主朝对面看去,无双铺子的门还没有开。
那天,张超阳心神不宁,隔会儿出去看看。到下午,无双铺子的门终于开了。坐在门前的却不是无双,而是位面孔黧黑的男人。他无精打采、目光呆滞。张超阳感觉他就是那个男的。果然,金龙他们兴奋了,他们装着去水渠里倒垃圾、提水、扔东西,轮流过去看那个男人。每次回来之后就把男人的状态通报一遍,然后再议论昨天的事情。张超阳忍不住好奇心,提了桶脏水,去水渠里倒。路过铺子时,偷偷看了下这个男人,他长得太平常了,性格也看不出奇伟,只有脸上两道鲜艳的抓痕才让人相信是这场事件的主角。张超阳想不通无双为什么要嫁给这样的男人。
从那天之后直到开学,无双一直没有在铺子里出现,不知道是男人怕她继续偷人,不让出来,还是自己羞得不愿意出来,或者有其它什么原因?
男人每天独自坐在铺子里,目光蘸了铅似的一天比一天阴沉。红色的夏利出租车整天停在水渠旁,没有客人。张超阳感觉压抑得难受。他不明白男人每天这样坐着,怎样挣钱养家?
开学前一天,张超阳特意去水渠边看。夏利车上落满灰尘,小孩子们在上面歪歪扭扭写着“王丽丽,我爱你”,“日”,“王八蛋”等字样,车轮胎瘪瘪的,一看就是被放了气,蜘蛛网结在倒车镜上,有蜘蛛在爬。
2
几年之后,张超阳辗转几个单位,从小学老师到县政府,最终到了市里一重要部门,完成一个三级跳,成了镇上的传奇。
谁也没有在意他在距离家乡两百里远的市里是被借调,做着自己很不喜欢的写公文工作。
每个周末下班之后,张超阳赶末班车回家,星期一则早早坐第一班车赶往单位。
那是冬天,早晨五点半整个县城笼罩在漆黑之中,风嗖嗖的像恶狗那样叫。张超阳第一次掀开汽车站售票厅厚厚的油渍麻花的棉门帘时,里面昏黄的灯发着让人迷糊的光,五十多岁的司机抱着黑色的人造革皮包坐在门口打盹。
张超阳走到售票口,说:“X市,一张。”
他突然看见了无双。她坐在对面两三尺远的售票室里面,与他只隔着层薄薄的玻璃。那一刹那,张超阳惊讶极了,不知道无双怎么就来了这里,成了运输公司的售票员?
几年过去,无双看起来似乎并没有老,只是大概因为起得早,脸上有些倦容,眼睛还是乌黑发亮,与她白皙的脸,白色的羽绒服对比起来,异常醒目。尽管她裹着厚厚的羽绒服,张超阳还是看见她挺拔的胸脯。
无双看见张超阳,没有特殊的表情,只是淡淡地说:“二十五。”
张超阳微微有些失望。隔着三百米远的距离,他望了一夏天的女孩,竟然对他没有点印象。
这是张超阳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听到无双的声音,清脆,带点嘶哑。
他掏出三十元,她找了五元。
拿着票张超阳从门口那位昏昏欲睡的司机旁穿过去,进了车站停车场。偌大的停车场黑乎乎的,里面只有两班早车,一班去太原,一班去X市。张超阳上了去X市那辆车,车上只有两个人。张超阳在发动机那块儿找个位置坐下,闭上眼睛边补觉,边想无双的事情。觉得还是很纳闷,她怎么来这里工作?她的丈夫在开出租车,还是开门市,或者离婚了?她的孩子呢?她这么早起来,谁来照看?一连串的问题使得张超阳脑子里乱哄哄的。
张超阳知道人和鸟类不同,只要迁移,不管距离多近,哪怕十公里远,也会面临大堆问题。
那天,直到来到两百里远的市里,迎接新一周的生活,张超阳才把无双的事情暂时搁在脑后。
一个星期匆匆忙忙过去,又一个星期一到来之后,张超阳又赶往车站。他想无双在不在了?她不会是上次偶尔顶替别人上几天班,或者像街上发传单的人,只是临时干干挣点零花钱?
还没到冬至,冬往深里走,这会儿天似乎更黑,路上连清洁工人都没有出来。
张超阳掀开那张棉门帘,昏黄欲睡的灯,打瞌睡的老司机,都还是老样子。
几步走到售票口前,他看到无双。她和一周前比没有什么变化,连衣服也还是那件白色羽绒衣。
张超阳说:“X市,一张。”
“二十五。”无双说。一个多余的字也没有。声音也不高不低,不冷不热,从里面听不出无双认出张超阳没有?反正语气中没有半点感情或类似熟人的感觉。
张超阳微微叹口气,想无双大概是这里的正式员工了,每天面对成千上万的旅客,哪里会注意到他这样普通的呢?
张超阳拿起票,走进停车场,上了发往X市的班车。
无双这样对张超阳,他有些遗憾,但是看到她张超阳还是快乐,尤其是在每周开始的时候这么早看到她,觉得是好生活开始的预兆。
以后的每个星期一,去市里时张超阳都有些期待。
每次都能看到无双,她总是穿着那件白色的羽绒服,眼睛漆黑发亮。
张超阳说:“X市,一张。”
她说:“二十五。”
他们没有多说过一句话。张超阳有满肚子的疑问想问她,但是觉得不合时宜。门口总是打盹的那个司机,让他觉得像卧着的狗,只要他多说一句话,他就会马上醒过来。
高兴的同时,张超阳又觉得无双可怜,还为她担忧。每周五点多他起一次,无双却天天这样。这么冷的天,别人都还在睡觉,她就早早起床,街上黑漆漆的几乎没有人,万一路上遇到坏人咋办呢?再说卖票也不是好工作,日复一日重复的事情想起来就无趣和恐惧,说社会价值,也没有多大社会价值,她是不是有难言之隐,或者被强迫来的?这样想,张超阳就觉得门口那位打瞌睡的司机像肮脏的鬣狗。
有时,张超阳有点小想法,比如借着取票的机会,轻轻触触无双的手指尖。可是她没有给过他这样的机会。每次她都是把票打出来之后,直接放到玻璃下面金属的凹槽中。没有这样的机会,张超阳便观察无双的手,发现她打票的时候,手指在键盘上敲打十分熟练,电脑旁边,没有那年夏天她手中常见的瓜子、辣条、薯条、鸭脖等零食,而是放着电脑教程书。看到这本书,张超阳对无双忽然有了丝敬意,似乎明白了她怎样从卖毛线的姑娘变成了运输公司的售票员,但经验又告诉他,生活没有这么简单,因为你会打几个字,就能找到相对稳定的工作。
从那之后,每次周一买票,张超阳就观察无双手边的书,看见除了电脑,还有英语字典。他猜她学电脑时有不认识的单词,所以查字典。他的包里也有本书,是小说。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只要出门,包里就带本书。看到无双也看书,尽管他们关心的书不同,但他还是觉得在他们中间找到了共同点,感到高兴。
一个星期天,忽然下起雪,从早上下到中午还没有停。张超阳担心第二天路滑,汽车不能准时发车,便在当天下午坐火车去了市里。
下火车时,雪停,天黑。在街上草草吃了饭,张超阳回到借宿的地方,感觉比平日冷许多,有种空朗朗的感觉。于是早早钻进被子里,拿起枕头边的书,百无聊赖地翻着,很快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屋里漆黑,看表五点多点,是他以往周一起床赶车的时间。张超阳睡不着了,他想不知道今天汽车站发不发车,不知道无双去了售票室没有?有这想法,就赶紧起床,奔市里车站。
十多分钟后,张超阳走进候车厅,黑乎乎的长椅上躺着个老头,身上盖着件已经不多见的白色羊皮大衣,羊毛发黑,有几块地方脱了毛,露出疥疮一样的白斑。不知怎样,他有种心酸的感觉。
售票口前,五个窗口只有一个里面有人。是个中年女人,涂着血红的嘴唇。
张超阳问:“今天发车吗?”
“发,推迟半小时。”
张超阳离开窗口,想到无双可能已经坐到两百里外的那个售票室的窗口,忽然有种奇怪的冲动,想回去看看她。于是买了回县里的车。
张超阳想假如上班后单位的同事看到他没有来,打电话的话,他就告诉他们,因为下雪,车发得迟。
在等发车的半小时里,没事可干,张超阳想到单位上给他们发的电脑教程书还没看,就跑回单位把这本书取上。打开后,发觉里面还有一张闪亮的光碟。
客车中途停下来拉人时,天亮起来,张超阳发现路的两边积着大约有两寸厚的雪。卖零食的女人提着篮子上了车,他买了两个烤红薯。
路上他吃了一个,留着一个。
八点多时,张超阳回到县里。想到单位已经上班了,以往这个时候,他已经把办公室打扫完,浇了花,打好了开水。今天竟破天荒地迟到了!张超阳心里发虚,但有种破坏了什么似的快感。进了候车室,那个打盹的司机不在,里面等车的人比以前早上多。售票口前,无双坐在那里,穿着白色羽绒服。
她看见张超阳,眼睛亮了,问:“X市?”
张超阳没想到她会先说话,感觉他们之间以前那种冷漠的僵局被打破。他说:“X市。”
她笑了,眼睛弯起来,显得很妩媚。但马上恢复以前的样子,边打票边问:“今天迟了吧?”
张超阳慌乱地回答:“没事儿。”把书和烤红薯递进去。
无双接过它们,放到她那本书上面,把票递给他说:“谢谢!”她的动作自然大方,仿佛他们是相熟多年的老朋友。
十分钟后,张超阳坐上县里开往X市的班车,发现车居然就是刚才他回来时坐的那辆,司机也是刚才的那位。车出站,他才想起没有给无双买票的钱。
路上,张超阳想起今天无双的变化,暗暗高兴。
快到八点半时,单位的同事给他打电话,通知九点开会。他说在路上,下雪了,不好走。
九点钟时,办公室主任给他打电话,说正要开会,领导问他呢?张超阳说下雪了,车走得慢。
又过大约二十分钟,办公室主任再次打过电话来,问他走哪里了?领导问还不到!张超阳说,他不到五点半就到车站,车不发啊!
此后,办公室主任又打过来两次电话,张超阳装作没听见,都没有接。他不知道单位发生什么事情,非要他这个借调人员马上赶去。以前他每周到那么早,也没见别人来几个呀。这样想,心里还是有些忐忑。
车到站,张超阳花五元钱打车去了单位,单位的会已经开完。一位同事告诉张超阳,刚才开会领导问他几次,开完会,带着办公室主任下乡去了。张超阳想,莫不是领导大发慈悲,觉得他还干得不错,要调他了?
3
又过三年,张超阳还在借调。单位每年年底进一两个人,但都是各种各样领导的侄子、侄女、外甥等关系。
张超阳的情绪负面到极点,多少次想返回县里原来单位,但是面子上抹不开。于是开始想种种办法。
在此期间,张超阳回镇上参加过老乡会,组织者是叫“球棒”的黑道老大。因为开地下赌场,1998年被省公安厅派人潜伏三个月抓获,判了十几年徒刑。当时新闻联播和许多重大媒体都报道了。张超阳被借到市里时,他经过几次减刑出狱,很快东山再起,开了铁矿,搞起运输车队。
老乡会上,“球棒”挨桌子敬酒。敬到张超阳他们这桌,有人轮流介绍宾客,“球棒”和张超阳握手时,手掂了两下。张超阳感到他的手热乎乎的,有点温暖,不像想象中的黑道老大那么邪恶。“球棒”和大家握完手,端起杯子说,人在社会上混,谁不需要谁啊,大家互相照顾,有啥需要麻烦我的尽管开口。
他在看着大家说,但张超阳感觉像在和他说。他的心跳得厉害。似乎看到希望。
喝完酒、聚完会,人们又各干各的去了。
张超阳回到单位,每天还在干着写公文这种憋气的活儿,还在借调着。他没有试着去找“球棒”,有时他想起“球棒”说的话,摇摇头,觉得自己幼稚。
无双,那年冬天之后,张超阳已经几年没见了。
最后一次见她,没啥异常。张超阳没有想到她会突然不见。那时,他觉得他们每周早上这样见面像生活中一些恒定的事情,会延续到老。他甚至连个联系电话都没要。
无双忽然不见,也没有个合适的地方去打听,售票室变得寒冷而孤寂。张超阳星期一五点左右起床,变成了折磨。他开始想办法搭便车或坐火车,后来竟然完全不坐汽车了。
无双像张超阳生活中偶然飘出的泡沫,随着他梦想的破灭不见了。
一个周末,张超阳加了整天班,头昏脑胀,嘴里黏糊糊的,嘴唇干得掉皮。晚上从单位出来,风吹得他打个趔趄,冷!才想起今天要大降温。可是尽管身上冷得要命,他心中却烦躁得有团火烧,想马上喝杯冰镇冷饮,或者干脆嚼几块冰。
路过大院中央的水池时,张超阳下意识地望了望,水早抽干,留下黑乎乎的假山像干瘪的笋,池底铺的卵石上面积了泥巴,风吹在上面发出硬梆梆的声音。张超阳忽然想起夏天、秋天时在池子里游弋的金鱼,那些活泼可爱的金鱼大概有上百条吧,现在它们哪里去了?
这个问题困惑着张超阳,像生活在困惑着他。
这时电话响了。爸爸在电话那头说金龙的老婆难产,要马上到市医院来,让张超阳帮她挂个号。
张超阳想起金龙的钉鞋摊子,那个让人煎熬而又充满怀念的夏天浮上他的脑海。他匆忙往医院赶。街上漂浮着冰冷的雾气,汽车都开着大灯,冻僵似的木木朝前行驶,路过体育广场的电子大屏幕时,画面上的人也仿佛冻僵似的机械地说话。
来到市人民医院,大冷的天,急诊室挤满人。椅子上坐着垂头丧气抱着孩子的女人,许多颤巍巍的老人仿佛碰碰就倒,过道里站满各种年龄的男人,都满脸焦虑。张超阳排在队伍的末尾,边看表边随着人群缓缓向前移动。刺鼻的福尔马林气味,散发着乳香的孩子,病人们身上的腐臭……混杂着涌过来,他晕晕乎乎,好不容易排到窗口挂上号,足足用了半小时。
仿佛过了半个世纪,出了门诊楼,张超阳仰头看到满天星星,猛地有种想流泪的冲动,进了旁边的“德克士”。
热气迎面而来,还有好听的钢琴声。吧台前有稀拉拉几个人。张超阳走过去说,来杯冰镇冷饮。服务员仿佛没有听到他的话,接过他旁边别人递过去的钱。张超阳又说遍,可是声音没有理直气壮地变大,而是奇怪地好像比上次弱了些。因为他环顾四周,发现这里顾客是一对对情侣,跟着大人的小孩,几个结伴的女孩。他忽然有种走错地方的感觉,低下头,推开门。寒冷又开始袭击他。
金龙和他老婆还没有到。
张超阳想自己是不是太敏感了?“德克士”的服务员肯定不认识他,没必要故意冷落他,可是他怎样也不想再进去,又不想去医院候诊室,便在马路牙子上踱起步来。
天气寒冷,张超阳感觉周围所有的东西都好像在巨大的冰层中移动,他似乎能清晰地听到各种东西移动时像卡了碟时发出嚓嚓声。
他心里越来越烦躁,越来越火大。他盼望路上突然出现小偷,或者抢包的歹徒,调戏女人的流氓,他要奋不顾身地冲上去,即使抓不住他们,被刀子捅死也比现在这样痛快。
正这样想着,突然有辆霸道越野车猛地停在张朝阳面前。他吓一跳,然后疑惑地望着车门。
车窗摇下,里面伸出美丽的头颅,招呼张超阳。竟然是无双!好几年没见,她比起以前更年轻了,穿着黑色的貂皮大衣,脸上光洁白嫩,没有丝毫岁月的痕迹。记得她以前非常喜欢穿白色的衣服,现在穿上黑色的,张超阳觉得也特别好看。
无双像熟悉多年的朋友,问张超阳:“干什么?”
张超阳像回答多年未见的朋友,说:“给人挂个急诊,还没来。”
无双招呼张超阳上车。因为街上太冷,张超阳又没地方去,关键是他发现这么多年过去,还是喜欢无双,便上了车。
车上只有无双,张超阳有些惊讶,几年没见,她就开上霸道?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她身上有又甜又香的气味散发出来,到张超阳鼻子前,徘徊着不走,越积越浓。张超阳不知道是哪个牌子的香水,只感觉很好闻。想大口吸气,又觉得不礼貌。他憋着气,想起自己刚才想喝杯冷饮来,于是便说:“要不我请你喝杯饮料吧?”
她说:“好呀!”眼睛闪闪发亮,张超阳想到刚才看到的星星,心里的烦躁消失,代替的是激动。她开始发动汽车。张超阳怕金龙他们来找不到他,就说:“去旁边的德克士吧?”无双说:“我带你去个地方,很不错!”张超阳含含糊糊点点头,很愿意跟她去,但摸摸口袋,又怕钱不够,到时尴尬。他说:“我等的人快来了,咱们别走远他找不着,”说着,他掏出手机给金龙打电话。金龙说:“已经进市里了,马上就到。”挂了电话,张超阳对无双说:“看病的人马上就来,等五分钟好吗?”没等无双答应,他便下了车,向医院跑去。进了医院,他到自动取款机前把工资卡插进去,里面只有两千多元,他把整的都取出来。
金龙和她姐姐领着难产的老婆来了之后,张超阳交给他们挂号单和病历本,连病房也顾不上带他们找,就快步朝无双奔去。
无双拉着金龙到了“王府会所”,领头走进去。来市里几年,张超阳多次听说这个地方,却没有来过。他隐隐约约盼望发生些什么事情。
无双点了包间,两人进去之后,张超阳感觉不冷了,大概因为空间小又封闭的缘故,无双身上的香味更加浓郁。张超阳觉得有些热。正想着,无双已经把外面的貂皮大衣脱下来放在旁边的椅子上。张超阳看见她白色的羊绒T恤,T恤下面隐隐起伏的胸脯,象牙果那样白的脖子。
服务生进来,轻轻把无双脱下来的大衣挂衣架上,问他们要什么?
无双用征询的口气问张超阳,“你喝什么?”
张超阳本来想说来杯冷饮,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他想起在书里读到过拿铁,便问:“有拿铁吗?”
服务员说:“先生,有的。”
无双菜单也不看,张嘴就点,眨眼间桌子上摆满东西,咖啡、沙拉、牛排、刺身、干果、水果、纸巾……还没吃东西,张超阳就感觉肚子胀得难受,隔段时期,用眼睛的余光瞄瞄菜单,猜测两千元够不够。
无双显然也不饿,吃两口沙拉,就用纸巾擦擦嘴问道:“你这两年过得怎样?”
张超阳满肚子苦水,却回答:“还好。”
无双好看的大眼睛笑了,她说:“你们活得质量高。这下我也要来市里工作?”
“哪里?”张超阳屏住呼吸问。脑子里猜测无双开着这样的豪华车,要去哪里上班才合适?金店、汽车销售公司、房地产……
“xx部。”无双居然说的是张超阳借调的单位。
张超阳下意识地马上就说:“千万别去,不好。”
无双好奇地瞪大眼睛说:“球棒说xx部挺好的,工作清闲,运气好的话,干上几年还可能下县里去当个领导。”她边说边优雅地剥着桔子,“球棒说他托了好大的关系,才办妥这件事。”
张超阳的脑袋嗡嗡响着,里面一片空白。他揪了揪领口,明白无双的来和他的来不一样。
果然无双接着说:“球棒把关系都已经办好了。”她打开精致的皮包,从里面拿出调令。
张超阳看到上面写着:现介绍陆无双同志到xx部门工作,请与接洽,下面盖着组织部的公章。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他的喉咙发干。无双,正式到他们单位工作?他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她凭什么到他们单位呀?几年前,她只是运输公司的售票员。再往前几年,她连工作也没有,只是街上卖毛线的。
他看着美丽的无双,强自镇静地问:“没说让你去干什么?”
“文秘吧?我会打字。”无双回答得很淡定,远远超出张超阳的想象。
张超阳想起无双当年售票时旁边放的电脑书,他还送了她电脑教程书。他顿时觉得自己喘不过气来,他拿起桌子上的东西乱吃几口,然后不管无双吃完没有,大声招呼服务员买单。服务员过来,无双抢在他前面,递出张卡。她问张超阳是不是不舒服?张超阳使劲摇头说没事,坚持要买单。数钞票时,他感觉眼泪在眼睛里打转。
出了会所,无双要送他回去,他坚决拒绝。
摇摇晃晃走在马路上,张超阳像喝多了酒,他想起以前在马路上看到这样的人,他还在心里嘲笑他们。他觉得自己真傻!
刺骨的寒风吹到脸上他丝毫感觉不到冷。他掏出手机给许多在县里工作的朋友打电话。问他们,认识陆无双吗?
几乎没有人不知道。
……
张超阳想找根烟抽,可他平时根本不抽烟,身上哪有?跑到最近的便利店,买了包领导们经常抽的软中华。风很大,点了几次才点着。他的脑子混乱,像短路后烧作一团的电线。一连大概抽了七八根烟,烟盒子瘪下去,他脑子里的东西也好像被烟吸完,变成空白。只是感觉夜色越来越浓,寒冷好像有颜色似的越来越稠,风从宽阔的马路和楼房的缝隙中扑面而来,像把他要摁倒在地上。他想起今天是想喝杯冷饮的,为什么不去呢?他把剩下的半盒烟掏出,揉成一团扔进垃圾箱,向近处的快餐店走去。很快,他看到了肯德基鲜明的标志,山德士上校系着蝶形领结,围着红色围裙向他微笑。
他对服务员说:“来杯冰可乐。”
服务员脸上显出惊讶的样子,但几乎不到一秒钟时间就换上微笑。她说:“先生,好的,请您坐下稍等。”
张超阳选了靠近窗户的桌子坐下,看见寒冷爬在外面像要把玻璃挤碎爬进来。
服务员端来冰可乐,张超阳吸了口,打个哆嗦,感觉骨髓也要冻住。他想为什么非要喝杯冰可乐呢?
这时他不由又想起院中池子里的金鱼,它们到冬天到底死去了,还是被移到室内养起来,等到来年春天再放到池子里?他不停地想啊想……
忽然他觉得池子里还有水,只不过是结了冰,金鱼就在那些冰层下面,等待春天。他站起来,要去池子那儿亲眼看看。
一出门,他看见刚才那辆霸道越野车停在面前,他觉得自己今天神经不正常。
车窗摇下,里面伸出美丽的头颅。无双关心地问:“你真没事吧?”张超阳恍惚看到巨大的美人鱼在冰层下面挣扎,他感觉说不出来的快感。他拉开副驾驶座的车门,坐上去。问道:“池子里的金鱼,它们到冬天到底死去了,还是被移到室内养了起来?”无双用美丽的大眼睛困惑地望着他。张超阳低声嘟哝句:“白痴!”然后说:“咱们到你要工作的地方看看吧?”无双甜甜地笑了。
越野车在大院门口停住时,张超阳摇下车窗和警卫打招呼,警卫向他敬礼。张超阳感觉心里甜甜的,来这儿几年,从来没有人向他敬过礼。
因为晚上,大院停车场空荡荡的。张超阳领无双停好车,带她向院子中央的池子走去。风又呼呼刮起来,他瞧无双,她把貂皮大衣裹得紧紧的,他发现自己也不怕冷了。
池子边闪烁着五颜六色的灯,国旗杆在风中摇晃,发出嗡嗡的声音。池底干干的,抹着水泥,几块破布与卫生棉被什么东西挂住,在风中挣扎。刚才怎么没有发现呢?张超阳心里发出冷笑,他朝五楼的个地方指了指,对无双说:“你来了就是到那个房间办公。”无双扬起脖子,朝黑洞洞的窗户张望。张超阳把手放在她屁股上,用劲一推,无双头朝下栽了下去。张超阳听到尖叫声,像多年前他在铺子里听到的尖叫声。他没有动,手上热乎乎的。
池底的冰破开,下面空空的,那些金鱼哪里去了?他放声哭起来。
(责编:王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