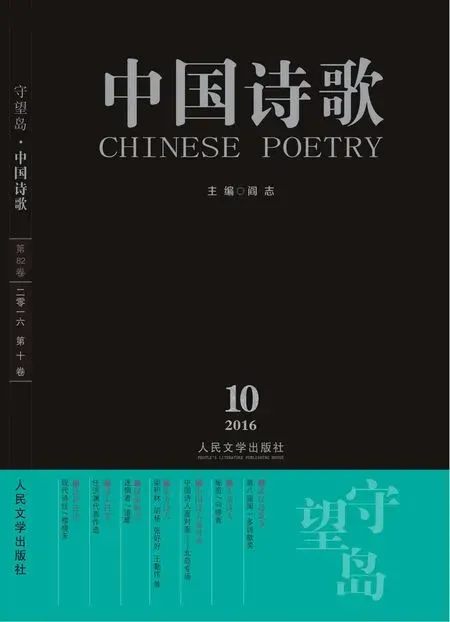长征在前我在后(十四章)
2016-11-26黄亚洲
□黄亚洲
长征在前我在后(十四章)
□黄亚洲
苏区即将喷发
这是哪一个夜晚,一盏油灯,在中国江西瑞金的哪一座瓦檐下,点亮了智慧?点亮了思想的导火索?
导火索,连着一座火山的根部。
苏区即将喷发。中国的火焰要向西北流动,以它岩浆的形态。而我知道,岩浆,是一个以忍耐著称的民族,最后的说话方式。
不是溃逃,也不是倒背旗帜,是土地和天空的更新。
就是这样,不能让蒋介石的四道封锁线,扎紧革命的主动脉,让中国,在江西失血。
把银元和药品分到各军团;储存草鞋,储存草一样顽强的生命力;把妇女编队;所有的文件,现在,都由扁担装订。
这是一个国度的整体移动。
由于摩擦,这个巨大的板块,将溅起火星或者太阳。
一些山峰注定要被撞开,一些江河注定要被蒸发,火山灰将以硝烟的姿势,使全世界的报章持续咳嗽;在那些报纸的报眼里,将流出中国西部所有的大河。
这是穿草鞋的马克思,在中国走路。他曾经在欧洲徘徊,现在,他把出发点定在江西。
毛泽东也被抬上担架,他正在病中;我们知道,最初的那盏油灯不属于他,但是随着与滚滚岩浆的一起奔流,他也将持续地低沉地发出一座火山的全部轰鸣,以他地地道道的、开满辣椒花的中国湖南方言。
岩浆流到哪里,辣椒花就开到哪里。土地的力量与土地的形态,是一致的。
血战湘江
如果湘江注定要染成一面红旗,那么,就让长江,腹痛一次。
毋庸置疑,湖南位于长江的盲肠部位;巨龙起飞之前,这一场疼痛,难以避免。
太多的东西在血中流淌——草鞋、八角军帽、手枪的皮套,以及,《关于土地问题》的文件。
一座山崩塌河中,红色泥沙,顺流而下。
多少年后,在中国革命的入海口,这些泥沙,会淤积起来,成为纪念碑的基座。
但是在那样的三天里,湘江一直流血。中央军的轰炸机,几乎扔下了天上所有的星座,而湘军和桂军,则一齐伸手,试图把湘江的血口子,掰得更宽。
红军的一半颜色失落在湘江。这些颜色,是分三天流尽的。那一轮暗红的带腥味的太阳,仿佛是湘江的源头,但是,重要的是但是:
但是,在后来的日子里,所有的军用地图都表明,那支蜿蜿蜒蜒的血红的箭头,其色泽,没有一点儿消褪。
历史永远记住了这一次腹痛,只要翻开那一页,湘江就会蜷曲;纸张,就会成为凝结的血浆。
不能等了,一次剖腹掏心的手术,需要在腾飞之前完成;湘江必须止血。有一些故作庄严的结石,需要从关键部位取出;不能等了,革命不需要止痛药。
正式缝合的手术室,可以考虑设在遵义城,那么,也就这样决定了吧,就在这一次疼痛的脐下三寸——贵州遵义城。
显然,遵义,这个冷峻的山城,其地理形状,有止血钳的模样。
遵义会议旧址
我窗户外头,有两株槐树,朱德的夫人后来这样回忆——于是,一间重要的房间被确定了。
于是,陆陆续续,所有参加会议的人物都被确定了。
会议中有些沉默的部分,也有了响亮的记录;连方桌底下那只火盆,也确定了火焰的样式。
中国革命的一段之字形历史,被制成精确的沙盘。
转折很重要。转折,是岁月拍痛的手掌;是史册上,章节与章节的装订线;是点燃在领袖嘴边的一句诗;是包扎完毕的历史,上路之前,一坛重开的酒。
现在就让我,对遵义表示敬意,那是重要得不能再重要的一天。它在火盆里点亮了一朵思想,使所有围聚的冻僵的脚指头,一齐温暖——中国的路,从此走通。
乌江渡口
乌江仿佛是以一种负面形象进入历史的,看上去,乌江确实有点黑。但我必须告诉你,那一日,当天色真正黑下来以后,乌江突然金光闪闪。
乌江从此竖了起来,在教科书里竖成里程碑;我必须告诉你,一条江能够像汉子一样站起来,是由于,江边出现了一些真正的汉子的缘故。
那些人不是诗人,但是他们敢于面对波涛,想象乌江,尽管所有的渡船都已被烧毁。
但是,在他们的想象中,渡船,并不是这条液体拉链能够合拢的惟一拉纽。
由于一只深夜的竹筏,由于几个共产党员和几颗手雷,金沙县和息烽县突然土地相连。一个县成了前脚掌,一个县成了后脚掌。
脚印中间,凹陷的部位,当然就是乌江。
其实,乌江也不是凹陷的概念,就在那一刻,我告诉你,乌江是竖了起来的——甚至,乌江进入了花岗岩,所有黑色的波纹,都成为碑上的文字。
就这样,一些戴八角帽的人,在遵义会议之后,重新定义了乌江;贵州之所以多雨,一大部分,都是碑上流下的江水。
征途中,一个神甫
神甫献出一张地图,洋手指,一路点着中国的地名,却一路读着法国字母——肖克听懂了,他知道,几天以后,这些地名就将由枪声和鲜血,重新拼出。
哦,法国神甫,你准备传教的地方,我们想先行一步;最浓重的黑暗,必须以最红的血冲洗,而有些火种,也需要,沿途珍储。
当然,我们也欢迎一枚十字架,临时入伍。
于是事情变得简单——红军长征的硝烟,从第二天起,就以长髯的方式,在神甫胸前飘拂。
每当枪声炒豆般响起,神甫都会滚到路边,卷成一节豆荚。他最善于以爆豆的频率,念叨一百遍圣母。
而这时候,肖克与贺龙们所指望的,则是人民,以及人民所赖以生存的思想,那些思想贴肉贴骨,补丁一样朴素。
其实,那些思想的缝纫者,也是欧洲人。一个叫马克思,一个叫恩格斯,都不是黑色眼珠。
而这个叫勃沙特的神甫,也来自欧洲,虽然现在,他已不知道他的教区,被鹰叼到了何处。他的大脚趾探出破皮鞋,每一天,都老老实实,探索马克思主义征途。
他的脚掌,则开始流出难闻的水;肚子饿极之时,他也无法把掌心伸向圣母。但是他知道,他猝然遭遇的是一种精神,而关于这种献身精神,他的玛利亚早有过描述。
那一夜,他曾经面对枪口,害怕得像一张索索发抖的地图。现在,他成了枪托的一部分。甚至,他在中国革命的黑暗的枪膛里,有了自己的转速。他做梦也没想到,在这个神秘的国度,他,会拥有一条手扶来复线的传教之路。
后来,长征成了他毕生的回忆。那天,他奔上山冈,双臂高舞。一杆红旗,在他的满眶泪水的帮助下,成为一只游向天空的鹰。那一天他哭了,他双臂高舞。
他知道有一队铁器,正向土地的深度掘进;他知道有一杆旗帜,超越了鲜血的浓度;他知道中国的土地很快就有开花的一天,而且花草的种子,并非来自万能的圣母。
我不知道圣母对一个归来的孩子,最终说了些什么,但我可以断定,他后来对玛利亚打的小报告,绝不仅仅是一张法文地图。
必定有关哲学,有关十字架与锤子镰刀的异同,有关——鹰翅的高度。
关于赤水的四渡
红军的先头部队,如同一枚缝衣针。就这么缝来缝去缝了四针,蒋介石便不知道,红军,要做一件什么样的褂子了。
其实,红军缝的是一面旗帜,为中国定做的。旗帜之颜色,与河水,高度地一致。
今天,我在丙安古镇看桥下流水,看见当年的旗帜仍在翻飞。河中有一些石头,凝结着镰刀和锤子的形态。
在军事上,这是一次奇异的缝纫。一些互不关联的土地,还有道路,突然,被拼接在了一起(顺便说一句,时隔五十年,邓小平缝纫香港,采用的,也是这种针法)。
于是,空间顿时开阔,密不透风的森林,被稀释成灌木和草地,传统的军事读本在错订页码之后,突然,变成经典。
古镇的老大爷指一个小木屋给我看,说这是红一军团的司令部,而我知道,这是毛泽东在缝纫之后,顺口,咬下的一个线结。
红军标语
红军走了,带走一群子弟,留下一批标语。
红军带走的子弟,会在另一处家乡,动用骨血,把墙,刷成标语。
红军留下的标语,会把这里的人,拉向墙的另一面,成为革命子弟。
字迹,总是如蒿草一样朴素,所以常在墙上扎根;笔画,能够钻进砖缝,成为庄稼的茎须。
毛泽东说长征是宣传队,毛泽东又说长征是播种机。毛泽东的话是一堵墙的两面。墙的两面,都是红军标语。
一条标语,使中国的墙,由阻力,变成动力。
墙上写完字,就匆匆走;他们太忙,常常不得休息;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
那是天安门大墙上,急需,两条标语。
战士如是说
我用枪的嗓音喊叫,用手雷的姿势舞蹈,如果,敌人不再是追兵而是大河,我就用舢板,制造横向的瀑布。
子弹带斜背在胸前,这是一场战争的全部声响,而那把决不离身的大刀,是我长在背脊上的肋骨。
如果,我举着火把走路,那就是中国有一条山脉,需要在夜间耸动;如果,我嚼的是生涩的青稞,那就是全中国的庄稼,都在苦候季节。
由于祖国始终在我胸中蛰伏,我的枪口,会持续不断地,吐出
惊蛰、清明、大暑和白露。我每年都在我自己的爆竹声中过年,始终,把准星,铆在火山的喷口上。
我听过毛委员和朱总司令的演讲,他们的教鞭,一直是那根长长的地平线;说到底,地平线也并不是很长,无非是,由上百条鞋带连结而成。我脚板上整齐的血泡,是一串土地绽放的灯。
每临黑夜,我都会把军衣上褴褛的布条、空弹匣,伤口新长的肉芽、溃烂的胃,叫拢在一起,开个民主生活会;我每次都提倡畅所欲言:关于疼痛,关于坚持,关于胜利。
因此,我必须,在自己的伤口里扎紧绑腿,并且,将鲜血撂在脚边,这送行的红花。
即便我倒下,我最后的子弹,也会从我的血管里,流完余下的半场战争。
我时刻准备军号与雷电同时响起,这样,我将立即把行军改成冲锋。在我高呼着我的神圣的主义,飞一般,踏过花朵和草尖的时候,我会始终把自己的头颅,以及,钉在头颅正中的那颗红星,提在手里!
是的,我的手,将始终攥成拳头,这是一个士兵的标准动作;曾经,在党旗下,它就是这个形状。
泸定桥
路,有时候是土地,有时候是水,有时候,是十三根铁链。
在铁链上走路,需要二十二个人,二十二支枪,二十二把马刀,以及,二十二句摘自《国际歌》的口号。
而且,需要匍匐前进;把目光,降低到火舌的高度;让皮肉与铁链的磨擦,发出骨头的声音。
敬礼,二连连长廖大珠;敬礼,廖大珠身边的战友;现在,铁链与你们背上的马刀,以及你们的脊梁骨,是同一块钢铁。
一个世界在阻挡一个世界的靠近。所有的蛇,都在吞吐机枪的舌头。但是,奴隶身上的铁链,已经不在奴隶身上了,它们,已直接钩紧了统治阶级的底座!
十三根铁链,全是由大渡河淬火的,专门选择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成为道路,成为一个阶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宽广的通途。
让我们永远记住《国际歌》的这一次特别演奏——在中国四川,在泸定,在机枪和军号的伴奏下,这二十二个跳动不息的音符,以及,由钢铁打制的晃动不息的两个半五线谱!
红薯,银元,藤蔓
每个士兵,可以挖两只红薯!
每个士兵,只准挖两只红薯!
吴焕先政委下达这道命令之后,便知道他有望突破封锁线了,他的所有将士的饥胃,一刻钟后,都会具有红薯的形状。
红二十五军的这位政委一边啃红薯,一边脱下军衣,他说:必须,包上一堆银元,埋入红薯地。挂在我们腰边的手雷,在老百姓面前,应该是秤砣。
老乡们后来使唤锄耙的时候,铁齿忽然就咬着了银元。这时候,老乡们的眼泪就流了下来,老乡们说:喔唷,喔唷,喔唷!
这时候,银元逢水发芽,就吐出了绿叶和藤蔓。
老乡们知道,这根藤蔓,后来就一直爬伸到了陕西延安,接着
又爬伸到了北京。但是,这根藤蔓最初的根系,老乡们尤其知道,出在哪里。
要告诉所有的块茎植物,不要骄傲;它们并不总像红薯一样,具有胃或者心的形状;而要,准确地告诉它们——
中国土地最肥沃的一块,是黄土地。
黄土地最黏厚的一块,是红薯地。
懋功,红军遇上红军
两支八角帽灰军装的部队,两支把山捆在腰边把河喝进肚里的部队,两支把生与死的锯齿当作磨刀石的部队——几乎同时,发现了对方。
起初,他们还以为,在夹金雪山这面镜子里,看见了自己。
一方面军!四方面军!——他们同时向对方欢呼着奔跑。军帽像雨一样泻到天上,而军帽像雨一样落下来的时候,罩上的,已经是同一支部队。
铁水应当跟铁水流在一起。是啊,懋功很小,小如一只铁砧;但是一把加长的利剑,就应该,在这里叮叮当当锻成。
河流应当跟河流奔在一起。是啊,懋功很狠,狠如一扇憋住气的闸门。很快了,阴暗的岁月,将很快出闸,咆哮成为汪洋。
懋功天主教堂全天不闻钟声,一千名团以上干部都挤在这里擂肩联欢;由于喜悦,墙上的那个十字架,也错看成了会师的符号。
革命搂住了革命的脖子。团结站到了团结的左肋。火焰托起了火焰的腰杆。胜利踩上了胜利的肩膀。
懋功狂欢的色泽,至今没有消褪。可以翻一翻中共军事史,翻到一九三五年六月,那里,必有一张——缤纷的彩页!
别让暴风雪丢下你们
我能否,谢绝你的一根火柴;能否,谢绝你的七粒青稞。我没有伤口,但是我知道,我身体里的河快流尽了。
夕阳照亮雪峰。我看见了我的墓碑。
指导员,谢谢你,快走吧,别让暴风雪丢下你们。
其实今天一早,我的视线就模糊了,但我的心一直是亮堂的,我的发白的眼睫毛,是太阳的光线。
你们快去,追旗帜上的那个弹洞吧,别让焦黑的锤子和镰刀,丢下握柄的人。
如果,你们穿过了暴风雪,能在当晚的星光下,开个支部大会,我是会很高兴的。关于一个组织,我想得到追认。
如果有可能,指导员,胜利了,递句话,给我老娘——就说,她每年过年在门口扫的雪,都是我从这座山里捎给她的;还有,叫翠芝别再等了,好在我俩还不曾圆房。
草地
如果,你的草尖,都像大肠纤毛一样晃动,又让我,如何来形容你大草原的美丽?
如果,你柔软的土地,都如胃壁一样贪婪,我又怎么敢让我的脚步,听从蝴蝶的引导?
现在我已走入了草原深处,我不知道,白花是不是你的牙齿,红花是不是你的舌苔?
风吹过的时候,黄花像眼球一样抖动;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你食欲的信号?
一个战士,一匹马,会在瞬间消失。泥浆吐出一串气泡,像是饱嗝。
“快抓住我的手!”有时候,动作必须疾如闪电,不要让士兵把二十岁的年龄,直接栽入土地。
队伍走出草地的时候,又短了一截。该让我,怎么来评价,大草原黄昏时分的宁静?
有时候,中指或者食指,会像草根一样裸露;一只蝴蝶,停在上头。
有时候,一顶孤单的军帽,会在草根间飘浮;那是思想在代替脚步,完成悲壮的征程。
如果说,中国革命曾经穿过几天刑衣,那么,就让我们,永远记住开满红花、黄花、白花的这片色彩斑斓的草地。
马
马,再不必辛苦,我的宛若兄弟一样的马啊!
一个使人悲伤的好消息,也许是:沉重的行军锅和弹药箱,从明天起,将不再成为你的背负。
篝火已经点燃,士兵们已经背过脸去。马啊马,今夜,是的,就在今夜,我们将分食你的坚硬的腿脚,以及,你的瘦削的屁股。
本来,这颗子弹,是准备对付蒋介石的,现在,却要用来结束你的痛苦——虽然我们知道,你蹄子深处,还沾有雪山的冰屑;川军的两处弹痕,至今留在你的腹部。
记得,你是从瑞金和我们一起出发的,骑过首长和伤员,驮过弹药和粮布;应该说,革命吃过多少苦,你也吃过多少苦。
你,当然没有想过,你自己的信念和肉体,在一个血色的黄昏,也会饱革命之腹。
你的眼里和我们的眼里,现在,都有泪水流出。篝火已经很旺了
铁锅里,水也已经烧开,前方和后方都没有敌人追堵,然而,枪声和鲜血,却要在革命内部,见证一次杀戮。
我的兄弟,闭上眼睛吧。如果,你不倒在草原深处,许多忠勇的士兵,将永远与青草为伍。告诉你啊,马——草根和树皮,已经使我们脸面浮肿。昨天,士兵最后的一根皮带,也已经水煮。
马啊马,让我们最后再叫你一声兄弟。现在,班长已经拉开枪栓,往枪膛里,压入了一颗泪珠。
许多年之后,亲爱的马,当长征士兵的形象,成为城市广场的雕塑;你,也必将与我们一起,高高地昂着你的头颅。当然,你那头颅的后侧,我们,并不会雕刻上一粒伤心的弹孔;我们不会的,我们只雕刻你暴烈如阳光的马鬃,拍打着所有未来的年代,迎风狂舞。
再提醒一遍,虽说这很痛苦:一颗沉甸甸的子弹,通常情况下
只指向革命的外部;有的时候,它,也是革命内部的一颗沉甸甸的泪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