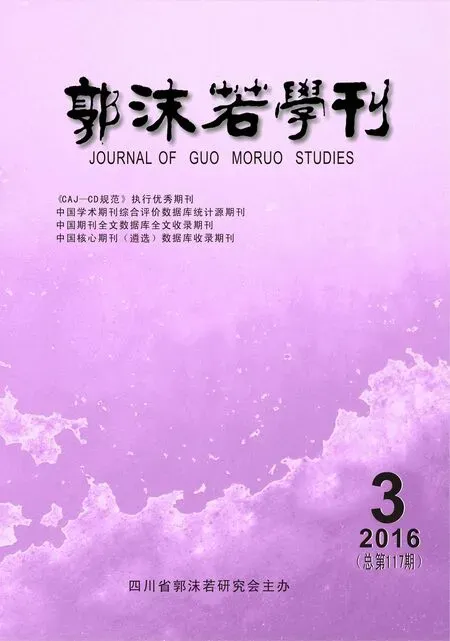艾芜与郭沫若的君子之交
2016-11-26陈俐
陈俐
(乐山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乐山 614000)
艾芜与郭沫若的君子之交
陈俐
(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乐山614000)
郭沫若曾分别在散文《痈》和给彭桂萼书信中两次赞扬艾芜的《南行记》,艾芜也曾两次撰文谈到郭沫若的作品对他一生的影响。本文详细地考察了艾芜与郭沫若文字交往的历史脉络及君子风范。
郭沫若;艾芫;《南行记》
1992年,艾芜先生的生命已快要走到尽头,9月16日那天,他躺在四川省人民医院的病房上,心情似乎很好。透过窗外,他注意到街道两旁绿茵茵的树叶,想起了郭沫若,于是提起笔,写下了一生中最后的文章《怀念郭沫若》。还在1978年,艾芜刚听到郭沫若逝世时,“仿佛遭到了七八级的地震,久久不能平静。”他情不自禁地提笔写下了《你放下的笔,我们要勇敢地拿起来》的悼念之文。文章真切地描绘了郭沫若这位五四时期的文化奶爸给予他的精神营养。
还在上个世纪20年代,艾芜和同学们就如饥似渴的读郭沫若的新诗集《女神》,诗歌中那全新的太阳,那澎湃的大海,那死而复生的凤凰,激发起他勇敢前进的信心。他年轻时之所以全心全意投入新文艺的潮流,一生从事文艺创作,“主要的原因之一,则是郭沫若同志领导的创造社引起来的。回忆二十年代,我在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课外的读物,几乎百分之七八十是《创造周报》《创造季刊》《创造月刊》以及《文化月刊》《洪水半月刊》等等。郭沫若同志的新诗,健康而又明朗,像民歌似的容易上口,尤其令人心醉”。[1]116艾芜也读郭沫若翻译的德国文学作品,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施笃姆的《茵湖梦》也惹起他们对青春的无限遐思。译著中那种纯粹的爱情,对大自然的敏感,给予他美的享受。对于这位喝着五四新文化乳汁长大的作家,郭沫若的作品和诗性人生给予他的是乐观向上、奋发有为、勇敢面对将来的宝贵启示。
艾芜最终从文艺的道路走向革命,郭沫若也是他的引路人之一。郭沫若在《洪水半月刊》上发表的《共产与共管》《马克思进文庙》等等文章,所翻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使艾芜突破了狭隘的文艺圈子,引起他更新更美好的憧憬,向着更广阔的天地探索。
艾芜在文中只着重谈郭沫若对他一生影响,而郭沫若对他作品的高度评价则在文中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他对郭沫若的崇敬是自然的,发自内心的,和郭沫若的交往是典型的君子之交。上个世纪30年代,任白戈同志去日本,把艾芜的《南行记》带给了逃亡中的郭沫若。关于这一点,1986年9月2日,艾芜在《悼念任白戈同志》一文中作了具体的说明:
一九三五年夏天,我同沙汀住在青岛。任白戈住在上海,特来青岛看我们。说他将去日本进修日文,还要把我们出的书带去送给郭沫若老前辈。郭老在日本写过一篇散文,谈到《南行记》中的一篇文章(发表在上海刊物《光明》上),就是任白戈推荐的。[2]154
郭沫若不仅认真地读了《南行记》,而且读出了作品的新意。1936年6月2日,郭沫若在日本的华文杂志《质文》上以《痈》为题,发表一篇精美的散文,文章由翻看刊物发现广告中的问题,非常幽默地引出“历史小”的论题,并高度评介了艾芜的《南行记》,他说:
我读过艾芜的《南行记》,这是一部满有将来的书,我最喜欢《松岭上》那篇中的一句名言,“同情和助力是应该放在年轻一代人身上的”。这句话深切地打动了我,使我始终不能忘记,这和“历史小”这个理论恰恰相为表里。
郭沫若和艾芜这两个四川同乡,都曾是天下沦落人,都有过漂泊异乡他国的经历。但艾芜的《南行记》与郭沫若《漂泊三部曲》的愤世嫉俗相比,多了几分沉毅和坚韧,多了几分对人对事的理解之同情,多了几分勇敢前进的希望。作品中溢出的满满的正能量,给郭沫若留下深刻印象,所以,郭沫若不仅在《痈》中赞扬了这部作品,后来的云南抗战诗人彭桂萼写信向郭沫若请教写作之时,他回信向这位边疆诗人推荐了艾芜的《南行记》:
边疆的风土人情,正是绝好的文学资料。希望能有人以静观的态度,以有诗意的笔调写出。艾芜的《南行记》便以此而成功者也。
虽是寥寥几句,却总结了艾芜小说的特殊魅力:绝好的异域风情、沉静从容的节奏、诗意葱郁的笔调,这些都是郭沫若所欣赏、所推崇的风格。
郭沫若致彭桂萼的这封信大概写于1945年,最早刊载在彭桂萼主办的《警钟》杂志第6期中。但这个杂志自1938年创刊,1945年秋停刊,先后7年只出了6期刊物和4本丛书,每期的发行量除第1期上千册外,其余各期只有几百册。且由于是自办发行,主要靠个人从云南边陲寄送,再加上处于战争年代,因此该刊绝少留存于世,人们也就很难读到这封信。一直以来,艾芜只知道郭沫若在《痈》这篇散文中对《南行记》的赞扬,并不知道后来郭沫若再次将《南行记》作为异域题材的成功范例推荐给彭氏兄弟。直至彭桂萼的胞弟彭桂蕊再次联系上他,并在信中告诉了他这件事,艾芜才知道。1979年8月由四川大学中文系编印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艾芜专辑》摘录了郭沫若给彭桂萼的这封信中对艾芜的那一段评价。这封信的全文刊发则是在后来的《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后收入张汝德,刘绍彬评著:《萼香蕊实亦芬芳——文学名家给彭氏兄弟书简评点》(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
对于彭桂萼、彭桂蕊兄弟俩,艾芜并不陌生,早在1939年,他们就曾为探讨文学创作有过通信。彭桂萼就读于云南省立第一中学。中学时代就写了不少新诗,得到楚图南和李生庄两老师的赞扬。抗战时期,时任云南缅宁师范学校校长的他积极投入到抗战的文艺宣传中去,他写有不少反映边疆生活的诗文、文学论文、散文、小说等。从1939年冬起,彭桂蕊自办并主编《警钟》季刊,刊载了许多唤醒后方民众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作品,领导学生开展各种抗日宣传活动。被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选为理事。他和国内文艺界的一些作家有广泛的接触和通讯联系,常常寄去自己的作品和自办刊物,向国内文坛大腕们请教,其中有郭沫若、艾芜、王亚平、臧克家、老舍、舒群、赵景深、闻一多、穆木天、孟十还等。这些名人也非常谦虚,热心为他的诗歌作专文评价、写序言、题字。彭桂蕊是彭桂萼的胞弟,也是文学爱好者,同时又是哥哥办刊宣传的得力助手。当年他也写信给那些他崇拜的文化名人,艾芜即是其中之一。1939年,彭桂蕊先生就给艾芜寄去他们的自办刊物《警钟》,希望能得到他们的指点。不负所望,艾芜很快就回信,充分肯定和鼓励了彭桂蕊的创作热情。艾芜的回信被彭氏兄弟以《开辟南国的文艺荒原》和《关于写作的三个问题》为题,分别刊于《警钟》的第5期和第6期。艾芜还为彭桂蕊先生题写《迎春桥头》的书名。后来因世事变迁,他们中断了书信联系。彭桂萼早已在1952年错被当作“反革命”枪毙镇压了,彭桂蕊则艰难支撑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艾芜接到彭桂蕊1979年的来信后,即回了信。这封回信最初刊发于1990年8月彭桂蕊先生委托王儒昌整理编辑、由临沧县图书馆编印的内部资料《南鸿北雁(作家书简)》中。《艾芜全集》第十五卷也收入了这封信,全信如下:
桂蕊同志:
接来信,知道你的生活情形,希望仍努力工作,为人民服务。你提供的文学资料,很是难得。尤其是郭沫若给你哥哥的回信,提到《南行记》是我第一次听见的,这很珍贵。这封信还在没有?如在,好好保存,将来可交郭沫若文集出版委员会。
四川今年六月将举行“郭沫若研究学术讨论会”,在郭沫若家乡乐山县举行,全国都有人参加,我也应邀参加,将于六月十日动身。发起的单位,即召集人,有四川大学,四川乐山地区、四川省乐山市。
关于文学方面的资料,尚望得提供一些。北京人民出版社出一内部刊物《新文学史料》(双月刊)已出三期,即需有关作家的史料或作家本人的回忆录,茅盾就在上面写有他的自传,还有别人写的闻一多传记。比如你哥哥收到的郭沫若的信,就可以抄录一份,寄去发表。
祝你身体健康
艾芜
1979年6月8日于成都[3]201
艾芜这封信正好写于被邀请参加“郭沫若研究学术讨论会”的两天前。这次会议是郭沫若逝世后一周年召开的大型学术研讨会,正如信中所说,会议是由四川大学、乐山地区、乐山市(县级)联合主办的一次盛会,会议地点在乐山大佛寺宾馆。来自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的13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召开了7天之久,其中一个重要议题是郭沫若全集的编辑出版问题。会上,吴伯萧代表“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对编辑工作的设想及工作进程作了介绍。“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是中国科学院报请中共中央组织成立的。周扬任主任,共有25个编委(其中于立群、郑伯奇、齐燕铭在召开第一次编委会之前就去世了,实际只有23个)。委员会在这次研讨会前的1978年10月27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显然艾芜事先早已知道“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成立并开始工作的情况,所以在给彭桂蕊的回信中,建议他将郭沫若的信件“好好保存,将来可交郭沫若文集出版委员会”,或者寄给《新文学史料》发表。经历时事磨难的艾芜,对郭沫若两次赞扬都没有更多的回应,只是嘱作者将此史料保存或发表。1979年的“郭沫若研究学术讨论会”名家荟萃,学者云集。经过文革十年的禁锢,大家争先恐后地发言,艾芜动情地谈到郭沫若对他一生的影响,即使是在遭到四人帮迫害期间,1968至1972年被关押在昭觉寺临时监狱四年之久,“每从牢里出来,往往自然地想起并轻声的诵读郭老的《晨安》一诗”。[4]艾芜在会上只是谈郭沫若对他的影响,却对于刚刚才获知的郭沫若对他和《南行记》的赞语只字未提,也没有谈及他与郭沫若的相识与相交。
其实,关于艾芜和郭沫若之间,可回忆的场景很多,譬如抗战初期,郭沫若刚刚从日本回国,当时正在上海的艾芜就同左联的负责人任白戈同志前去拜访,那一夜,他们在一起谈鲁迅的《阿Q正传》,谈新文学的发展。郭沫若的年轻和生气勃勃给他留下深刻印象。1937年上海召开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会,他又亲耳聆听了郭沫若的重要的讲话。后来他们又相遇在抗战陪都重庆,1946年5月4日,在重庆的“抗建堂”举行了一次文学工作者的集会。那次会上有郭沫若的演讲,也有艾芜、杨晦等有关小说、理论等方面的工作报告。新中国成立后,在文联的会议上,他们也经常相见。借会议的发言,艾芜大可就他与郭沫若的关系畅所欲言,但他仍然只是谈起郭沫若对他的人生影响。
充盈成熟的麦穗总是沉甸甸的低着头。谦和、朴实的艾芜先生就是这样:他和文学前辈大家郭沫若的交往,正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责任编辑:廖久明)
[1]艾芜.你放下的笔,我们要勇敢地拿起来[A].艾芜全集·第13卷(散文·诗歌·戏剧)[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
[2]艾芜.悼念任白戈同志[A].艾芜全集·第13卷(散文·诗歌·戏剧)[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
[3]艾芜.致彭桂蕊[A].艾芜全集·第15卷(书信)[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
[4]关辰.郭沫若研究学术讨论会简介[J].四平师范学院学报,1979(3).
中国分类号:C912.1文献标识符:A1003-7225(2016)03-0049-03
2016-06-08
陈俐,女,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