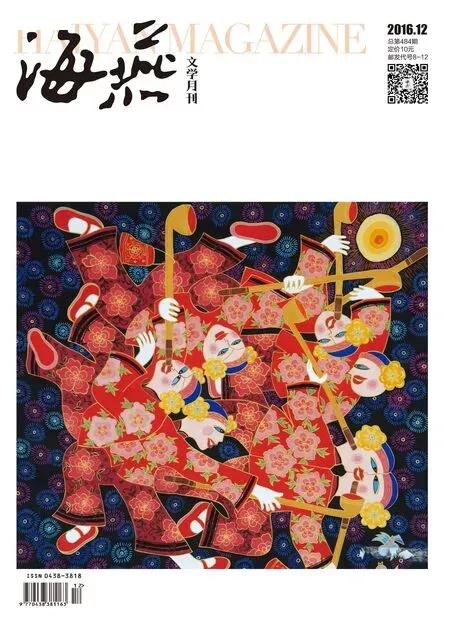寂寞的石板(散文)
2016-11-26何双
□何双
寂寞的石板(散文)
□何双
一
十八年前的一个雨天,我和同村的飞子、大象打赌,说谁要是敢喝屋檐水,谁就算有本事。大象二话不说,用飞子从铁路上捡拾回来的矿泉水瓶,站在老陈家二楼的木质回廊下,对准瓦檐的流水槽接了满满一瓶屋檐水,然后一饮而尽。我永远也无法忘记大象昂着头喝屋檐水的情景,当时雨正哗啦啦地拍打着屋顶,积水顺着瓦檐跌落地面,溅起朵朵水花,于是,成千上万朵雨花就在道场的石板上绽开了。
毫无疑问,我和伙伴们都把掌声送给了大象!就连老陈家道场上溅起的雨花,也仿佛是有意用曼妙的歌喉和婀娜的舞姿为大象助兴呢。
当我重提这段往事,我依然能听见雨点溅落地面的声音,它导引我穿过老陈家二楼的回廊,看到回廊尽头停留的少年。雨还在下着,道场上的石板湿漉漉的,被雨水冲洗过后的石板,简直就像一面镜子,其上投影着人生。
二
石板的主人是陈老大,也就是老陈家当家的。
要说陈老大,在村子里可谓无人不知。且不论他的辈分,单是他那一院瓦房,就足以显示主人的身份了。
我所生活的乡村,过去大多数住宅以石板房为主,黄土围成的墙面抬着木头搭起的屋架,屋面上再盖着一层石板,这就能住人了。土屋大多是单层,大概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吧!再说,那个年代,有一间土屋栖身,不漏雨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了。瓦房是不敢奢想的,村子里只有少数富贵点的人家,才能盖得起瓦房。
陈老大家就坐落在村子的中央,是村子里唯一的双层建制瓦房。房内设有木质回廊,墙也用白灰刷过,窗子嵌在向阳的墙面上,木质格子窗上雕刻的花纹显然是老一辈匠人的手艺。
道场也很别致。别家的都是泥土夯实而成,下雨了很难下脚,唯独陈老大家的道场错落有致地铺着大大小小的青石板,就像现在的地板砖,不仅看着美观别致,而且雨天里不会积水,下脚不沾泥。
我小的时候,经常会不自觉地走进老陈家的道场!也实在是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吧,毕竟,村子里的路在那里是一个十字交汇处。道场的东北角有石凳,我总喜欢坐在上面吃饭;西南角有一口长方形的石头大缸,我渴了会在那里喝水;正南方有二十多级石砌的台阶,往上通往陈老大的正房,我和伙伴们经常会在台阶上滚铁环;正北方有一棵杏树,弓着腰,很容易爬上去的,大抵是被我们这帮野孩子压弯了。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会在道场上打沙包蹦弹球,道场足够宽敞,其上的每一块石板我们都曾跪伏过、用手触摸过,我们熟悉道场的任意角落。
三
听村里人讲,老陈家以前住过红军,柴房的墙面上至今还有当年红军留下的宣传标语。老陈家也住燕子,我小的时候,总是羡慕他家有很多燕窝,恨那燕子也是个势利的鸟,偏不在我家的土房子里筑巢呢!
土地包产到户后,陈老大继续当选为一村之长。记得那时候村里常开会,商量农耕和村子建设事宜,当然也要经常宣传党的政策,通知村里人上缴农业税等,而老陈家的道场就充当了固定的会议场所。经常是星期天的下午,几声锣响,村里人就知道是陈老大通知大家开会了,于是,一批一批的人聚到道场,先来的往屋里钻,接着就是占领道场东北角的石头凳子。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干脆就坐在道场的石板上,石板很干净,坐上去也很凉爽。
小孩子是喜欢大人开会的,因为人多热闹。人多的时候,大人便顾不上小孩子胡作非为了!在会场,男人使劲地抽烟、喝茶,女人们就悄悄地说话,经常会有哪一家的妇女吊着大布袋奶子在人堆里哺乳,这谁也不忌讳。陈老大主持会议,他的声音就像牙膏一样在人缝里挤,我曾经也装模作样地模仿过他说话的腔调。
道场的石板,留下了村里所有人的脚印,也抬过大多数乡亲的屁股,总之,不管是谁来到过,石板都无声地接纳他们。
四
我至今没有打听过老陈家道场上那些石板的来历。在巴山汉水之间,所有的石板都不诉说自己的身世。它们不仅有巴山的筋骨,历经风吹日晒而不断裂;也有汉水一样光亮的肌肤,遭遇千磨万击更显柔情万种。
就像村里的农民。
他们一辈子都滚在巴山汉水之间,勤恳地打理庄稼地,平常地过日子。
依然记得陈老大在瓦房的堂屋打草鞋的情景,那必定是一个雨天。雨点轻快地在道场的石板上舞蹈,陈老大头也不抬,恨不得把所有空闲的时间都织进草鞋里。每年的十月,是上山收割龙须草的最佳日子,陈老大用背篓背回来一捆一捆的龙须草,晾干后存储在柴房里,逢着雨天无活可干,他就开始打草鞋。春耕秋收,没它不行,手上的活儿不能停,脚自然也不能休息。
陈老大家还有一台脱粒机,五月下旬,割完麦子,要赶在雨季到来之前将麦子收进屋里。每逢打麦子的时候,左邻右舍会相互换工,通常是从老陈家开始,一家来一个劳力,自带一把杨叉,打麦就浩浩荡荡地开始了。杨叉将麦草挑起来,下面就是黄澄澄的麦粒了。陈老大家的麦草垛就在道场的东北角,打完麦子,麦草已堆成山高。麦粒在石板上跳跃,麦草就堆在石板上,杨叉会与石板亲昵,汗水也滴在石板上,石板就笑了。
五
老陈家的石板,继续抬着人来往人的脚步。陈老大在石板上来回地走,走着走着,他就60岁了。
在村人眼里,60岁是一个坎儿,陈老大走得很结实,尽管腿脚已经不灵便了,但他没有停下来。
到生日那天,四面八方的人都赶来给陈老大祝寿,鞭炮响不停。火红的炮花纸散落在石板上,道场烟雾弥漫。
也就是在那一年,老村长卸任了。毕竟是年纪大了呀,连道场北旁的杏树都是老气横秋的样子。
陈老大卸任以后,生活的节奏慢了下来。有时候他会在道场晒晒太阳,有时候就和年纪相当的老人聊聊天。他的耳朵越来越不好使了,但胃口还和年轻时一样好,能大块大块地吃肥肉,酒也喝,他好白水煮鸡蛋,一顿还能消化七八个。
但是,他却越来越孤单了。
起先是常和他一起聊天的老人相继离世,让他越来越觉得生之寂寞;后来,干脆村里开会也挪了地方,陈老大的院子一下子落寞了;更要命的是,几乎所有的土屋都被推倒了,越来越多的乡亲住进了平房,再没有人整天无事了就拥在他家道场抽烟喝茶扯闲篇。
老村长的情绪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他经常在房屋里大声说话,发脾气,还没完没了地咳嗽……这些,道场的石板都听在耳里,石板也明显地感觉到,来往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六
当冬天落日的余晖铺满石板,陈老大穿着他的呢子大衣坐在道场的凳子上打盹。如今,他已是耄耋之年。当年站在他家二楼回廊上的三个小孩都已长大成人,大象当了老板,飞子结了婚,唯独我漂泊在别人的城市,总回忆小时候的时光。
村子越来越空。年轻人总在赶火车,地也就荒下了。偶尔还有一些种麦子的,但成不了什么气候,道场也就跟着空了。草鞋是彻底不用了,即便是雨天,也有筒子鞋,更不用担心脚下会带泥,现在的道场都是混凝土铺成的路面,哪里有泥巴粘脚呢?
不必解释,这是村里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物质的丰裕,使旧时的村子穿上了时尚的新装。我无意批判某些乡亲数典忘祖,只是旧物上的时光,在某些场合能够慰藉人心,投影着稍不留意便会失去的文化元素。
我知道,开春以后,陈老大家道场北旁的那棵杏树还会开满杏花,继续招蜂引蝶;我也知道,南飞的燕子还会再回来,只是我已经无法辨识它们还是不是我小时候恨过的雨燕;我害怕有一天陈老大不在了,那么,那些石板又会是怎样的命运呢?
想象着有那么一个雨天:瓦房的屋顶站满瓦松,瓦松上凝结着透明的水珠;雨水顺着瓦檐跌落下来,溅在石板上,所有的水珠就开始舞蹈。一位老人,安静地坐在堂屋的门口,他在听雨……
有位哲人说过:文化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当新的事物代替旧的事物,人们充分享受着变化带来的便利和自由。然而,石板之于村庄,就像一代人的生命年轮,是用时间一圈一圈丰盈起来的。
我不禁要追问:有谁曾从石板上走过?又是谁踩碎了谁的一地心事呢?石板不语,它或是在等待一场霏霏细雨,又或是独自承受了旷世的寂寞。
责任编辑 董晓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