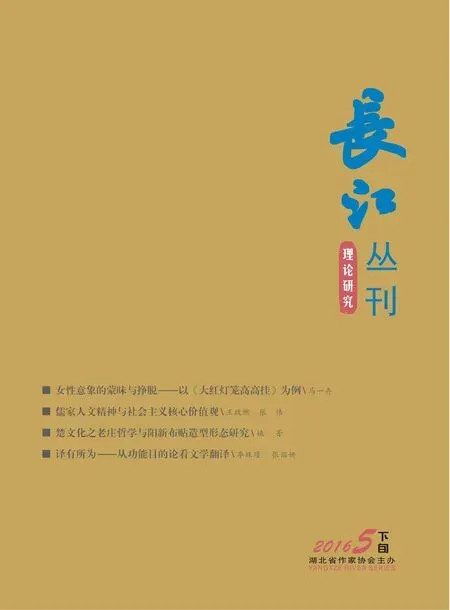震惊报界的“妃子革命”
2016-11-26黄韶海
黄韶海
震惊报界的“妃子革命”
黄韶海
民国时期,在“婚姻自主”的思想潮流下,寓居天津的逊清“淑妃”文绣毅然提出要与“皇帝”溥仪离婚,立时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一事件被当时的京津地区报纸所广泛关注,文绣的这一举动也被《国强报》誉为“妃子革命”。本文试从报界的反应探讨这一事件,并提出笔者个人的一些思考。
妃子革命 报界 文绣 溥仪
在传统婚姻中,女性只不过是男性的依附品,要遵守三从四德,受旧式礼教的约束,地位低下,缺乏自由,几无权利可言。但是辛亥革命后,随着中国传统体制受到激烈震荡,纲常名教走向瓦解,人们的思想逐渐开放,妇女的女权意识也随之萌生并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的社会和思想文化发生了重要变革,妇女解放运动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进。不少有识之士揭露和抨击了旧式婚姻家庭制度对妇女的摧残,提出了“婚姻自主”的口号,这给无数处于婚姻痛苦中的女性指明了方向。因而在此期间,离婚现象频发,尤其是女方提出离婚的案件显著增多,“出走的娜拉”成为当时社会颇引人注目的现象。而在其中,影响最大的事件估计要属逊清朝廷的“淑妃”文绣和“皇帝”溥仪的离婚案。
一、“妃子革命”之始末
1912年,统治中国达268年的清王朝灭亡,历史进入了民国时代。但是,由于清、民两方签订有《清室优待条件》,因而清皇室尊号不变,依然能够在紫禁城里维持一个“小朝廷”的局面。1922年,逊帝溥仪在紫禁城举行大婚,迎娶了自己的“皇后”婉容和“淑妃”文绣。1924年,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决定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废除清皇室尊号并逼令溥仪等出宫。溥仪携其一后一妃辗转来到天津日租界,先住“张园”,后住“静园”。虽然已经没有了皇帝的名号,但溥仪却依旧在遗老遗少的簇拥下心安理得地坐着“皇帝”。
“淑妃”文绣聪慧贤德,但入宫以来,却备受溥仪的冷遇和“皇后”婉容的排挤,由于地位低下、不受重视,甚至经常受到太监的奚落。文绣起初由于受到礼教的束缚,一直默默地忍受着,生不如死。但最后,在其妹文珊、表妹玉芬的鼓励和“妇女解放”新思潮的影响下,文绣终于鼓起勇气,擅自出“宫”,聘请律师,向法院起诉,要求与溥仪离婚。此事一出,舆论哗然,京津地区大小报纸纷纷报道评述,逊清皇室颜面大损。溥仪一开始为了维护自己的皇帝尊严,不同意文绣的要求,但结果却在舆论的压力和自己急于投靠日本去东北“兴复大业”的紧迫形势之下,同意与文绣协议离婚并给予抚养费,条件是文绣不得再嫁。最终,“淑妃”掀起的这场“妃子革命”取得了成功,她也由此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敢于休掉“皇帝”的妃子。[1]
二、舆论报界之反应
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舆论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京津地区的报纸大量报道此事,给溥仪的小朝廷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事态的发展。
首先,部分报纸对于该事件的经过作了极为细致的描述。《兴华》报1931年的第33期,以《溥仪亦有离婚之诉》为题,以“皇妃不堪虐待、律师承办离婚、废皇商议对付、面子丑态百出”为副标题,十分简洁地概括了“帝妃离婚”事件的发展脉络。在正文的报道中,它谈到了一个细节:“今午溥仪之后往访该妃,谓夫君毕竟是个皇上,面子要紧,请回宅,继和好。妃态度仍坚决。”这一情节在一方面说明溥仪和其皇族在该事件中的态度:“皇上”的尊严是凌然不可犯的,“皇家”的面子是万万不可破坏的。这体现了“遗老遗少”们的虚伪,他们从未想到过要为文绣的未来作丝毫的考虑。而另一方面,这一情节又反映了文绣反抗婚姻压迫、追求个人幸福的坚决。毕竟时代变了,民国以来的女性解放思潮深深影响了这位来自深宫的“妃子”。接着,《兴华》报1931年的第34期又以《溥仪之妃声请脱离》为题,以“先偕其妹出门,旋请律师交涉,现仍在磋商中”为副标题,从“淑妃”文绣的角度对该事件进行了一番深入报道。正文首先对于文绣的生平和其与溥仪的婚后生活做了简单的介绍,然后详细讲述了文绣的离婚原因,“妃向人申诉:‘九年来在溥仪家,绝对无行动自由,饱受凌虐。第一,后不许与溥仪接近,已断人生之乐,更无夫妻之情;第二,太监威势逼人,凡事均须仰其鼻息。某太监且谓皇上与汝无恩情,汝惟有速死,皇上命汝死,汝不能不死等。'”由此可见,文绣在宫中受着溥仪、婉容和太监的三重压迫,不受重视,地位低下。报纸通过对文绣这番申诉的报道,意在引起人们对“淑妃”悲惨遭遇的深切同情。[2]
另有一些报纸对于“帝妃离婚”事件作了评论,从这些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舆论界三种观点的激烈角逐。其中一派是站在文绣的一边,为“淑妃”敢于向“皇上”提出离婚而拍手叫好。除了上引报刊外,尚有《国强报》1931年8月26日,发文给予文绣以极高的评价:“淑妃不堪皇帝虐待,太监威逼,自杀未遂,设计逃出,聘请律师离婚,这是数千年来皇帝爷宫中破天荒的一次妃子革命。”这一文字热烈地赞扬了文绣敢于冲破礼教的藩篱,追求个人幸福和婚姻解放的非凡勇气。但是还有一些人站在卫道士的角度,对文绣的这一“大逆不道”的行为进行鞭挞。文绣的族兄文绮就曾给其去信并在报上刊登:“蕙心二妹鉴:顷闻汝将与逊帝请求离异,不胜骇诧。此等事件,岂我守旧人家所可行者?我家受清室厚恩二百余载,我祖我宗四代官至一品。且漫云逊帝对汝并无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亦应耐死忍受,以报清室之恩。今竟出此,吾妹吾妹,汝实糊涂万分,荒谬万分矣!”用传统礼教和君臣观念批评文绣,表达了对其所作所为的不满。除这两种观点之外,还有一种声音,属于中间派。如《白河周刊》1931年的第9期中,有一笔名为“去疾”的记者写了一篇名为《溥仪逃妾事件略评》的文章。文中称:“我们对于这件事情的关系各方的态度,觉得都很同情。溥妾为争自己的自由人格而出逃,乃是现代女子当然的觉悟,不足为罪,溥仪氏为顾全名誉起见,不愿深究,而以和平手段出之,也不失为明白事理之举。……至于溥妾之兄文绮对其妹的劝告,也系旧式道德观念下应有的文章,自有其思想立场,也不必责备,甚至如报载溥妾之出走,乃因不堪溥妻之压迫而然,‘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妒乃人之常情,非妇人之恶德,古人已先说过了,我们对于‘中宫娘娘'的‘一妻专夫主义',也可加以原谅,所以对于此事的各方面的关系者,都颇同情。”这篇评论既没有卫道士的固执,也没有革命者的慷慨激昂,多了几分冷静,认为处于事件漩涡的每一个人的行为都受制于他所处的客观环境和其特有的思维模式,评价较为公允。[3]
三、“帝妃离婚”之再思
叙述完民国沸沸扬扬的文妃离婚案,转入冷静思考,我们该如何来看待“帝妃离婚”、“妃子革命”这一事件呢?笔者以为,可从以下三方面考量:
首先,“妃子革命”事件反映了辛亥革命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女权的伸张和人们婚姻观的改变。20世纪10、20年代的先进知识分子倡导婚姻自由,反对旧式家庭制度,这对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既表现在思想变革方面,也明显体现在社会生活中。文绣的“妃子革命“正是对于传统礼教的一次巨大冲击,也是追求个人自由与妇女解放的一个典型案例,因而为时人所赞赏,人们从中明显感觉到社会的进步。[4]
其次,文绣为个人幸福而坚持斗争的精神值得我们赞叹和敬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有许多卫道士,对于文绣敢于向皇帝提出离婚的做法感到不能容忍。逊清的遗老遗少认为她丢尽了皇家的脸面,她的族兄文绮也还专门发文声讨,觉得她败坏了家族的门风,京津地区的部分报纸也对“淑妃”的“大逆不道”之举进行了口诛笔伐。可以说,支持她这样做的人并不多,她的亲戚中只有其妹文珊和表妹玉芬鼓励她,然后就是部分舆论地支持了。在这种情况下,她能够坚持自己的决定,执着地争取自己法定的权利和自由,最终获得了胜利。这种执着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值得我们佩服。文绣离婚后做过教员,也卖过体力,当过小摊贩,在抗日战争后嫁给了一个国民党军官,1953年在44岁的年华香消玉殒了。虽然说日子过得十分艰苦,但比起跟她一同进宫的“皇后”婉容来说,她可是幸福多了。文绣,正是靠着她自己的抗争与努力,换来了一个属于正常人的平凡生活。
其三,“妃子革命”这一事件中的所有当事者,其实都是中国旧制度的牺牲品。他们的行为受制于自身所处的环境,以致构成了各人不同的命运。“皇帝”溥仪一心要维护自己与“皇室”的所谓“尊严”而完全不顾他人的感受,包括后来他到东北做了汉奸,也是因为他自认为肩负着“兴复大清”的宏图大业。他的一辈子都为“皇帝”的名头所累,最终酿成了自己的悲剧;“皇后”婉容爱慕虚荣,自视甚高,对于名分十分在乎,容不得身边的一个“妃子”作为竞争者。她的这辈子也是为“皇后”这一称号所累,终于在旧制度的压迫下被彻底逼疯了;文绣作为出自皇宫的一个“妃子”,在传统的伦理纲常中地位低下,对于所谓的“皇帝”和“皇后”,她只能服从,只能忍耐,甚至还得忍受太监等下人的奚落。但最后,她抗争了,她坚定地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最终成了自己命运的主宰。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妃子革命”这一事件,虽然对于几个当事人来说,是各有自己的苦衷,但从时代发展的趋势来看,反映了历史的进步,是值得肯定的社会现象。
[1]溥仪妃子离婚[N].《国强报》1931年8月26日/转引自周英才.末代皇妃离婚案[J].贵州文史天地,1998(01).
[2]转引自王庆祥,李玉琴,李淑贤.末代皇后与皇妃[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80.
[3]去疾.溥仪逃妾事件略评[J].《白河周刊》1931,01(09):80.
[4]转引自徐莉.末代皇妃文绣的身世和下落[N].中国档案报,2004-12-24.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