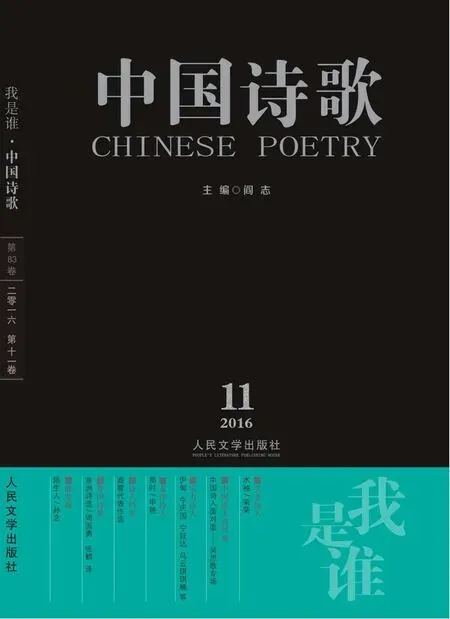水袖(组诗)
2016-11-25□荣荣
□荣 荣
水袖(组诗)
□荣 荣
代拟诗信
阿某:没有你的日子时光常常断流
我一次次起身 看到夜晚这只太老的猫
蹲在浓黑里 我害怕与它对峙
如同你那年的逃离
有些事我不想继续了 它们不再是必须的
比如维持好名声或好身体
它们曾是攀附你的闪电 而爱情雷声在外
比如与你重逢 幕布再次掀开
看芥蒂和伤害的暗器又一次摸向胸口
阿某:其实托人写信是多余的
你疏离已久 地址不详
像好消息走失于人群
我费劲地描画你几近消蚀的脸庞
半夜醒来 疑惑是停不下的钟摆
这世间是否真有过一个你?
但你决绝的话语炸裂每一处静谧
最后那次相见也历历在目
一个章回小说里的情节:
一个不正经的帝王与失宠的侍女
你过大的雄心 我过度的卑微
时间的剑刃带着尖锐的呼啸
阿某:我知道我早被彻底丢弃
我知道我也该丢弃你
所有有关你的回忆全是致幻物
你给过的烂漫和明亮也只是
向命运高利借贷的油彩 由我独自偿还
一块板结的泥土起身行走
是为了赶一场透雨
而我仍停留在你预设的路线上
眼下的你 多么适合抱怨
但你生来并非为我
你深入我的身体里 也只是一把意外的刀子
现在 我疯狂地安静着 仿佛垂死之物
仿佛命运眼皮底下 一件被退回的廉价赠品
站在一片沃土上想起的几组词
丰美和柔软是一组词
这是它惬意生活的感性部分
宽阔和强大是一组词
这是它内在的意志被隆重说出
科技与艺术是一组词
这是阳光和雨露 它的名词和动词
雄心勃勃 血气方刚也是一组词
直接接驳风生水起 日新月异这一组
还有潮流与激情 智慧和创新
它们都带着鲜活的让这片沃土沸腾的巨能
而心灵与家园是一组更深邃的词
它们是这片沃土的底蕴 温暖和芬芳
是这片沃土最寻常的爱的表情
幸运
闲下来突然惦记你。
真是幸运啊,你说你活着。
这是你惯常的语气:
“真是幸运啊!
名利是夜街上追逐的猫狗。
我有真正的健康,童心和安宁。”
我想象你穿着阔大的衣服,
在菜场里恣意晃荡,也学你造句:
真是幸运啊,生活可以如此宽松。
比起更艰难的旅人,我可以停顿。
比起更黑暗的行走,我可以等候。
真是幸运啊,这些年锁孔没有锈蚀,
门前地毡下总能摸到家的钥匙。
真是幸运啊,我还能去看你。
听细小的火花在我俩掌间毕毕剥剥跳动。
陈腐的爱情故事
他们只是牵挂着 越说越近
某一天才发觉已难分彼此
像两只小心接近水源的羚羊
猜度和想象几次将饥渴之心逼到绝境
也只相信眼泪渲染的爱情
众里寻她千百度 她的悲伤闪闪发亮
也只是天各一方的辗转反侧
他短缺的梦里 尽显她的星月乱象
时光窝在眉眼里
近些再挨近些 留一张剪不开的合影
相见已恨须发白
他眼观镰刀铁锤 她身怀六甲刀剑
但一次次分手 她十步一回头
他在那里 仍在那里 还在那里
和一个懒人隔空对火
仅仅出于想象 相隔一千公里
他摸出烟 她举起火机
夜晚同样空旷 她这边海风正疾
像是没能憋住 一朵火蹿出来
一朵一心想要献身的火
那支烟要内敛些
并不急于将烟雾与灰烬分开
那支烟耐心地与懒人同持一个仰姿
看上去是一朵火在找一缕烟
看上去是一朵火在冒险夜奔
它就要挣脱一双手的遮挡
海风正疾 一朵孤单的火危在旦夕
小心!她赶紧敛神屏息
一朵火重回火机 他也消遁无形
我喜欢看你入睡
我喜欢看你入睡 看你一点一点远离
你的柔情在嗓子里卡着蜜意又有什么关系
你进入的时空不再有我又有什么关系
像一艘船浅浅地靠往亲爱的水边
我是沉浸的月色 我是凌晨一点
我就在你身边 这真的很美
你不再关心我的存在又有什么关系
那一会儿 你需要入睡你不需要我
又有什么关系
缺少睡眠的孩子 找到久违的家
我愿意看着你 躲开忽远忽近的嘈杂
穿过睡眠的门廊 客厅 进入卧房
我愿意你安静下来
那一会儿我是多余的又有什么关系
又有什么关系 等你醒来
等你一点一点回转 我们又重逢了
瞧 良辰与美景就在一步开外
走心走肺的情意会多么坦荡
醉的时候他们才是相爱的
醉的时候他们才是相爱的
酒到七分 他牵着她手当众盟誓
酒到八分 他跳上台为她且歌且舞
“酒真是好东西。”朋友们起哄:
“亲一个。亲一个。”
第二天他不再记得 也没人提起
也只有在酒醉时 他心里的老虎才放归山林
单独遇见 他却总是垂头擦汗眼睛转向别处
他几次提起初见场景 她不记得
却不忘第一次同醉 那时她正遭逢击打
心有万古愁 求一时忘却
服务生一次次送酒送到手软
红的白的啤的堆高暧昧的酒沫
一帮人疯闹到非男非女屋顶微掀天色渐明
这个不自信的女子真的感动
她说 酒醉时分与她夫妻相称的男子
相见时总给她一份敬重
送行时又抢先提上她的行李走在众人前头
他自然流露的好 那么天经地义
拥别时 她的身子想柔软些却总显僵硬
她说 那时候她只想流泪:
“真好啊。想起他我就是快乐的。”
他的情谊是她罕有的珍宝
这不是爱 但比爱或被爱更好
水袖
那年小红越过矮墙
她的水袖挂破在刺槐树下
那年梅娘嚼着槟榔 她的水袖
被扯得山高水长 然后断了
现在是她们 集体亮出的水袖
仿佛要先她们一步找到极乐之地
我如此清白又坎坷的情路啊
至今我的水袖仍深藏在肌肤里
仍没撞到那一片
容我试探深浅的月光
背离
1
她的锁心里没有真爱的牙齿
但她仍是美妙的
他说:我只想做点我喜欢的
比如老年的迷醉和沉沦
春天继续丰饶 怀想之痛也在
他的一意孤行 磨损多少耐心
“你开心就好!”空城里危机四伏
你反复出走 他永不归来
2
还是说背离 作为情感的判断词
似乎它才是可信任的
就像真实的苦难让幸福虚弱
就像相爱一再流于形式
当众多的美只是附庸了春天
繁花落尽露出背离的骨头
当肉体的亲近也变得盲目
“也许。一切很快。”她说:
“我不阻止旁人,但可以叫停自己。”
突然被一句诗噎着了
那个年轻人将一句话藏在一首诗里
为了不被识破 他开始东拐西绕
东风破了西风续上
长城一角挂着晓风残月
来些物理结构化学组合
再加一两个虚拟的天体
一首多少有些被轻视的诗
眼下 谁相信还有不朽的篇章?
像习惯于门前小径的漫步
你仍在阅读 却内心无聊眼神散乱
零星的花朵 略过不提
如同许多人 你早已丢下揪心的事物
也失落了较真的耐心
纵使满腹锦绣终究归于草莽
但那句话就藏在一首诗里
你突然被它噎着了
风里一缕细致的花香
又惊跳起来 像躲避踩着一朵鲜花
并且听到细碎的骨骼碎裂声
你停下来 茫然四顾
晚凉的风在草丛中的形状
莫名
原谅我的迟钝吧 我要慢慢确定一个事实
我肯定看到了一把刀 或者是剑
还有寒光 像晨曦划开梦的口子
然后是血 但疼在哪里
原谅我的迟钝吧 待我慢慢寻找疼的位置
它在心的正中 偏左或偏右
抑或在稍远的地方
抑或只是新鲜的血在疼
我退在角落里 从头搜寻这个事端
原谅我的迟钝吧 没有制造事端的人
没有刀剑 也没有真实的伤口
我的体内却站着一个满脸委屈的人
他的竭力否认 是否也是一种澄清
杜丽娘
她退回到那个梦里 抱住一对翅膀里的两份轻盈
她退回到死亡里 等待一个人
在镜月里捧起碎了一地的影子
仅仅相隔了四百年 前朝的生死已难以辨认
只有她 仍被分散在一出出戏里
昆腔绵柔而真爱铿锵
她婉转的袍袖里空余多少顾盼
“不到园里,怎知春色如许。”
这个善情者 一味恣意着
人生很长 她只要一个春梦
死又何惧 她还能为一个人复生
当更多的后来者止于回避 不信任甚至厌倦
这个善情者 仍一次次出场并再三告白
她并非死于情灭 只是死于渴望
灵魂之爱永生于等待之中
文字的杯盘狼藉
她暮年的文字里有妒妇 怨女及抗暴者
也有复仇狂 焦躁病人和通灵者
这些寄生体
它们的活力来源于她内心的
累赘 毒瘤 浓烈的阴影
为什么不再有早先的洁净和小腰
为什么不是和风细雨
掌灯夜读 向旧事物里寻宽宥之心
为什么慢慢地跑偏了
慢慢地跟着她的人生走上歧路
眼下 她呜咽的文字满目苍凉
双刃
促膝不谈心 只谈眼前的风景
风景是新的 他的眼神也新
新单词的新 新事物的新
只是他一起身
身边的风景也旧下来了
是寒意丛生的旧 是薄薄的刀片
插入半明半昧寒意里的旧
而他近处的坦荡和朝气
与她远离他的落寞
是它的双刃
九回肠
这是否是不被原谅的?
当他用手揽住她 她更往他的身上靠了靠
是否同样不被原谅:她竟喜欢他微微的碰触
有一会儿 还以为她暗自发热的左腿
能与他瘦长的右腿有一段亲爱之旅
车窗外 山楂树果仍是青的
满山的绿藏起了满坡的石头
被一杯酒打开的身体
被一杯酒打开的身体
里面有一只空置的酒杯
你看见的是一个新鲜撕裂的伤口
你看见的是一只蜷缩之鸟的战栗
被一杯酒打开的身体
也许会毁于再一次的打开
现在 她露出空置的酒杯
里面有她自酿的酒水残留
像被狂风猛然撬开的窗户
太长的时间里她有太多必须消化的风雨
四眼井
四十岁前纯洁身体 五十岁后纯洁灵魂
但随意的清洗仍是冒险的
清澈甘美的泉水更适合忏悔
瞧 这个负罪之人在自怨自艾
她在四眼井里看到四种过错四样轻蔑
还有四个反纯洁之词
她也无法从怀里掏出月亮星星
车船兼程 什么时候它们不再如影随形?
她只是路过 又一次路过
此刻 她的愧疚之影不被宽恕
未清除的戾气 激怒了水中雄狮
此刻 她像一杯薄情之酒停于宽阔之源
找不到一种可以倾倒的理由
抱怨之诗
一个女人毫无预兆的愤怒嘴脸
转向你 她言语里的电闪雷鸣夹杂着
风雨的腿脚 那个男人也是
很快 他们结成一个阵营
很快 身体里的一队人马也呼啸而去
那张脸一改往日的柔情蜜意
多少年了 你总是侧身行走
绕过是非小径 仇恨大道
良善之人 还是步入了严酷时辰
像是酿坏的又一坛米酒
像安静的伤口剥落了膏药
像尘土四起 狼烟滚滚
你无法抹平内心的皱褶
纵千般委屈能与万人说也一说就错
只写下几句抱怨之诗看着天黑
昨夜突然失火的教堂
一座教堂的失火是上帝允诺的
或许是它尖顶的指向需要重新调校
这座失火的教堂他俩曾一同眺望
它一直突悬在一个街区的灰暗之上
景观灯下教堂之美和尖顶之上的那片虚空
恍如天外之物 恍如不被信任的明天
他指尖的火焰来自他们失火的灵魂
他的指点里有一弯虚幻的月亮
而这之前她与他共有一个心脏
总以为一分开谁就会死
那天是哪天?现在是这场火与那场火
燃烧之物 都那么壮怀激烈
至今他俩仍失陷于空茫之境
内心的荒草掩埋了早年并不真切的脸
我是谁
我赞美过你的羽毛 服饰 声音
有时候我忽视你过于浑圆或瘦削的身子
只赞美你笨拙的手指
它在指点:“茫然是一种更终极的前程。”
我也曾匍匐于地 为了不安的现实里
让你多一块立命之所
但我始终知道你是什么——
多么令人恐慌
当我走近 我以为你会认出我
像你的小短腿认出我的步子
你的小颜面认出我的泪水
好大风
好大风 它咆哮着
发动起亿万匹马力的推土机
大地似乎也在为它挪移
好大风 它揭起了那么多疮疤
让黏在地面的厌弃物
有了逃跑的腿脚
好大风 它挨个儿敲打着窗户
它要去熄灭
躲闪的眼睛里那些黯淡的火
甚至敲落了那颗来不及藏匿的星星
将许多落单的人
吹成愤世嫉俗者
但不用慌乱 正是大风时节
灯影乱舞 我一个人的想
像一张薄纸挣扎在半空
朵上茶吧
一提年代久远 她就暗自摸一摸身体里
藏掖已久的这个词
一提年代久远 枫杨树悬铃木不动声色
巷子的浓荫却晃了一晃
跟着晃荡的还有朵上茶吧里暗藏的
一些身影 那么的仿佛曾经依稀
那么的惺惺相惜 情愫低回
亲爱的地方亲爱的幽暗气息
亲爱的年代久远的记忆
但为何她还在怅然四顾
还假装成千疮百孔的失怙之人
外露的忧伤涂一层合法的迷彩
像是
像是有个男人正在来路上
她的轻举妄动需一捺再捺
他只想与她谈谈禁忌
或单纯日常里的种种调剂?
还是为了这场擦肩戏里的
两颗真实之泪?
从大老远跑来 他就要到了
像是邻桌上那道跑味的荤菜
北方白桦林上的苍茫
北方平原上大片的白桦林
在道路的两边尽情铺排开去
遮天蔽日的苍茫
也从这些阔大的林中升起
我喜欢这样的苍茫
它们一定安抚了我的内心悲怆
我也喜欢看那些长尾鹊
在这样的苍茫里悠然地来回
将窝筑在或高或低的枝杈上
仿佛白桦林给了它们更开阔的选择
它们可以是苍茫的主人
也可以是苍茫的仲裁者或代言人
在沂蒙 一位水瓶座的女子只有泪水
一位水瓶座的女子动辄流泪
欢喜流泪 落寞流泪
她多么任性 远山远水想个人
见或不见 直泪一道横泪一道
半夜梦回泪两行
高兴一行 失意一行
在沂蒙 这位水瓶座女子也只有泪水
是感动之泪 感激之泪
多畅快的热泪啊 只是她不再掩饰
只想让泪水奔腾着 跟着英雄的热血
在这片土地上恣意地流淌一遍
在沂蒙 这位水瓶座女子
头一回觉得自己的泪水是真实的
与这里的山川河流同质
头一回觉得泪水可以那么滚烫
那是贴着英雄的热血而流
在沂蒙 她流着泪走过一个个山头
忍不住将亲爱的祖国又狠狠地爱了一层楼
忍不住将眼下的日子又狠狠地爱了一层楼
忍不住将深爱的人儿又狠狠地爱了一层楼
沂蒙红嫂
如果可以 我也要进入这个群体
用初识的自由 民主 富饶这几个字眼
憧憬共和国的蓝天
我也会像她们一样 春种秋收 纺纱织布
最后一口粮食 留给战士
最后一丝布 纳成军鞋
最后一个孩子 送上战场
最后一滴乳汁 喂养革命
我也要成为这方土地洒不尽热血的一个源头
朴素的情感 从心底里搬出来
便是人性浩大的盛宴
虚化
那么多人!每一个都闪着
自以为耀眼的光芒
每一个都有许多方向
每一个身后都跟着许多条大道
还有更多的争吵和结论
声音像是潭底一次次搅起的泥沙
他们更诧异于我这卑微之人的孑然独行
带着如此微弱的声音和光亮
诧异于泪水铺就的小路
竟是我从心所欲的那一条
潘天寿
我的叙述 始于名叫冠庄的村庄
它有质朴的心 淳厚的肺 坚硬的骨骼
它有绕树三匝的刚山柔水
一个慷慨的长者 从它的肺腑里掏出全部颜色
铺就他血液和肌肉里原始的底色
我的叙述 始于那座雷婆头峰
始于它的突兀嶙峋 聪颖灵秀
始于它的疏枝密影 碧波千仞
在那里 他第一次望见了未来之路
从此高山流水 家乡千里
我的叙述 始于一个渐行渐远的身影
这个终生的跋涉者
背囊里装着山水绝句 性情文章
一双脚用来丈量群峰
走得如此之快
像要赶着节气开满树的花结满树的果
将俗世远远甩在后面
走着走着路就深了天就宽了
走着走着他就走到了云端
尘埃向下落定 众人仰头看他
看他张扬狂放中的清丽 率真
看得十分骨气十分才学
看一幅天地立轴 鬼斧神工
然后 我要提到那些石头
看得见的坚硬 看不见的陡峭
一块 又一块
他几乎掏出了伟岸肉身里的全部钙质
霜花一两朵 寒鸟三四只
瘦诗七八行 说着深浅
说着天地间的孤悬或隐喻
这些石头横空出世 让酣畅之美无处逃逸
这些石头搁在心里 他便有了扛鼎之力
便一味霸悍 勇于不敢之敢
这是艺术的骨头 美的脊梁
他喜欢与石头说话 这一说就是一生
他说了很多 有些我们听懂了
那些方的更方的 锐利的更锐利的
一个惜言如金的人 在石头上露出他的阳刚
他喜欢与石头说话 这一说就说出了不朽
他说了很多 有些我们一时听不懂
听不懂还是想听 趴在石头上听
隆隆声由远及近 天上人间听得分外肃穆
然后 我要说到一只灵鹫
雄踞于方岩之上
或踱步 左一爪孤傲右一爪孤傲
天空藏不住无边的蔚蓝和辽阔
一飞冲天的翅膀藏不住渴望
一只灵鹫 就要抓起一块生根的磐石
直上云霄 眼下它仍在等待
仍在蓄积更大的力量
那一刻 群山寂默
他让一只巨鸟的筋骨在渴望中疼痛
这只灵鹫 同样也说出了他内心的敬畏
内敛的豪情和凌云壮志
也许 我还要从一朵花说到另一朵花
从山花烂漫 清荷新放 菊气熏风
说到一枝寂寞的劲梅 独傲霜雪
这些高洁的花朵说出他的高洁
这些干净的花朵 疏影浮动
将污泥和浊水逼开三丈
一只鸟在盘旋雀跃 许多只鸟在盘旋雀跃
溅起惊讶的春光 一片两片
这也是他的心花 他捧出来
细致地移栽在纸墨上
为我们说出隔世的孤独和芬芳
现在 我要说到他的手指了
不指点江山 江山千里万里的锦绣
他用指力搬来一角
只一角 就气象万千
都说他的手指比别人灵巧
这说法总显轻浅 抹煞了多少
长夜苦熬 百锤千炼
都说指墨画大师 缘于他小时候
被收缴了画笔 美景空对
画事总被误为“君子不齿之事”
他满腹荆棘 但不辩白
深入骨髓的 是热爱至死的疾病
我更愿相信 他以指代笔
只因笔之柔软无法绷直他的灵魂
磨秃了千支万支
最终 他拿自己的骨头作笔
现在 我的叙述里还要提到一场战争
一面破碎的镜子 照着走散的笑脸
同胞在水深火热 艺术在流离失所
多少新愁与旧伤 握不住一支离乱之笔
没有所谓的后方
他如何扶正歪斜的画案
如何画出愿望里的晴空和蓝天
整整八年 悲愤是一块卡住喉咙的坚冰
迁徙途中 学生在课堂上围着要他画山水
他举起笔 叹口气又放下了
“半壁江山都沦陷了,等抗战胜利了再画吧。”
一滴滚烫的泪来自心底的乌云
一滴泪的热度来自于信念
——腥风血雨总会过去
祖国一定会重开艺术的笑靥
现在 我的叙述里还要提到他命里的三个女人
自由地爱 自由地结合和分离
是长在他生命之树上的三颗果子
是他一生的甜 一生的不安和愧疚
三条河流 流出他生命里的华章
三场戏 多少悲情多少精彩
他用一生的真诚出场
她们用全部的生命演绎
一个在家乡望断秋水
一个为爱终身凄苦
一个是几十年同甘共苦的患难妻子
时间翻过去流水的册页
翻过他的青葱 他的老年
翻过高大的身躯为柔弱的肩膀挡风遮雨的他
翻过他一世的坚守 暗中的无奈和唏嘘
就像他较真了一辈子的国画艺术
他天分独厚 英年得志
“行不由径!” 多少类似的诘问
不改他执着于艺术之真 执着于永恒之道
——“天惊地怪见落笔”
他大笔淋漓 别开生面
“画当出己意” 他谨记着
又不断地为自己设置雷霆
一个自我博弈之人 在渴求完胜
画不惊人死不休 每一张都必须是精品
便画了撕撕了画
有时撕得多了撕得重了
落在纸上的花鸟虫草
隐隐传出肝脏和骨架细细的碎裂声
心血红黄黑白地洇湿了指尖
他每天都要画完一刀纸
这些纸 只用来承载和渲染他的不羁
——“师其意不师其迹”
传统和外来文化
像两只慧眼左右盯视他
他独立其中 为自己辟开一条大师之路
多少声誉 也视作身前身后土
多少年的践行践言
他著书立说 桃李天下
却始终放低自己 只愿是一个平凡的画者
——“做人要如履薄冰。”
一个敦厚的师长
一个朴实讷言的人
众人眼里一座巍峨的高峰
却常三思己过 心怀愧意:
“对国家、父母、兄弟是嫌不够所想,
于心殊感不安。”
他甚至认为自己:
“因为欢喜弄弄国画,
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表不知其里。”
木秀于林 风必摧之
不愿变通的铁 宁折不弯的钢
如何能躲在画里 撑住清白的颜色
人情世故的薄冰 他可以从容勘破
颠倒的天地 莫须有的罪名
却让坦荡之心找不到躲藏的缝隙
“莫嫌笼絷浅,心如天地宽。
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
雷婆头峰从不弯腰
倔强的石头不说软话
我依稀看到 故乡的清晨里
一个羸弱的老人跪在风雪之中
天空低垂 仿佛在安抚一对折伤的翅膀
我依稀看到 斯文扫地的日子
他用倔强 和被摧残的身心
画着世间最寒冷的一幅图画
那些日子没有太阳
他就是太阳 被无知和野蛮之箭射落
那个夜晚没有月亮
他就是月亮 他落形的身体
再也扛不住内心的光辉 他在陨落
巨大的陨落声 很少有人听见
一个世界在装聋作哑
一块大色掉了 天光陡暗
苦难在辗转反侧 伤痛在辗转反侧
他只想静下来
静 或者长久地睡去
他抱怨一时还静不下来的身体
他的双脚不停地抽搐着
它们走得够远的了
它们是否还想走得更远
它们已不听使唤了
这心外之体啊——
“我想叫它不要动,不成功……”
“我想叫它不要抖,不成功……”
没有医生的看护 或许他真的不需要了
没有更多的人来送别
只有亲人 放不开他的手
这与一个世界的寒冷相连的手啊
只有拳拳老友毫无顾忌的悲伤
一双颤抖的手摸遍他的全身
一双颤抖的手摸着他一生的痛
想摸平它们 好让他不再痛
病房里真安静 像自制砚台里
他亲手研磨的新墨 倾入时间之水
漾开去 漾开去 漾开去
直到今天 我似乎还能听到
刺穿心肺的钢针的落地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