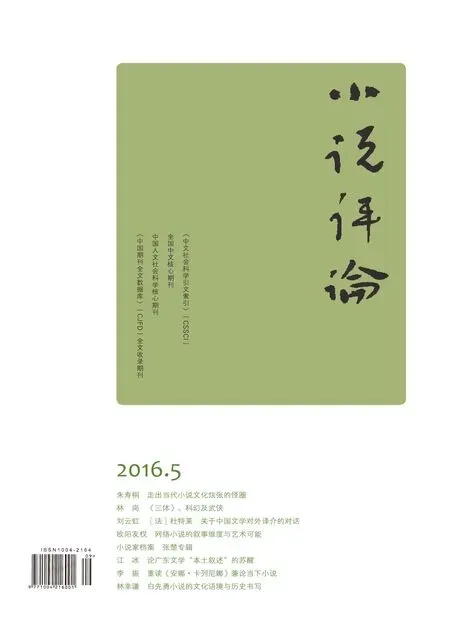张楚小说论
2016-11-25李建周
李建周
张楚小说论
李建周
张楚的小说,给人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修辞可信感。这种修辞可信感并非来自故事的传奇性和事件的轰动性,而是来自作家对民众熟知生活的戏剧性处理,来自隐藏与作家内心深处的空洞感,以及这种空洞感带来的残酷的诗意。日常生活的戏剧化处理使得张楚的小说带有某种程度的先锋性。这也是很多人在私下里讨论张楚小说时经常谈到的。但是细究起来,在先锋写作已经成为文学史常识的今天,仅凭这个概念标签无法确切表述作家的真正创作内涵。那么,张楚的小说到底“先锋”在什么地方呢?在笔者看来,这个秘密隐藏在文本的结构张力和作家的情感张力之中。
一、作为“认识装置”的望远镜
初次在张楚的小说中读到望远镜,是在《七根孔雀羽毛》的开头。当“我”在阳台上向对面楼房窥探时,蓦然发现对面那个经常开着浴霸洗澡的女人,正在“裸着乳房驾着一台望远镜四处鸟瞰”。这个“胖得像头刮了毛的荷兰猪”的窥视者,恰恰出现在“我”兴致勃勃的窥视中。如此精妙的一个看与被看的场景,自然让人联想到视觉文化中的权力关系。有经验的读者会不由自主猜想,这个场景很可能是作家在为之后不同寻常的情节做铺垫,可是张楚的兴奋点却很快发生了转移,这一看似别有用心的场景倏忽一闪而过,除了使“我”远离阳台之外,并没有暗藏更为隐秘的叙述动机。其实这种不经意间“浪费”的细节,在张楚的小说中还有很多,一方面可以看出作家在叙事策略上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作家捕捉日常生活细节的功力。
曲别针、长发、蜂房、孔雀羽毛、野薄荷等等,这些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平常物象,经过作家的精心打磨,在文本中获得了自足的生命和自由的生长空间。那些经过了作家类似现象学还原式处理的“事物”,成为文本的重要支撑点,与人物的命运发生隐秘的内在关联,同时负载了作家对自我意识的探究。进而,这些有着很真确的具体性的小道具有可能成为张楚小说的重要装置,起到关联文本结构层级的作用。在我看来,《夏朗的望远镜》中的“望远镜”,就具有这种结构性意义。对我而言,“望远镜”是进入张楚小说世界的一个重要通道。
小说很容易让人想到清代李渔的《夏宜楼》。我无法断定张楚是否读过《夏宜楼》,但可以肯定的是,望远镜在两部小说中同样具有支撑性作用。李渔把故事放在元朝末年,仅为极少数人所知的望远镜,在小说中成为超于世间的“神物”,在结构上成为故事发展的重要推手。偶得望远镜的书生瞿佶,跑到高山寺租下一间僧房,终日以读书登眺为名窥视大家院户,搜寻意中佳人。如果说李渔把望远镜的实用功能发挥到极致的话,那么张楚则把望远镜的非实用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在西方各国用望远镜四处开拓殖民地的时候,书生瞿佶对它的中国式使用,读来不免让人唏嘘。在《夏朗的望远镜》中,那架更为高级的天文望远镜的意义,恰恰在于它的实用功能在夏朗现实生活中的“无用性”。这个关于日常生活微观政治的故事,并无大喜大悲的离奇情节,却让人看到隐藏在日常生活表象下的令人震惊的精神处境。夏朗与方雯是同一单位的公务员,一个老实厚道,一个通情达理。双方父母同样为子女辛勤操劳,算得上和谐;两家也都是县城里的“中产阶级”,算得上门当户对;两人恋爱既偶然有平常,算得上美满。但就是这样看似和谐幸福的家庭,却在上演着惊心动魄的日常生活微观权力的斗争。因方雯的父母买下婚房,所以与小两口婚后同处一室。慢慢地,姑爷在方雯父母眼里由心头肉变成了眼中钉,于是他们对夏朗由嘘寒问暖变成处处刁难,由近乎谄媚的讨好变成满脸威严的训斥。一心想摆脱被方家控制的夏朗,想自己买房,结果还是不得不和岳父家买了对门。同时由于孩子的出生,夏朗也一直在方家“优雅的蔑视”中和岳父母居住在一起,由座上宾变成了一个真正的陌生人。“望远镜”这个在夏朗庸常生命中至关重要的精神性存在,在岳父方有礼眼里只不过是个让人“玩物丧志”的破玩具。它的“无用性”隐喻夏朗的精神追求在现实世界的无用性。这种精神生活的“无用性”,正如艺术在现代社会实用意义上的“无用性”一样,成为反思现代性危机的重要切入点。
作为“窗口”的望远镜,让夏朗发现了生活的另一面。换句话说,望远镜在小说中是夏朗的“认识装置”,通过它,一个高于刻板的现实生活的另一个生存空间的大幕徐徐拉开。在这个意义上,看似无用的望远镜和《夏宜楼》中的望远镜,甚至和艾特玛托夫《白轮船》、王小波《寻找无双》中的望远镜,就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这里的望远镜不单单是小说的道具,而且是启开文本深层结构的一个开关。通过这样一个“认识装置”,呈现一个如梦境般虚假和飘忽的世界,从而为千疮百孔的日常生活找到一个对称域,在既承受又抗辩的结构中呈现了欣悦与酸楚的内心张力。
如果说《夏朗的望远镜》中的“望远镜”具有结构意义的话,那么在其他多数作品中存在同样的结构。在隐喻的意义上,张楚小说中呈现的日常生活,正像是“望远镜”中变形的“风景”。作家借助自己的“认识装置”提炼“风景”时,将日常生活进行了变焦。这样,在叙述日常生活故事时,扩展了文本的审美空间,呈现一种更为审慎的结构和情感的张力关系。
二、结构张力:“细菌”与“羽毛”
作家将目光聚焦日常生活的具体性,曾经是80年代后期的一种小说写作策略。这一文学策略集中体现在新写实小说家身上。从文化政治的角度来看,有对抗意识形态的操控和升华的隐秘动机。问题是这一叙述指向在新写实作家那里并不是自明的。当他们将自己的笔触转向具体生活时,和内心的理想主义气质形成一种尖锐的冲突,所以流水账式的生活背后流露的是作家对自己所写生活的抵制和抗拒。在之后大量的仿写者那里,这种具体性的叙述策略滑向了简单的经验主义,甚至连基本的个人审美乌托邦都被扫除一空。在当下,面对爆炸式网络信息的现场感和时效性,日常经验书写的有效性显得十分可疑。在此背景下,张楚的探索显现出了不寻常的意义。
张楚小说呈现的日常具体性严谨精准,掺杂着细微的社会观察,以及阶层的分化而滋生的复杂心态。作家并没有仅仅满足于对日常生活细节的还原,而是对这种具体性有着某种程度的反拨与抗衡,形成一种隐秘的内在张力。小说试图呈现一种基质性的情境,将琐屑、矫饰与残酷、忧郁的东西放在一起,使得日常琐事与内心的绝望相结合,通过并置构成小说的戏剧性。借助此,张楚一方面在经验描述上精准地放大细部,显示出日常生活令人惊心动魄的一面;另一方面在不同的结构层面努力发掘探究精神救赎的可能。
张楚小说到处有令人震惊的“细部”,这些地方真实可感、精确鲜明,让人念念不忘。《七根孔雀羽毛》中李浩宇对宗建明讲的“玩具上的细菌”非常典型:
“有谁会跟玩具过不去呢?我们这些人,不过是依附在玩具上的细菌。或者说连细菌都不如,只是一个个原子那么大的物质。外星人肯定也不是以我们通常认为的方式存在,他们可能是气体,也可能是液体,更有可能是透明的非物质。他们干嘛非得以人类肉体的方式存在呢?”
这个被宗建明认为是基督徒或者疯子的李浩宇,本来有着显赫的家庭背景,父亲是远近闻名的大款丁胜,自己在县城当公务员,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社会地位都有明显的优越性,但是富二代的身份并没有给他带来内心的幸福安乐。相反,精神上不断积累的伤痕使他极力渴望摆脱污浊的现实,而宁愿把心灵寄托在遥远的外太空。“宇宙恐惧症”表明其内心深深渴望心灵的依靠。他的“细菌理论”不仅是对自己生活基本状况的描述,更是对当下现实生活真相的洞察,甚至是中国走向现代过程中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自我纠缠的显影化和具相化。
如同李浩宇的“细菌”一样,宗建明对羽毛的珍爱同样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宗建明十分小心地把那七根孔雀羽毛放在已经破了口子的,上大学时买的棕色皮箱内。与之相伴的是开胶的乒乓球球拍,散发着霉味的奖状,干掉的野花。这些物象构成一种挽歌式的回忆:“我已经忘记了这是我多少次打开它,在冬日昏暗的光线里欣赏这些羽毛了。屋子里没有开灯。羽毛色泽黯淡,密集的绒毛上长着一只沉郁的蓝眼睛。”这种个人回忆与80年代的理性主义氛围是相互交融的。张楚的作品中时不时出现对80年代的眷恋与怅惘,但是历史已经将两个时代拦腰斩断。在伯林看来,“对过去岁月的浪漫渴望,实质上是一种取消事件‘无情的’逻辑性的欲望。”①现实的逻辑是无情的,如同被人抛弃的理想主义一样,这些宗建明个人记忆中神圣之物,在他的同居情人李红看来不过是毫无用处的“破羽毛”。也只有在丁丁这样不懂事的小孩子眼里,羽毛才莫名其妙具有了非要得到的重要意义。而那些“懂事”的大人,已经无法看到羽毛的诗意光泽。小说中七根孔雀羽毛“无意义”的意义,一如艺术作品之于物质现实。
“细菌”同“羽毛”在小说结构上是对称的,就像李浩宇和宗建明是对称的一样。宗建明的坚守和李浩宇的彷徨形成一种对应,共同拓展了文本的精神空间。或者说,这两个人和周围的人形成一种对峙与张力,提示着小说中另一审美空间的存在。从这两个人来看,他们有着不同的生活经验,在叙述进程中又各自走向自己的反面,在文本结构上形成一种反向呼应。这种呼应的背后体现的是作家的一种询唤,对日常生活逻辑“另一面”的询唤。它不是意识形态抗辩似的“旷野呼告”,却是一种更为内在的忍耐与坚守,虽然这种坚守在遭遇冰冷的现实时往往是失败的,但是小说人物的失败恰恰促成了艺术上的成功,一种在高速飞驰的时代列车上产生的眩晕感和揪心感油然而生。
现实的残酷与内心的诗意如果纠结于一个人身上,会让人骨子里感到黑暗的虚无,这样的时代紧张感简直是难以承受的。《曲别针》中的李志国,一个现实生活逻辑中司空见惯的成功者。他适应现代生活,不择手段赚钱,因欲望膨胀与妻子感情淡漠,和妓女纠缠不清。不过这个兼具商人、嫖客和杀人犯多重身份的人,却曾经是个爱写诗的文艺青年。虽然诗意的梦想逐渐被现实生活碾碎,但是李志国并没有完全被强大的现实逻辑所淹没。为了缓解内心的紧张和焦虑,他迷上了路易斯裘德的曲别针艺术。由于和妓女的纠缠,他没能接到病中的女儿打来的电话。当妓女想抢走女儿送给他的水晶手链作为报酬时,对妓女的愤怒和对女儿的愧歉终于在一瞬间爆发了。掐死人后的李志国,接到女儿再次打来的电话后却一句话没说,内心的紧张和纠葛也达到了可以忍受的边界。曲别针这一封闭的回环式几何图形,与李志国内心的纠缠互为印证。生存困境、心灵扭曲、道德危机、良心发现等等多重时代意涵共存于一身。沉浸于欲望洪流中的李志国,在心灵不堪重负的折磨下付出了死亡的代价。尽管小说的结局略显简单,但人物的内心紧张感却清晰可见。
如果没有李志国的悲剧,这个厂长嫖娼的故事很可能成为一种生活轻喜剧,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张楚极力渲染李志国嚼曲别针自杀的悲剧场景,试图寻找一种隐在的救赎的可能性。在社会矛盾激化、生存环境恶化、人欲肆虐的当下,这种审美乌托邦显示出自身可贵的一面。作家对人物命运的悲剧性处理,背后隐含的是当下人和自己的物质世界之间的矛盾。个人审美乌托邦不是以构想美好的社会理想为特征,而是从个人理想出发,试图维护人的自然属性和拯救人性。它可以冷静测量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也可以自由拉近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距离。虽然张楚并没有刻意强调个人审美乌托邦,但文本结构上有意进行了探索,试图在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之间建构某种张力的平衡。在乌托邦审美救赎被无限推延的时代,这一做法显得尤为可贵。
文学解决现实的能力是有限的,让文学回到文学,这其实也是当代作家的一个隐秘的叙事传统。对于小说艺术来说,试图以喧闹吼叫凸现自身价值仅仅是自欺欺人的艺术幻觉而已。张楚有意将生存场景与背后的多重精神幕布进行深层勾连,在沉静下来的情感模糊地带勘探真正的精神密码,因为精神变得过分清晰的时候,恰恰是精确的算计取代了复杂的情感。
三、“风景”的冷与热
“望远镜”中变形的“风景”是有温度的,这一温度负载着作家的自我意识及其美学评判。张楚小说呈现的日常生活“风景”,多是处于乡村和都市两个极端之间的小城镇,这里几乎集中了当代中国的社会综合症。作家描摹“风景”时,不经意间会透露出民众秘而不宣的内心风景。当张楚以一种波澜不惊,从容不迫的语调叙述时,还是能让人很容易感到“风景”背后作家温暖隐痛的内心情感。读者在“风景”中蓦然发现作家的心灵投影,在严峻的生活背后感到一种忧伤的抚慰。风景之冷和内心之暖的对比,预示着作家强烈的内心挣扎。隐藏在“风景”背后的作家自我意识的纠缠给文本带来令人震惊的戏剧性。
在张楚的小说中,文本表面呈现的是一幅幅“冷风景”。在阴霾笼罩的华北平原,在处于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小城镇上,从街头到家庭,从工地到工厂,从酒吧到网吧,只要深入人物内心,就会发现一种沉浸在时代喧嚣背后的不安和焦虑。这从普通民众时时显露出来的戾气中可见一斑。冰冷的现实以及人们各自的生命轨迹交错混杂。底层民众的内心生活与精神疑难,被各种形形色色的叙事不断删改和编纂,每一种叙事背后都是一种或宏大或微观的权力关系。只要稍微留意从各种叙事的缝隙流露出来的真实的侧影,就会发现当下生存境遇的严峻和精神的大面积溃败。
人们的生活境遇却并没有因为财富的积累而有所改观,依旧是低矮的平房,泥泞的乡土路,被浓烟熏染的天空,更可怕的是小镇人内心的龌龊与焦躁,贫瘠和悲凉。
《刹那记》中樱桃,一个只有三个手指的丑姑娘,在母亲的情感阴影中顽强地活着,唯一的女友刘若英不断奚落和利用她,唯一惦念的男友罗小军一直追打和羞辱她。被强奸却连真相都没有人可以诉说。既使九十多岁的老人,也无法逃脱步步紧逼的“冷风景”:“苏玉美缓缓坐进铲车里。她那么小,那么瘦,坐在里面,就像是铲车随便从哪里铲出一个衰老皮肤皲裂的塑料娃娃。这个老塑料娃娃望了望众人,然后,将老虎鞋放到离眼睛不到一寸远的地方,舔了舔食指上亮闪闪的顶针,一针针、一针针地绣起来。”这是《老娘子》中出现的令人震惊的场景,这些“冷风景”是普通民众真实的生活境遇的历史见证,同时也是他们心灵伤痛的无望呼告。
在一路高歌猛进的现代化高速公路上,很容易忽视道路两旁那些灰烬般的底层人群。他们常常要面对的精神的溃败与物质的匮乏,他们想尽办法逃离却一次次陷入困境,他们有的用谎言来与现实困境抗衡,他们有的苦中作乐以期谋求一点点生存空间。对于关注底层生活景况的人来说,这样的现实图景并不陌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下室式的“冷风景”,在张楚小说中并不是用来展示的,这使得张楚的小说和底层叙事区分了开来。张楚虽然写到底层,但是并不愿意刻意展示底层的伤口,也无心像经典现实主义作家那样,为时代提供历史精确性的模拟图景。作家意识到历史的精确或准确并不能保证小说的品质,艺术真实有着更高的要求,所以试图把小说的真实提升到生存的普遍性的层面,并与具体个人的个性生活融为一体。与模仿或复制现实相比,张楚的小说更像一个象征世界,通过对日常生活忧郁感伤的体验,深入到多重人性的暗道,为人们提供思考当下精神处境的契机。
同样是地下室式的“冷风景”,安德列耶夫的《在地下室里》探讨了救赎的可能。一无所有的希日尼亚科夫生活于令人毛骨悚然的死神的注视中,荒诞可怕的恶梦和强烈的内心痛苦交织在一起。娜塔丽雅,一个没有出嫁的姑娘手里抱着出生才六天的婴儿,独自行走在刮着彻骨寒风的冰天雪地里,却不知道自己唯一可去投靠的妓女姐姐卡佳刚刚去世。然而正是在这样绝望的令人窒息的场景中,女房东玛特莲娜老太太接下了娜塔丽雅的孩子,给婴儿洗澡时孩子的哭声使得整个世界都变了。无论是小偷、妓女,还是孤独者、垂死者全都伸长脖子,脸上焕发出惊讶、幸福、灿烂的笑容。这个脆弱的小生命像草原上的一星火光,逐渐照亮了人们内心仅存的希望,就连垂死的希日尼亚科夫也获得了新生,“破碎的胸膛里滚起热泪的新浪花”。这并不是作家的天真浪漫,也不是简单的理想主义,而是文学中发生的“事实”。在有着浓郁宗教背景的俄罗斯,故事中的婴儿恰如隐身的上帝,负载着救赎的希望和信仰的力量。
在没有严格宗教背景的当下中国,张楚不会像安德列耶夫那样处理作品。尽管张楚对自己笔下的“冷风景”有着不满,但却并没有直截了当给人救赎的力量。在书写自己并不愿意看到的“冷风景”的时候,与之对话和抗争就成为张楚的必然选择。张楚的对话姿态不是横眉冷对,有时候更像一个天真的大孩子,让“冷风景”发出谈谈的诗意的光泽。看似“弱”的回应,却显示了更为内在的坚忍和耐心。张楚当然知道这样处理是“弱”的,但是正如上帝之爱的“弱”一样,尽管是微茫的,但却是作为时代良心的作家不得不真正面对的。于是,就有了《大象》中温暖的双线结构:孙志刚夫妇寻找救助过患病养女孙明净的恩人,病友劳晨刚帮助孙明净寻找生父母,就有了《刹那记》结尾的七星瓢虫,《地下室》中突然出现的凤尾蝶,《细嗓门》中不断闪现的粉红色乌鸦,《七根孔雀羽毛》中反复渲染的长着眼睛的“羽毛”。这种诗意的光泽渐渐开始照亮地下室式的“冷风景”。或者说,它们和地下室式的“冷风景”构成一种结构上的对话。
在柄谷行人看来,作品中的风景是和作家孤独的内心状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见,风景不是自在的,对风景的发现和描摹与作家的对内心的强烈关注是同时发生的,所以内心生活越是繁复和纠结,越有可能发现别人不能发现的风景。这样,风景也就成了现实的一部分:“我们称之为‘现实’者,已经成了内在化的风景,也即是‘自我意识’。”②在这个意义上,张楚小说中有两个风景:外在的“冷风景”和内在的“热风景”。而“风景”的冷热正是张楚自我意识的两面。尽管希望是微茫的,但是作家并没有放弃在内心深处以审美之热抗衡现实之冷。
张楚观察世界的眼光和情绪,决定了小说如话家常式的叙述语调。和先锋小说非人格化的叙述语调相比,张楚的小说对读者没有强烈的压迫感,作者与读者的情感交流是充分的和内在的。在先锋作家笔下,非理性行为在人物面临绝境时经常会被放纵,进行充满恐惧感和荒诞感的实验,这种实验在当下的现实情境中,很容易演变成新的苦难奇观和酷烈表演。同时,日常碎碎生活书写中世俗形象持续发酵,小说中人物成为欲望的符号和化身。作家往往仅仅拘泥于现实经验或感官感受,对之进行直接的演绎书写,将深层的心灵悸动悬置。这两种叙事策略在张楚身上,开始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张楚有意对生活保持了恰当的克制与忍耐,并试图寻找冷酷后面的悲悯,阴影背后的温暖。自我意识中暖色调的存在,使得张楚的小说有着内在的理想主义气质,但这种理想建基于对当下生存“冷风景”的洞察之上,并且在“冷”与“热”的强烈对比中,呈现一种忧伤的紧张感。
本文系河北师大博士基金“文学体制与先锋文学(W2010B05)”成果之一。
李建周 河北师范大学
注释:
①【英】以赛亚·伯林:《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潘荣荣、林茂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②【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