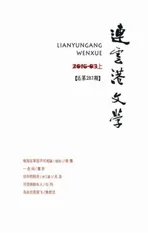一念间
2016-11-25慧好上海
慧好/上海
一念间
慧好/上海
遇到她是九月初在青海塔尔寺。
青藏高原正午的阳光毒晒,我又累又渴,随地在路边树荫下的台阶沿上坐下,咕咚咕咚喝了半瓶矿泉水,然后美美地抽了根烟。
不想说话,一个人跑到青海来晃就是为了不说话。
塔尔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也可以叫它“十万狮子吼佛像的弥勒寺”。然而此刻我更着迷放眼望去那些重檐庙宇,金顶黄墙红门映衬在碧蓝碧蓝的天空下,斜披红袍的喇嘛三三两两穿行其间,整齐的白塔在午后金色透明的阳光照耀下无欲无求。
一阵风吹过,头顶的树叶和树叶摩挲着,发出沙沙的声音,这些风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它们自由自在地吹过转经筒,吹过五彩的经幡,从专注磕长头的虔诚藏民身上穿过,吹得佛塔的梵铃叮当作响。据说这梵铃被风吹响一次,就如念佛一声,听者可借得佛缘。此情此景让人忘却一切众生烦恼,仿佛整个世界的时钟都暂停下来打个午盹。
树荫就这么大,我不远处还坐着一个单身的女游客,头上裹着桃红披肩防晒,蓝格子衬衣迷彩裤旅游鞋,旁边放着个简单的双肩包。有的人什么都不说你也不能在他旁边待下去,但这个女人的气场让人感觉很适宜。我们就那么几乎算是肩并肩静静地坐着看景待了好一会儿,只有知了狠命的叫声。
我悠闲地抽完烟,美美地伸了个懒腰,站起身来准备走时,她说:“给我来一根吧。”声音有点沙哑,和明显的为了礼貌勉强的微笑。
我把一盒烟和火机一起拿出来,“都给你。”
她拿过烟盒抽出两支,“不用。”
她说时我已经走了。走了两步想起这是我的最后半盒烟,又走回去说,“行,你要不需要还给我吧,我也没有了。”
她刚点上了一支,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在男人面前吸烟。这和她看起来三十岁左右的年纪不太相符。
她把烟和火机递回给我,那手白皙纤细,手背上两个输液的针孔很明显。
我拿了烟就走了。
各处都充满了寺庙的深邃之美。比如日昏影斜,偌大的经堂里只有静静的脚步声和经筒转动的声音在廊道间回响,我迟迟不舍离去。
一路走一路拍,直到天已经黑透了还意犹未尽。想到明早还要早早起来拍日出,这才恋恋不舍地回到我住的小旅馆,正看见那艳丽的桃红披肩。
她趴在柜台上问:“一间都没了吗?随便什么房间都行。”
柜台里的少数民族帅哥没正经笑嘻嘻地说:“没了没了。要不就住我的值班室也行。”她锲而不舍地说:“特别贵的也行。”帅哥说:“值班室不要钱嘛。”
我回头问她:“你没到了先订房?这种小地方一定要提前定好房间。”
她看看我,我突然发现她的眼睛乌黑幽深,是一双忧郁的眼睛。
“我在网上订了,他们没看。”她轻轻地说。
我上了两级台阶,心里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好心说:“我是标间,两张床,要不你帮我分担一半房费?”
当然这样说不过是为了让她不那么难堪。她想了一下,又走到旅馆门口望了望。外面灯光寥落,陌生的异域小镇在午夜一点也不可爱。
“不来我就走了。”我说着就开始上楼。
她没说话,只是默默跟了上来。
柜台里的帅哥说:“大哥,还是你厉害!”
我也是临时起意来青海的,简单的一个大号的双肩包就扔在地板上。没什么贵重物品,但专业相机比命还金贵,而且睡眠不能被打扰,所以进门时已经有点懊悔自己嘴快,冒失地收留一个陌生人。
我放下相机包就进了洗手间,等我简单冲完澡出来,打算叫她去洗洗的时候,发现她已经和衣侧躺在门口的床上睡着了,被子拉了个角盖在身上,小小的双肩包和我的并排放着,上面搭着那条披肩。
我轻轻擦着头发,一边打开电脑将相机里的照片导进去,一边琢磨着,是什么样的故事会让这还算漂亮的女人有这样一双忧郁的眼睛。每个放逐自己到这里来流浪的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女人的伤心不外乎负心人这个主角吧。
我睡觉时已经凌晨了。半夜里突然被一种奇怪的声音惊醒。从最初的混沌中慢慢分辨出是洗手间的水流声。我以为是马桶的下水坏了,破旅馆经常这样。我咒骂着下床去关,路过另一张床时被一只鞋绊了个趔趄。当我恼怒地踢开那只鞋后我想起了女人,想起了还应该有一个人在这屋里。
借着微光我看见那床是空的,悄悄贴近洗手间的门,听见里面被水流掩盖的压低的哭泣声,哭得痛彻心扉。我算是心上结了铁痂的人,听久了都不能不心酸。我踮着脚偷偷回到床上,很想抽支烟。
足足过了有个把小时,水声停了,洗手间的门轻轻打开,屋里亮了一些,她光着脚走无声地出来。我装作睡着,眯着眼睛看她轻轻拉开自己的包,拿出一个笔记本和笔回到了洗手间去。洗手间的门再次关上,屋里重新陷入黑暗。
等了一歇,门又开了。她径直走到我放衣服的椅子边,开始摸我的口袋。我静静看着,等着当场捉赃。
她从我口袋拿出的东西让我松了口气:烟和打火机。她打开烟盒抽出两根,烟盒仍旧放了回去。房间重回黑暗,我慢慢又睡着了,直到天亮。
早起她的床空着,被子平铺,双肩包没了,洗手间也没人。我想她也许走了。
走出旅馆的大门,看见她靠墙坐在自己的包上眯着眼睛,津津有味地看着前面几个回族小孩嘻嘻哈哈地在争相踢一个瓶子盖。青藏高原的晨曦洒满她的全身,像极了一个晒暖的老人。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画面让我心动。
“吃早饭去。”我说。
她抬头看到是我,就站起来背着包跟上我。
吃早饭的时候她说:“我昨晚在你的口袋里拿了两根烟。”
“我知道。”
默默吃完了早饭,她付钱我也没客气。
我说:“赶不上拍日出了,我去拍白塔。”
“我也去。”
没什么目标地晃在一重又一重的寺庙院落里。我拍我的照片,她随便站在哪里看着什么发呆。出了庙门不远,一个红袍喇嘛坐在山墙下微笑地看着我们,一只手摩挲着怀中的小猫,另一只手安详地转着经筒。征得他的同意拍完了他,我索性就在他旁边席地而坐和他攀谈起来。她默默地坐在我身边,用一根手指轻轻点了点小猫的脑门。那猫微微睁眼懒洋洋地瞄了我们一眼,继续在转经筒的响声里打盹。偶尔有飞蛾落在喇嘛的脚边,喇嘛就会停下说话,小心翼翼捏着翅膀将它放入草丛里去。我佛慈悲。
有时候我们都不说话,静静看着磕长头的藏民三步一拜,口中念念有词,掌心合十在头顶、额头、胸口各停一下,然后全身匍匐在地上,额头轻叩地面,从我们脚边过去。我们的头顶上一棵翠绿的菩提树枝叶伸展遮阴蔽日,鸟雀跳跃鸣叫其中。夏日的阳光透过叶片的缝隙慵懒地洒落下来,而我们坐在菩提树下,好像已经坐了一百年。
过了一会儿喇嘛起身离开,我发现她靠墙睡着了,迎着塔尔寺塔尖的阳光,睡得很安心。两只白皙的手交叠放在自己的包上,手背上各有两个输液留下的针孔。我在她身边默默抽着烟,守着她。本来想赶紧去拍阳光照在寺墙上的样子,现在就索性什么都不想了,靠墙翻着我刚才拍的那些照片,研究光线和构图。正入神的时候,一只手拿过我的相机,她一张张认真地翻看着里面的照片。她看的时候,我又点了根烟。她看完了说:“给我来一根吧。”
我拿给她,给她点上。她抽烟的样子不算老练。
我俩默默地抽着烟,看着远远的行人和蓝天。塔尔寺的天空格外的蓝,大朵大朵的白云慵懒地浮在蓝天上,寺庙的金顶在阳光里闪闪发光,宗教为什么教人有安全感?是因为足够富有吗?
“进去看过了吗?”我问。
“还没。再等等。”
“等人?”
“等感觉。”
“你住几天?”
“不知道。”
我起身伸了个懒腰:“我下午要去山上拍塔尔寺的全景。”
“我和你一起会影响你吗?”
我犹豫了一下,老实说:“会。”
她抽完了烟,用餐巾纸将我们的烟蒂包好,起身准备走。
我问:“你晚上还住吗?”
“住。”
她就走了。
我晚上回到旅馆时她已经又睡了,长发散了一枕头。洗手间里晾着那条桃红色的披肩,还在若有似无地滴着水。
半夜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朦胧中看她正在穿衣服。
“干嘛?”我问。
“抱歉吵醒你。我去看月亮。”
我看她无声地系鞋带,也起床穿衣。
“你干嘛?”她问。
“看月亮。”
出门时我手里拎着我俩的两条厚被子。她惊异地看着我。我解释说,这里的晚上跟冬天一样,这是必须的。
我跟着她沿着水泥楼梯悄悄往上走,楼顶的门用链条锁着。我疑惑地看看她,她小心地用力一拽,锁就开了,看来她踩过点。一走上楼顶平台,清冽新鲜的空气扑面而来,让人不禁深深吸了一口气。她小心让门虚掩着,然后指着门边的水泥台阶说:“坐这里。”
水泥地太凉了,我俩将一条被子折得厚厚的坐着,共同披着另一条被子。然后各自从被子里伸出一只胳膊抽着烟。
楼顶的感觉果然不一样,月光雪亮、月色溶溶,高原夜半的空气清寒得让人难以置信。我们俯视着月光下空旷孤独的西北小镇,街道幽深荒凉,远远的狗叫声像是投入深不可测的夜的回音,而这灰白的人间烟火以外,塔尔寺的影子绵延山间、神秘莫测。
不知道有多少来看塔尔寺的游客从楼顶看到过它午夜的样子。它依山而起、层层抬高,古老的殿阁威严矗立,带着主宰万物灵魂的沉静和不容置疑。佛门如海,千古沧桑,若隐若现的佛法无边在黑夜里乘着长风,穿越万丈红尘来普度众生。长风是夜的呼吸,看不见树弯腰,看不见云飞动,只看见千丝万缕的月光随风飞散。风是从亘古的雪山深处吹来的,伴着羌管悠悠霜满地,直吹进孤独的灵魂深处。
繁星是千手观音手里的眼睛,月亮扬起手臂,眼睛满天都是,它们俯视着我们,无所不知无所不晓,高贵清远、悲悯宽怀。此情此景让人想要放声痛哭,又敬畏地不敢轻易打破这种静谧。
生命如此渺小,心如莲花绽放,往事历历在目。
突然想起十几年前曾经迷恋过的它: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市……
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我恨……却原来我依然爱……我疼得揪心,疼得几乎要哭出声来。
“太美了。”我说,“我去拿相机。”其实我不想她看见我的眼泪。
“不,别动。”
我就没动。
管他呢!命运安排我们从不同的世界、不同的空间同时来到这座高原小城,一定有他的理由吧。在这样空旷渺茫的时空里,原本陌生的我们自然地相互靠近取暖,很容易产生彼此相依的感觉。
我是摄影记者,潜台词不是女人要多少有多少,而是美女要多少有多少。这个算不上美女的女人,一共只跟我说过几句话,却自有她打动我的地方。
我揽过她,轻轻吻着她。她的鼻子尖凉凉的,像小狗的鼻子。
回到房间后,刚才用来坐的那条被子不能盖了,我们只能共同盖一条被子睡觉。我搂着她,她轻声说:“不要,行吗?”
“行。”
我搂着她稳稳地睡了一夜。
清晨醒来,她仍旧不在,我仍旧在旅馆的大门外找到了晒暖的她。吃完了早饭,我说:“今天陪你去里面看看吧。”
我们跟着游客,一间间地穿过寺舍,上了这个台阶或者下到那个院落。有时我会拉她一把,她的手柔软冰凉。我们像一对情侣,但是我们没有语言,也从不互相拍照。她没拿相机,甚至手机也没有拿出来过。
跟着人群走到大佛殿拜佛时,我远远站着,看她走到佛像前弯下腰去,却久久没有直起来。我挤过人群到她身边,她用披肩的一角捂着脸,双肩剧烈地抖动着。我搂着她,随着人流走到人少的地方,她在我的肩上抽泣了很久才渐渐止住。
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分开过。我们一起看壁画,一起默默伫立在喜欢的佛像前,一起跟随着转经的藏民们亦步亦趋地伸手转动每一个遇到的经筒。
“那一月
我转动所有的经筒
不为超度
只为碰触你的指尖”
她的手指苍白修长,手背上的红点依然明显,在每一个经筒上抚摸、旋转、落下,我的手指紧跟在后面,在她触摸过的地方重复着她的动作:抚摸、旋转、落下……
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在啤酒和白酒间她选了白酒,在普通白酒和本地白酒之间她选了高度青稞酒,那酒灌在喉咙里,明显觉得一条火焰沿着喉咙燃烧下去。
“过瘾!”我说。将一杯酒一饮而尽,将杯底亮给她,挑衅地看着她。
她将小酒杯举到口边,微微歪着头看着我,然后不紧不慢地也一饮而尽,将杯底也亮给我。
我实在是喜欢她的这个样子,旖旎又不做作。我俩白酒小菜,随意闲散地吃得很是舒心。她的酒量出乎意料的好,我都晕乎了,她仍然面不改色从容镇定,只是在我倾诉的时候,忧郁的眼睛不再是那么离人千里的淡漠,而是有了温柔。
我说,“我是个爱无能患者。”
她微微扬了一下眉毛。
我知道她的疑问,“不,不是性无能,我的性能力很好。是爱无能,我失去了爱的能力,我既不能爱亲人,又不会爱女人……我感觉自己正在慢慢坠入孤独地狱。”
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
我接着说:“有人说过,佛经上有‘从南瞻部洲下过五百逾缮那乃有地狱’。地狱也分好多种,唯有孤独地狱,在山间旷野、树下空中,到处都可以突然出现,也就是说人会无缘无故马上出现地狱般的痛苦。十几年以来,我感觉自己越来越接近这个地狱了。我拼命赚钱拼命花钱,却觉得活得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我夜夜笙歌人模狗样,却逃脱不掉孤独的痛苦。我既活得无趣,却又觉得没有死的必要,所谓地狱煎熬,莫过于此吧。”
“你这样,一定有你的理由。”
我醉眼迷离地看着她,她身后的灯给她镀了一圈光亮的金边,叫人看了安心平和。这些年来我第一次想要倾诉。我紧紧握着她的手:“我读研时爱上了我的英语老师。在第一堂课时对她一见钟情。她比我大7岁,那时刚刚有孩子。我们爱得天昏地暗、不顾一切。她说,等孩子上了幼儿园能够离开妈妈、我研究生也毕业了,她就跟我走。我出身寒门,父亲早亡,母亲视我为命。于是母亲在知道这件事后到学校里找到她,把她大骂了几个小时,在我们学校轰动一时。”
我看着她。她平静如水地回视我。
我继续说,“她没有因此离开我。相反,她跟我说,事已至此,就什么也不能把我们分开了。只要我不退缩,她可以放弃一切。她丈夫在国外无法立即离婚,她将自己起草的离婚协议书公证好后贴在学校布告栏内,公然和我出双入对。”
“可是……”
“是的。我本来应当想到‘可是’,我应当顾及我的母亲的。然而当时的我被冲昏了头脑。于是,我母亲被我气死了。是真的气死的……”
我仰头干了一杯酒让眼泪流回去,笑说:“后来她丈夫回国,我等着她恢复自由,却等来了她随夫出国消息。然后她就消失了。卖了房子、注销了手机号、注销了邮箱,消失得干干净净……我还得顶着天字第一号白痴的名头在学校里度过剩下的一年半。记不清有多少个夜里我在梦中终于狠狠抓住了她,我只问她一句话: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毕业后,我努力让自己正常生活,恋爱结婚,但很快就离婚了。无论是恋爱还是结婚,都丝毫不能带给我所谓的快乐幸福,只有烦躁厌倦。开始我想是因为女人不够漂亮,后来我发现越漂亮的女人在我这里的保质期越短。我失去了七情,却又不甘心失去六欲,我仿佛看见孤独地狱就在眼前,而我无能为力。想到也许还有漫长的生命要度过,简直是无边无际的害怕恐惧……”
她将纸巾递给我,被我抓住的那只手反手和我握在一起,另一只手举起酒杯干脆地一饮而尽。
等我平静下来,她说:“所以你来这里,就是想解脱,对吗?”
“是。”
“那你解脱了吗?”
“也许吧。”我挥挥手,“你看这塔尔寺白天壮观威严、唯我独尊,晚上看起来在天地之间还不是一样渺小孤独?佛陀在菩提树下不是说过:‘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能德相,只因妄想执念而不能证得’。放下妄想执念即是自我救赎解脱,不是吗?即便我抓到了她,得到了为什么的答案,又能怎么样呢?时光能倒流吗?死去的能够复生吗?错过的能够再来一次吗?当然是都不可能!所谓一念生缘起,一念生缘灭,就是这样吧……”
她没有讲她的故事,我也没有问。饭店关门我们才相互搀扶着出来。天已经黑了,空气充满了高原特有的透骨清寒,小镇的夜市都已经收摊,小街上路灯昏黄,已经没有什么行人了。
我疯疯癫癫拉着她的手说:“喂,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吻着她手背上的针眼:“生病到要输液的地步,不会是小病。针眼刚结痂,你是拔了吊针就来青海了吗?倒头就能睡着,你为谁几十个小时没睡觉吗?你在逃什么吗?”
她过身看着夜色中的塔尔寺说:“你说宗教为什么会让人有安全感?”
难道她偷看过我的思想?
我傻笑着摇头:“因为无所不能吧,把一切交给无所不能的宗教是最实在的安全感。你说呢?”
她认真地思考着说:“我说不好,大概觉得,是灵魂找到归宿的感觉。一看到佛像,就觉得沉沉的重担都可以卸下来给他了。”
我站住了,从后面拥住她的腰说:“那么,把你的重担给我吧,我来背着”。
她没动,任我将下巴放在她的肩上。
我说:“我从不和女人过夜,但是昨晚你在我身边,我却连一个梦都没做一觉睡到天亮。佛为什么要让你这么匆匆忙忙地到青海来?就是因为我在这里等你。为什么要让你没有地方可住?就是为了让你不能与我擦肩而过。为什么让你在佛前哭泣时让我守在你身边?就是要让你把你的重担卸在我的肩上。”
她用一只手背捂住了口。
我继续说:“你看,我们都是在这个世界上孤独地流浪的人,气味相投,在茫茫人海中又能够幸运的遇见,多好。”
我板着她的肩将她转向我。月光下她泪眼蒙眬,楚楚动人地看着我。我的心简直被她这双眼睛融化得一塌糊涂。
“不如我们试一试。爱我吧!”我将她拥进怀里。
她在我耳边哽咽着说:“谢谢你。”
这一夜我们仍旧相拥入睡。两人朝着同一个方向侧躺着,像两柄汤匙心心相印。她的头发细软地拂在我的脸上,满足而温柔。
清晨醒来,一半床是空的,她仍旧不在。我使劲摇着酒后初醒的头企图赶走心慌。她的双肩包不在,洗手间里的桃红披肩已经没有了。跑到旅馆的大门外,在她每天坐着晒暖的地方,什么也没有,只有黄黄的阳光和尘土。
我回到柜台问:“看到我同屋的女孩了吗?”
那帅哥懒懒地回答:“大哥,她走了。房账都结了。”
我眼前一黑!“走了?什么时候?”
“天刚刚亮的时候嘛。我就是她叫醒的。现在已经走了快一个小时了。”
回到房间,房间寂静得可怕,冰冰冷冷,好像被抽空了氧气。在窒息中艰难地一个长长的换气,整个胸口都充满了呼吸之间的疼痛。桌上放着一页纸。我拿过来,应该是从她的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上面写着:
佛说,爱恨一念间
为了永远不要走到下个一念间
我只能离开
因为这一念间
我爱你
(责任编辑解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