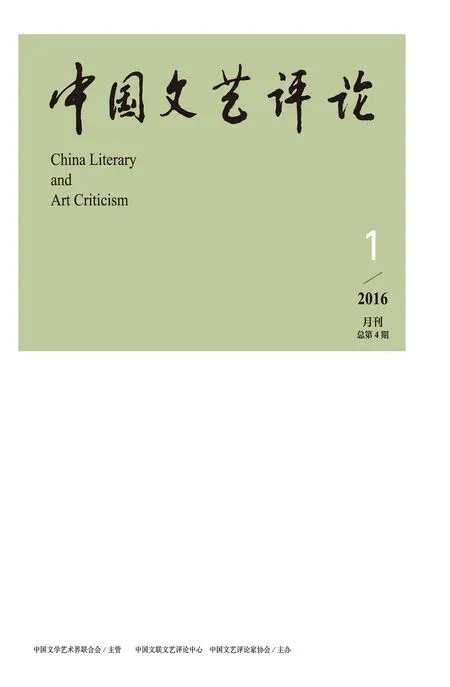论新时期现代主义美术批评的重启
2016-11-25陈旭光
陈旭光
论新时期现代主义美术批评的重启
陈旭光
在20世纪的美术史中,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纠葛几乎是贯穿始终。受制约于20世纪中国独特的社会政治形势和文化环境,现实主义一直占据主流性、主导性的地位。相应地,形成了对表现自我,注重形式、抽象的艺术思想——从某种角度说是现代主义倾向的艺术批评思想的压抑态势。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现代主义开始“复苏”,中国艺术逐渐呈现出多元并存、百花齐放的局面。但这个进程却非一帆风顺,一蹴而就。20世纪80年代,关于“形式”的论争与对现实主义的反思,创作上“表现自我”的潮流等,都在现代主义创作和批评的重启中起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
一、艺术史参照: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纠葛与命运
在20世纪的美术史中,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是总结、梳理美术批评史写作的重要而有效的线索。这不仅仅是因为围绕着两大主义的论争和较量极为激烈明显,而且因为与这种论争相应,形成了各自为自己阐发辩护的批评观、艺术观以及相应批评模式和方法。
当然,笔者在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创作方法,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创作流派,更应该理解成为某种创作倾向、走向、创作特点或艺术风格与追求等。以现实主义为例,它作为一种创作流派或思潮是特定历史阶段有特定内涵的艺术史术语,但作为创作方法则有所泛化,可以说是古已有之,甚至是中外皆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作为思潮、流派不可能在中国本土原原本本再现,但作为进入中国本土或本土化之后的创作追求而形成的某种风格、倾向却是有可能的。
归根结底,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作为艺术思潮在西方本就是庞杂的——不仅有时间维度上的演变,在流派团体的构成上也非常庞杂,在进入中国后的本土化过程中无疑愈益复杂化。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中间,还有大量的“中间物”,现实主义还常常与写实主义或写实手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手法等部分重叠或总是捆绑在一起。现代主义则不仅流派众多构成复杂,而且本身与浪漫主义、后现代主义也颇多叠合,较难明确区分。
在20世纪中国艺术的语境中,我们依据它们的原始意义但结合被人理解和使用的状况,可以大体归纳出它们主要的特征性差异:
其一,现实主义强调“写实原则”和真实性原则,塑造“典型”形象,往往要求创作主体客观冷静,强调理性意识;强调艺术社会功能的功利主义,追求大众化、通俗化、平民化的表达,主张追求民族形式、民族化。现代主义则是偏主观的、激情的,极力追求表现自我意识、心理意识或潜意识心理,技巧上可以变形、扭曲、夸张、抽象,具有某种纯粹的,形式主义倾向、偏向“艺术为艺术”或“艺术为自我”,更偏向于西化、现代化。现实主义与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不少叠合或纠葛,现代主义则与浪漫主义尤其是消极浪漫主义、后现代主义有部分重叠或纠葛。
其二,从现代主义艺术的创作主体——艺术家来看,现代主义的艺术家一般而言,“是一批具有自身相对的独立性,承继了‘五四’现代知识分子个性主义精神传统,在艺术表现上偏重自我和内心世界,尊重形式的独立性价值,表现出较大程度上的‘艺术至上’和‘文的自觉’精神,并因而与提倡‘大众化’、‘民族形式’方向、‘革命文学’、‘两结合’创作方法的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一定疏离和对抗关系的现代自由知识分子。他们之选择或倾心于现代主义,自然有着耐人寻味的意识形态蕴含。”[1]陈旭光:《中西诗学的会通——论二十世纪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页。
在“五四”新文化的发轫期,与其他西方文艺思潮相比,从时间上看,现实主义思潮进入中国并不算早。从影响力看,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美术上的“写实”追求、话剧中的现实主义追求,都很难说就占据了绝对的主流地位,现实主义往往与从西方传入的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包括表现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野兽派等等)同台竞技。至少在文学中,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传入中国还早于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因为浪漫主义中蕴含的张扬个性、自我抒情、反抗社会等特征投合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狂飙突进的精神。但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到了抗战时期,尤其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由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地位愈益提升和强化,现实主义越来越得到了张扬并逐渐主流化。
例如,在美术领域,不仅从西方传入的油画以徐悲鸿等的呼吁和亲力亲为为代表,以写实风格为主,在中国画领域,写实,也成为无论是改良论者还是革命论者改造中国画的不二法宝,成为许多革新者、学人、艺术家为中国美术开出的一个重要处方。[2]参见陈旭光:《论“五四”前后中国美术批评中“写实”观念的崛起》,《美育》2014年第5期。正如专家指出的那样,“研究写实主义在中国画变革中的作用和影响,研究从西方引进写实主义的得和失,对于探讨中国画的现状和它的未来发展,不无意义。”“写实绘画不能概括20世纪中国画的全部面貌,但是写实主义的影响无所不在。”[3]邵大箴:《写实主义与20世纪中国画》,《美术史论》1993年第3期。
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在20世纪艺术创作中的繁盛乃至占据主流性、主导性的地位,甚至成为不可动摇、无法逾越的创作原则,主要有以下如下几个原因:
一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往往从艺术为社会、为人生的功利性角度出发来提倡现实主义,又在现实主义的高扬中强化这种功利性。在他们看来,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原则能保证艺术的社会功利性,只有真实地表现社会、人生、现实,“不语怪力乱神”,才能对受众发生良好的影响,才有利于世事人心、社会人生。
二是灾难深重、民族危机不断的20世纪现实的需要。20世纪的中国面临民族存亡的抉择。“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与社会责任感空前高涨,再加之世界上‘红色三十年代’的左派思潮影响,除了小部分作家在有限的范围内试验着现代主义的创作外,极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4]陈思和:《七十年外来思潮影响通论》,《鸡鸣风雨》,学林出版社,1994年,第146页。在艺术领域显然也不例外。
三是提倡践行者认为大众易于接受的需要。抗日战争把千千万万的中国农民投入了战争的熔炉。在农民的政治热情高涨的同时,以农民为主要的宣传、动员、服务对象的战争文化规范悄悄取代了五四以来逐渐形成的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现代文化规范。因为要强化文艺的宣传功能,要给工农兵“雪中送炭”,更要让工农兵“喜闻乐见”,就必须要走通俗易懂的通俗化道路,要利用“民族形式”和民间形式,确立文艺的工农兵方向。
四是马克思主义强调艺术的社会属性,艺术对现实、政治的反映和宣传、服务的功能,因而尊崇、提倡甚至是独尊现实主义。
与现实主义的逐渐主流化相反,现代主义则在与现实主义的相持相抗中越来越边缘化。现代主义的艺术家还常常或真诚或出于现实主义的威力而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在一段时期几乎逐渐销声匿迹。但到70年代末80年代又小心翼翼地复苏,并在85新潮美术、先锋派文学、实验戏剧等领域达到了一个高潮,高潮之后又经历了解体或被告别,然后,迅即通过89后新潮等美术潮流而趋向后现代意味的实验艺术。但现代主义创作和批评的复苏却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尤其在“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开端发蒙之时,现代主义(当时被称为“现代派”)可以说是步步维艰,常常伴随着艺术创作的艰难探索和艺术批评的激烈争议。到20世纪末,中国艺术逐渐从原先比较单一的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进入到多元并存、百花齐放的局面。或者可以说,在一个商品化、市场经济的时代,不同创作方法的意识形态含义在大众性和商品化的氛围中不同程度遭到消解。秉持解构精神的后现代文化、后现代艺术崛起了,无论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都已经成为被“后”(颠覆、解构、讽刺、滑稽模仿等)的对象了。
二、批评的先声:“形式”论争与现实主义的反思
形式,在新中国艺术界很长时期内带有贬义。“形式主义”更是一个分量颇重的批评标准。在新时期整个艺术创作领域,涌动着阵阵艺术创作与思想的春潮,形式意识的觉醒,对形式美的追求也是在这样一个文化“解冻”的背景下出现的,它与以往主流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明显不同。相应地,艺术批评也出现了呼唤关注形式的探讨。
围绕《绘画的形式美》[5]吴冠中:《绘画的形式美》,《美术》1979年第5期。《关于抽象美》[6]吴冠中:《关于抽象美》,《美术》1980年第10期。《内容决定形式?》[7]吴冠中:《内容决定形式?》,《美术》1981年第3期。等文章,美术批评界展开了热烈的争议。关于“形式美”、关于“抽象美”、关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的三次批评争议,都与形式问题密切相关,都是美术界形式意识觉醒的表现。这是新时期首次非常集中的形式批评潮流,其功用主要是通过理论探讨,标举形式的独立性,并突显其与强调集体、国家、内容、主题的现实主义的创作与理论之不同。
更为重要的是,由此发端的关于形式与内容关系的探讨,对于“内容决定形式”的反思,对于抽象美、形式美的认知,对于形式的独立性、自足性的认知,都是通过批评论争逐渐明晰而达成的思考或共识。形式意识的觉醒和强化表征了艺术创作的宽阔道路,也表明了某种有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而趋向于现代主义的美术创作道路和艺术批评思想的萌生。当然,历史地看,这更是一种恢复和再生。
广义地说,关于形式、形式美、抽象美、内容与形式关系等问题的探讨均属于现实主义反思的范畴之内。而对现实主义的反思则不可避免地与对现代主义的重新认识密切相关。“从1979年开始,中国的艺术界从沉默寡言中挣扎出来,对艺术形式的大量关注,引发了人们对现代主义的重新认识。在关于艺术形式和抽象的讨论中,人们事实上已经触及了这样一些问题:现实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定义?它在艺术领域中的内涵和外延应该是什么?现实主义是否就是真实地描绘对象的外在特征?”[8]吕澎:《20世纪中国艺术史》(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01页。
比如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江丰从宏观的高度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对美术界“形式”意识觉醒的思潮提出了明确的批评。[9]见《关于美术的形式与内容问题的讨论》,《美术》1983年第4期。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批评的标准是“现实主义”或更狭义一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从维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主流性地位的角度而对形式意识觉醒的潮流进行的批评。
因此,毫无疑问,关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矛盾与关系的争论,开启了艺术创作自由要求的表达和多元化创作的道路。虽然,关于现实主义的定义最终并没有产生一个大家公认的定论。“然而,对于现实主义的争论本身,却构成了一个恰到好处的隐喻。这个隐喻的中心意义是:在中国这个国度里,现代主义是否能够被容纳宽容?或者甚至,中国的艺术家能不能涉足与现实主义大相径庭的现代主义?这个问题出现在1979年间的中国,就更显得意义重大了。1979年以后,如果没有一场关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讨论,中国现代艺术要形成一股潮流和力量是不可想象的。”[10]吕澎:《20世纪中国艺术史》(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01页。从某个角度看,正是在关于形式、形式美、抽象美这些似乎非现实主义或反现实主义的东西能否存在、能否发展?能否在现实主义中发展或能否在现实主义之外独立发展等对于现代艺术具有先验性话语权和意识形态权威性含义的“现实主义”大讨论之后,现代主义开始登堂入室。
三、表现“自我”、创作自由与现代主义的暗流
在20世纪艺术批评的主流中,现实主义无疑一直处于主流的地位,现代主义倾向的艺术批评思想则受到压抑。因此,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在20世纪中国艺术的语境中,并非如一般艺术流派、艺术创作方法那样超脱和纯粹,而是被赋予了浓重的意识形态含义甚至权力话语性。这二者之间的消长形成为或激烈或微妙的权力话语冲突。正如在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中,“在这些讨论现实主义自身概念的文章中,现代主义‘创作方法’总是无时不在地作为参照系被提及和援引。”[11]吕澎:《20世纪中国艺术史》(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01页。
因为“文革”对个性、自我的压抑。“表现自我”的艺术问题或美学问题在文学(尤其是诗歌如“朦胧诗”)等领域几乎同时有过争鸣。在美术领域也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批评现象。
1977年举办的民间性、非体制内的“星星美展”及相关评论文章开启了美术界长达两年之久的“表现自我”问题争鸣讨论。所以从某种角度看,美术中关于现代派,关于表现“自我意识”的讨论是与标榜自己向西方现代派学习、宣扬“自我表现”的“星星画派”密切相关的。
在“星星画派”之外,首都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引发了闻名全国的风波,创作者还在北京市美协和北京油画研究会的一次座谈会上借题抒怀,发表了“艺术个性与自我表现”的发言,强调艺术个性,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社会的发展要求艺术家充分地表现艺术个性与自我”[12]《美术》1981年第3期。。
“星星画展”的展出及其成员对自己的阐述和评论家对之的关注评论引发了批评。实际上,自我表现与“艺术个性”等联系在一起,就其现实语境而言,是对创作自由、艺术表现风格多元化的呼唤,是一代艺术家创作主体“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自表现”这一口号在当时的中国现实语境中具有厚重的意识形态内涵,是一个事关争取人的自由、独立与解放的问题,所以才会在许多艺术领域里几乎同时出现。
四、判然的批评与艰难的思考:“阀门”终于打开
不少学者对“自我表现”的口号提出了批评。一般而言,批评者往往把“自我表现”与“人民”对立起来,与现实主义对立起来,同时与西方“现代派”联系起来,认为强调“自我意识”就意味着对现实的背叛,对人民的漠视、对现实主义道路的违背和对西方现代派的顶礼膜拜。可以说,对现代派的评价,是现代主义批评崛起的重要内容,主要涉及印象派、表现主义、抽象派、超现实主义等现代绘画流派。但鉴于现实主义的强大和意识形态含义,对作为支流的现代主义的评价和肯定乃至大声疾呼,都是渐进式的。上世纪70年代末期,至少在美术界,印象派还是一个没有人敢大胆说自己喜爱,敢于大力提倡的流派。人们对之的态度是试探性的,常常需要“顾左右而言他”。
《印象主义绘画的前前后后》一文以一个普通观众参观1979年6月到7月在北京中山公园的一个印象主义绘画展之后的留言[13]1979年的中山公园印象主义绘画展,有位观众的留言是:“我的妈呀!可怕的印象派原来是这么回事——太可爱了。”来支持自己对印象派的介绍,文中说印象主义虽然在西方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但在中国却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继而以其一贯的大胆直率,以一种进化论式的现代性理念呼吁:而对于印象主义,“已不是该不该,可不可以学的问题,而是仅仅学印象主义那是太落后了”。[14]《美术研究》1979年第4期。
1979年的《世界美术》第一期即创刊号上,集中刊发了《印象派》《梵高论画》《莫底格利阿尼》《西方现代美术流派简介》等文章,介绍西方现代美术流派与创作方法。《西方现代美术流派》一文,介绍了“新印象派”“后期印象派”“象征主义”“野兽派”“立体派”“未来派”“表现主义”等。在《世界美术》第2期的续文中又接着介绍“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波普艺术”“视觉派艺术”“活动派艺术”“超级现实主义”等。一时琳琅满目,几乎让人目不暇接。文中提出,“印象派属于哪个阶级的艺术?他们的艺术实践所反映出来的政治倾向性符合哪个阶级的愿望和要求?他们流露出来的审美趣味打上了哪个阶级的烙印?人们常说,印象派是资产阶级的艺术,这并不错,但总觉得不够确切。”他用当时常用也不能不用的阶级分析法分析印象派的画家们,首先是肯定:“印象派的画家们多数来自小资产阶级和手工艺人的社会阶层。即使出身于富裕资产阶级家庭的马奈和德加,也都是爱国主义者。”继而是批评:“不过,这些印象派画家们的阶级局限性,使他们的创作反映不出革命者的心声,更不用说和战斗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行动吻合了。”不难看出,虽然对印象派的推介视野开阔,开风气之先,但对印象主义的评价标准只能是绕不过去“现实主义”的先验性标准。“我们应该有气魄、有胆识,肯定现代派艺术中一切从内容到形式有价值的东西,但不能全盘肯定现代派,不能不加分析地给现代派送上一顶‘现实主义精神’的桂冠”,文章甚至努力地把印象主义往现实主义里装:“人物画(包括肖像和‘主题画’)、风景画、静物画,都可以是现实主义的。自然,人物画在反映生活方面比起风景和其他形式来有更大的优越性,因此绘画应以人物为主体。如果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这样理解不违背马列主义认识论,那么印象派的一些优秀的风俗画、肖像画和有艺术魅力的风景画,应该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15]邵大箴:《现实主义精神与现代派艺术》,《美术》1981年第11期。
有的观点认为“印象派是不是现实主义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颇值得怀疑。印象派情况非常复杂,不能以现实主义来划线,或做出非此即彼的评判。而即使印象派不属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现实主义,也不能成为我们今天否定它的依据。[16]吴甲丰:《印象派的再认识》,《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
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印象派、抽象派等现代派有着特殊的含义。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美术界曾对西方印象主义进行过讨论,当时认为印象主义的哲学基础是马赫主义,印象主义绘画被看作自然主义的艺术和形式主义的艺术而受到批判。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现实主义、印象派或现代派的问题,都不仅仅是艺术流派、艺术风格或创作手法的问题,而是事关政治立场、对人民和现实的态度问题。当然,随着“星星画展”的展出、“星星画派”的渐为人知,以及首都机场壁画风波等等,现代主义的创作和理念不再让人谈虎色变。人们开始从小心翼翼到逐渐理直气壮地为现代派辩解或张目,有时还更为具体地涉及对抽象、变形、象征等现代主义绘画常用手法的探讨。
比如,有观点认为现实主义是一种可以包含写实手法和夸张变形手法的创作方法,其本质含义是“以现实生活的本来样式把一定的时代和社会生活现象加以典型化”,但这只是选择之一,只是“真实反映现实”的方法之一。“现实主义产生过伟大的作品,非现实主义也产生过伟大作品。美术界也产生过像莫奈、毕加索、马蒂斯这样的大师,他们完全不因为不是现实主义者而在艺术上变得渺小。换句话说,即使我们不承认他们是现实主义者,我们也得承认他们的伟大。”[17]栗宪庭:《现实主义不是唯一正确的途径》,《美术》1981年第2期。
无疑,在渐进式地慢慢扫清了思想观念上的障碍之后,现代主义的创作也才能结束欲说还羞、遮遮掩掩的“半地下状态”,进而开始在中国蓬勃发展。
如果说“星星画展”只是表现出了现代主义的“星星之火”的话,经过一批画家对“形式美”“抽象美”的探索,首都机场壁画“抽象”“表现”“变形”等艺术手法的探索,最后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汇聚成为蔚为可观的,流派、旗号众多,各种美学、风格多元并存的,却是有着明显的“现代主义”味道的现代美术潮流。
陈旭光: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程阳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