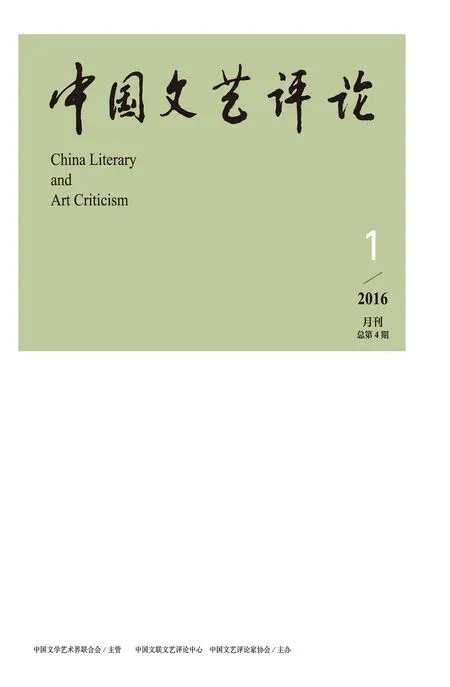中国文艺“走向世界”亟需国际化的文艺评论相伴而行
2016-11-25曹卫东
曹卫东
中国文艺“走向世界”亟需国际化的文艺评论相伴而行
曹卫东
随着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全文公开发表,《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全文发布,文艺事业加速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清晰凸显。文艺作为时代前进号角和民族精神火炬的重大意义,再次得到高度的强调。文艺领域存在的与此不相配的不足和弊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正视,改进不足、革除弊病,全面繁荣发展文艺事业,强化文艺事业的时代担当,成为包括高等院校人文艺术学科在内的文艺建设者队伍的迫切任务。
按照总书记讲话和中央关于繁荣发展文艺工作意见的精神,改进和加强文艺评论是加强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促进文艺创作不断进步、切实履行好时代使命的重要环节。在全球化潮流日趋深入,世界范围内各民族-国家和区域文化的发展,既呈现出宏观一体化的倾向,又展示着尖锐具体的差异化冲突。以中国精神为灵魂、以爱国主义为价值核心的当代中国文艺,肩负着在这一格局中参与国际对话,对内凝聚民族精神、对外建构民族新形象的特殊使命。
一
从近年我国优秀文艺作品在海外被翻译、出版和行销的实际看,总体上的态势是外国译者相对国内译者占据压倒优势,归化处理远远胜过异化处理。除了科幻小说《三体》等少数在国外获奖的作品在英语世界的情况外,目前我们所知的其他在国外能销得好、传得开的中国作家作品的译本,几乎都是出自以外语为母语的外籍译者之手。甚至一些外文版的文学期刊,几经尝试,最后也只能把翻译的最终支配权委托给外方。这种情况其实早已有之,并非近年新出,其成因也并不单一,不少学界同仁也正在探讨中。但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仅仅关乎翻译技巧或者语言能力的问题,更是与国外的文艺市场、文艺评价以至意识形态语境直接相关的系统性的症结。
优秀的文艺作品不能受制于国内的市场,同样也不应该受制于国外的市场。被集纳着意识形态偏见、成见和庸见的国际文化市场牵着鼻子走的文艺作品,虽然走红,但终究只是在一时或者一个有限的层面。长久看来,被严重归化,甚至边翻译边改写而成的译本,不但不可能在传播和接受环节上散发民族精神的光彩,而且也并不是对作家和艺术家本人才情的忠实反映,即使被译介的作家、艺术家本身可能确实是独具才华的,他们的这路译本也最终只能落入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境地。更糟的话,就是在翻译中,让译者替代了作者的本尊,译本传得越远,作者被扭曲得越严重。
问题既然不仅仅关乎翻译,解决问题也必须杜绝单打一,做多管齐下的努力。应加强对国外文艺评价机制的调查研究,通过了解国外文艺评价现状,为我们的文艺评论打开一扇知己之外也要知彼的窗口;从对国外文艺评价机制内在机理和相关社会背景的研究着力,为我们的文艺评论提供一个知识和观念上的可靠支撑点,以促使和帮助我们新一代的文艺评论家从思维视野上养成化“异己”为“自己”的一部分、变“他者”为“自我”的一侧面的新习惯,为迄今为止尚在对外翻译的道路上深受多方牵掣的中国文艺精品,增添一份来自文艺评论的助力。
二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间中国文艺走过的道路,在面向世界和对外交流方面,很明显地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十多年,是以急促“补课”性质的单向译介引进为主,这一时期最醒目的一个高潮就是“八五新潮”;1990年代初期开始,伴随市场经济的加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化,文化艺术的国际交流日益转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新格局;新世纪以来,文化“走出去”战略全面布局,通过孔子学院、外译项目、国际书展、影视和舞台艺术剧目生产国际交易机制的建立,形成了横跨教育、学术、出版、文艺多领域的宽广渠道和稳定平台,借助于此,中华文艺经典和精品“走出去”的数量规模有了前所未有的扩大。
但贯穿、累积在上述三个阶段的瓶颈问题——“走出去”之后的“走进去”成效如何落实并持续深化,并没有随着渠道、平台的拓展和增量的加速,而得到根本解决,相反,被衬托得越来越突出。在当今文艺国际化的多边双向交流已呈新常态的大趋势、大背景下,“走出去”的频率和密度必须保持,“走进去”、“留得住”以至“扎下根”的成效,也必须全力争取实现。表面上这似乎只是文艺国际交流的形式对等问题,实质上更是来自审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体系层面的跨国界、跨民族、跨文化竞争的客观挑战。
检审“走出去”道路上阻碍“走进去”或消解“走进去”效应的种种因素,接受需求的低落和期待视野的偏差这两点,显露得最长久也最普遍。一方面,这固然是冷战时期西方各国的所谓现代中国学研究,将我们的文学和其他各艺术门类的作品长期当作探察我国世风民意的社会学素材和国情资料的一种历史后遗症;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我们以往至今对此一直未能予以充分重视和有力反制的疏失。域外接受情境中存在的这种把我们的文艺作品扭曲、翻转、异化为社会学素材和国情资料的认知偏向,具有深层次的社会心理根基,它会作为军事政经领域的冷战余留在思维空间里的一份遗产,长时间地延续、发酵,对人们的文化接受取向暗中发挥支配作用。
这种生成于外部的接受习惯和认知偏向,足以直接导致文艺作品整体肌理的瓦解。因而要克服或节制它,不可能靠文艺创作本身,只能依赖创作之外的助力。为此,迫切需要探索、发展一种有针对性的外向型的文艺评论模式。而且这种文艺评论模式,必须建立在包括但是绝不能局限于文艺范畴的外向型的民族精神文化主体的自我阐释基础上。换句话说,这个外向型的民族精神文化主体的自我阐释基础,就是在理念世界里可以同时照亮我们自身和我们所关联的“他者”视野的“民族魂”的灯火。
关于这一点,一个特别值得镜鉴的范例,是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和精神哲学的理念天地里营造起来的个人、国家、民族精神和世界历史的逻辑同构体。在这个极宏大、极抽象而又极微观、极具体的逻辑同构体中,不可重复的、抽象化和一般化的个性人格,以自身的发展延展出了国家、世界和普遍理念发展的唯一途径,而且在从这一个性人格到国家、再到世界,最后到普遍理念的三环节构成的全过程中,后面的每一节点都是紧邻在它前面的一个节点自身发展的完成形态。就这样,个性人格、国家、世界、普遍理念,就一脉相承地贯穿在了历史发展的链条上。依照这一理念图景,晚年的黑格尔在梳理世界各国各民族历史的前提下,高度肯定了当时他所在普鲁士君主国,甚至认定世界精神发展的完成已在此实现。
尽管这种一触及实际就显然失之荒谬的唯心论的判断,后来被马克思辛辣地批评为“奴颜婢膝”、“妄自尊大”。黑格尔有关个性人格、国家、世界和普遍理念的历史发展蓝图,也被恩格斯揭示为“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1]参见[苏联]阿尔森·古留加:《黑格尔传》,刘半九、伯幼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21、127页。但在创制理念体系的视野深广度,以及坚守民族国家意识的自觉性和自信心上,黑格尔的思想策略,对置身当前国际文化语境中、正面临重铸精神世界的“民族魂”这一紧迫理论创新使命的我们,仍有他山之石似的独到参考意义和批判借鉴价值。
三
历史内涵充盈、逻辑架构严谨的“民族魂”的理念阐释基础,既是外向型的文艺评论话语生发的根本起点,也是支撑这样的文艺评论在国际化语境中展开有效对话的价值主体。国际化语境迥异于本国本民族内部社会语境的鲜明特点,就在于价值观的多元并存和价值评判标准的相对化。在此语境中,展开对话的有效目标,首先不是求得共识,而是足够自明;进行价值评判的有效意义,也并非首先体现在为“他者”所认同,而是为自我做充分的确证。只有实现足够的自明和充分的自证,才能为赢得最大限度的“他者”认同准备好必要的条件。
就具体针对某一文艺作品或文艺现象的个案式的评论来说,这里所谓的足够的自明和充分的自证,实质也就是要凭着坚实明晰的历史阐释和逻辑推演,穿越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化壁垒,把在壁垒另一侧被“他者”有意无意地扭曲、撕裂了的我们民族的文艺作品和文艺现象,用理念化的论证和阐发复原和缝合起来,还它们以饱满、完整的话语形态和精神肌体。
无疑,要发展这样的文艺评论,需要我们从习以为常的对自己人说话的思维定势中跳出来,来一个面向外部世界和异己力量的思维与表达模式上的大转变。至于促进这种思维和表达模式的深层转变的可行手段,实际上早已存在。在近现代中外文学交流和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它体现为与创作实践相交织的翻译实践。中国现代文学以及整个中国现代文艺创作的话语面貌和修辞肌理,追根溯源,在很大程度上都源自民族语体与翻译语体的融合互渗。语体新变的背后,同步发生的更深变化,就在思维模式。
现在看来多少有些惋惜的是,进入20世纪后半叶,受制于多方面的客观因素,翻译实践一度大规模收缩进了大中专院校的外语教学体制,而后者的重心,又越来越严重地偏离了文学艺术、倾向了语言实用。直到近二三十年,趋势才渐有放缓。经年累积之下,优秀文学翻译人的涌现已蔚为大观。如今,在“走出去”战略的号角频频催动文艺事业实现益趋纵深的国际化发展的新形势下,具备中外语言文学学科群的外语大学,更应根据自身优势,在改革、创新文学翻译人才培养模式,探求促进翻译技能的教育与整个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人才培养的深层次融合等方面,多做积极尝试。积极参与探索和践行国家文艺事业新一轮大发展战略的具体路径。以此,为培育和发展服务于文艺“走出去”和“走进去”的文艺评论国际化,贡献应尽的力量。
曹卫东: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校长、教授
(责任编辑:杨静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