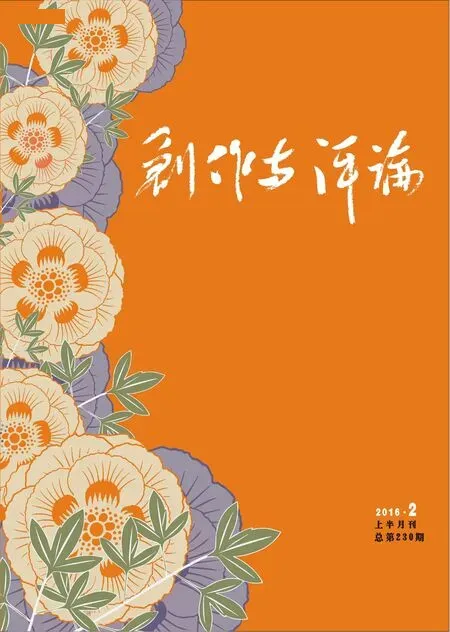水边
2016-11-22姜贻斌
○姜贻斌
○姜贻斌
晨雾尚未来得及散去,我独自站在氵舞水边,隔水往对岸望去。氵舞水那边,山脉一起一伏,酷似男人弓形的背脊,这些背脊居然一弯连着一弯,一不见头,二不见脚,像有一种男人的羞赧。偌多的背脊,就是那样默默而坚韧地弓曲着,像把天地撑开的拱顶。至于许多背脊的铜鼓色,自然是看不到了,全被青翠的绿叶所覆盖。茂密的树林,婀娜地靠在那些背脊上,像披发的女人在撒娇,并且,发出喋喋的外人不懂的细语。她们撒娇的缘由,是因了男人那坚韧而结实的背脊。就猛然觉得,天地间阳刚与阴柔的搭配,竟然是如此之美妙。
还有农舍。它们错落在山脚下,像黑白相间的眼睛,在羡慕地仰望着那些男人的背脊,以及女人的撒娇。它们没有发出任何响动,像懂事的孩子,似乎生怕惊动了他们的美事,却希望他们相拥着款款地回到农舍,这样能够多一点含蓄跟闹热,少一点张扬跟炫耀,同时,也能够让它们的空间生动跟充实起来。然后呢,再让它们的屋顶闪出炊烟的气味。没有鸡鸣,也没有狗叫,它们似乎也跟农舍一样,担心惊动了他们,把声音憋在细小的喉咙里,眼睛呢,一眨不眨地望着同一个目标。
还有氵舞水。它像一条新娘的宽大的腰带,深蓝色地无声地流淌在大地上,似乎在诱惑那些新娘,让她们自己从男人们的背脊上慵懒地下来,然后,走到氵舞水边,把它捡起来,红着脸色,系在自己的腰间。也好像呢,叫那些男人兴奋地跑下来,双手捧起这条腰带,深情地扎在新娘的腰子上。却总也不见他们下来,男人没有来捡,女人也没有来捡,他们似乎都已沉浸在甜蜜的境界中,忘记了这桩喜事所必需的饰物。所以,腰带也许在生着闷气,嘴里老是在说,你们再不来,我就要走了嘞。那一荡一荡的水花,就是它生气的语言。它真的在走,看到他们都不下来,就显得有点孤独地往下游飘去。其实,它可能还不知道,自己是一条多么长的腰带,你飘走了多少,还有多少,真的是无穷无尽。所以,那些男人跟女人并不性急,悠闲得很,贴得更加紧密了——这条深蓝色的腰带,终归是要系在新娘身上的。
还有晨雾。它像一幅巨大的白色纱幔,轻轻扬扬地飘逸在天地之间,这让那些男人的背脊跟撒娇的女人,显得朦朦胧胧,这样一来,就多出了一些韵味跟想象,多出了一些含蓄跟回味,已经看不出了张扬跟炫耀。所以,看起来晨雾是在自然地舞蹈,展示着柔软的腰肢,其实,它还有另一重任务,似乎在有意地为他们掩饰,所以,是他们最好的天然的帐幔。也所以,它有些看不起那些黑白相间的农舍,你一个狭窄的空间,也能够装得下他们炽烈的情感么?他们在你那里能够尽情地浪漫么?有我这幅偌大的帐幔在此,他们就能够尽情地展示自己的力量跟温柔了,就能够无所顾忌地唱一曲人间好戏。这帐幔般的晨雾,也是可爱得很,天真得很,似乎在跟农舍抢夺着他们充满爱意的空间。
氵舞水边,一幅淡淡的水墨画。
姜贻斌,当过知青,矿工,教师,编辑。著有长篇小说《左邻右舍》《酒歌》《火鲤鱼》,小说集《女人不回头》《窑祭》《追星家族》《肇事者》《最高奖赏》等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