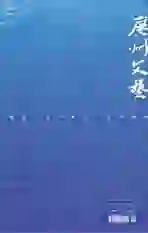陈崇正:恐惧的对面站着麻木
2016-11-21苏沙丽陈崇正马亿李敏锐宋雯唐诗
苏沙丽 陈崇正 马亿 李敏锐 宋雯 唐诗人 赵斌 李兰 崔迪
苏沙丽:对于陈崇正小说的接触,开始于手头上这两本书,《半步村叙事》和《我的恐惧是一只黑鸟》,我很容易就被他笔下的世界所吸引,因为这里面有我熟悉的、感兴趣的乡土世界。近几年一直在做有关乡土文学的研究,基于中国的乡土现实,还有对这一现实的表现力,乡土文学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当中国的现代性进程越来越深入乡土中国时,更具体地说,城市化及城镇化成为我们的社会现实和社会结构时,乡土书写也在发生或隐或显的变化。简单地从个体的乡土经验、作家所汲取的乡土资源、在乡土之上赋予的文学精神来看,在鲁迅、沈从文的乡土书写中,我们看到有浓郁的地域特色,作者在鲁镇、湘西边地寄予了文化理想,或批判,或建构。到了莫言、阎连科、刘震云这一批作家,他们是现代主义文学实验的践行者,亦有着对传统乡土书写的反叛精神,他们有高密东北乡、耙耧山脉、延津,但是我们无法从中感知到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是对乡土基于人之境遇的考察,如后现代时空里人终归无处归乡的问题、灵魂之乡的问题等等。而到70后、80后这两代作家,乡土可以说只是一个稀薄的背景,只是一段清淡如水的回忆,是之于小说中主人公的故乡意味,如徐则臣、盛可以的小说。在这里没有宏大叙事,更没有心绪理想的托寄。但是,来自乡土的文学资源就此完结了吗?在陈崇正的小说里,一方面,我们可以感知到他的乡土叙事已经难以在前辈的作品中找到相识的影子,乡土同样是衍化为背景而存在;另一方面,又可以看到,小说中的人事仍然有着乡土的影子,我们的精神信仰里、意识空间里仍然抹不掉乡土的因子。也是基于这样的阅读体验,我更愿意来谈谈80后的乡土书写,还有弥散在写作背景的、我们每个人精神空间里的乡土意识。
接下来,就请各位来谈谈阅读陈崇正小说的感受吧。
一、“半步村”的虚构与现实
宋雯:陈崇正小说中有比较明显的地域色彩,比方说,神秘气息。《半步村叙事》中的故事大多从一开始,就弥漫在一股神秘的氛围中。他在故事开头就丢给读者一个很大的“悬念”,这个“悬念”往往与死亡、暴力、罪恶或灾难相关,这样的“悬念”对于读者来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大概陈崇正爱看悬疑类电影,也许这类电影正是他创作灵感的来源。此外,他的故事通常充斥着“符咒”“拜佛”“预兆”“阴阳眼”“分身术”等具有浓厚鬼神信仰的物象,使得他的作品总是透着一股巫气,这或许与作者成长的地域环境相关。陈崇正的故乡潮州正是岭南地区鬼神信仰最盛的地区,文化心理不可避免打上了该地的印记。小说里还有较强的男性中心意识,《半步村叙事》中反复出现的观念就是“重男轻女”,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半步村的村民为了“生男孩”想尽了一切办法,把男孩当作宝,把女孩当作草。这里面的女性形象也大多缺乏鲜明的主体意识,要么是乐于奉献,充当“圣母”,如陈小路、向娟娟、苗姑姑;要么被“欲望化”,如孙保尔的众多女友;要么是精神、心理有问题的疯子,如钱书琴、阿敏。这体现了作者的男权思想和较强的男性中心意识,或许也与潮汕地区“重男轻女”的传统有着很大关系。此外,还可以看到陈崇正小说中有一种“大侠情结”。《半步村叙事》的时代背景以当下为主,最远也不过“文革”,可里面的很多故事和人物让我们联想到武侠小说和警匪片中血雨腥风的“江湖”“黑道”“大侠”“黑帮老大”,再加上描写细致的武打动作、武侠味道浓厚的人物语言,可以看出他骨子里浓厚的“大侠情结”。我想这跟他自幼就喜爱金庸有关,是金庸小说中的武侠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写作。
苏沙丽:宋雯的博士论文是探讨童年经验与作家的创作问题,在对陈崇正小说的阅读中,以专业的眼光看到了一个人从小耳濡目染的风俗习惯、集体无意识对创作的影响。
赵斌:我的硕士论文关注的是乡村权力叙事,我觉得现当代文学都离不开乡土文学的范畴。谈到乡土文学的创作都要追寻到经典,也就是鲁迅那里,乡土文学发展下来,其实有三个方向:一个是像鲁迅那样的思想性的建构,一个是像沈从文那样的理想自由主义的建构,还有就是像赵树理那样的基于乡村现实的叙事。其实我感觉乡土小说的写作是越来越成熟了,尤其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脱离了意识形态的钳制,回归到乡村现实,或者是之于文化的意味。当我读到《我的恐惧是一只黑鸟》时,感觉小说与作者之间有一种不相称,也就是说,作品写得比较老到。也感觉到这是处在一个现代、后现代的时空,这样一个过渡性的时空,作者很想把所有的资源融入到一起,来建构自己的叙事。我在想,陈崇正是不是受到了昆德拉存在主义叙事的影响。我们看待乡土文学时,要注意一个问题,也就是不能把乡村想象得太好太简单了,《我的恐惧是一只黑鸟》里就有这样一种复杂性,甚至在一些语句里就能感觉到农村生存的复杂性。再说到傻正这个人物,感觉不像阿Q,也有研究者说像狂人,也是有道理的,我觉得有点像贾平凹《秦腔》里的引生,有一种神秘主义,人物有一种通灵感,还有一种智慧。从情节到人物是晚清到“五四”的一个重要过渡,晚清阶段就是注重情节,“五四”虽然出现了人的觉醒,但是对人物的书写,要写到人心的复杂性是很难的。我感觉陈崇正是塑造得比较好的,而且会写得更好。因为从一些细节就可以看得出来,也处理得很好,例如,死亡叙事、暴力细节等等。陈崇正的小说里还有历史化的叙事,包括“文革”叙事。如若从后现代叙事来看,这些历史事件都只是作为背景的碎片化存在;如若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又是没有过多的细节与史实,不像是贾平凹作品中的乡土叙事。
宋雯:我比较欣赏陈崇正的一点是,这些乡村的历史事件、秘史,都是作为背景融入到创作里面的,有现实的影子,不像另外一些80后作家只是凭空虚构。
苏沙丽:刚才赵斌、宋雯讲到乡土叙事的问题,有关乡土的历史事件怎样融入到写作当中,其实,我一直想做这样一个探讨,我们所处的乡土日渐破败的社会背景,还有作家自身的乡土经验,之于一个作家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陈崇正小说中的乡土是作为一种背景来处理的,像“文革”“非典”等事件,也都是作为碎片化的背景来融解在作品当中,点到为止,而不是像贾平凹、莫言那样将乡土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哪怕贾平凹的《秦腔》是日常生活的碎片化叙事,但不妨碍我们对乡土有一种整体的认知,他们对“文革”、对暴力、对当前的乡村状况都有整体的思考。那么,我很想问陈崇正一个问题,像你这样一种乡土叙事是之于一个作家没有完整的乡土经验的缘故,还是之于一种叙事的缘故?
陈崇正:在我的第二本书《我的恐惧是一只鸟》设计出版的时候,有一个小插曲:校对样稿的时候发现多设计了一个扉页。然后编辑说,要不要在这里写上一句献给谁的话。我想写的是:献给没有故乡的人。但这一页最后还是被拿掉了。也是从这以后,我开始思考,从写作的精神地理的层面上看,我是一个有故乡的人。我从上高中开始走出那个小村落以后,再回去也只是很零散地了解一下乡村的情况,邻里之间建立的熟悉世界已然变得陌生;许多乡间的小路小巷子不再走了,很多人也不认识了。我能够获得的有关故乡的消息也越来越少了。我也常常反思,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我再来写现实中那个真正的村庄,写出来也是没有根的。一个写作者想在没有根的故乡背景下写作,不妨换一种叙事策略,村庄当然可以是凌空的,它跟地面不是紧贴着的,而是凌空三尺飞在空中的,这样一个村庄有我故乡的投射,但它更是当下许多村庄的综合体。结合我所看到的许多乡村,甚至包括我现在居住的城中村的现状,有时候我觉得我所书写的村庄更像是城中村,或者离城市不太远的村庄。它有自己的文化个性,也被种种社会现状牵扯着,比如,拆迁、拐卖儿童、校园暴力等等,这些社会事件都投射进来。这样我们也很难再找到像沈从文所写的乡土世界。
苏沙丽:我想,不仅是我们当下的乡土文学中,难以再见到如沈从文一样田园牧歌似的书写,事实上,即使你去到湘西或许也难找到沈从文乡土世界的影子,终归乡土文学是作家的一种思想投射,精神还乡。
陈崇正:在一次新书发布会上,我也讲到过“半步村”的由来,它其实就是取一个谐音“半不存”,意指乡村伦理和文化脉搏半生不死的状态。比如,我在《碧河往事》中就提到这样一个背景:“文革”的记忆,乡村的败落。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是:物理时间的“文革”已经结束,但精神遗留的“文革”还在影响着,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城市的广场舞,也体现在我们当下的乡绅阶层已经全部没有了。现在掌握着乡村命运的是一些暴发户、恶势力,很多莫测的力量,他们主宰着土地的买卖,主宰着很多人伦的走向,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些事,这些对乡村的侵蚀,是从根部开始的,是对伦理之根的切断。一方面是这种侵蚀在影响着乡村的走向,另一方面是由于人们的迁徙,比如很多读书的人也就不再回去了,空巢,乡村只剩一个壳。我所描述的乡村江湖,不是骇人听闻的,它是有现实依据的。我们现在的村庄与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边城”大不一样了,我们也很难再找寻到田园牧歌似的村庄,也难以再像鲁迅、沈从文那样来书写乡村,毕竟对作家来讲,有一种书写的责任。它选择歌颂,或者实录、批判,甚至抹黑来看取乡村,也就必然意味着另外的途径已经关闭。其实,我们当下的乡村都有着后现代性,有些荒诞的色彩,我们所经历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乡村其实已经截然不同了。单靠一个村庄是不足以支撑乡村的写作,它一定要腾空而起,离地三尺,不把它抽象起来,也是不足以去看待当下的乡村。
宋雯:其实我感觉莫言所写的乡土,与沈从文笔下的乡土又有了不同。莫言是将天南地北的东西融入到一起,我觉得陈崇正跟他所写的乡土还是有些相通之处。
苏沙丽:对,莫言有过一个观点就是“超越故乡”,从叙事资源来讲,“超越故乡的能力也就是同化生活的能力”,以想象力来充实可以作为叙事的经验,叙事的对象也就不再局限于一个有实在地理位置的地方,飞升的想象替代了实有的经历和体验,“村庄”仿佛只是沦为作家们生发想象的背景空间;而从情感态度上来说,“超越”也就意味着作家不再带着一种特殊的情感方式来写作,即将乡土视为唯一的精神家园。每一代作家笔下乡村内蕴的变迁,其实也跟每一代作家之于乡土的情感及经验相关。像鲁迅,他在乡土之上寄寓的是启蒙变革思想;沈从文寄寓的是乌托邦的思想,他同样将对生命对人性重造的文学理想投射进来。而到了莫言、刘震云、阎连科这代人,他们经历乡村的动乱年代、自然灾害,也经受一种极不平等的城乡制度的桎梏,他们对乡土固然有很深的感情,但他们更能理性地去理解,去对待,他们在作品中呈现出来的姿态是有反讽的。再到当下,我们谈到陈崇正的乡土书写,“半步”是取半步存亡的意思,一种凌空的姿态,这同样表征着书写背后乡土的变迁、作家情感姿态的变迁。
唐诗人:也就是说,陈崇正所讲述的故事,不只是记忆,更是他所了解、理解的乡土现状。记忆或者现状,在组合润饰下,失去原貌后,呈现为一个个令人唏嘘的故事,成为我们窥视一个村庄甚至瞥见整个民族故乡沦陷的寓言。就像《夏雨斋》里,拆迁工程所拆毁的,不仅仅是那些有代表性的“物”,更是人的记忆和情感。也像《双线笔记》中的情和钱,被利欲腐蚀了的乡村,还有多少值得怀念?还有《冬雨楼》里的黑帮和官僚劣迹……在这个时代,官、商、匪等一切恶的力量都挤往乡土世界,不仅要掘毁残留在乡村里的古物和风水,更要捅灭乡村几千年建构起来的信仰和希望。陈崇正的“半步村”不是一个现实的村庄,而是作为一个寓言的村落。
二、恐惧及生命的隐秘
崔迪:我主要想谈谈《我的恐惧是一只黑鸟》这本小说集,《我的恐惧是一只黑鸟》《碧河往事》《绿锁记》《遇见陆小雪》四篇作品,表达了作者不同的恐惧感受,是关于死亡、历史、话语权、生存、爱无能。四个虚构的故事,串连起作者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的思索:过去、现在与未来,外部规约与内部伦理。乡土成为背景化的材料进入到文本,巨大的虚无感伴随而生。都市物质文明也无法掩盖的虚无感,在乡土中被彻底放大了,它成为所有恐惧的来源。在对比萧红和张爱玲这两个作家的时候,就有研究者说萧红的《小城三月》写得比较好的原因,就在于她所面对的乡土,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有包容性的世界。张爱玲为什么一直迷恋城市写城市,是因为乡村的虚无会吞噬掉她,城市的那些器物能够让她得到暂时性的满足。在陈崇正的作品中,不管是在城市还是乡村,他们都有两个共同的关键词:虚无、恐惧。
唐诗人:其实我更想说说关于“恐惧”的问题,因为这是精神问题,而所有题材性的考虑,若从文学审美角度考虑,最终都应该上升到精神层面去探究。对于恐惧,克尔恺郭尔在其专著中写道:“精神越少,恐惧也就越少。”他的意思是,人不能如同动物一般没有精神性的恐惧感。他认为“精神”是综合灵魂与肉体的“第三项”,表现为恐惧的精神,它沟通、干扰着人的灵魂与肉体,使它们的关系得以持存在一种有良知的身体感觉和灵魂视域之间。这一观念,即使从非宗教视角也可理解。没有丝毫恐惧感的人是不可想象的。而当我们将恐惧与一种精神联系起来时,我们所恐惧的对象会是一些值得恐惧的东西。比如对过去历史的铭记、对自我过失的羞愧与警觉、对未知事物的敬畏与爱护,以及对他人遭受苦难的不安与怜悯……这些都与作为精神内容的恐惧心理相关。陈崇正在小说序言里也提到:“活在恐惧当中,与恐惧共存,是我们真实的状态。”由此可见,陈崇正应该对恐惧有所思考。他的小说文本中,我比较喜欢的一篇是《碧河往事》。这篇小说主题有些含糊,或者说它有着好些解读的可能,比如老母亲的脾气和最后提供的墓碑名字,是有意识的还是精神错乱中无意识的行为?但不管如何,这里的老母亲都是有恐惧感、被罪感笼罩的人物形象。即使精神错乱,很大可能也是因为她一直纠结于过去的“罪”,她恐惧于自己的过去。这种“恐惧”,指向的是罪感,但又不是宗教式的,而是生命的、历史的罪感。有罪意识,意味着人物具有一颗敏感而审慎的良心。老母亲的形象,就是承担历史罪责的形象,她的恐惧,是内心中那颗沉重的灵魂在跳动。而我们对这一小说的恐惧体验,也是一种罪感体验。
赵 斌:我也来谈谈恐惧,这篇《我的恐惧是一只黑鸟》,故事情节十分简单,二叔死后,“我”用一具尸体替代二叔的尸体去火化,从而实现二叔土葬的愿望。但作者没有严格按照时间去组织故事,而是把几个零星的小事件按照主人公傻正的意识流动随意地放置在一起,并且,在小事件之间穿插介入一些哲理化语句或者其他隐喻性事件以打破故事的流畅性。如小说中写黑猫的情节就是例证,猫的故事与二叔的故事有关,但猫于故事本身也是一种隐喻。更为重要的是,小说的空间化是通过营造一种浓重的“恐惧”氛围完成的。黑格尔说,人要有现实客观存在,就必须有一个周围的世界,正如神像不能没有一座庙宇来安顿一样。意思是说,人需要一个生存的空间环境。显然,小说《我的恐惧是一只黑鸟》是一个没有生存环境的故事,或者说,在小说中,人物一直在寻找一个能够“诗意栖居”的地方。比如,二叔曾经把自己囚居在自我编织的“黑屋子”里,放逐在尼姑庵里,似乎都无法得到救赎,依然恐惧。傻正也一直在寻找,他在寻找什么呢?仅仅寻找二叔吗?显然不是。二叔不是傻正的人生理想,卢寡妇那里也不是傻正的藏身之所,二叔死后的黑屋子更不是,傻正的灵魂也是漂泊的,所以很恐惧。那么,另一个问题就出现了,人物为什么会恐惧?显然,人物的生存空间与人物是矛盾的。这是小说的高明之处,在波澜不惊之处影射了很多社会现实。火葬与二叔,二叔与尼姑庵,傻正与二牛子、卢寡妇等等都构成了很多矛盾关系。小说叙事隐晦,寓言性特别强。在小说中,二叔先“臭骂那群尼姑一顿……没过多久……和主持静安师太成为好朋友”。后来,他把墓地落实在长乐庵的后面。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想象的空间?是不是有很多交易呢?但最起码可以看到,二叔作为一种乡村精神在现代经济运行模式中的破败,无法坚守内心的理想。到这个时候,二叔恐怕不再恐惧,没有灵魂了,而让傻正更恐惧了。二牛子之死也充满着反讽,有荒诞意味,是不是情杀呢?作者给我们开了一个玩笑,却能够引起我们深深的反思。
唐诗人:在我看来,除了《碧河往事》,其他几篇对恐惧的思考都不够深入。比如与书同名的小说《我的恐惧是一只黑鸟》,小说中“我”的恐惧非常实在,“我”只不过是恐惧失去父亲、二叔之后如何生存,而对尸体和屠杀凌虐动物却并不存恐惧,这是生存性恐惧,甚至颠倒了该与不该恐惧的东西。而二叔的恐惧,是对死后会被世人如何处理的恐惧,非现世的恐惧。在这里,恐惧意味着人对未知世界的一种不可解的根本性恐慌,但小说对这个层面挖掘得不够力度。用“一只黑鸟”来比喻,其实就是一种惶惑感、困惑感。死亡的困惑缠着二叔的生命。他的生活是困惑、痛苦于可能无法按自己希望的方式死,因为恐惧,所以痛苦,但这正是一种灵魂内容,这可以是一种灵魂叙事。但小说花在这个方面的笔墨并不多,我猜这还是一种无意识的触及。而另外的那些篇幅,也谈到各种恐惧,但都很具体,还停留于对生存痛苦和人生困惑感的恐惧揭示。即使是隐喻性的对体制控制的恐惧,也并不令人惊异。而一些对不可名状事物的恐惧,比如睡觉时隔壁房间的女人可穿墙而滚过来跟小说主人公“同床”,这些都不过是奇异而已,并不恐惧。或者说,这些恐惧还不是精神性的恐惧,生理上的恐惧感要同精神性的恐惧结合起来,小说才能够深入人的内心世界,我认为这是文学真正该着力的层面。我很期待陈崇正对“恐惧”挖掘得更广、更深。
陈崇正:刚才唐诗人提到穿墙而过的女人,认为并非恐惧。我觉得这是在恐惧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理解还是有一些不同。这篇小说中人物对于一种奇异现实的理解仿佛非常正常,就如同小孩拿着炸弹当玩具,身处其中他自己是不知道恐惧为何物的。有一些恐惧感来自于浑然不觉,来自于若有若无的异化。我在序言里写道:恐惧的对面并非不恐惧而是站着麻木。或者说,麻木是恐惧的另外一种形式。
三、自我批判意识与小说文体的“实验”
李兰:作为同龄人,带着相似的成长记忆,还有来自同一个地域的乡土体验,我很好奇陈崇正会思考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以《我的恐惧是一只黑鸟》为例,文末一句“门锁被捅开了,但开锁的人一直站在门外,一声不响”,作者想要结束的不仅是小说文本,还有对二叔生命结束的确认,暗示着“我”精神与灵魂的重生,是二叔与“我”叔侄情意的升华,更是二叔之死对“我”心灵的触动——难过、悲伤,背后隐含着“我”深深的反思与自我救赎。我想知道,你在写这篇小说、这个人物时,心里在想些什么?
陈崇正:当时我是怎么想的已经忘记了,你提到的这个具体的情景,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人物的重要性、人物的觉醒。所谓把人物写活,不是字眼中意识到,而是实践中体验出来。人物的生存感觉对小说的重要性,让我意识到写人物不是简单地写人物,而是写人物的生存感。他内心弥漫的对生存的焦虑,如何活,如何死,这些问题的思索会直接让小说成立。我们说小说成立与否,很多时候不是故事让小说成立,而是人物本身所体现的生存经验让小说成立。你提到的这个情节,故事结束的地方,刚好是人物最难过、最莫测的地方。
李兰:我试着把自己代入你的小说来读,但到最后会觉得比较感伤,那个时候一定会有很多种情愫,像你所说的愧疚,包括对自我灵魂的追问。我发现对生活中的细节,都会有很多的反思,这种反思在你的作品中特别明显。
陈崇正:对于作家来说,可能都希望与人物有一种陪伴关系,他会陪伴人物一直走,思考生与死的东西,比如经历拐卖儿童的事件,进入故事里面作者和人物的边界就会变得模糊。人物会有作家生命的脉动,是带着作家的生命意识在历险的。这样的历险是带着属于作家自己的那部分忧伤进入到莫测的世界。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也都是过着一种莫测生活,有很多个自我共存于一个躯体之中,你不知道哪一个自我何时会占了上风,于是你会喜悦和愤怒,会悲伤和恐惧。在我的写作中,我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自我批判,自我批判意识是一个作家的发动机,是作家创作永恒的驱动力。写作对于我的意义,就是我身体中的A看着B,B看着C,他们彼此共存又互相批判。“哪个是真的我?”我相信很多人一定这样问过自己。所以我们会懊悔,会绝望,也会沾沾自喜。对于写作者而言,我们只有自己这样一个标本,我们不研究自己,不审判自己,不追问自己,就无法触及灵魂深邃的那一部分。
李兰:所以,我觉得你的作品为我看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
李敏锐:我看得比较松散,一下子说不出整体的感受,就说下阅读《半步村叙事》第一篇小说的看法。我也是写小说的,我很看重第一章,如果是作为普通读者,可能看到《检讨书》这一章就会翻过去,可能不会沉下心来看,你当初是怎么设想的呢?
陈崇正:我觉得这样写蛮好玩的,把《检讨书》放前面,其实跟后面的情节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李敏锐:以我自己的阅读和写作感觉来说,我觉得陈崇正的小说是中规中矩的,在趣味上还不够,如果趣味性更强一点,读者的受众面会更广。
宋雯: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我觉得《半步村叙事》越到后面,趣味性越强。我觉得这样写也有一种好处,开始并不太顺,前面运用一些先锋的写法,类似一种文体实验,读起来有点难度,反而给人一种陌生化的感觉。对于小说的深度而言,也有它的意义所在。
陈崇正:这个小说应该是从2007年开始写的,写了两三年,换了好几种写法。后来受到《我的名字叫红》的启发,每个人每个事物都站出来说话,想改一改,整个结构重新调整了一下。最后,我想这个小说为什么会写不好,它里面有时间线与叙事容量之间的矛盾,战线拉得太长,时间长达百年,也许需要二三十万字来写完,我居然妄想在几万字里面写完。这个小说的写作其实给了我一个探索的过程,虽是最不成熟的一篇,但体现了我写作的一个痕迹。改了很多次之后,还是有一些硬伤在里面,所以也在小说第一句给了自己一个“解脱”,强调这是一个虚构的村庄,独立于时间和历史之外。我在这篇小说中所投射的东西也影响了后面的写作基调,比如人物错综复杂的命运、多元的可能性、不同的视角,这样一种操练对我来说蛮重要。《半步村叙事》是对村庄的构型,《我的恐惧是一只黑鸟》是对人物的转折,包括后面的小说,我自己感觉也越来越成熟。
马亿:我不从纯理论的角度来说,而是从一个写作者的角度来谈,而且是谈一点缺点。看《半步村叙事》的第一篇小说,我就感觉陈崇正的文体意识特别强,分成了几个小节,从零开始叙述,语言的密度不是很强,我想陈崇正应该也能感觉到。之前谢有顺老师说过,小说是由两条线索组成的,一根经线,一根纬线,就是由情节和语言组成。我觉得第一篇小说相对于后面的小说来说,要弱一些,虽然把它放在第一篇,但明显感觉上下联结有点零散。说到语言,有的小说为什么读起来会觉着厚重,有的小说三十万字读起来像是百万字,而有的小说正好相反。在语言方面,《半步村叙事》的后面几篇有了很大的进步。对于中篇小说来说,虽然都是几万字的篇幅,但是每个几万字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平常写短篇小说,靠的是灵感,描摹某个生活画面;中篇小说是对生活的把握,包括将生活经验揉和到小说的技巧、小说的情节怎么组织。我觉得这一点还要多向陈崇正学习。
苏沙丽:刚刚大家都谈了陈崇正小说的两大主题:乡土与恐惧,我们可以感受到陈崇正小说的多重解读空间,无论是思想内蕴还是文本形式。这些小说建构了一个叫“半步村”的乡土世界,透视着人物内心的隐秘、生命生存之感。与此同时,也明显地感觉到陈崇正对小说这种文体的探索和尝试仍然行进在路上。正是基于这种丰富性和实验性,我们看到了一个作家蓬勃的成长力量。期待陈崇正今后写出越来越多的好作品!
责任编辑 梁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