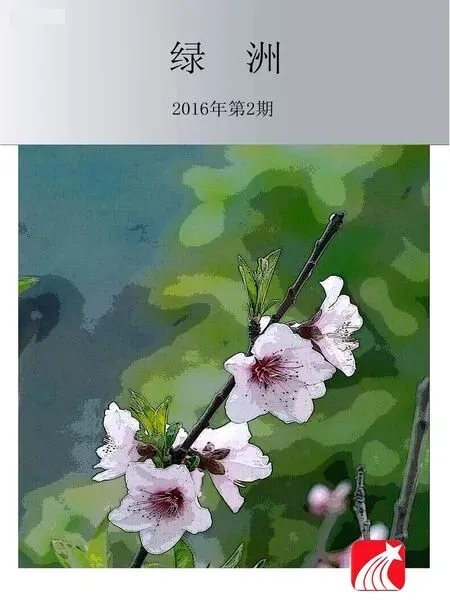在路上
2016-11-21王善让
王善让
在路上
王善让
被季节忽略的生命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季节的脚步。即便生命无比的坚硬,仍然无法逃脱季节的追赶,最后被季节无情地抛弃,就像秋风抛弃那些树叶,就像河流抛弃那些朴实的河岸。
我已经感觉到被季节抛弃的轨迹。正如现在的天气,昨天还是满树的绿叶,今天已经风中飘雪。那些看起来似乎很坚强的柳树,其实根本经不起一场寒夜。在雪花飘下来的时候,我看到那些泛黄的柳叶纷纷争抢着脱离枝条,比雪花早一些着地。纷纷扬扬,眼前似乎下着一场关于柳叶的雨。
或许再过几年,这个地方的柳树也要被抛弃。这个地方,已经抛弃了超过30年的一切东西,包括树木和建筑。当然,还留下一些已经在这个地方生活了30多年的人。但用不了多久,它也要抛弃他们。
离此不远的地方,有着几棵被季节忽略了的大榆树。它们明显已经超过30年,但仍然在矗立着,在大理石地面的广场边缘,在人工的绿篱间,就像绿色的雕像一样,被季节忽略了生命的存在。有人说那些榆树是“左公榆”,和原来四处可见如今也难寻觅的“左公柳”一样,都是当年左宗棠及其将士们亲手栽种的。如果是真的,那这些树木已经跨越了3个世纪,它们的记忆一定非常饱满。
我其实知道它们的历史,并没有传说中的那样长。因为我曾经接待过一批人,他们当中就有当年亲手栽种这些榆树的人。他们是1949年底进驻这片地方的解放军,叫六军十六师。而我见到的那一批人中,有一个姓田的老同志,是当年十六师红星剧社的指导员,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仍然清晰地记得这个地方原来的样子。其实,离别几十年之后,几乎所有的能唤醒记忆的建筑都不存在了,只有这些树。但他们说,当年他们种下这些树的时候,这片土地上并没有多少绿色。也就是说,这些树是他们种的,并不是左宗棠和将士们种的。这样算来,这些树也不过60多年的光景。边疆的树和人一样,常年的风沙磨砺着,就显得沧桑和老气。在内地很多地方,60多年的树仍然郁郁葱葱傲然挺立,而边疆的树看着好像已经经历了几个世纪。
那就不能不提胡杨。大漠胡杨是边疆的一道风景,是内地很多人都向往的美景。事实上,边疆地区有很多胡杨,由于地质、水源并不一样,它们的生长状况并不一样。
先说南疆的胡杨,因为南疆相对水源稍丰,所以很多胡杨长得挺拔高峻,完全可以当防风林。即便河流改道、水源枯竭,那些胡杨仍然站立得有模有样。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那些已经枯死的胡杨犹如战后的沙场,有着明显的悲壮。那些活着的胡杨,一到秋天呈现出金黄的叶片,用颜色滋润着南疆。无论活着的和死去的,给人的感觉无非是清爽和悲壮。
再说淖毛湖的胡杨,其实二十年前还不怎么出名,但如今已经被誉为世界三大胡杨林区之一,我并不明白世界上还有哪两大胡杨林区,很多人都不明白,就像我们常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却并不知道不孝究竟还有哪两个似的。淖毛湖的胡杨和南疆的胡杨截然不同,因为这片土地十分缺水,每年降水量只有30多毫米,却有4400毫米的蒸发量,从鲜活的肉体到干透的木乃伊可能用不了几天就可以完成。这种情况下,淖毛湖这片方圆200平方公里的胡杨林,是不是已经死去?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一到春夏季节,这片胡杨依然有着绿色的枝叶,只不过不像南疆的胡杨那样茂密和健康,而是显得非常不协调的一种生命体征,就像一段枯死的树干上,三天前被人插上一枝柳条,看起来有些绿色,但枝叶已经发蔫。所以说淖毛湖的胡杨与南疆的胡杨不一样,你说它死了吧,它还活着,你说它活着吧,它其实已经接近死亡。它的树干几乎没有一根是直的、光滑的、顺眼的,几百平方公里的胡杨,少说有上千万棵,但真的没有一棵是直的,没有一棵看上去让你爽心悦目的,都是还没有发育好就开始衰老的感觉。塔里木河畔的胡杨与之相比,简直就是都市里的摩登女郎。在这样的胡杨林里,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想哭,没有理由地伤感。
人们说胡杨有三千年的生命,活着一千年不死,死了一千年不倒,倒了一千年不朽。那其实是说南疆的胡杨。在淖毛湖,当地人说这里的胡杨有九千年的生命,活着三千年不死,死了三千年不倒,倒了三千年不朽。倒并不是真的活那么长,而是它们身上承载的沧桑和悲壮,已经跨越了我们平庸的经历和苍白的想像。
在边疆,胡杨就是被季节忽略的生命。所以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够看得到它,它们。
寻找干涸的河流
随着故乡渐渐远去,那些流淌在平原上的河流也渐渐远去。其实那些河流本身并没有多少知名度,充其量被算作淮河的支流。在中东部平原上,纵横交错的河流太多,很多根本就不知道名字,也没有想知道名字的欲望。所以,那些河流渐渐远离着身边,远离着记忆。正如忘却了擦肩而过的路人,本来就没有在意,又何谈错过呢?所以,从没有过的记忆渐渐淡去,没有伤感。
从十八九岁开始,我的生活便远离了河流。我的视野所及,都是茫茫的戈壁和常年积雪的山峰,甚至连草原都很少。在经历过短暂的新鲜之后,我觉得自己在戈壁中迷失了。有那么一阵子,逃出戈壁的愿望特别强烈,甚至觉得自己就是在炼狱,能够离开就是最完美地逃出戈壁。经过一段时间的折腾,自己筋疲力尽,不得不接受现实——所有的出路都已经被堵死,被时间堵死,被体制堵死,被现实堵死。于是不得不重新面对戈壁,面对那座叫做喀尔里克的雪山,面对那些能把最悲壮的事业演绎成革命乐观主义诗篇的朴实的兵团人。
在过去的二十年时间里,我一直不承认自己是新疆人。就像自己是来串门的,走亲戚的,度假的,旅游的,探险的,讨饭的,迟早是要回到故乡的。因为我的潜意识中,没有河流的地方,是缺乏文明传承的。人类文明是起源于河流的,不管那些文明是否已经像河流一样已经断流,河流却已经被载入历史。所以,我决心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走回故乡,走近那些被遗忘的河流,在岸边回忆我的西域时光。
一位首长刚到这片地方任职,问我这里有没有河流。我几乎不假思索就回答,没有。那个时候我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十二年,到了而立的年纪。这片土地虽然我并没有走遍,但有关这片土地风物地理的记载,我基本都浏览过。确实,没有河流。当然,如果坎儿井算得上河流的话,我收回自己的武断。
首长也是几乎不假思索,很不给面子地回了我一句:不可能!像这样一个有着历史传承的地方,不可能没有河流。首长说,你好好查查史料记载,这个地方一定曾经有过大河。
曾经有过?多少年前?亿万年前还是二十年前?我说的是眼前!
但我不敢跟首长顶嘴,尽管我的个性很强,很爱和人抬杠。因为那时我是他的秘书,而他来这里之前,已经是一个享誉西域的文化名人,即便不是我的首长,在他面前我也只能是无知的学生。所以,我很快找来一堆书,好好查一查,过去这个地方是否真的有一条河。
没有用几天时间,我就被自己查到的结果打了响亮的耳光。这个地方过去的确有一条河,而且是相当宽的一条河流。到现在,河中依然有水流——尽管就像坎儿井水一样细微,但它依然使用着过去的名字——白杨河。
据记载,这条河发源于东天山南麓的山谷,汉唐时期已经是很具规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唐朝曾在此地设郡县,屯良田,司稻黍,育牛羊。数万居民依河而居,五谷丰登,牛肥马壮,和谐富足。应该可以说,是这条河流养育了这片土地,承载了千年的文明。佛教盛行时期,这条河两岸建了很多庙宇,画了很多精美的壁画,至今还有残存。当年玄奘法师西行取经,高昌国王为了表示对东土大唐王朝的尊敬,派使者从吐鲁番赶路800里,在白杨河西岸迎接圣僧,唐僧不胜感激,指着桥下淙淙流水道:王之盛情,如河水之滔滔啊。
后来,东征的十字军曾一路打过来,与当地的伊斯兰武装展开了一次大战,战场就是白杨河上的一座大桥——布古尔大桥。本来战斗力就很差的十字军,结果在桥上遭到迎头痛击,很快大败,西行溃逃。如果不是这条河,十字军很有可能突破这西域襟喉,对中原造成威胁。
白杨河啊,原来你曾经孕育过滔天大浪,经历过世事沧桑。
我把结果告诉了首长,首长笑了笑,有人类文明的地方,一定会有河流,这是规律。
我佩服首长,能挥洒自如地把规律性的东西应用到生活中。而我,在这片土地生活了那么多年,只是察觉到土地表面没有河流,却没有思考过去的河流流向了哪里。
前段日子,我有机会去了一次南疆,在最近被评为“鬼城”的阿拉尔市,我见到了久仰大名的塔里木河。
我一直认为全世界只有脚下这片土地干旱缺水,因为没有河流。甚至我曾经在给上级的汇报材料中,擅自把这片土地定位为“全国唯一没有河流的地区”,并没有遭到反对和批判。新疆的河流,最著名的有额尔齐斯河、塔里木河、伊犁河等,但距离我脚下的土地都太远,几乎都在1000多公里之外。没见过这些河流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河流流经的地方,都是水草丰美的草原和庄稼、森林。最早见到的是额尔齐斯河,在北屯附近,河岸有很多白桦树,齐腰深的杂草,硕大的蚊子,狗鱼,乔尔泰,并没有江南水乡的感觉。每到夏天,都要用飞机沿着河流两岸打药,不然的话蚊子能把人咬死。所以对额尔齐斯河的印象就平淡极了。伊犁河没有去过,但并没有太多的奢望。对塔里木河,我的意识中一直是宽阔、水深、多弯,养育了整个南疆。
那天朋友开车带我去另一个垦区,路过一座桥,我还以为是一条普通的河,结果朋友说这就是塔里木河。
我真的无法接受,这就是塔里木河?是的,桥修的很长,有一两公里的样子,河床很宽,和岸上的戈壁一样。可是,水呢?河里的水呢?
河道的中间,只有很窄的一条水道,水很浅,远远地就看到水底的泥沙。这就是那个养育着南疆的塔里木河吗?我真的不敢相信。
从南疆返回,我变得沉默了。原来,并不是只有脚下这片土地没有河流,边疆的很多地方,都没有河流,没有一条能承载奢华梦想的河流。但是,正是这条随时都可能断流的河,却给了土地上的生命一丝希望。
其实,我何尝不是这样。在这片土地上,我就是一棵经常喝不到水的胡杨。我的心里渴望河流,但我的根一直在努力深扎。我知道,河流已经干涸,我必须用根须找到最近的水源。因为根扎得太深,我已经无法离去。
我的团长
和田有一位我的老团长,我一直想找机会去看看他。
但是我知道,他有可能最近一两年退休,因为平时并没有联系,甚至我连他的手机号码都没有保存,所以并不确定是否还在和田工作。也许已经退居二线,返回乌鲁木齐定居了。我找忠胜核实了消息,果然已经退居二线了。
我的那位首长是我到新疆第二年认识的,我在他担任团长的那个团里当开荒工人,经历了一年多的苦难悲欢之后,在我对前途感到几近绝望计划离开新疆的时候,是他给了我一个希望。我常常在心里说,大恩不言谢,心里一定要记着这份恩情。其实当初到新疆来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性,从来也没有想过自己的未来会跟新疆产生联系。所以当自己在这里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之后,决定离开。
那是一个早春,新疆的春天田野里是没有绿色和鲜花的。我从一个盲流、开荒工人,被连队赏识聘为文教,好不容易有了生活来源,但又因为写东西得罪了领导,把我的饭碗给打破了。这个时候,我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继续留在这里,种地,但我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我担心辛苦劳作一年之后,自己不仅没有收入,还有可能倒欠连队的土地费;另一条路就是离开,要么回家,要么去沿海地区打工。回家我是不会选择的,因为没有脸面进家门。那只有去沿海打工了,但我其实并不知道打工是干什么的,而且对沿海城市一无所知。一位朋友告诉我,像我这样的人在沿海打工不仅能挣钱,而且还有很多发展的机会。所以我决定,等天气稍稍暖和些的时候,到沿海城市去看看——也许不是看看,而是和新疆告别了。
因为没有了生活来源,我的生存状态处于最低谷,距离连队生活水平最差的农工张老五还有很大一段距离。张老五是种地的,每年都亏损,不仅没有收入,倒欠连队很多承包费和生产资料费用。可是兵团的团场是不允许饿死人的,何况张老五是正儿八经的团场职工,所以尽管账面上是负数,每个月一袋面粉两斤清油是有保证的,就好像如今的最低生活保障一样。也就是说,虽然张老五手里没有钱,但吃饭不成问题。但我的吃饭已经成了很大的问题,因为我还不是团场的正式职工,我没有资格到连队、团部去要粮要油,我更没有脸向家人写信要钱。所以我活得很艰难,基本上靠那些微不足道的稿费维持生计,当地的报纸电台稿酬很低,发一篇稿件只有一两块钱的稿费,省级报刊的稿费稍高一些,但都是几个月以后才能收到,所以那阵子生存压力特别大。我已经连续三天靠喝面糊糊维持生命了。
那天,我提着一个尿素袋子到林带里捡柴火——就算每天喝糊糊也需要柴火烧熟啊。我已经记不起当时的状态怎么样,但可以想象一个年轻人喝了三天糊糊之后还能走着捡柴火,那种状态一定好不到哪儿去。林带里本来就很僻静,何况我又是特别爱面子的人,捡柴火一定要到远离居民区、远离人群的地方。就在我有气无力地捡着柴禾的时候,不经意抬头看到林带的另一头有一辆自行车驶了过来。由于公路是戈壁滩上的石子垫成的,并没有铺柏油,骑自行车比较费力,不少人都喜欢从林带中骑行,所以有自行车驶来属于非常正常的现象。我继续弯下身子捡柴火。没想到的是,那辆自行车到我跟前停下了。我记得那是一辆26型的女式自行车,看上去比较新,但骑车的是一个男的,三四十岁的样子,个头不高,但眼睛很有神,感觉不像我所在连队的干部,更不像是职工。他把自行车停好,给我打了个招呼。虽然我对他点了点头,但内心仍然不免保持一种警惕,这人是干嘛的?要干什么?
你就是那个王善让吧。来人说着我的名字,我感到很惊呀。我不认识他呀,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呢?
我是李××。
李××?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熟悉?哦,想起来了,是我在的这个团场的团长!
原来是团长,怪不得感觉气势上有些压人,比我们连长指导员有威严。只是我还是不明白,那么大的团长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全团上万口子人几万亩地都归他管,还有闲工夫找我聊天?难道要抓我?我好像也没犯过什么错误啊,是的,我偷过几次连队菜地里的菜,摘过职工地里的哈密瓜,拿过连队食堂的几个馒头,可这也犯不着团长亲自来抓我吧,连长指导员都行,团里不还有派出所、警察嘛。
是这样,团里刚刚开了一个会,研究决定,把你调到团部机关工作,具体工作是给我当秘书,事先没有征求你的意见,不知道你有啥想法。去连部找你,你们连长说不知道你在哪儿,碰巧有人说看到你到这个林带来了,我就过来找你。李团长平静地告诉我,就像我们是一起工作了好多年的同事一样。
我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
团长说那好吧,明天早晨到我办公室报到。说完,他骑着那辆女式自行车走了,我傻傻地站在林带里,感觉在做梦。
当天中午,我把剩余的面粉全和成面团,烙了一张葱油饼,那个味道至今还在我的嗅觉中萦绕。吃饱真的很幸福。
第二天,我到团部报到,团长在他对面给我摆了一张桌子,给了我一把办公室的钥匙,并告诉我已经安排后勤让我在机关食堂一日三餐。我正式成为团长的秘书。
没有文凭,没有靠山,没有阅历,只有一腔热血,有一个个破灭之后重新产生的梦想。在戈壁之上,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种成长的温暖。
那一年,我十九岁。
擦肩而过的痛
在阿拉尔,我默默地想,如果当初我来了,会是什么样子。
那一年,我的一位老领导被调到阿拉尔工作。走之前,他曾问我,去不去南疆。我犹豫了很久,最终没有答应。当时工作上的事儿折磨得我已经觉得疲惫不堪,好不容易换了个环境,我不想再动了。再说我已经在这个地方生活了十多年,刚刚适应这里的气候、饮食和民俗、文化,觉得再到一个新地方,可能根本无法适应。我是在新疆生活了十多年之后才开始适应新疆的拉条子拌面、烤肉、大盘鸡这些东西的,此前的十多年里我不喜欢吃这些食物,因为吃了很难消化。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固执地认为羊肉烩面、胡辣汤、烧饼才是一生都吃不够的东西。当我悄悄地接受了拉条子、过油肉拌面之后,突然感觉羊肉烩面和胡辣汤于我竟是那样陌生,里面的味道好像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内心开始有一种抵触。
但在我的情感深处,却一直觉得对老领导有一种歉疚。当秘书的,一般都会随着领导的变动而变动,因为长期的工作关系已经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状态。而像他们这样的职业官员,只要不犯错误,年龄上保持优势,应该是有再上层楼的可能,到那时,秘书当然也能有更广阔的前途和舞台。但我却显得那样不随和,拒绝了领导的好意。我已经跟他相处8年了,虽然工作上很愉快,但围绕领导们之间的各种斗争却让我看得心烦,处的很累,有时候觉得自己就在一种危险的漩涡当中,显得无助和可怜。
当然,权力斗争的中心跟我无关,我只是一枚小卒,即便过了河也只能一步一步本分地走自己的路。但是我接触到的人却都是有着车、马、炮的能力,他们可以不走寻常路,而且如果我这个小卒有碍路的嫌疑时,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吃掉我。很多时候,我工作是为了谋生,不是为了哪一个人,也不是为了要站在哪一边。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我才侥幸躲过了一次次的危机,我才能够平静地伺候了了三届班子。因为每个人都能够看得出来,我不属于哪一个人的人,也不属于任何一边的人,我就是一个单位里的人,我的眼里除了工作,就是老婆孩子,我的任务就是让她们生活的安逸、幸福。
所以,我拒绝了老领导的好意,没有去阿拉尔。而且老领导在阿拉尔工作的近3年时间里,我也没有去阿拉尔看看。也许有人说我这个人不懂得人情世故,甚至骂我不懂感恩。我毕竟只是一个地位卑微、胆小怕事、老实本分的工作人员,我的眼光看不远也没有必要看得太远,我只希望自己的一生能平静安详地度过。
记得有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去办公室取一份资料,因为是休息时间,穿的比较随意,体恤衫、运动裤。我的办公室在一家酒店的七楼,当我拿到资料乘坐电梯下到一楼大厅,电梯门打开的瞬间,我看到我的这位老领导站在对面。陪着他的有一大群人,都是我的上司。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也不知道老领导是怎么想的,反正我们就稀里糊涂地拥抱在一起了。老领导当时还在阿拉尔工作,到这儿是带团考察,已经来了两天,今晚就要乘火车返回。随后他一直搂着我的肩膀,我也一直陪着把他送上当晚返程的列车。列车开动之后,看着车窗内招手的老领导,我的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之后我在想,也许我和老领导之间不仅仅是纯粹的工作关系,8年的相处,人与人之间已经融入了一种亲情,兄弟情,父子情,朋友情。当时我想,也许没有去阿拉尔是一种错误的选择。但无论如何,我一定想办法创造机会去阿拉尔看看,看看阿拉尔这座城市,看看我的老领导。
还没有等到我去阿拉尔,老领导就调到乌鲁木齐工作了。我想这下子就方便多了,每年去乌鲁木齐出差开会很多次,可以随时去看望老领导了。也许是太方便了,所以没有当回事儿,每次没有去看成老领导都会自我安慰说,反正过两天就来了,还有机会。这样又拖了一年多。
有一次和单位同事聊天,有人说某某领导去世了。我一愣,不会这么巧吧,还有重名的领导。再次核实,证实去世的确实是我的老领导。他是病逝在岗位上的,距离退休还有将近三年的时间。
回到家里,我失声痛哭。
阿拉尔,我一定要来,我要看一看老领导曾经工作的地方,看一看他走过的路,看一看他书写的风景。
走近“鬼城”阿拉尔
其实,关于最新的“鬼城”报道,阿拉尔被列在全国第二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阿拉尔是一座非常年轻的城市,和同被列为“鬼城”的北屯市一样,她们不过在共和国的行政区划图上才出现十几年时间,甚至可以说是在戈壁荒滩上直接建起的一座城市。最为关键的是,她们都是属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管理的城市,她们的存在,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巩固西北边防、增进民族团结、加快边疆发展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到过新疆的人大都会知道,新疆有座被称为戈壁花园的绿洲城市——石河子市。但知道石河子市怎么建成的就不多了。石河子市也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城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新疆兵团在那片亘古荒原上开荒造田、建设家园,60多年过去了,石河子从一片荒原成长为一座现代化城市,曾被联合国授予“联合国人居环境改善良好范例城市”。如果当时评“鬼城”,石河子绝对是当之无愧的,而且很有可能拿到头筹。因为当时的石河子大都是转业军人,在市区居住的充其量不过几千人,而现在仍然在使用的马路、规划,据说都是当年的军垦人自行设计规划的。60年前的一处不起眼的荒原,如今已是“戈壁明珠”,还有一所“211”大学——石河子大学。谁能否认,再过60年,阿拉尔会成为南疆的石河子呢?
阿拉尔的建设,超出我的想象。因为在我心中,石河子、阿拉尔这些军垦城市都是一直向往的地方。作为一个兵团人,我一直为兵团在新疆创造的一个又一个奇迹感到自豪和自信。对于阿拉尔,我已经慕名多年。阿拉尔市的缔造者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而第一师的前身,就是赫赫有名的三五九旅,王震将军的老部队。提及三五九旅,大家不由自主会想到南泥湾,嘴里会哼起那首耳熟能详的曲子。我总是在想,历史难道会真的有那么多的巧合吗?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名声鹊起,就有了后来的将军率领部队进疆屯垦戍边的续篇,这究竟是无心插柳还是有意而为,至少目前我不太清楚。从民间的传言来看,应该是纯属偶合。据说王震领导的这支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兵团,是要留在首都担任党中央、毛主席的卫戍部队的。这一点并不是空穴来风。一兵团有两个军,一个是二军,一个是六军,二军的根子是三五九旅,王震的老部队,六军的前身是中央教导旅。王震的老部队南征北战大捷无数,那是有目共睹的,可是有几个人了解中央教导旅是干什么的?其实,这支部队就是延安时期的中央卫戍部队。当年胡宗南进攻延安,而当时延安并没有多少兵力,承担保卫延安任务的主力,就有中央教导旅,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奠定了保卫延安战役的胜利基础。后来部队整编,把王震的部队和中央教导旅整编为一兵团,能扛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旗帜的部队,一定是党中央、毛主席绝对信任的部队,承担中央卫戍部队的责任也是责无旁贷。但历史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解放西安、攻克兰州、平定河西、凯歌进疆,王震率领着十万大军一路向西,再也没有回头。
南疆的城市,如阿克苏、喀什、和田都是围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建成的,那么阿拉尔是从阿克苏向东南方向深入了120公里,也就是说,阿拉尔更亲近了塔克拉玛干沙漠。新疆的三山夹两盆地形,除了气候相差太多之外,两盆的地貌还真有些相似。比如南疆的塔里木盆地的中心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国第一大沙漠,世界流动沙漠中排名第二,面积33万平方公里,是内地两个省的面积,绿洲只能沿着沙漠边缘设置。而北疆的准噶尔盆地腹地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国第二大沙漠,垦区也是围绕沙漠周边布置。也就是说,石河子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绿洲,阿拉尔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绿洲。
从上世纪50年代部队屯垦阿拉尔以后,经广大军垦战士披荆斩棘,艰苦创业,在沙漠边缘开垦良田120万余亩,兴建了10个农牧团场,创造了人进沙退、人造绿洲的旷世奇迹。上世纪60年代初,王震就提出了“北有石河子,南有阿拉尔,两颗明珠交相辉映”的兵团城市建设的战略构想,可惜由于时势变幻,这一构想一直未能实现。二十世纪末,中央决定加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力量,探索新的屯垦戍边形式,在天山南北兵团垦区条件成熟的地方设市。2002年,国务院批准阿拉尔设市,2004年正式挂牌成立阿拉尔市。随后,图木舒克市、五家渠市、北屯市、铁门关市、双河市、可克达拉市相继挂牌成立,她们这些共和国最年轻的城市,如同上天撒下的瑰宝,点缀在天山南北,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十万大军出天山,且守边关且屯田。塞上风光无限好,何须争入玉门关。”这是何等的豪迈与自信!正是有这样的决心,阿拉尔才有了今天的模样。看看吧,看看被微信称作全国排名第二的“鬼城”吧,亘古荒原上耸立起一幢幢高楼,超市商场、学校医院、政府机关、文化场馆、科研院校、居民小区、人工湖泊、宽阔马路、法国梧桐、挺拔胡杨、鲜花盛开、文明时尚,和石河子一样,这座军垦新城也有一座大学——塔里木大学,早于这座城市半个世纪就建成了,面向全国招生,在校生两万多人。这就是兵团城市的特色,城市是文明的集中体现,也是文明传播的重要平台。
漫步街头,我感到这是当年的三五九旅60多年后呈现给世界的一份厚重的礼物。如果说南泥湾成为那段特殊时期留给全国人民的一个记忆符号,那么阿拉尔,这座瀚海中的灯塔,将是三五九旅用魂魄在南疆大地树立的永恒丰碑!
责任编辑王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