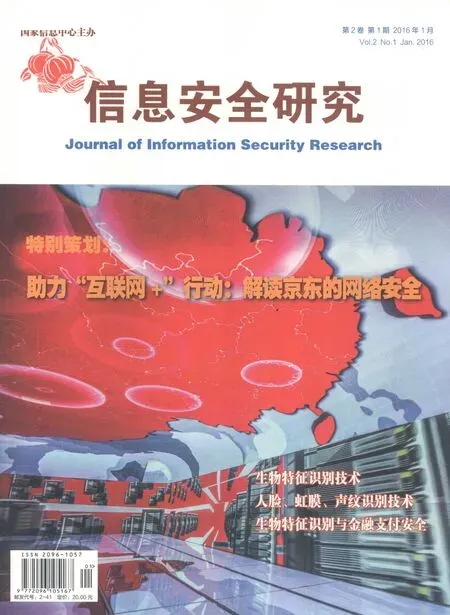全球互联网治理的中国速度和力量
2016-11-18杜雁芸
□ 杜雁芸
全球互联网治理的中国速度和力量
□ 杜雁芸
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及其引领下的全球化浪潮,推动着人类社会迈向网络时代的崭新阶段。随着网络空间重要性不断提升和人类对网络空间的依赖性逐渐增强,互联网发展对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出新的挑战。如何妥善处理来自网络空间这一新兴疆域呈几何级数增长的安全威胁,如何有效化解网络大国间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结构性矛盾”,网络空间治理已成为全球治理领域日益凸显的新议题,这迫切需要国际社会认真应对、谋求共治、实现共赢。中国是世界网络大国,还兼具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大国的双重身份,在推进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通过强化自身网络实力提升全球治理发言权
当前,全球网络空间仍处于“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尚待建立,在缺乏国际层面有效制约的情况下,中国积极加强自身网络实力来提升其在全球网络治理中的作用和地位。一国的网络实力包括国家的网络战略、网络技术及参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能力。中国从这3个层面着手,不断强化自身网络实力。
首先,将网络空间安全战略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网络强国的战略目标,他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在保障网络安全、维护国家利益、推动信息化发展上的决心,使中国走出了网络空间治理的“战略茫然期”,中国网络空间安全战略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可以看出中国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已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其次,提高网络技术实力以增强网络空间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中国虽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网络大国,但还不是网络强国,我们面临着“关键的技术买不来,引进的技术靠不住,跟踪仿制没有出路”的困局。据《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发展报告(2015)》显示,微软、英特尔、思科“八大金刚”对中国的全覆盖已经到触目惊心的地步,仅思科一家在中国金融行业、政府机构、运输系统、基础设施行业,都有50%~80%以上份额[1]。斯诺登事件后,为了避免网络空间安全受制于人的危险境地,中国积极去除关键信息技术领域的“空心化”问题,更加注重网络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一方面“去IOE”,降低对美国产品的技术依赖,发展国内技术进行替代;另一方面,暂时无法取代的领域,争取做到可控,即安全可控、技术可控和数据可控。目前,中国以自主技术和民族产业发展为聚焦点,加大网络技术的研发投入,努力攻关网络空间的关键技术,特别是操作系统、终端芯片、超级计算机、互联网新应用以及安全防御体系等。“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依靠技术力量才能降低网络风险,只有拥有较强的网络实力才能在全球治理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
再次,增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能力。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此举打破了职能部门的条块分割,防止“九龙治网”的分散管理,有利于整合统揽网络空间安全全局。今年《网络安全法》制定,中国网络空间治理体制不断完善,治理能力不断提升,为我国参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制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经验支持。
双边层面中国强化中美网络空间治理的合作
当前网络空间的猜忌指责、网络攻击频发以及网络军备竞赛的升级,主要根源在于行为体间对彼此意图不确定带来的“战略互疑”;而这种不信任又加剧了双方在网络空间的对抗升级。这种双向互化的恶性循环严重阻碍网络空间治理进程的推进。例如,随着中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中美非对称性均衡已打破,中美在网络空间已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美国指责中国政府封锁境外网站、限制网络信息自由流动和支持网络窃密用于商业用途。由此,美国在国际舆论场上掀起了一波又一波“中国黑客威胁论”的喧嚣热浪,从山东蓝翔技校的黑客攻击到起诉5名中国军方人士窃取美国商业机密等,美国已占据网络舆论主战场并对中国大肆攻击。中国揭露美国通过“棱镜”、“旅伴”、“肌肉发达”等计划对中国主干网络进行大规模监控、攻击以及入侵活动,并通过“信息自由流动”传播美国价值观、侵蚀中国意识形态安全。
管控好中美网络分歧,构建中美网络互信,这需将中美网络关系置于“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框架下。
首先,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建立网络战略透明机制和网络危机解决机制实现不冲突、不对抗。中美在网络空间的双边会谈可以增信释疑,减少彼此间的战略猜忌,扩大双方核心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而不是陷入网络空间的“修昔底德陷阱”。2013年7月网络安全问题被纳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被双方视为重点议题。中美学术界也积极开展对话,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已多次开展“中美网络安全二轨对话”,成为中美研究网络安全的重要平台。诸如这种半官半民、亦官亦民的灵活对话形式,构成了增进相互理解、减少战略误判、加强公民网络安全观念培育、探讨国际网络空间制度合作的重要途径。
其次,中美通过签署双边、多边乃至普适性的协定,增强彼此间透明与信任建设,做到相互尊重。中美以官方或非官方的形式对网络空间本身的属性、网络权力性质、网络空间中的行为准则等问题进行协商讨论。通过这种方式,双方可以澄清误解,培育互信,以及确认最终的合作基础。2015年9月22日至25日,在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中美在应对恶意网络活动、反对网络商业窃密、制定网络空间行为准则、打击网络犯罪、信息通信技术贸易和外资安全审查六大领域达成共识。这对缓和中美在网络安全领域的矛盾局势,进一步加强双方合作有重大意义。同时也为全球网络治理的双边合作提供了成功范例。
再次,中美通过维护网络空间共同的安全利益实现合作共赢。中美在保障网络基础设施安全、维护国际网络连通、打击网络恐怖主义、反对网络犯罪行为上存在着共同利益,中美可以通过这些方面的合作实现共赢[2]。中美应尽一切可能手段去有效降低横亘在前的、由对彼此意图之不确定性带来的“战略互疑”,努力培育惠及双方的“战略互信”,将互动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的美好愿景延伸至网络空间[3]。
全球层面中国积极推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互联网对人类文明进步将发挥更大促进作用。同时,互联网领域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问题日益凸显。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中国呼吁国际社会应该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加强对话合作,推动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一是尊重网络主权。网络主权,是指一国独立自主处理网络空间事务的权利,由网络政治、经济、文化主权和军事安全构成。主要表现为3个方面:网络最高管辖权,即国家对其网络空间内一切基础设施、软件、信息等的控制权、管理权、传播权;网络事务排他权,即国家拥有行使网络空间事务的排他性自主权,如网络犯罪司法管辖权;网络侵略的自卫权,即国家为维护网络安全而对外来侵略或威胁进行防卫的权利。中国积极主张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网络发展道路、网络管理模式、互联网公共政策和平等参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权利,不搞网络霸权,不干涉他国内政,不从事、纵容或支持危害他国国家安全的网络活动。早在2010年《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就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互联网属于中国主权管辖范围,中国的互联网主权应受到尊重和维护[4]。当前,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在网络主权问题上分歧很大,中国可以先从网络数据的主权管辖入手,使西方意识到其网络攻击实际上侵犯了中国境内网络用户的隐私权和企业的财产权,促使其放弃针对中国网络和通信系统的入侵,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彼此相互尊重对方网络空间权益的共识。
二是维护和平安全。国际互联网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应该被人类和平利用,成为不同国家人民友好交流、相互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但网络技术的发展普及造就了西方网络大国的天然优势,他们在网络资源配置、技术标准、内容生成等方面都处于垄断地位,这促成了他们在虚拟空间新的霸权优势,也成为网络空间治理体系进程中的最大障碍。为此,中国呼吁应摈弃“零和”思维和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在充分尊重别国安全的基础上,致力于在共同安全中实现自身安全,切实防止网络军事化和网络军备竞赛。2011年中国与俄罗斯等国向第66届联大提交了由俄起草的《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呼吁各国“不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包括网络实施敌对行动、侵略行径和制造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等”[5]。该文件是目前国际上关于信息和网络安全国际规则的首个比较全面和系统的规范性倡议,就维护信息和网络安全提出了一系列基本原则。2015年1月9日,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联名致函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请其将由上述国家共同提交的“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更新草案作为第69届联大正式文件散发,呼吁各国在联合国框架内就此展开进一步讨论,尽早就规范各国在信息和网络空间行为的国际准则和规则达成共识。
三是促进开放合作。网络空间互联互通,各国在网络空间利益交融、休戚与共,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全球网络治理中,中国倡导互利共赢理念,鼓励开展双边、区域及国际发展合作,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积极推动信息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速度,特别是将自身在信息产业发展、网络战略制定、社会信息化上的相关经验教训与发展中国家分享,帮助他们跨越“数字鸿沟”。例如,尼日利亚通信委员会公共事务部主任托尼·奥约波称,没有中国的帮助,尼日利亚电信业不可能发展得如此迅速。2012非洲信息通信大会期间,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曾表示,非洲电信业的发展离不开与中国的合作。今年12月16日以“互联互通、共享共治——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召开,其宗旨就是希望全球着眼于网络互联互通,不分东西南北、贫穷富裕的国家都携起手来,共同谋划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才能真正搭建起全球70多亿人民都能平等共享的网络平台。
四是构建良好秩序。网络空间同现实社会一样,既要提倡自由,也要保持秩序。网络的适度开放和数据跨境流动有助于各国间的友好交流和经济互动,这也是互联网创立的宗旨。而网络的独立开放性逐步侵蚀国家主权的有形和无形疆界,使主权国家的地理边疆在数据流动中日渐虚化。更有甚者,一些国家打着“网络自由”的旗号,通过让信息自由流通,积极推广其“民主”、“人权”价值观,逐步构建网上意识形态霸权。习总书记指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网络空间是虚拟的,但运用网络空间的主体是现实的,大家都应该遵守法律,明确各方权利义务。要坚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让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
网络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提供了强劲动力,在未来全球发展议程中也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携手努力,本着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原则,深化国际合作,尊重网络主权,维护网络安全,推动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
[1] 惠志斌,唐涛. 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发展报告(2015)[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74
[2] 杜雁芸. 中美战略对话或将为网络空间安全建设答疑解惑[OL].国际在线.[2015-06-24].http://gb.cri.cn/42071/2015/06/24/8211s5007705.htm
[3] 檀有志. 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中美在网络空间的竞争与合作[J]. 外交评论,2014(5):38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互联网状况[OL].(2010-06-08)[2015-12-11].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1813615.html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军控司. 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OL].[2015-12-11].http://www.fmprc.gov.cn/chn/pds/wjb/zzjg/jks/fywj/t858317.htm

杜雁芸
博士,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电磁空间安全和中美关系、数据主权。
christinadyy@qq.com
Chinese Speed and Strength of the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Du Yany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