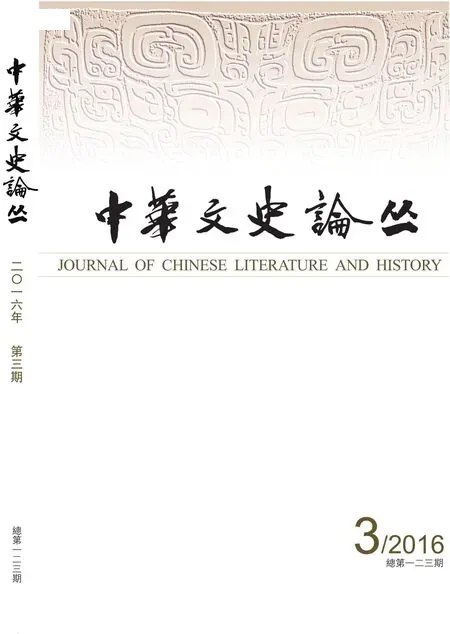唐初史臣文論的南朝批評及其對詩歌體式的要求*
2016-11-16劉順
劉 順
唐初史臣文論的南朝批評及其對詩歌體式的要求*
劉順
唐初史臣文論的南朝批評,以回應“南方的失敗”爲其初衷。雖然對“道德”的過度關注,影響了批評話語的理論深度,但其對於人性的理解、權力私化的反思以及文學觀念的構建努力,均展現出儒家文論批評自我體系化的特點。史臣文論批評確立了以不轉韻、尾押平聲之五古爲典範的詩歌體式,但理論的構想常錯位於文學史的實際。武德、貞觀文壇的創作既鮮少關涉南方話題,也在詩歌體式上,表現出對典範的背離。
關鍵詞: 南朝批評詩歌體式文質論南方主題
在中國傳統文論的研究中,對於思想觀念本身的關注,似乎是一個不言而喻的共識。雖然,作爲一種不失有效的研究方式,其流行本身並無太多可議之處,然而當研究者於不經意間做出“將觀念約等於現實”的跨界斷言時,卻常常會忽視兩者之間所可能存在的斷痕與錯位。唐初的文論批評,在通行的文學批評史的價值定位中,並無特出之處。即使數十年來詩格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已逐步提升了唐初文學批評的地位與影響,詩格興起之前的武德、貞觀時期的文論批評,“政教詩説之復興”的定位一仍其舊。雖然,强大的文獻基礎,支撑了此一表述的有效性,但在儒學影響持續不衰的傳統社會,如若止步於此表述本身,又自難以跳出對“寫什麼”及“爲何而寫”過度關注的言説傳統。只是,批評指向的高度集中,並不必然帶來觀念闡釋的系統與周密。至少,在“詩教説”產生的動力與條件以及體式技法與主題功能之內在關聯等問題上,猶存有考辨之空間。唐初史臣文論的南朝批評,對於文學功能與價值的强調,同步於詩教説的强大傳統,但此種批評常常逸出主題與功能之外,注目形式與技法的特性,又提示着史臣文論作爲分析樣本的獨特價值。無論儒學在觀念層面如何要求或指導文學,其影響效果的考察,都無法不最終落實到文學作品的書寫本身。故而,“如何寫”是政教詩説理論邏輯的內在延伸。當儒學對於理想文學體式的要求與文學的特性及書寫傳統互生影響之時,儒學影響文學的可能與限度,方能得到恰到的展現。唐初政教詩説與詩格興起的內在關聯,在此邏輯之下,亦或可尋得一不失合理的解釋。
一 史臣文論的“南朝批評”
開皇九年(589),隋滅陳,虜後主於井中,南北長達三百餘年的分立至此而終。雖然,歷史演進的主導因素終究在北不在南,南并於北乃歷史之必然,但後來擁有“南朝”之共名的南方各朝,在文明創造上所形成的影響力,卻成爲來自北方的征服者不得不面對的歷史重負。作爲“南方”的學習者與征服者,同樣以華夏正統自居的北方王朝,如何利用傳統的思想資源以調適“文明”與失敗之間的落差,既關聯於北方王朝的合法性論證,同樣也關聯着歷史觀念的推演。當“文學”在南北互動中,已確立作爲南方“文明”之標識的地位時,對於“文學”的批評,也隨即成爲歷史理解的文學投影。
唐初的史臣文論並無意於文學歷史的線性描述與技法演進的細緻勾勒,中古史學的體例特點,決定了“南方失敗的合理化”方是史臣文論批評的動力所在:
江左梁末,彌尚輕險,始自儲宮,刑乎流俗,雜惉懘以成音,故雖悲而不雅。……原夫兩朝叔世,俱肆淫聲,而齊氏變風,屬諸絃管,梁時變雅,在夫篇什。莫非易俗所致,並爲亡國之音。*《北齊書》卷四五《文苑傳序》,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頁602。
在王朝自我合法性論證的言説傳統中,勝利方“有征無戰”的道德標榜,自然而然地將“失敗者”道德感的喪失作爲言説的重點,故而,推敲權力私化與腐化的起點與根源便成爲基本的敍述模式。雖然,此種最終常會將權力的腐化與私化作爲王朝或某一政治共同體失敗之根本內因的解釋模式,足以見出史家見解的理性與深刻,但試圖將對抗權力私化與腐化的可能奠基於人性的道德自覺,則無疑又可見出史家的無奈與無識。唐初史臣受南朝史學影響,好以論、序剖析歷史之得失成敗,然而史識之水準卻似乎並無顯著之提升。相較於干寶《晉紀總論》歸亡國之因於清談,李百藥以變風變雅爲亡國之徵兆,雖可透露出南方數百年間士人風習的流轉變遷,但對於道德的關注卻始終一貫,文論批評的焦點自然而然地指向“道德腐化的可能性”。
遐觀列辟,纂武嗣興,其始也皆欲齊明日月,合德天地,高視五帝,俯協三王,然而靡不有初,克終蓋寡,其故何哉?竝以中庸之才,懷可移之性,口存於仁義,心怵於嗜慾。仁義利物而道遠,嗜慾遂性而便身。便身不可久違,道遠難以固志。佞諂之倫,承顏候色,因其所好,以悦導之,若下坂以走丸,譬順流而決壅。非夫感靈辰象,降生明德,孰能遺其所樂,而以百姓爲心哉?此所以成、康、文、景千載而罕遇,癸、辛、幽、厲靡代而不有,毒被宗社,身嬰戮辱,爲天下笑,可不痛乎!古人有言,亡國之主,多有才蓺,考之梁、陳及隋,信非虛論。然則不崇教義之本,偏尚淫麗之文,徒長澆僞之風,無救亂亡之禍矣。*《陳書》卷六《後主紀》史臣魏徵曰,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頁120。人有善端或人有爲善之可能,然聖人千載一逢,中人可以向善卻更易爲惡,儒家對人性的基本共識,實隱含着人性不可依賴而又不得不依賴的深沉感喟。史家試圖以“教義”阻斷爲政者道德滑落的嘗試,似乎總難破解王朝榮辱興衰與爲政者道德良窳似影如形般的疊加交纏。當道德水準的考量成爲王朝盛衰的標誌時,道德也隨同王朝的興起與滅亡,具有了一種週期性的生命形式,歷史由此便可簡化成道德的興起—滑落—中興—滑落—滅亡的過程,文學在此種歷史觀念之內,同樣也難以跳出文—質相替的古今迴圈。如果説,此種難以跳脱的古今迴圈,其內在推動爲“人之爲善”的可能不可能,其外在的推動則爲相關的誘導力量,“淫麗之文”作爲“教義之本”的腐蝕劑,自難逃史臣的嚴厲抨擊:
及後主嗣位,耽荒於酒,視朝之外,多在宴筵。尤重聲樂,遣宮女習北方簫鼓,謂之《代北》,酒酣則奏之。又於清樂中造《黄鸝留》及《玉樹後庭花》、《金釵兩臂垂》等曲,與幸臣等製其歌詞,綺豔相高,極於輕薄。男女唱和,其音甚哀。*《隋書》卷一三《音樂志上》,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頁309。
“淫麗”含有“邪”、“偏而不正”之義,首先關聯於“寫什麼”的主題選擇。政教詩説雖然在現代學術興起以來的文學批評中飽受抨擊,但儒家宣揚政教詩説的苦心孤詣,卻是植根於對維持“道德共同體”越挫越勇的期盼與渴望。當史家對於歷史的理解無法突破治亂相仍的迴圈史觀,上古三代依然擁有不可置疑的“神話”位置時,對於“教化”的宣揚,即有其難以替代的功用與位置。雖然,道德懲戒的成本限制、道德標準自身的歷史性以及權力必然私化與腐化的內在邏輯,往往讓“教化之説”的高自標置難以真切應對歷史變局的深沉危機,而受迂腐浮虛之譏;政教詩説對於道德腐化的敏感,也難以避免言説者出於私利的策略展演,但前後一貫的堅持也更易見出建立於歷史經驗之上的真誠。陳後主與幸臣所製之歌詞以及蕭梁所流行的宮體,無論其所關注之聲色物象有何種差異,主題上注重個體性情感與慾望的書寫卻爲其共通之處,此一點,無疑背離了政教詩説對題材之“公共性”的要求。同時,此類題材在形式上的出巧翻新,也因其“過度”而偏離政教詩説在形式上的“雅正”要求。
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隋書》卷七六《文學傳序》,頁1730。
與主題上注重“公共性”相應,形式上的古樸與率直通常會成爲政教詩説所認可的書寫風格。雖然,“文質彬彬”的典範標榜,總在提示政教詩説對於“文飾”的認可,但文明意味着成熟,而成熟必將走向衰敗的認知習慣,又暗示着“文飾”與“過度”的一體兩面。“江南”以及後來流行的“南朝”,在標示地理方位與在地王朝之外,總夾雜着企羨、哀嘆甚或强作鄙夷的複雜情緒。南方的王朝更迭,伴隨着史學與文學的逐步獨立,當文學在南北互動中,成爲南方以及“華夏”的符號時,文學的“過度”也即成爲南方腐化與失敗的表徵。“爭馳新巧”的南方文學,梁陳之際,業已其在音韻與韻律上的四聲八病之説與修辭上的偶對隸事聳動南北。
上古漢語本無聲調,由韻素調聲,及聲調漸興,音節長短的調聲作用,遂受壓制,韻素音步逐漸過渡至音節音步,漢字單音節化,複合詞批量增加,五七言詩歌發展的韻律基礎由此奠定。雖然,“四聲八病”説的成型依賴於聲調在齊梁時的四聲俱全,但聲律在詩歌成句、成聯以及成章中的重要作用卻與詩歌相始終,故而,“四聲八病”説不過是詩歌發展對聲律理論系統化的歷史要求。但“如何寫”與“寫什麼”、“爲何而寫”的內在關聯,也預示着四聲八病的流行必然帶來詩歌體制與主題的變化,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詩歌功能的變化。
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别?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秘未睹”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弦管之聲曲,則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猶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闡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沈約《答陸厥書》,《全梁文》卷二八,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58年,頁3116上。
二十世紀的文學批評史多在詩樂分立的框架內,解讀並定位四聲八病説,但近十年來的研究已大體勾勒出四聲八病説與合詩入樂的關聯線索,服務宴會享樂之需乃四聲八病説興起直接推力。*參見吴相洲《論永明體的出現與音樂之關係》,《中國詩歌研究》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117—144。沉溺享樂與權力的腐化及道德的敗壞不過一步之遥,而服務於詩歌入樂的功能定位,也必然導致詩歌主題與風格的變化:
然則子山之文,發源於宋末,盛行於梁季。其體以淫放爲本,其詞以輕險爲宗。故能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昔楊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周書》卷四一《庾信傳》,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頁744。
雖然,“掇彼清音,簡兹累句”的表述隱含了聲律風骨合一的可能,但在南北詩人尚未能找到兩者有效結合的路徑之時,四聲八病便成爲詩歌“淫放”、“輕險”的替罪者。如此認識,也自然影響了武德、貞觀文壇對聲律説的接受。北魏末期,沈約《四聲論》已播於北土,然士人之態度莫或一是。四聲八病之説,至北齊北周,方始盛行,南北聲律之探求,至此大體同步。*“要之,北朝詩歌在聲律的探求上走過了漫長的道路。就北魏來説,從第一期的游雅,到第三期的溫子昇,有近百年的時間。和南朝一樣,一開始他們也不注意人爲的聲律。永明聲律説產生之後,沈約《四聲譜》是比較快地傳到了北魏,並且得到了人們的贊賞(如常景)。但是,北魏當時的文學氛圍畢竟不如南朝的齊梁,加上有人不理解(如甄琛),因此詩歌聲律的變化開始比較緩慢,遠不能和南朝同步。直到第三期,纔有比較大的變化。而到了北齊北周,詩歌聲律的探求則大爲發展,不僅南北可以同步,而且北方本土文人也可以和由南入北的文人同步。南北文學合流在北齊北周之上聲律上已經完成。”盧盛江《文鏡秘府論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頁385。唐初史臣以“河朔詞義貞剛,貴乎氣質”,*《隋書》卷七六《文學傳序》,頁1730。常會造成河朔文風宏壯而技法粗率的接受印象,但若以南北對立末期,北方詩歌聲律技法之演進而言,恐未必確當。史臣對“四聲八病”的批評,雖並未能抵抗齊梁體流行的歷史大勢,但畢竟延緩了詩律理論精密化的腳步。*參見杜曉勤《齊梁詩歌向盛唐詩歌的嬗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25。
古典詩歌雙(音)節成(音)步、雙步成句以及雙句成聯的特點,*參見馮勝利《漢語韻律詩體學論稿》第三章相關論述,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頁51—66。決定了詩歌對於對偶的依賴。雖然,唐代詩格關於對偶的討論,多聚焦於其作爲修辭術的層面,但對偶作爲詩體建築術的角色卻有着更爲基礎性的影響,五言詩由“體俳”而“體語俱俳”的歷史進程即可爲注腳。*“晉則嗣宗詠懷,興寄沖遠,太沖詠史,骨力莽蒼,雖途轍稍歧,一代傑作也。安仁、士衡,實曰冢嫡,而俳偶漸開。康樂風神華暢,似得天授,而駢儷已極。至於玄暉,古意盡矣。……何仲默云:‘陸詩體俳語不俳,謝則體語俱俳。’可謂千古卓識。”胡應麟《詩藪·古體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頁29。作爲組建詩歌(韻文)的基本方式,對偶會增强一行之內,上句與下句之間的呼應感,並以語言與節奏上的對稱强化詩行語義與韻律的閉合性(穩定感)。但詩歌對於語意脈絡連貫性的要求,又同時呈現出“去對偶化”的傾向。故而,“作詩不對,本是吼文,不名爲詩”雖爲共識,*“凡文章不得不對。上句若安重字、雙聲、疊韻,下句亦然。若上句偏安,下句不安,即名爲離支;若上句用事,下句不用事,名爲缺偶。”舊題王昌齡《詩格》,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171。但對偶的過度使用,在增强詩歌鋪敍功能的同時,也會帶來章節、語義的複遝以及節奏的遲緩,並進而影響詩歌主題選擇與功能定位。詩教化對於對偶精緻化的警惕實亦導源於此。而當對偶的特别形式——“隸事”,被頻繁使用時,語詞的典雅與語義的密集必然放大詩文的形式特徵,但其知識化與學術化,也同樣爲詩歌功能的作用發揮,設置難以跨越的障礙:
近任昉、王元長等,詞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納,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鍾嶸撰,曹旭《詩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頁180—181。
清談的風氣消歇,南方的世家大族也在王朝更迭中,威勢漸損。庶族及南方土著的興起,挑戰着世家大族的政治與社會地位,並在對士族風流的模仿與參與中,分享曾爲世家高門所獨享的榮光。雖然,自學術風氣的轉圜,如古文經學的興起、史學的興盛諸角度均可爲隸事之風的興起尋得一合理的解釋,*參見何詩海《漢魏六朝問題與文化研究》第六章的相關論述,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236—278。但士人在營造或參與此種風習之養成過程的動力與心態,或許即會遭到忽視。從隸事之風,倡始於南齊之王儉,而擅長且樂於此道者多出身高門,亦可見出知識的展演已成爲輝光黯淡的南方士族維持自我身份與特性的最後防線。以詩文之隸事而言,劉宋同樣是一個重要的歷史節點:“詩以用事爲博,始於顏光祿而極於杜子美。”*張戒撰,陳應鸞《歲寒堂詩話校箋》,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頁16。齊梁之時,詩文用典之繁複,又遠過之,至有以隸事爲戲而成文者。*蕭衍《戲作詩》即羅列典故成文:“宓妃生洛浦,遊女出漢陽。妖閑逾下蔡,神妙絕高唐。綿駒且變俗,王豹復移鄉。況兹集靈異,豈得無方將。長袂必留客,清哇咸繞梁。燕趙羞容止,西妲慚芬芳。徒聞殊可弄,定自乏明璫。”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535。隸事之習,由南而北,流風所及,鄴下遂有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顏之推撰,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卷三《勉學》,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177。伴隨聲律、屬對技巧的提升以及學術趣味的增長,日益技術化的“文學”,逐步疏離了政教詩説所宣導的實用價值:
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惟務吟詠。……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兹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説,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勳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隋書》卷六六《李諤傳》,頁1544—1545。
雖然,此段論述采自楊隋治書侍御史李諤的上疏,但據李延壽《北史·文苑傳序》關於隋文“斲彫爲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之論述,*《北史》卷八三,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2782。所表現出的情感認同,實可將其與史臣文論同等視之。李延壽在同篇傳序中雖然並不認可蘇綽的文體改革,但同樣也未認可當時風行關右的江南文風。經典的萬世光芒與文運隨世而遷之間的錯位,構成了政教詩説難以平衡而又無法回避的一組難題。唐初史臣類如“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的常態表述,*《梁昭明太子文集》卷三《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一首》,四部叢刊縮印本,134册,頁22上。看似在提供可作爲標準的典範,但對平衡與完善的過度追尋及技法探究的缺失,卻恰恰暴露出史臣難以提示有效路徑時的虛與委蛇。在此邏輯上,善於以儒家理論爲支撑的《詩格》的流行,便可視作對史臣文論的補白。
史臣文論主要見之於各書《文學傳序》或《文苑傳序》的體例安排以及好爲通論的批評習慣,都具有鮮明的南朝史學的烙印。然而形式上的相近,並未帶來文學理解上的相互認可。唐初史臣文論的內在邏輯,必然導致“淫麗之文”出於無德者之手的結論,此一點相較於以立身與爲文可以兩分的南朝文論,無疑過於保守。而在“文人無行”的理解上,北齊楊遵彥《文德論》“以爲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的表述,*轉自《魏書》卷八五《文苑傳·温子昇》,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1876。雖非爲北人之孤鳴獨響,但相較於南方對於“文士無行”追問中的理性與溫情,北人的表述無疑簡單而粗率:
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淩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顏氏家訓集解》卷四《文章》,頁238。
很難設想,如若南方文學的進程未爲政治的變動所阻斷,南方的文學批評又將會呈現出何種面貌。畢竟在唐初史臣文論還徘徊於“人品與文品”、“風雅與鄭衛”這類話題之時,南方已經擁有了諸如《詩品》與《文心雕龍》之類的文論佳構。其所討論問題的廣度與深度也非北方所可比肩。北方以及因“南方的失敗”而面臨巨大道德壓力的南方史臣在尋找“失敗之因”的初衷之下,矮化同時也簡化了南方的文學。所幸,歷史文本的字裏行間,總會留有不同於主流的異調别響:

雖然,試圖在歷史的編撰中融入書寫者對歷史的理解,已是七世紀初史家的共識,但對“人”、“事”的過度聚焦,卻讓史家難以衡量獨立或半獨立於人事的因素在歷史演進中的影響。史家以“數終三百”之氣運,回應南方的失敗,在時人的知識結構與接受習慣中,或許同樣的真誠而有效。但如此的回應又很難不被視爲對問題本身的回避,然而,史家的困惑,又往往在提示着扭轉探求方向的可能。至少在以上的論述中,作爲南方文明之表徵的文學,已不再是南方失敗的罪責承擔者,相反卻是南方王朝命運的榮辱與共者。雖然,偶一展現的對梁陳文學的肯定,並不足以影響史臣文論的主流觀念,然而唐初文論欲試圖重新接榫南方文論的進程,跳出“文質”論體系的約束,將爲其必由之徑,這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文學演進的內在要求。
二 構建典範: 史臣文論對詩歌體式的要求
對南方文學的批評,並未影響唐初史臣對文學功用的肯定,甚而,其關於“文用”論述之系統較前賢猶有過之,*“然則文之爲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於下,下所以達情志於上,大則經緯天地,作訓垂範,次則風謠歌頌,匡主和民。或離讒放逐之臣,塗窮後門之士,道轗軻而未遇,志鬱抑而不申,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雲,振沈溺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隋書》卷七六《文學傳序》,頁1729。但禁忌的設置,卻隱含着壓制詩文寫作熱情的可能。在“文學”已成爲王朝正統性之表徵的時代,禁忌的提示以及缺少實例支撑的理想宣導都不足以迎合大一統帝國對於“文學”的期待。當“寫什麼”與“如何寫”之間的內在關係已被魏晉以來的文論批評所點明並强化之時,史臣文論無論其立意如何高遠、初衷如何動人,都無法漠視文學演進之事實對政教詩説的歷史影響。故而,大一統時代的文學典範,既需要在“寫什麼”的主題選擇上畫定較爲穩定的界限,同樣也需要在“如何寫”的體式規定上提供可資效仿的樣板。
李延壽《北史·文苑傳序》曰:
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暨乎即位,一變其體。《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並存雅體,歸於典則,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北史》卷八三,頁2782。
隋煬帝是齊梁之後,南北文壇爲數不多,受到史臣如此肯定的“綴文者”。李延壽的此段論述在史臣文論中所以特别,正在於以例證的方式,給出了“並存雅體,歸於典則”的樣板。*由於《與越公書》及《建東都詔》的文章體式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故置而不論。《冬至受朝詩》與《擬飲馬長城窟》,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收錄(頁2661,2666),惟文題稍異。這也爲探究唐初官方理想的詩歌體式,提供了可供具體討論的案例。楊隋之時,詩歌已可謂各體兼備,李延壽惟取以上兩詩爲樣板,其要因乃爲語體之“雅正、典則”。由於政教詩説對於教化功能的强調,語體在確立詩歌典範的過濾機制中作用最爲根本。
語體是語言在直接交際中包含正式與非正式及俗常與莊典兩組二元對立的功能體系。*參見馮勝利《漢語韻律詩體學論稿》第四章相關論述,頁67—89。作爲語言交際時,標識“説者與聽者”相互關係的產物,語體的形成機制,依賴於距離感的判斷與呈現。共時性的距離判斷,形成正式與非正式的區分,而歷時性的距離感則形成俗常與典雅的差異。雖然,語體非文體,但以“物件、場合、內容、態度”爲判斷要素的語體在爲文體形成提供原初動力時,通常也受制於文體的內在構造機制。故而,在文學文體的演化過程中,文體與語體之間自然而然地形成高度的對應關係:
古之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漢郊廟歌多用之;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於俳諧倡樂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樂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黄鳥止于桑”之屬是也,於俳諧倡樂世用之;古詩之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之屬是也,不入歌謠之章,故世希爲之。夫詩雖以情志爲本,而以成聲爲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爲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摯虞《文章流别論》,《全晉文》卷七七,《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1905下。
以語體之雅正而言,摯虞《文章流别論》排列的先後次序爲四言、三言、六言、五言、七言與九言,然較之於隋唐之際以四言、五言爲典正的批評實際,西晉以降,詩體的語體功能已有明顯的移位現象。
四言的最早成熟以及在傳統社會百代不降的典範地位,源於四言的興盛與漢字單音節化之歷史趨勢的合拍,以及四言的二二成句對傳統詩歌構造機制上“雙分枝”要求的應合。*葛曉音在論及四言何以最早成熟時,也認爲二二的主導節奏、兩句一行爲主的基本結構具有重要作用。參見《先秦漢魏六朝詩歌體式研究》的相關論述,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21—42。另王雲路《中古漢語詞彙史》也曾論及四言的特性:“《昭通方言疏證》曾專設‘説四言式片語’一節,指出:‘四字片語即得成爲一完整簡單之語句,言語之用遂爾完備。’四字句‘使漢語語言多具美感之音與通利之質’,是漢語‘變化萬端、肆應無方之基礎’,‘四字式片語爲漢語之特殊形式,自其發展之史實論之,其根源蓋本於漢語二字爲一音步之定則,兩音步即得組成一語句,此表現於《詩經》時代最突出。’姜亮夫師談到了四字句的功用、特色與產生原因,簡潔而實在。一個音步由兩個音節組成,兩個音步就構成了和諧的韻律,就構成了一個基本的句子。這就是漢語逐漸雙音化的動因之一,更是四字句產生的原因。”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頁127—128。但中古時期,漢語詞彙的大量雙音節化,*“與之同理,中古詩歌中產生大量的雙音詞,一個重要原因,是同步構詞。同步構詞包括兩個方面: 一是一組意義相近的單音詞可以同樣的方式構成雙音詞,也表示同樣的意思,這就是我們所説的同步構詞;另一個類型是同義詞,往往同樣與一個語素結合而構成雙音詞。”王雲路《中古詩歌語言研究》,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頁445。所造成的二二節奏的固定化,已不同於《詩經》以單音詞爲主,通過添加虛字或襯字以形成雙音結構的組合方式。相較於《詩經》以單音詞爲主之四言長於抒情,雙音詞爲主的四言,業已呈現出適合鋪敍的賦化特徵,四言作爲詩體的獨立價值逐步降低。雖然,由於《詩經》的經典地位以及二二節奏的標準性,四言依然擁有其他詩體無可比擬的崇高位置,但四言的使用範圍已被逐步壓縮入特定的,以凸顯莊重、肅穆與典雅之氛圍爲主的場合。兩漢之後,四言創作,雖依然產生了曹操、嵇康與陶潛等四言高手,但“四言詩締造良難,於《三百篇》太離不得,太肖不得;太離則失其源,太肖祗襲其貌也”的感慨,*沈德潛《説詩晬語》卷上《四六》,《清詩話》,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3年,頁530。方是後世對待四言的基本態度。三言雖有較爲古老的出身,漢時亦多郊廟歌辭之作,但三言在音步組合上的懸差效應(一個殘音步加一個標準音步),讓三言在語體上難以承擔雅正的要求:“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於鐘律,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漢書》卷二二《禮樂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1071。雖兩漢之後,三言仍不乏郊廟歌辭與文人之作,但“語既短簡”的三言,作爲意義的表達單位過於短小;且其節奏短促,“聲易粗澀”,極易形成上下句之間在語義與節奏上的高度依賴。詩體對詩歌語義與情感節奏的主導,壓縮了詩人的騰挪空間,自然也即限制了三言的發展。三言可與五言特别是七言形成相應詩體,在雜言體中具有重要的節奏調節功能,後世詩歌創作對三言的使用,多止步於此。而六言如若無調節詞的加入,則會形成三三或二二二的基本節奏。此類六言句不可有間拍成分且上下句的句式必須一致,對於詩歌而言,則極易造成因音節過於急促而難以延展氣脈,或音節過於舒緩而節奏遲澀拖遝的不良效果,*盧冠忠《論六言詩與駢文六言句的韻律及其句法之異同》分析六言詩的韻律結構類型,有以下結論: 第一,六言詩的韻律結構不外乎三個兩音步與兩個三音步;第二,六言詩不可出現間拍成分;三,六言詩中,雙音步和三音步必須跟同類的音步組合;四,六言詩的三音步數量較少。馮勝利編《漢語韻律語法新探》,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頁465— 486。故而中古時期的六言多以歌詞的方式出現,但這又造成六言低俗的接受印象:“竊尋樂府雅歌,多皆不用六字。近代有《三臺》、《傾杯樂》等豔曲之例,始用六言。今故雜以‘兮’字,稍欲存於古體。起草適畢,未敢爲定。蒙假不獲面啓對,封稿本上呈,可不之宜,伏聽後命。”*許敬宗《上恩光曲歌詞啓》,《全唐文》卷一五二,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3年,頁1550上。與六言相類,七言同樣有“俗體”之稱,且其得名應更早於六言。故余冠英先生説:
從“七言不名詩”這一層來看,知道當時人對於七言韻語視爲俗體。從傅玄《擬四愁詩序》(序云:“張平子作四愁詩,體小而俗,七言類也。”)看來,知道晉人觀念亦尚如此。從歌訣、零丁都用七言這一事實看來,可以知道七言韻語確爲當時流行的俗體。*余冠英《關於七言詩起源問題的討論》,《漢魏六朝詩論叢》,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2年,頁160—161。七言在漢代的使用主要見之於字書、鏡銘、醫書以及民間謠諺等與日常生活相關的領域,即使在精英的文化活動中,七言曾偶露頭角,但“體小而俗”,在七言的雅化尚未完成之前,依然是其難以擺脱的身份定位。雖然,典型七言句式“二二三”的三分節奏及兩個標準韻律詞與一個超韻律詞的構成結構,可視爲中國詩歌韻律結構的基本完成,*參見趙敏俐《論七言詩的起源及其在漢代的發展》,《文史哲》2010年第3期。但隋唐之際的七言尚是一種技法有待提升的詩歌體式。當三言、六言、七言均不能成爲唐初史臣所認可的詩歌體式,而四言的應用又有場合的限制時,五言即成爲最終的選擇。但劉宋永嘉之際,五言已呈體語盡俳之勢,及永明聲律論大行,齊梁調及徐庾體遂與五言古體並肩通衢成五言之新典型。故而,對於唐初史臣而言,五言古體與近體之間的關係處理,又將成爲必然要跨越的障礙。
五言繼四言之後,成爲發展最快,技法提升最爲迅猛的詩體。摯虞之時尚被俗體之名,至鍾嶸《詩品》已有“居文質之要”的美譽。五言古體以《古詩十九首》爲典範。楊載《詩法家數》曰: 五言古詩“須要寓意深遠,托詞溫厚,反復優遊,雍容不迫。或感古懷今,或懷人傷己,或瀟灑閑適。寫景要雅淡,推人心之至情,寫感慨之微意,悲歡含蓄而不傷,美刺婉曲而不露,要有《三百篇》之遺意方是。觀漢魏古詩,藹然有感動人處,如《古詩十九首》”。*楊載《詩法家數》,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731。漢魏五古長於書寫“人同有之情”,*《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古詩十九首》,《續修四庫全書》,159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642下。故相較於宋齊而下之五言,其主題的公共性更爲明確。而技術手法上,五古“場景片斷的單一性、敍述的連貫性、比興和場景的互補性和互相轉化以及對面傾訴的抒情方式”,*葛曉音《先秦漢魏六朝詩歌體式研究》,頁321。確保了其意象的渾融與結構的自然天成。元嘉以降,俳偶俱開的近體五言,雖然一度突破了五古單一場景的時空限制,增大了詩作的層次與容量,但敍事與鋪敍能力的放大,在帶來“繁文縟旨”之美學風格的同時,也逐步拉大了情景之間的距離。及此種體調與聲律之説相融合,五言逐步形成以兩句一轉勢的四句或八句爲主的結構形式,格調漸趨淺俗,主題的選擇也逐步趨同於詠物、閨情與離别。*參見《先秦漢魏六朝詩歌體式研究》,頁275— 433。由此,當唐初史臣在可能的範圍之內嘗試確立可謂典範的詩體時,自主題公共性的角度而言,五言近體似乎已然落入下風。然而李延壽對風格有明顯近體特徵的《冬至受朝詩》與古體之《擬飲馬長城窟》“並存雅體”的判斷,又在提示着唐初史臣在典範選擇上“主題優先”的原則。只是,一旦回到具體的詩歌文本,五言的近體化對於主題選擇的影響又展露無遺。隋煬帝《冬至受朝詩》:
北陸玄冬盛,南至晷漏長。端拱朝萬國,守文繼百王。至德慚日用,治道愧時康。新邑建嵩岳,雙闕臨洛陽。圭景正八表,道路均四方。碧空霜華淨,朱庭皎日光。纓珮既濟濟,鐘鼓何鍠鍠。文戟翊高殿,采眊分脩廊。元首乏明哲,股肱貴惟良。舟檝行有寄,庶此王化昌。*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題作《冬至乾陽殿受朝詩》,頁2666。
楊廣此詩,“體語俱俳”,雖尚無用典晦澀之弊,但對句以及相同句式(二一二)的過度使用,依然讓此首可稱華淨的五言詩,節奏單調而遲緩。詩歌的整體風格典雅莊重有餘而流暢不足,述志寫景俱佳而感發不足。故而在五言近體解決節奏的變化與氣脈的流暢之前,齊梁調式的五言即使可以被用於“公共性”題材的書寫,其所適合者也更偏向於冷靜、客觀可加鋪敍的題材,而抒發個體情志,能以情氣相感發的主題類型則更適宜由五古承擔。*隋煬帝《飲馬長城窟行》:“肅肅秋風起,悠悠行萬里。萬里何所行,橫漠築長城。豈合小子智,先聖之所營。樹兹萬世策,安此億兆生。詎敢憚焦思,高枕於上京。北河秉武節,千里捲戎旌。山川互出沒,原野窮超忽。摐金止行陣,鳴鼓興士卒。千乘萬騎動,飲馬長城窟。秋昏塞外雲,霧暗關山月。緣嚴驛馬上,乘空烽火發。借問長城候,單于入朝謁。濁氣靜天山,晨光照高闕。釋兵仍振旅,要荒事方舉。飲至告言旋,功歸清廟前。”《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2661。由此,綜合五言演進的歷史進程與史臣對南方接受的一般心理,雖然近體化的五言依然分有着部分“公共性”題材的書寫責任,但影響在史臣體式典範的設想中已難及古體。
人工聲律以及句式與語詞偶對的講求是五言近體化的重要標誌,基於自然聲律之上的漢魏五古,雖然不必如近體技法的精密與工緻,但在聲律及偶對上,依然有其所必須遵循的原則。以聲律而言,相對於近體結構漸趨簡單,篇制多爲四句體與八句體,可不必轉韻的特點,五古首先面臨的問題,即爲是否轉韻:
劉勰云:“改韻從調,所以節文辭氣。”“兩韻輒易,則聲韻微燥;百句不遷,則唇吻告勞。”七古改韻,宜衷此論爲裁。若五言古畢竟以不轉韻爲正。漢魏古詩多不轉韻,十九首中亦只有兩首轉韻耳。……一韻五言正體,轉韻五言變體也。*胡震亨《唐音癸籤》卷四《法微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33。
五言詩的基本節拍爲可以細分爲二一二或二二一的“二三”節奏。相較四言二二主導節奏易於單調而不乏渾厚的穩定之感,五言的節奏則具有更爲明顯的流動性。但二三的節奏所形成的前輕後重效應,卻讓五言詩在語體上,相較於其他詩體更爲接近四言:
五言古如澄波安流,清風飄拂,切不可務爲新警,致令色澤不雅,體裁不圓。至其用韻,則但當一韻到底,不必轉換。轉換則調急,失閑雅之度。譬如秋水潺湲,遇石而激,其下必駛也。*于祉《澹園詩話》,張寅彭選輯《清詩話三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5457。
五言古以“古澹”爲貴,其對詩歌流動性的接受,以保持情感基調的閑雅穩定爲限。一韻到底會增强詩歌不同部分的呼應與回環,並因而放大詩歌內部的閉合相應,從而保持整體基調的均衡。
轉韻問題的討論,自然已預設了押韻現象的存在。雖然永明之前,尚無四聲之説,更無論四聲之二元化,然漢魏五古之作,未始無暗合四聲之事實。故爲方便計,遂可以四聲平、上、去、入之分類爲標準,初步推測史臣所認可之五古的尾韻偏好。
然聲之不等,義各隨焉。平聲哀而安,上聲厲而舉,去聲清而遠,入聲直而促。詞人參用,體固不恒。請試論之:“筆以四句爲科,其內兩句末並用平聲,則言音流利,得靡麗矣。兼用上、去、入者,則文體動發,成宏壯矣。看徐、魏二作,足以知之。徐陵《定襄侯表》云:‘鴻都寫狀,皆旌烈士之風;麟閣圖形,咸紀誠臣之節。莫不輕死重氣,效命酬恩。棄草莽者如歸,膏平原者相襲。’魏收《赤雀頌序》云:‘蒼精父天,銓與象立;黃神母地,輔政機修。靈圖之迹鱗襲,天啓之期翼布。乃有道之公器,爲至人之大寶。’徐以靡麗摽名,魏以宏壯流稱,觀於斯文,亦其效也。又名之曰文,皆附之於韻。韻之字類,事甚區分。緝句成章,不可違越。若令義雖可取,韻弗相依,則猶舉足而失路,弄掌而乖節矣。故作者先在定聲,務諧於韻,文之病累,庶可免矣。”*佚名《文筆式》,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97。
《文筆式》之論,雖爲四六發聲,非爲論詩,然四聲各别,義隨聲轉,則聲調之選用,關涉體式之全貌,詩賦之間自可互通。平聲哀而安,有賒緩之稱,句末平聲連用,詩風平和流利。上聲尖銳,去聲清亮,入聲短促,須參互使用,如劉勰之“飛沉”迭用,則詩風宏壯。永明聲律論雖有四聲八病之説,但南方詩歌病犯多犯平聲,流風所及,隋唐之時蜂腰平聲已不爲病犯。魏徵以“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或因江左尾韻好用平聲。*參見盧盛江《文鏡秘府論匯校匯考》,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473。如此,“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當與北方士人尚用上去入聲存有關聯。但詩歌二句一聯,所產生的語義與節奏閉合性的要求,以及漢魏五古多尾押平聲的事實,都在提示尾押平聲並不必然與宏壯之詩風相違。唐初史臣論文論,於南方文學雖貶多譽少,但“掇彼輕音,簡兹累句”的目標設想,以及盛唐詩“聲律風骨兼備”的完美實現,*參見殷璠《河嶽英靈集序》,元結《唐人選唐詩(十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40。卻無疑體現了史臣對詩歌近體化趨勢的尊重及在近體多押平聲的特點中尋求突破的路徑設定。
對偶作爲一種表現技法,具有“自我完結的功能”。漢語本身的特性及詩歌體式的要求,奠定了對偶作爲基礎技法的重要地位。*松浦友久説:“如此來看可以認爲,所謂中國語(漢語)的對偶表現,歸根到底是用漢語本身‘在對偶構成上的適應性’來補救漢語本身‘在傳達功能上的限制’這樣一種獨特的相互作用的系統。即① 一詞一音一字性、② 聲調性、③ 節奏性是其本身適於構成對偶的適應性條件;另一方面,由於④ 孤立語的性質、⑤ 一字多義性、⑥ 典故性而需要(乃至不可缺少)對偶,它們則是促成對偶發達的促進條件。”氏著《中國詩歌原理》,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0年,頁221。對偶在詩歌書寫中的出場,遠遠領先於對偶理論的自覺與成熟。然而,後世對偶理論的演進並未改變對偶在聲、形、義上追求對稱與均衡的基本原則。
夫爲文章詩賦,皆須屬對,不得令有跛眇者。跛者,謂前句雙聲,後句直語,或復空談。如此例,名爲跛。眇者,謂前句物色,後句人名,或前句語風空,後句山水。如此之例,名眇。何者?風與空無形而不見,山與水有蹤而可尋,以有形對無色。如此之例,名曰眇。*崔融《唐朝新定詩格》,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135。
唐初《詩格》對偶技法的精密與工巧化是詩歌近體化的必然結果。而建立在自然聲律基礎上的五言古體,在語詞聲調、形式乃至句式的對偶上,至曹植之時,方見有意爲之的詩法自覺,漢魏間五古猶難脱質樸之風貌。
《詩》曰:“覯閔既多,受侮不少。”初無意於對也。《十九首》云:“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屬對雖切,亦自古老。六朝惟淵明得之,若“芳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是也。*謝榛《四溟詩話》卷一,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138。
漢魏五古於對偶既處有意與無意之間,唐初史臣所認定之典範亦不得不如是。然所謂“有意”即不妨人工雕飾之痕迹,而“無意”則又求化人工於自然,如此,在對偶上,必然產生對風格簡明而流暢的要求,過於妝飾或過於知識化的對偶風格均與此不合,而此種風格,也會形成五言古體在語義上對“反對”使用的注重。
三 史臣的詩歌創作與文學中的“南朝”主題
唐初史臣對文學歷史的回眸及南北文學的批評,爲唐初文學在經典的四言而外,確立了理想的五言古體模式。但是理論的構造者,一旦突破解釋詩歌的角色定位,試圖進行詩歌創作時,卻常會發現理論領域的高屋建瓴,難敵詩歌傳統的水靜流深。由於史臣的四言主要見之於郊廟歌辭,詩歌功能已呈現出服務特定場合的專業性。使用場合的特殊與詩歌形式本身因場所而有的特定要求,讓四言具有了半封閉性的特點,故而,也宜於保持書寫傳統的穩定性。相較而言,五言則成爲流通性最强的詩歌形式。由於五言無法回避悠長而有其內在邏輯的詩歌傳統以及社會生活的古今差異,由此五言古詩的創作,即成爲考察史臣理論踐履的主要對象。雖然唐初參與修史的人數衆多,但因相關文論多出自於文學或文苑傳序,常由領銜者執筆,故而,史臣詩歌書寫的考察,將聚焦於作爲領銜者的修史人。
據《全唐詩》所錄武德、貞觀兩朝詩歌,四言郊廟歌辭而外,李百藥存詩九首,令狐德棻存詩一首,魏徵存詩三首,均爲五言;房玄齡存柏梁體聯詩一句;姚察、李延壽則無詩留存。合而計之,史臣共有五言詩十三首。但五言古體,只有魏徵作於武德元年(618)的《出關》一首,自數量而言,已入下風。此時期五古數量較多者,乃爲《晉書》留下四篇史論的唐太宗李世民,但唐初的五古,已難免五言近體化的影響:
五言自漢魏流至元嘉,而古體亡。自齊梁流至唐初而古、律混淆,詞語綺靡。陳子昂始復古體,效阮公《詠懷》爲《感遇》三十八首,王適見之,曰:“是必爲海內文宗。”然李于鱗云:“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何耶?蓋子昂《感遇》雖僅復古,然終是唐人古詩,非漢魏古詩也。且其詩尚雜用律句,平韻者猶忌上尾。至如《鴛鴦篇》、《修竹篇》等,亦皆古、律混淆,自是六朝餘弊,正猶叔孫通之興禮樂耳。*許學夷《詩源辨體》卷一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頁144。
五古的律化,已是詩歌體式演進的必然,史臣對五古歷史回顧與評判,雖然對後世的詩歌批評產生了重要影響,“漢魏風骨”因之而成爲文學批評史上的價值典型,俯視並衡量着後世文學創作的風貌與價值。然而,史臣的詩歌創作,卻再次證明了一種古典而理想的價值,通常適宜於爲“現實奠基”或“與現實對立”,但絕難成爲現實。
史臣對詩歌體式的用心,流露的是對道德共同體的期盼,其對詩歌主題有着較爲嚴格的規定,但此種規定,似乎也總有被突破的可能。
歌聲扇出後,妝影鏡中輕。未能令掩笑,何處欲障聲。知音自不惑,得念是分明。莫見雙嚬斂,疑人含笑情。
佳人靚晚妝,清唱動蘭房。影出含風扇,聲飛照日梁。嬌嚬眉際斂,逸韻口中香。自有橫陳會,應憐秋夜長。*《火鳳辭》,《全唐詩》卷二七,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頁393。
《火鳳》爲曲名,最早見於《洛陽伽藍記》卷三《高陽王寺》:“王有二美姬,一名豔姿,善《火鳳》舞。”*范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178。雖《火鳳》是否出自胡樂,尚存爭議,但據貞觀時,裴神符善琵琶,惟作三曲,《火鳳》即其一,“人稱聲度清美”之記載,*參見袁繡柏《“火鳳”來源考》,《浙江大學學報》2005年第3期。《火鳳》當具有婉媚動人的娱樂效果。李百藥《火鳳詞》乃唐代此曲僅存之曲詞,歌詞香豔,頗近宮體風格。較之貞觀七年(633)虞世南以死諫止唐太宗“戲作豔詩”,*《唐會要》卷六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1328。二十二年,李百藥《火鳳詞》主動疏離史臣“道德至上”原則,則可視爲貞觀中後期的詩歌所呈現出少規諫、多頌媚之詩風轉向的重要注腳。史臣關於主題的見解,也難經時間與世風的消磨。
“南朝”因李延壽的《北史》而成爲代指宋齊梁陳四個南方王朝的共名,雖然,這個兼顧時間與空間雙重指謂的“南朝”概念,在後世的使用中,曾上溯至東晉,但並未改變因爲“南方的失敗”與“南方的高度文明”錯位重疊,所帶給“南朝”的特定意味。文明/衰亡、精緻/病弱乃至豔羨/拒斥,完美無缺地拼合在“南朝”之中。曾流播南北的高度華美的南方文學一度成爲南方的表徵,但與史論對南方文學的集中關注相比,武德、貞觀時期的詩歌似乎在壓抑着“南朝”的過往。歐陽詢貞觀時所作的《道失》是爲數不多的與南朝有關的詩作:
已惑孔貴嬪,又被辭人侮。花箋一何榮,七字誰曾許。不下結綺閣,空迷江令語。琱戈動地來,誤殺陳後主。*《全唐詩》卷三九,頁502。
歐陽詢依然在“君賢臣忠”解釋框架內,尋找南陳衰亡的原因,複雜的歷史事件,也由之被簡化爲個體或某羣體的道德問題,這是史臣理解“南方的失敗”的基本思路。但對文學道德化的理解,必然陷入文質相替的迴圈觀念,而在南方已可稱爲共識的文學新變的理解即同樣處於壓抑之中:
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疏朴,未爲密緻耳。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製裁爲本,今之辭調爲末,並須兩存,不可偏棄也。*《顏氏家訓集解》,頁268—269。
“復古的高調”與“新變的低音”是唐代文學演進的雙聲,而對南朝特别是齊梁以下文學的理解,即成爲判分的重要標準。史臣文論的意識形態性,讓“復古”擁有了巨大的道德優位,也決定了在詩歌創作上影響明顯的南朝文學更多地以理論上的沉默來保持創作上的實際影響。影響所及,新變的理念也同樣需要在儒學理論的內部,尋找理論資源。許敬宗《芳林要覽序》云:
功成作樂,非文不宣,理定制禮,非文不載。與星辰而等煥,隨橐籥而俱隆,雖正朔屢移,文質更變,而清濁之音是一,宮商之調斯在。……然近代詞人,爭趍誕節,殊流並派,異轍同歸。文乖麗則,聽無宮羽。……以重濁爲氣質,以鄙直爲形似,以冗長爲繁富,以夸誕爲情理。……奔激黄潦,汩蕩泥波,波瀾浸盛,有年載矣。*盧盛江《文鏡秘府論匯校匯考》南卷《集論》,頁1567—1568。
許敬宗以“文質”意涵的重新理解,嘗試完成文學近體化或南方化的合法性證明,其理路與主張四聲論者以《周禮》爲立論依據同一機杼。*劉善經《四聲論》:“齊太子舍人李節,知音之士,撰《音韻決疑》,其序云:‘案《周禮》:“凡樂: 圜鍾爲宮,黄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商不合律,蓋與宮同聲也。五行則火土同位,五音則宮商同律,闇與理合,不其然乎?呂靜之撰《韻集》,分取無方;王微之制《鴻寶》,詠歌少驗。平上去入,出行閭里。沈約取以和聲之律呂相合。竊謂宮商徵羽角,即四聲也。羽,讀如括羽之羽。亦之和同,以拉羣音,無所不盡。豈其藏埋萬古,而未改於先悟者乎?’經每見當世文人,論四聲者衆矣,然其以五音配偶,多不能諧,李氏忽以《周禮》證明,商不合律,與四聲相配便合,恰然懸同。愚謂鍾、蔡以還,斯人而已。”盧盛江《文鏡秘府論匯校匯考》天卷《四聲論》,頁317。高宗時期興起的詩格類著作大體均沿此一思路,而廣其波瀾而已。
史臣對於詩歌體式與詩歌主題的設想,在詩歌創作的實踐中,遭遇了詩歌傳統的抵抗。特别是在詩歌體式上,詩歌自身的演進脈絡決定了詩歌體式的呈現樣態。史臣的南方論述,無疑强化了“南朝”在李唐的影響,在主題的政治性、技法的雙聲性、情感體驗的複雜性以及歷史觀念多元性上均可感受到“南朝”身影的存在。
在唐初史臣對“南方失敗”的闡釋中,過度修飾且逐步偏離共同性主題的文學成爲南方腐化乃至失敗的重要因素。對於文學道德因素的標榜,讓唐初的官方文論不得不重新回歸文質迴圈的傳統思路,南方文學以及文論的成就在複雜的打量眼光中被窄化乃至矮化。雖然史臣所構想的五言古體的典範模式,因詩歌傳統的無聲抵抗,而未能在創作踐履中完美實現,但意識形態的助推,確保了史臣文論對於李唐一代“南朝”主題定位的影響。
(本文作者係蘭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本研究爲國家社科重大基金項目“唐代詩學研究”(12&ZD156)、蘭州大學中央高校基本業務費項目“文學記憶理論研究”(lzu15862001)的階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