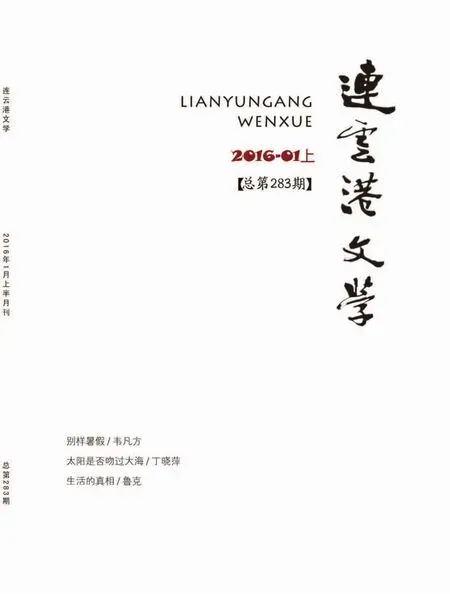行旅看花
2016-11-14吴祖丽
吴祖丽
行旅看花
吴祖丽
牡丹
不太喜欢牡丹,因为它美得隆重,以至浓烈艳丽。过于隆重的东西总是令我生畏。
还因为它的国色天香和雍容华贵,都是离日常太遥远的东西。
一国之色是皇后,要不就是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宠妃。或者是武则天。史料说她,“方额广颐,面如牡丹,堪称国色”。她有牡丹的美艳,亦有牡丹的骄傲,故而才流传出一段“号令百花开,怒贬牡丹花”的传说吧。
幼时,连牡丹图案都嫌弃。
整幅密密连缀着牡丹花的大红被面,只觉得流于俗丽,是属于尘封的过去的。
母亲不理会这些,什么在她眼里都是一视同仁,无不贴心贴肺。有一年,母亲在月季边上种了一株牡丹,第一年什么动静也没有,第二年倒是开了几朵浅粉镶紫色细纹的小花,跟月季没多少分别,看不出国色天香。及至读到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种花必择善地,尽去旧土,以细土用蔹末一斤和之。”白蔹是种中草药,可以杀虫的,如此烦琐和矜贵,牡丹果然不是寻常百姓可以亲近的。
多年之后,在千灯又见牡丹。
轻阴的天色,微带些薄暮,没有雨也像酝着些雨意,正是我魂牵梦萦的江南。
千灯有很多水很多桥,像是另一种形式的乌镇和周庄。但是比乌镇和周庄安静。最重要的是,千灯是昆曲的发源地。
喜欢昆曲,喜欢牡丹亭,有一年时间我的博客门铃一直是“游园惊梦”。细究起来,昆曲和牡丹有某种相似的质地,华丽浓艳的唱词,摄魂夺魄的唱腔,一如牡丹花的国色天香和雍容华贵。
不同的是,昆曲的繁密浓丽里藏不住那一声叹息和苍凉悲寂。像烟花,璀璨的结果,即是湮灭。
随着三三两两的人流,走在青石板街道上,两边乌砖青瓦的人家屋宇相连,木板门陈迹斑斑刻着似水流年,红灯笼下面挑出一个个幌子,写着或是芝麻糖或是熏香豆或是青团子或是老米酒或茶艺馆等等字样,都是有些家世和来历的。
我们一行七八个人,跟着导游走走停停,碧粼粼的尚书浦上停着游船画舫,河水里除了两岸的倒影和落日的余晖外,什么也没留下。岸上的美人靠一溜排虚席以待,并没有美人靠上去,倒是有几个看上去是当地的孩子爬上爬下嬉笑打闹。相比乌镇稠密的人流,周庄浓郁的商业氛围,千墩稍微寂寞些,也从容淡然些,反倒添了点宠辱不惊的气质。
顾坚纪念馆,牌匾是旧旧的红色,似乎正是昆曲的颜色。
转过寂寂的青砖小院,沿着一架红漆木楼梯蜿蜒而上,是个不大的戏台。下面空荡荡放着七八排老凳子,几个镇上的老人坐在斑驳的老凳子上嗑瓜子,闲话家常,等着开场。
戏台正面背景绘着一株牡丹,很大很大,枝叶散开,数不清的花,花团锦簇万分妖娆,却并不富丽典雅。布景黯淡,牡丹花也自黯淡。两边的“出将、入相”处仓促破旧。
想起幼时盖在身上的密密绘满牡丹花的大红被面,反复拆洗之后,泛白泛旧,也是这样的黯淡。牡丹的大红褪成暗红,反而觉出一点亲切。直到有一天,母亲卸下门板,准备糊鞋骨子,她铺上的第一层布就是牡丹花的被面,破了旧了,撕成一块一块,摊在门板上,糨糊刷上去,牡丹花渐渐寂然隐去,像失宠后寂然老去,或者打入冷宫的妃子。我的心里竟起了一些哀伤。
纪念馆后面有个园子,园子很大,没有几个人。四月的春风,带着暖意,吹来满园春色。
绿柳,碧水,漫无边际的迎春和连翘,都是开得正好。
迎面撞上牡丹。牡丹开在断墙后面,一大片的姹紫嫣红,千朵万朵,饱满绚丽。
“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所有写牡丹的诗词里,再不能有好过这一句了。
我立在断墙下,看了看四周,不能置信,竟然只有我一个观众,满园牡丹,如此寂寞。
我半梦半醒,看着这些牡丹,牡丹也看着我。
晚霞映着如染的柳丝随风拂过脸庞发际,隔墙忽有丝竹之声传来,袅袅绕绕,应是方才的戏台开场了:“遍青山啼红了杜鹃,那荼蘼外烟丝醉软,那牡丹虽好它春归怎占的先……”嗓子略微有些哑,吴侬软语中,于缱绻幽怨处带着点寂寞苍凉。
一切都刚刚好,烟花在头顶灿然绽放,对应着牡丹的艳与寂。
野杜鹃
那年去香港,从机场到酒店的路上,一蓬一蓬火红的野杜鹃,不时从车窗一角闪过,恍恍惚惚地像在做梦。
去之前做了些功课,知道香港大学在香港岛西部的薄扶林道以东。每天上课下课都在心里念几遍:薄扶林,薄扶林,薄扶林。
可惜一直到离岛也没去成,张爱玲的港大,注定是要留给我遗憾的。
她与香港有三段缘分:1939年到港大读书,1942年因战争中断学业仓促返沪。1952年以恢复香港大学学业的理由赴港,因种种原由闹了很多不愉快,1955年离港赴美。1961年10月,她最后一次到香港,为了改剧本,曾短暂住在宋淇家中,外面是农历年的烟火熣灿,室内是简陋旅馆的四壁萧条,心中万分凄凉,这里面有着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曲折难言。
回头望去,香港似乎是张爱玲永远的苍凉和悲伤之地。1962年离开,她再也没有回来过。对她而言,想必也是在这里栽个跟头,比别处也痛些的。
早期我们在《烬余录》里,后来我们在《易经》和《小团圆》里读到她记忆中的香港和香港大学。正如她所写:“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生存在车子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道,可是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
可是,她爱香港。不然她也不会一次次以其为背景写下《茉莉香片》、《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和《倾城之恋》。
在香港的八天,每天都被笼罩在张爱玲的作品里,走在骆克道上看到铛铛的有轨电车声,想着这或许是聂传庆和言丹朱坐过的那种。在湾仔路过一处小小的菜场,想到范柳原和流苏的劫后余生,在菜场买了去壳的小蚝,碰到那个冒牌公主,不请自到地要去蹭饭。在浅水湾,看到那月牙形优美到性感的海岸线,静蓝起伏的大海,美丽的白色建筑群,静静停泊的游船。初冬的上午,阳光竟也很好,沙滩上游人寥寥无几,对面就是浅水湾饭店旧址,我想象当年她坐着浅水湾巴士去见母亲,走过干净的碎石子路,路两侧绿意盎然的植物,她的心情却不见得明媚。她们之间,从来都是母亲不像母亲,女儿亦不像女儿。
我们住的地方,邻近著名的红灯区,接待方的沈女士反复叮嘱晚间外出务必结伴而行。果然看到酒吧挨着酒吧,彻夜灯火通明,聚会的人群室内挤不下,都站到街道上,举着啤酒瓶,尖声锐叫,混杂着各种语言。凌晨三四点钟惊醒起身,静静掀起灰色窗帘一角,只见外面警灯闪烁,一个白种男子正伏在楼下的墙角呕吐,他猛一抬头的瞬间,我猝不及防接上两道猫样幽蓝诡秘的目光,寒噤噤的。吓得我退后一步,松开窗帘,静下来想想,其实他根本不可能看到我。
中午开始就有各种肤色的女子散坐在门前,穿得少得不能少了。某天出门路遇一个七八岁男童穿着藏蓝校服白球鞋迎面走来,目不斜视地低头进了侧门,透明玻璃门里看到一个电梯,我抬头看了看上面,楼上居然有住家,阳台上一盆胭脂红的杜鹃正开得泼泼洒洒,爬下铅灰色栏杆。
香港的杜鹃开得比别处都好,这里湿润温暖的气候给了它适宜的温度,从春天开到冬天。可是这里的杜鹃也比别处孤独,四面环海的孤岛,野杜鹃的梦里想必也是蓝色的海水。
在太平山下,走过一段石阶,石阶两边是高大的阔叶乔木,乔木下面匍匐着一丛丛的野杜鹃,绿叶葳蕤,大朵大朵的红花开得铺天盖地,从栏杆那边翻越过来,伸到行人脚上,热情得不容拒绝。一路穿行在野杜鹃的怀抱里,像是穿越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情之旅。
想到《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第一次去见姑母,看到的野杜鹃: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地烧下山坡子去了。
她写过很多花,最让我难忘的还是这一段野杜鹃的描写,每次想起来都有惊心动魄之感,鲜明,浓烈,艳丽,草蛇灰线似的暗示着葛薇龙看似鲜花着锦却险不可测的命运。
站在台阶顶端远眺,是浅水湾一角宝石蓝的大海。那也是葛薇龙看到的海:“杜鹃花外面,是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
十一月末了,气温还在二十五度左右徘徊,海风带着腥咸之意呼呼吹着,阳光透过树叶雨点似地洒下来,着薄衫的我微有凉意,并且无端感到一阵眩晕。
三角梅
初识三角梅,是在昆明。
三角梅是寻常品种,想必见过,但是没有打动到我。
云南温暖如春的亚热带气候中,三角梅生长得异常丰沛和妖娆,让人无法忽略。
黄昏的时候,我和婉儿并肩走在昆明街头,傍晚的太阳将落未落,光线清澈透明,缓缓透过隐隐约约的群山照射下来,映着路边高大的法国梧桐,披散着长发的棕榈树,绿得润开来的龟背竹。
婉儿一路惊呼,这里的树木跟寻常看到的都不同,全变异了似的。
不是变异了,只是遇到了合适的土壤和温度。
就像女人遇到了爱情,容光焕发。婉儿若有所思。
路边新挖的树坑翻开一堆鲜艳的砖红色土壤,一群背着书包回家的孩子,嬉闹着擦肩而过,烤玉米的小车叮叮当当走过,烘山芋的炉子远远送来甜香,金碧广场已经遥遥在望。
婉儿捧着热腾腾的烤山芋站着不动,指着前面问,那是什么花?
只见路边围墙上爬满了火红的花朵,约摸五十多米长的栏杆像是凌空端出来的一处布景,满架红花艳得像是醉了,醉在夕阳中。三三两两的行人走过花下,踩着一地泣红的花瓣,人浑然不觉,花也浑然不觉。
烘山芋的大叔略抬了抬头,淡然地说,三角梅啊。
百度三角梅。紫茉莉科,叶子花属,又叫九重葛、三叶梅、毛宝巾、簕杜鹃等。仔细看看,果然是三片三角形花瓣,中间藏着长长的黄色花蕊,叶片轻柔微皱,质地如纸。
我握着相机,有一刹那的走神,它的美丽里带着一点点满不在乎的不管不顾的神气,轰轰烈烈,甚至喧嚣嘈杂,其实已经在走向另一个极致,端凝而有静气,像是会地老天荒开下去,红永远是红,绿永远是绿。
婉儿着白衣蓝裙站在花下,让我想《绿野仙踪》里的多萝茜。想想云南这一路不都在绿野仙踪里。这一场旅行,她称之为放逐之旅,我隐隐知道她正在经历中年人的情感危机。她不说,我且不问。
再见三角梅,是大理。
我们像一朵白云似的在莽莽峡谷之上左右盘旋,下面是蓝得死寂一般的洱海。婉儿有点晕机,她俯在我耳边说,我怀疑我们会不会就此掉下去,那么洱海会不会接受两个陌生女人的投奔呢?说罢抚脸大笑。邻座是个白皮肤蓝眼睛老外,诧异地扭过头。
飞机转了几圈,终于落了下去。大理机场建在山顶,刀砍斧削,有如神迹。四顾众山茫茫,山风扑面而来,几面旗帜哗然翻飞。
把行李放在宾馆,我们迫不及待去看洱海。大理新城就建在海边,步行不过十来分钟。太阳温煦和暖,街道整洁宽阔,沿街银杏色泽明丽,白云堆积在头顶,像棉花糖似的,踮起脚尖就可以一扯一大把。
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在海边的礁石上爬来爬去,手持小小的网兜,问他在做什么,他说,捉了小鱼回家喂乌龟。趴过去细看,礁石间果然有虾米一样的小鱼在石缝间游来游去。阳光沉沉地洒在海面,一片浮光跃金,苍山倒映水中,白云温柔,大地庄严。
下午,导游带我们去看真正的白族民居。
白族人崇尚白色,其建筑外墙以白色为主调。他们的一切建筑,都离不开精美的雕刻、绘画装饰。“粉墙画壁”是白族民居特色,白族男子都是能工巧匠,天生的画家,家家墙上的花鸟、山水装饰雕刻都必得是这家男主人的手艺。大理男人自古有“雕民”之称。
爱花爱草亦是白族人传统,这里几乎家家墙头都生着一大簇红艳艳的三角梅,衬着白墙黑瓦。
婉儿说,怎么到了大理,红还是这个红,三角梅倒变得朴素大方起来了。
回去的路上,看到一户人家门楣的青石板,上书:苍洱作证。映着门头上红色的三角梅,只觉无比郑重和稳妥。苍山在上,洱海在侧,那是谁对谁的承诺呢?
我的心震了一震了。婉儿也看到了,她悄悄伸过手,握住我的。原来再荒凉怪诞的世界,总也还有这样一些东西,让人心生安定和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