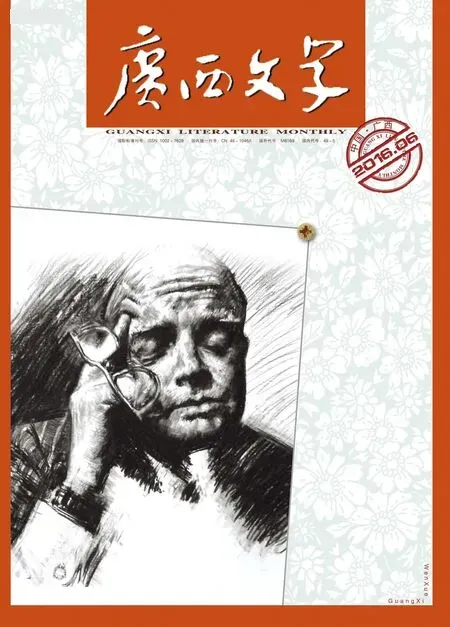会飞的父亲
2016-11-14短篇小说李浩
短篇小说·李浩/著
我再次讲述父亲的故事。我且放入一点儿寓意。
——仿米沃什诗句
1
把我的父亲囚禁起来的是……一次车祸。据说他本可躲过那劫,然而一向善于奔跑的父亲却突然在路中间停了下来,直到失控的桑塔纳2000将他撞飞出去。那是我父亲生命中的最后一次飞跃,那么高,超越了他所能的想象,他感觉自己在天上飞了一天或者更久——这当然是我父亲说的,是他后来说的。等我父亲从昏迷中醒来,他就成了这样子:右腿膝盖以下粉碎性骨折,左腿小腿骨裂,脚踝处粉碎性骨折——医生说,他们已经尽力,但我父亲,再无站起来的可能。买台轮椅吧。
略过和车主的纠缠,和医院的纠缠,和交警们的纠缠,和父亲的纠缠:这些都是让我们心力交瘁的事,不说也罢。坐上轮椅的时候父亲哭了,他哭得相当难看,长长的鼻涕也来不及擦,这些不说也罢。“爸,他们说,他们说,你那天本来可以……你为什么停下来呢?在路中间?”我的弟媳海芸追在轮椅的后面,和车主之间的往来商讨主要由她完成,在我们家,她也最合适——要不是他们咬定,咱爸在路上停了下来,而且路过的司机也作证,我们至少能多得两万块钱。她这一问,父亲哭得更厉害了——但他依然没有解释。
继续略掉这些,不说也罢。我要说的,是父亲的囚禁。在经历了那次车祸之后,他就把自己囚禁在了家里。
足不出户的生活。
2
父亲足不出户的生活是要说的,这个不能省略。
我们先把父亲接到浮阳小区301的楼上——上楼颇费了些周折,那是座面临拆迁的旧楼,没有电梯,虽然已经初冬,等把父亲推进屋里的时候我们几个已经满头大汗。“哎呀,真是累人。”海芸擦着头上的汗,“你和哥哥把东西搬上来,水壶牙刷,被子,别忘了……”这时,我们听到了重重的关门声——父亲将自己关进了卧室。
“爸,你没事吧?”海芸把耳朵凑向门口,她敲了敲门,“咱爸怎么啦?”“出了这样的事,他可能……过几天就好啦。”我妻子拉拉她的手,咱们做饭,让他们收拾东西。
“他不会有什么事吧?”海芸并没有压低自己的声音,“要是……”
“他会有什么事?”母亲阴下脸,这些日子,也真够她受的,“先做饭吧,饭好了再叫他。过一会儿就好啦。”母亲以为她理解我父亲的脾气,然而这次错了。
一切安排妥当,我们当然做得小心翼翼,包括我的弟媳海芸。饭做好了,四个菜,我和弟弟拉出椅子,这时母亲绕过来把其中的一把挪开饭桌——是啊,父亲用不到它了,他,现在在轮椅上。
“爸,吃饭吧。”
“爸,吃饭吧。”里面没有回声,他在里面上了锁,我们无法打开。
“爸,饭熟了,你出来吃点吧。”
“出来吧,孩子们都等着呢。”母亲伸过三根手指,她用出的力气更大一些,“你难受,大家也都不好受。别光想着自己。”——妈,你别这样,弟弟推了推我母亲,我爸怎么会光想自己?你还是让我父亲……
“你看看他,你看他的脾气!”母亲的眼红了,脸红了,她已经积攒了太多的怨怼:“我这一天就容易?我天天提着心,小心伺候,天天看那脸色,我的滋味就好?你想过我嘛,我多大年纪了?你想过孩子们不!孩子们,也是有家有口的人啦!”
“你们吃吧!我不吃!吃不下!”低低的吼叫从里面传出来——“爱吃不吃!我们吃!”母亲的怒气也没有半点消融的意思。
那是一顿缺乏味道的午餐。似乎盐放少了,我弟弟抱怨,海芸的筷子敲到了他的碗上:“怎么就堵不住你的嘴!”
3
需要声明,父亲的囚禁是自己给的,他固执地把自己封在浮阳小区301的房间里,不,他要的是更小的范围:有阳台的那间卧室。他在自己的领地里保持着旧日的专横与威严,只有我的母亲可以进入到他的领地中去,为他收拾、打扫、洗漱、盛饭、倒痰盂——这个小区完成于20世纪90年代,家里只有一个卫生间,在卧室的外面——可我的父亲,从来不肯离开他为自己划定的牢笼,一步也不曾……“你爸这个人”,母亲当然有理由抱怨,她抱怨屋里浑浊着的气息,抱怨我父亲的固执,抱怨被绳索缠住的生活,抱怨……“他这个人,就从来没有过人心眼。光想着自己,眼里只有自己,总感觉别人欠他的,该他的,总觉得连老天爷也对不起他。老天爷对不起你,你耍给老天爷看啊,天天给我吊着脸子,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啦?你说,小便你不出来,没关系,我给你端,大便你还不出来,你们闻闻,那个屋里那个味,你让他们闻闻!”
我们一起来劝慰她,妈,他这不是,不是,病着嘛?你也知道我父亲一向要强,现在这个样子……要有个适应的过程,慢慢地,就好了。你看谁谁谁家,你看谁谁谁,得了脑血栓拴住了嘴,歪着,愣是小半年没出门,现在不……“让谁谁也接受不了。我爸那些年,当体育老师的时候,身体多棒!他还教过我跳高,我总是跳不过去,你家李强也不帮我。”“我跳了成绩能算你的?”弟弟把牙签丢在桌上,“那时要让咱爸看见,哼,他那脾气。”“他那脾气怎么啦,我就觉得咱爸脾气好……”
他脾气好?母亲的火焰又一次冒起来,你问问,家里人、单位上、邻居们哪一个说他脾气好?他看谁都不顺眼,只要人家从他身边过就踩了他的尾巴!人家都叫他李老邪,谁不知道!他脾气好,那是对外人,对八竿打不到的人……“妈,你也别这样说”,我推推母亲,她的声音也太大了,以前,她可不是这样,“妈,我父亲脾气不好,但对人……”你们说,他对你们哪一个好过?从小到大,他怎么对你们?跟你俩笑过亲过?他的心里就他自己,他是个自私鬼!现在,他不出来,他不出来是干吗?还不是折磨别人!
“妈,你可别这么说。”我们继续劝慰,用可能想到的词,用能想到的方法,包括转移视线——“学校里没有来人?他们就一直装死?我爸都这样了他们就不……”海芸把戴着的围巾甩在椅子上,“哥,我们得找他们,他们的教师,不能这样不闻不问。咱爸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人家早来过。”母亲的火焰小了,“那个姓姜的校长,大牙的,他和于华、赵胜一起来的。你爹,就隔着房门和人家说的话,没让人进去。”“他们就空着手来的?”“不是,拿了东西。”母亲似乎不愿意在这事上纠缠,“校长他们说得挺好。就是你爹!拉不出来扶不起来!你们是没看到他那样!”
他们的声音都很大,没有有意地控制,我想我父亲是能听到的,尽管隔着房门。然而,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插过一句话,仿佛他所处的那间房子是独立的、漂泊着的,他和我们隔得很远。很远。
离开小区,弟弟说嫂子我们去你那。好啊好啊,我买点水果,家里没有了。别买了,我们就坐一会。没事,我们自己也吃。
“嫂子,你的围巾和衣服真是很搭,真好看,我也想买一条这样的。李博就是不给买,他有钱也舍不得给我花啊。他外面相好的多了去了。你才是放屁呢。嗯,你说,咱爸这样……要真憋出病来……他可是个要强的人……”
“不要强还不这样呢。这个时候,我们要尽可能地关心他。”
“你怎么关心他?他不要你的关心,根本就不。他门都不给你开。”
“咱爸,也是板的时间太久了。他下不来。你看出院那天,他哭得成什么。之前你见过他这样吗?他总是,总是,本质就是大男子主义。装得多累。”
“他的心里苦着呢。我们不理解他,不可能理解他,说实话他也不希望我们理解。不是说嘛,电视上说的,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
“你听错了!电视上不是这么说的,电视上说的是,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我们是联系在一起的。”
“我没有错,你说,谁他妈的不是孤岛?你觉得你能真正理解别人吗?不可能,绝不可能。海芸,你理解过咱爸咱妈,理解咱哥咱嫂?他们现在想什么你根本不知道。我告诉你,你想什么你自己都不知道,还别说别人了。”
“哼,你想什么我就知道,你想着天上掉馅饼,想着当个科长,想着林青霞张曼玉。”
“屁,林青霞多老了!我现在想的是小甜甜布兰妮,这个你都不知道。”
“对了,咱妈现在的脾气……你们觉不觉得,她的脾气越来越大?”
“是啊,是呢。他们打了半辈子,几乎天天吵,其实咱妈,挺委屈的。咱爸动不了,威势也下来了。那时,我们都怕他。”
“我也看出来了,咱妈现在……她实际是在出气。对了,我还听说,咱妈其实不像她说的那样,她对咱爸……她有时还去打牌,根本不管咱爸。”
“你是听孟大娘说的?她也和我说过。原来我对咱爸,这时觉得,他挺可怜的。这样,待在楼上也不是办法。不好。哎,再把咱爸憋出抑郁症来。”
“哼,以咱爸这脾气,谁能劝得了他?要真是得了抑郁症,我们可就……”
“咱们得想想办法。哥,你说,怎么办?”
“咱哥听咱嫂子的。嫂子,你说,咱们怎么办?不能总让他们这样下去吧。在外人眼里,我们也太……反正好说不好听。像我们都不管了似的。”
在一阵纷乱的七嘴八舌之后,话题渐渐有了核心:不肯出门的父亲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没错儿,他的心里有个固执的结,我们解不开他。我们解不开,就只得继续七嘴八舌,后来,还是海芸有了突然的灵光:“哥,要不这样,你看,你住的是平房,有个院子。咱爸好强不愿意见人,但至少可在你的院子里……”“是啊,哥,你院子里还有桃树、枣树。让他出来晒晒太阳也好。”我的弟弟跟着附和,他略略沉吟了一下,“那样,那样……”“嫂子,你没意见吧?其实这主意也不是我的,咱妈,那天透过这个意思。”“她说什么?说让咱哥接来?”“她倒也没,就是说,怎么也得让你爸见见阳光吧。我说,我们家也是楼房。”“咱妈提到咱哥的院子了?”“倒也没有。咱妈没有直说。”
……送走了弟弟和弟媳,妻子开始摔摔打打:他们就是插好了圈让我们钻。当我们是傻子?这也太明显了吧。“没有吧,”我收拾着桌子,“咱爸也的确是,唉,他这个人。要真是再添别的……”我没有说不管咱爸,我刚才也是答应了的,我恨的是,他们什么都商量好了,然后再做个套让我们钻!比吃苍蝇还让人恶心!你说咱妈要是那么想,为什么不先和我们商量!非要让他们这样敲敲打打!
“我和咱妈说去!我告诉她,这样,我们不接受!咱爸不能来我们这。”
——得了吧,你少来!我还不知道你?算了,我们当然可以接受咱爸,他是我们的家人我们不能不管,但,我们必须点给他们,这样不行,这是欺侮人,根本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这套房子是我们分到的,他们的房子是老人买的,他们倒好,把老人推给我们,还落个孝顺的名声!你看他们刚才,一唱一和,说得都天花乱坠了!
4
母亲拒绝了我们,“你爸,还是待在这边吧。你们上班也忙。”我说我没多少事,再说,母亲你也过去,只是,为了让我父亲有个晒太阳的地方。“对,晒晒太阳好,能心情好些,还能补钙。”妻子接过话茬,“这是海芸想到的,我们当时就没想到。她说你也是这个意思。”“我说什么?我可什么也没说,”母亲沉了下脸,“暂时不过去了,再看看。你爸这个倔老头,真拿他没办法。”“他还不肯出门?都这么长时间了。”“不肯。连阳台都不去。”“妈,还是上我们那边吧。我们是平房,有个院子,就是他不肯,你也可推着他出来走走。”“嗯……”母亲沉吟了一下,“再等等吧。要是我一个人弄得过来,也不麻烦你们。”没事,我说,我们都商量好了,就是那边屋小了点儿,你和我爸在外屋,倒也没有特别不方便的地方。“就是,妈,你可别这样说。”妻子递过纸巾,“干吗要再等?早过去,换个环境,说不定我爸就……”
“我不过去。”父亲打开门。我仿佛,是第一次见他坐在轮椅上的样子——后来,我妻子说,她也有这种感觉,那一时刻,她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我没事。”已经消瘦许多的父亲终于有了耐心,他愿意和我们说话了——“我就待在家里,这里挺好。”
“孩子们也是好心。”母亲站起来,她对父亲在门口的出现也有些不适,“其实,去小浩那也挺好,你也散散心,总闷着有什么好?”母亲朝着门口走过去,而这时,父亲又将门关上了。“我说了不去。”
父亲的话当然有效,我们没有人能说服他,一向如此。“可别说孩子们不管你。”母亲愤愤地说,这,当然已没有任何作用,“他愿意在哪就在哪吧。反正也不缺他吃也不缺他喝。”
余下的三个多月,属于冬季的三个月,父亲就坚持在他的那个房间里,仿佛遭受了某种魔法,使他无法跨越出自己的房门。不过,好一点儿的是,他终于肯和别人说话了,终于,肯让来探望的亲友进入他的空间——是是,是啊。是。没什么。当时,是接受不了。是是。他重复着这些,这些就够了。这些就够奢侈了,相对于之前。不过,人们并不常来,我的父亲也没有那么多的朋友。余下的时间……余下的时间他就在屋里坐着,一个人坐着,从早上的时光一直坐到天黑。其间,他有时会移动几步,追着或避开外面变化的光。母亲说,阳台他是不去的。从来不去。晒衣服,水滴下来,母亲叫他把盆推过去,这点父亲明明能做到,可是,没用,他根本不理。母亲说,偶尔,父亲会围着床转一转,但这样的时候也不多,多数时候他就一个人待着,盯着一个地方看一会儿,睡一会儿。不看书,报纸也很少看。电视,电视在外屋,他没有出来过。“那他在想什么?”要知道他想什么就好啦,母亲说,我就是不知道他想什么,你问三句答不了一句,答也非所问。谁能是他肚子里的蛔虫?憋,憋死他!他就是要折磨人的,他自己不痛快,就不想别人痛快,他见不得别人有一天高兴的时候。“妈,你别这样想我爸,他可不是这样。你想,他一个体育老师,天天蹦蹦跳跳的,一下子变成这样……”他不是这样是哪样?你觉得是哪样?你还能比我了解他?他的心里阴着呢暗着呢!你爷爷就说他,没长出好心眼来。
“妈,你下午打牌,他一个人在家里,不也……”谁告诉你的,谁告诉你我出去打牌了?我就去过一次,那还是你邱大姨看我……她非叫,非要叫,你爸也说你去吧去吧,我才去的……你们就盯着这个!平时,平时我的累你们就看不到!好像我多没人心眼似的,你们又照顾多少?你们,哼,一个个……“妈,我们不是那个意思,真不是,我们是说……”说什么说!母亲哭泣起来,她背过身去——他,就是在折磨人嘛。要是能扔的物件,早就丢了他了。让你们也经历经历,你们就没那么多话了!
5
春节。父亲出事之后的第一个春节。我想,它应当是我们所经历的最为艰难的一个春节,空气最为稀薄的一个春节,甚至是,最冷的。一家人,都付出着小心,仿佛在房间的某处埋藏着小小的炸药,它,很可能因为某句话的火花而发生爆炸,而每个人,在这样的爆炸当中都会受损——一向快人快语的海芸竟然也变了,她竟然也跟着欲言又止,还不时抬头看一眼我母亲或者父亲的表情。雪真大。她说。其实,雪下得不大,远处的屋顶仅有一层薄薄的积雪,犹如一条磨得露出了织纹的旧桌布。她说,瑞雪兆丰年啊,说完了这句话她就咯咯咯咯地笑起来,仿佛这句话里包含着不少可笑的内容。妈,我去那屋,我去剁白菜吧!“不用。我和你嫂子都剁完了。”母亲白了她一眼,“今天不能动刀。”
上午聚在一起,我们寻找着各种可说的话。不过面对家人、新年,可说的话似乎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多。父亲的囚禁还没有完全地解除,我和弟弟几次请他到客厅里去都被他拒绝了,没事儿,我不想出去。也帮不上你们。没有人可以强迫他,不能,尤其是在这样的节日里。临近中午。我们的饭已经做熟,饭桌上备好了碗筷,“咱爸出来吃吧?”海芸手里拿着两双筷子,她向母亲、弟弟和我征询,然而我们真的无法回答她——就在这时,敲门声响了起来。
旧邻居杨伯,我父亲的同事,他带着妻子、儿子和孙子。“老李,你还不出屋?你到底想什么?”他在寒暄之后突然问道。他说这话的时候我的身体颤了一下,仿佛,他点燃了存放着的火药。“走吧,你看孩子们都给你准备好啦。出去吃饭吧,我再坐一会儿就走,还有三个门要串呢。”明显,父亲试图拒绝,他想说不,他的手在使劲,面部的表情在使劲,然而杨伯并没有顾及,他推起我父亲的轮椅,径直把他推到了饭桌前。“你看,你看你,”父亲推推他的手,“你这个人,你,真是的。”父亲显得缺乏力气,他变得弱而小,完全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老李,不是我说你,人,就得乐观点儿,遇到什么事儿说什么事儿。人家不是说嘛,这日子,高兴你得过不高兴你也得过,干吗不给它高兴点呢?”“就是,兄弟,你也是明白人,这个理你肯定懂。过日子就像照镜子,你对它笑它就对你笑,你冲着它哭它也就给你个哭脸。”杨大娘也跟过来,她把我妻子递给她的橘子放在桌上,“有时坏事儿啊也是好事儿,不出这事儿就出那事儿,反正也躲不过,躲过了这一劫说不定有更大的劫。上帝都给安排好啦。人类和世间的万物都是他创造的,他安排了一切。大兄弟,你平时要多念念福音……”“得啦得啦少来你那套吧,”杨伯转了转眼白,“哪来的上帝?完全是走火入魔。你家的经书上说坏事变好事好事变坏事啦?这些话是经上说的?赵之福也就是骗骗你们这些没文化的人,看把你们弄得!”“人家说的都是事实,是你们不肯觉悟……”杨伯的儿子急急插进来,“爸、妈,你们少说两句吧,有什么好吵的?反正一时也吵不明白。”他冲着我笑了笑,“他们两个,天天在家里争,谁也不服谁,谁也不听谁的。我妈是去年信的教,虔诚得很,却连《圣经》都没有读过。对了,你现在的工作……”
“还好,其实上了年纪,信点什么挺好的。”我说,我把烟塞回到烟盒里,“你们就在这里吃吧,大过年的,也不用多准备,就是添几双筷子。再说我爸也特别希望见杨伯,他们那时多亲。”
“你还记得我和兄弟俩人淘气的事吧?把几家晒在外面的鞋子都收起来,里面塞上泥……”“是你干的好不好?我就是提了半桶水,别的都没干!”弟弟也插进来,这时,我家的空气似乎氧气多了些,大家敞开了部分的肺叶,不需要再小口地呼吸。
“你们在这里吃吧,弄点酒。”父亲的脸上有了光,“我这半年……老杨,你坐,嫂子你坐。”
“不啦不啦我们还要串几家,都是老邻居们。还真是想大家。一年到头,就这几天能见到。”
“把他们叫我家来。我还存着几瓶好酒,没让孩子们给我提走。她看不住家。”
“爸,谁偷你酒了?反正不是我。”弟弟给我父亲倒上水,“要偷,就是我哥偷的,他从小就喜欢偷你的东西,偷了啤酒在被窝里喝,我妈来查岗,吓得他洒了一被窝。就是他就是他。”
“哼,我说的是你。”父亲也笑了,他是小偷,你明目张胆。你小子是明抢。——爸,可不来这么冤枉人的!我也就拿过一箱海兴御苑醇,看你记得那么清楚。杨伯,你是我们家邻居,你最知道我们的情况,我哥是不是爱偷吃?我小的时候就没有那个习惯,偷了吃的东西都给他!
“你们忙着,吃饭吧,我们走啦,过几天我再来看你。”杨伯拍拍我父亲的肩,“那么生龙活虎的一个人。唉。不过孩子们好,你有福啊。”“我这算什么福!”父亲拍拍他的腿,不过这时,他的脸色依然是晴朗的,外面的寒意进入不到我们的房间,“就在这里吧,你们能来,我高兴。老杨,老嫂子,你们别走啦。”
我们当然留不下杨伯他们,尽管我们用尽了挽留,用尽了可能的喧哗。临出门,杨大娘拉着我母亲的手,她的眼圈红了:好好照顾自己。妹妹。你也信福音吧,上帝会保佑你的,他爱人,爱信他的子民。我们是一个大家庭。“走啦走啦,”杨伯拉着大娘的衣袖,“什么大家庭?神神叨叨的,让人家也清静会儿。”
杨伯一家人走后,我们家里立刻清静了许多,那里面带有丝丝缕缕的不安和无法说出的东西,它们悬浮在空气里。“吃饭吧。”母亲的声音明显是弱的,她斜着眼看了一眼父亲的脸色,吃饭吧,海芸、慧兰,把菜端过来。李博,把电视关了。
我弟弟没动。是啊,此时,至少有电视的声响,它或许不能吸引我们,但有它在,总比没有会好一些。我们需要这个背景。
6
午饭之后,父亲又退回到自己的房间,这是他的坚持,他说要休息一会儿。父亲说,你们也去串串门,我没事。你们去吧。你们都去吧。他自己移动着轮椅,甚至在经历虚拟的栅栏的时候还略晃了一下身子,仿佛,他的轮椅碰到了栅栏的下沿儿,让他的行动无法保持顺畅。门,在他进入房间之后关出了声响,我和弟弟分别看了母亲两眼,她,没有特别的表情。
当然不能都出去,要再来人怎么办?商议之后做出选择:我负责照看父亲和迎接可能的客人,而我母亲带着我妻子和弟弟弟媳,到邻居和亲友们家里转转。有些人家我们在节前已经去过,但母亲坚持要去,“我没去就等于没去。天天待在家里,有些老朋友都不来往,就生疏了。”她是有道理的,而我和弟弟他们也愿意让她出去走走,过年了,也去散散心吧。
年三十。下午。窗外是阔大的安静,或高或矮的楼房并不能阻挡它,只有零星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提醒此时的节日。我躺在沙发上,把电视的声音放小,不停地换台——净是些虚假的客套、虚假的繁荣和虚假的欢乐,那些突然蓬勃起来的笑脸就像一朵朵塑料花——在我的家里何尝不是如此?我一个人躺在沙发上,一台台地换下去,心里竟有些悲凉。
父亲在他的房间,像往日那样,他接受了囚禁,而根本不顾及马上到来的新年。“爸,”我站到门口去,敲敲门,里面没有声响。安徽台,《西游记》,猴子再次落难,他揪红了呆子的耳朵也无济于事;浙江台,欢歌笑语,镜头不断给到台下的领导和观众们,他们和上次的出现几乎一模一样;CCTV3,欢歌笑语,一片蹦蹦跳跳的红色海洋,和我们房间里的安静有些格格不入。“爸爸,你喝水吧?”我再次站到门口——那个虚拟的栅栏似乎对我也有效,让我多出了忐忑和艰难。“不喝。”父亲的声音。“你自己看电视吧。”
你也出来看吧。大过年的。我用力呼吸了两次,然后拧动门的把手——它开了。父亲并没有将它锁住——我只得走进父亲有气味的空间里,好在他并没有任何不快的表示。“我这条腿,”他敲打着自己右腿的膝盖,“它一直有些麻。好几天了。”父亲说,他的这条腿,从受伤之后就是木的,没有什么知觉,可这几天,它开始麻,有了丝丝缕缕的痛。“这也许是个好兆头,说明,它有知觉了,说不定,说不定……”“怎么也不可能站起来啦。”父亲的脸色黯淡着,像有一层薄薄的灰。“那种麻,让人难受。像小虫子似的。”父亲的手掌放在膝盖上,不停地摩擦着,似乎通过这种摩擦,他的血、骨、肉,便会有了新的连接,便会部分地复活,甚至可以……“爸,我们出去看电视吧,别总一个人待在屋里。今天是年三十。”我强调了一下,今天是年三十,这一天多少与曾经的每一天有些不同——父亲低着头,盯着右腿,没有拒绝。
我推动轮椅,它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有的地方可能锈住了——我的父亲再次离开了囚禁他的房间,那条装在门口的、虚拟的栅栏获得了拆除。“看体育台吧。”
体育台,李宁的广告,NBA球星拜年,安踏和脑白金,然后是冰壶比赛,许多年前的录像——大年三十,最匮乏新节目的就是体育频道了,这一天国内没有任何比赛,而欧洲和美国的比赛因为时差的关系也多是晚上,下午的时间便多是录像和广告,透着一股可以理解的慵懒。而我的父亲盯着,仔细地抻长着脖子——要知道,他,将自己囚禁在狭小的区域之后便再没有看过电视。要知道,久违的体育台曾是我父亲的最爱,之前,他曾霸占着电视的遥控不许我母亲换台,哪怕是广告时间,哪怕是马拉松或者大力士们的较量,哪怕是我父亲看着看着偶尔地睡着了。不行。他在的时候,便只有体育频道,父亲在意这个权利,他要掌握手里的遥控,谁也不能在他在场的时候更换其他频道。此时,他重新回到了客厅,我们的电视很可能就又固定在这个台上。他抻长了脖子,而右手,则一直在揉着自己的右腿:“它,比以前短了。”
我陪着父亲,刚刚从牢笼里走出的父亲,他的出现其实更让我感觉百无聊赖。尤其是缺少新意的电视,这个录像,我已经看过至少八遍,在中国女队刚刚夺冠后不久,下一句的解说词会是什么我都记得,大体不差。而父亲,目不转睛的父亲,则完全像是第一次看那样,甚至还有些紧张,仿佛恐惧录像里的哪个动作突然地溢出原来的剧情,中国冰壶队的冠军就会不翼而飞……
——爸,你喝水吧。
“不。”
——你吃瓜子?这是原味的,这是五香的。
“不。”
——你是不是觉得冷?大过年的,烧锅炉的也不认真。我给你拿件上衣出来?
“不。”
父亲专注于电视,专注于电视里的每个镜头,他不在这边。看着他专注的样子我突然有些心酸,在遭遇车祸之后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他都是怎么过的,在他的内心里该有一股怎样的暗流……“爸,你的腿,是不是有感觉了?这,也许是好事儿。”我绕到前面,“你的左腿,是不是也有感觉了?它麻不?疼不?”
“没有。早废了。”父亲偏了偏身体,他的目光始终粘在电视上,冰壶的录像已经结束,华晨汽车、阿迪达斯、姚明、女排、奥尼尔与詹姆斯,之后是休闲体育,北京蟒山的滑翔。也是旧日的录像。此时的北京正是冬季,树木萧瑟,或有点点的白雪,而电视里的蟒山竟然是初夏时节,郁郁葱葱,绿意盎然。队员采访。我们都是业余爱好者,团队成立于前年。我们来自各行各业,有三个教练。参加的人数……三十几位,我们还去过内蒙古赤峰、河北天目山,下一步的计划是去日本。队员采访:这是滑翔伞,采用的是低重量的织布,能抗紫外线。凯夫拉绳,很结实,不能拉伸,你看,它分成了四组,从前到后,ABCD。是这样。伞翼,你看,翼面分成了上下两层,在这两层之间是连通的气室,由横隔膜隔开……
父亲抻着脖子。这时,他的脖子垂下来,之前他也这样,看着看着就会打瞌睡。我不想打扰他,这个时刻就留给他自己吧。开始,他还在抗争,但慢慢地,鼾声起来了。
7
开门的声音,外出的人叽叽喳喳地回来了,我从沙发上坐起来——刚才,我也睡着了,睡得有些冷。“爸,你也出来啦。”海芸愣了一下,慌忙捂住自己的嘴,“太好啦,咱们一家人看电视。这是什么?好看吗?”
电视上,另一个清瘦的女队员在接受采访:现在的风,嗯,很合适,起飞时需要正对风的方向。滑翔这项运动吧,其实挺简单的,嗯,它对坡度是有要求,一般来说十五度左右就行。嗯,你看,他已经准备好啦,好,他已经飞起来啦……
“爸,这有什么意思?联欢会马上要开始啦,说是有法国一个美女,叫什么,李博就喜欢她。你吃个橘子吧,是我弟弟从广西带回来的,可甜了,无污染无公害。我这弟弟,什么事都想着他姐。你说带着橘子多沉多累。”“他还想着咱家的钱。”我弟弟把橘子的皮丢进垃圾桶,“他说没公害就没公害啦?我觉得他是在市场上买的。”“净胡说八道!你别吃,嫌你就别吃!上次人家给你送一箱酒,你非猜是假酒,非在人家走了之后打开看看,说一瓶也就值二十块钱,酒类专卖的赵四去我们家,他还让人验验!结果怎么样?”“怎么样?他说八成是真的——他说八成是真的就等于说是假的!你反复说是你弟弟送的,人家不能说实话。这你还听不出来!”“八成是真的就等于假的?他没有检验工具当然不能打保票啦!看你这个人,就是一肚子坏心眼,总觉得别人对你就没安好心。也不知道随谁。”“这橘子好。和市场上的不一样。”我接过话茬,“市场上的橘子干,明显是放熟的,缺乏水分。而海芸带来的不一样。”“就是,还是哥哥说得公道。爸,我们准备准备,你换到中央一套吧。”
“不换。”父亲摇摇头,“我看这个就行。”
好吧。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海芸背过身子,冲着我妻子挤了挤眼,嫂子,你看年夜饭,我去给你帮把手。咱爸终于肯出来了,真好。我们过个好年。
“说的什么话?”母亲阴了下脸,“小浩小博,你们把纸给我准备好,看看供品,把香点了。把门也开一下,把这一年的晦气都赶走。”
我们开始忙碌,来来回回,说说笑笑,把我父亲剩在了电视机的前面。滑翔的节目还在继续,此时,它采用的是装在滑翔伞上的“主观镜头”,它在飞,从这个角度可以看见景色的倒退、起伏和抖动。父亲没有注意我们的来来往往,而是,再一次把自己沉进了电视里,他的身体随着镜头的变幻而调整着,或者左侧,或者右侧,或者抬头……父亲在飞翔,一个健全的父亲在飞翔,这时他完全忽略了“在这边”的生活,忽略了自己头上渐多的白发和有着复杂气味的身体,忽略了折断的腿和里面的钉子,忽略了胃痛、绝望和不安——他和电视里的那个飞翔者融成了一个。他听得见风声的呼啸,他感觉得到身体的起伏,感觉得到在气流中攀升时的艰难,感觉得到来自山谷的巨大吸力,感觉得到风打在脸上时的抖动,他……在经过他身侧的时候我偷偷看到,父亲的眼里含着泪水。我将水杯放在桌上,装作没有看到的样子从他身侧绕到背后,拿起扫帚然后又放下:按照风俗,这一天的地,是不能扫的。
“爸,咱们换到中央一套吧,”海芸凑到父亲的身边,“时间到啦。预告上说,今年的节目都挺好的,还有意外的惊喜。前几天就预告呢。”——你就让咱爸看吧,弟弟将她拉到一边,我觉得这个节目挺好。我也喜欢。“这有什么好看的?”海芸依然茫然,“还不如看篮球呢,还能看看姚明。排球也行,中国女排那些年多好,多给咱长志气,这两年不行,成绩下来了。得换教练。”——就你懂。你什么都懂。弟弟的表情有些特别,他推着海芸的肩:哥,咱们等会儿要不喝两杯?你不是不服嘛,看你今年的酒量长了没有。“得了吧,不喝了,”海芸动了动身子,压低声音,“咱爸这样,你们还闹。别让他们不高兴。”
“喝、喝两杯吧。”父亲转过身,电视里的飞翔已经结束,它重新是安踏、李宁、华晨汽车、平安人寿、阿迪达斯和姚明的时间,“我也陪你们喝两杯。”好,好好!父亲能有这样的态度绝对出乎意外,我们包括我的母亲,都有种“受宠若惊”的忐忑,很怕它会转瞬就被摔碎。“妈,拿我爸存的好酒,你可别舍不得!”弟弟冲着母亲叫喊,他的声调都有些变。
“你俩自己去挑吧。在阳台上有,在床底下也有。我得看着锅。”
好,弟弟拉着我朝阳台的方向走去——咱爸今天……不太对劲。你看出来了吧。有什么不对?我用同样低的声音回他,随手拉上阳台和父亲卧室之间的玻璃门。咱爸哭了。我看到了。我以为你没有看到呢。之前,他可不是这个样子,别看他装得若无其事。我怕……你怕什么?我怕,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感觉,不安。怕有什么事。没事儿,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不会的。他坐轮椅,不方便,没有机会。可他哭了。除了出院那天,我就没见他哭过!我觉得,咱爸是,刚才太投入了。他看人家滑翔想到自己的腿。没事当然好,大过年的,我也怕咱妈,到时候再多说几句,让他想不开。你知道咱妈那性格。都大半辈子了,他们谁都知道谁,没事的。不过我们今天是得小心。不知道咱爸想什么。要不这样,等过了十五,天暖和一点儿,我把咱爸接到我们那去,海芸那种大大咧咧的脾气,反而让咱爸没办法,他还挺接受的。要接,也要接到我那里去,至少让咱爸在院子里转转,晒晒太阳。我觉得咱爸,是抑郁症。我看书上介绍的症状,挺像的。书上说抑郁症……不好治,好多病人都挨不下去。那天回去,海芸还和我辩了一路,她说人就是孤岛,有时想想,也在理。你说像咱爸这样,让我们怎么理解他?
“酒选好了没有?”外面喊。“马上,”弟弟抻长脖子,然后又转向我:他要真是抑郁症,要再厉害些,咱妈根本弄不了他。别把咱妈也弄病啦。那时候,我们就有得受啦。我们也不能不管他。要不别人怎么看咱俩。别人怎么看咱俩倒是小事,关键是,我们怎么做也不可能称他的心,而工作……我那单位你也知道,总加班,以后。唉,想想都有点后怕。
“你们选的酒呢?”母亲推开门,探进半个身子,“快点,菜都凉了。让你爸都等急啦。”“马上,”弟弟抱起两瓶金剑南,“我这哥哥就是嘴馋,他非要找茅台,还说越陈的越好。”“茅台,可能还有一瓶……”“算啦算啦,我们就喝这个,凭什么他想要什么就给他什么?不能惯他这个毛病。”
“哼,你的毛病就少。”父亲移动着他的轮椅,“让你妈找找那瓶酒。要是没有了,肯定就是你给我偷走的。”“爸,可不能这样冤枉好人,”弟弟笑着,“你的意思是家贼难防对不对?我在你眼里就这样不堪?我都是副科长了你知道不?也是个人物呢。”
电视里一片喧嚣,有一种热闹的喜庆:它,已经转到了CCTV1,在欢跳着的孩子们中间,衣着靓丽的主持人们在向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拜年:祝愿大家新年快乐阖家幸福事事顺意健康平安……
8
噼噼啪啪的声响时远时近,我们家的气氛也调到了之前所没有的,哦,我不知道该用一个什么样的词,反正,我们显得合适地欢乐着,仿佛有些事不存在,有些事没有发生,至少是不关于我们——我们被电视里的欢笑感染着,尽管,尽管没有一个人愿意送出好评。《想你的365天》、《万马奔腾》、《时间都去哪儿啦》、《英雄组歌》,苏菲·玛索也等到了,和她一起上场的是刘欢,小马奔腾——哪来这么多的马。真是大马小马老马一个都不能少。弟弟抱怨,他的抱怨让我们又笑起来,我们笑得精彩极了。父亲也融在我们的笑声里,他不再是格格不入的那个人,至少表面上如此,他甚至比之前的每一年都更融入些。“你别喝了,”母亲劝阻,“让孩子们多喝点,你们俩也喝点酒,别总是饮料,有什么好?”“没事儿。我清醒着呢。”父亲端起酒杯,把剩下的半杯又倒进了嘴里,“你们也喝点吧。”“嫂子,要不咱们也喝点?大过年的,让咱爸也高兴。”海芸将第二瓶酒打开,“我也不爱喝饮料。谁知道里面添了些什么东西!我从小就不爱吃甜的。”“得了吧,你还不爱喝饮料,咱家那两箱露露都让谁喝啦?我说少喝点吧,哼,人家还有理由,美容。要长成杏仁的样儿不吓死人。”“我不是听小巧说的嘛!她说能美容养颜我才喝,要不,我一口也不喝它。让咱爸咱妈评评,我说一句你就顶一句,我说一句你就堵十句,一年到头就没说过我一句好话!”“褒贬是买主,这都不知道,明显是智商不够。行啦老婆,我知道你也不容易,天天忙,今天我敬你一杯酒表示表示。”“表示什么?怎么表示?我要香奈尔、LV,从去年就说给我买,都一年了。光让嘴哄不管用。”“别敬酒不吃吃罚酒,香奈尔、LV当菜篮子好使?让你提着也是地摊货,别糟蹋人家啦。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咱是小职员,不是大富翁,没那个命啊。”“我敬你们俩吧,”我冲着海芸和我妻子举了举杯,“你们是不容易,感谢你们。”“看咱哥,多会说话,你也不学着点!”
就在这时母亲突然哭了起来。妈,你怎么啦?“没什么,没事儿,”母亲用手捂着自己的脸,她依然在哭泣中,“我是在想,这一年,这一年……谁理解过我啊?”
好说歹说才把母亲劝住,把她劝住之后我们才想起父亲来。他还在,当然还在,就坐在轮椅上,端着酒杯,像一块朽了的木头。窗外的噼噼啪啪响得更热烈起来,郭冬临、牛莉的小品《人到礼到》也演至了一半儿,母亲把自己的失控怪罪在节目上:他们总说祝你平安祝你平安,说得人……她当然有些强词夺理,《祝你平安》是十几年前的旧歌曲,并不在春晚的节目单上,但我们没有将它看成是漏洞去拆穿它。
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爸,你别喝了。”弟弟朝我使了个眼色,他把余下的酒分别倒在我和他自己、我妻子和海芸的杯子里,“咱们也加快点速度。愿爸爸、妈妈,新的一年里,能快快乐乐的,再难的事,我们一家人一起面对,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如我们的多了去了。高高兴兴是一天,生气郁闷也是一天,我们干吗不让自己快乐一点高兴一点呢?”“妈,就是这样,凡事往好处想,多往好处想,别总让自己沉在负面的情绪里。又起不到作用。”
这时父亲涨红着脸,笑起来。
“爸……”
我没事,我是真没事儿。父亲依然笑着,他笑得眼泪都下来了:刚才那个小品,哈哈哈。太有意思啦。人们说生活远比小品精彩,瞎说,还是小品精彩,精彩得多。
“爸……”
我没事儿。唉,想想自己这一辈子。再给我倒杯酒。“爸,不喝了,咱不喝了。妈,你和嫂子去煮饺子去吧,时候不早啦。”我就再喝一杯,我知道自己的量。刚才,我喝了那些酒,感觉两条腿都是热的,连左腿也在发热。刚才我在想,去年过年的时候它们都还好好的,不疼也不麻,现在它们也好好的,不疼不麻,可我怎么就坐到轮椅上了呢?早三分钟晚三分钟,都不是这个结果。可我就是赶上了。你问我怎么在路中间不走啦,我不知道,我想了三个月自己都没有明白,越想越觉得奇怪,我怎么跑到路中间去的,又怎么不动了?我以为是车灯晃的,后来想不对,那是白天,不可能开车灯。我怎么走到那条路上去的?因为什么事?我也想不起来,完全想不起来。
“爸,那事,已经过去了。想也没有用,也改变不了什么。我们向前面看吧。日子还得过啊。”
日子还得过。父亲点点头,他脸上的红在灯光下似乎更厚重些了,谁让自己遇上了呢?好吧,你们接着喝,我回去睡。让你妈来扶我。
“爸,你再等一会儿。”海芸挡住我父亲的轮椅,“吃几个饺子,过年嘛,饺子一定要吃。多吃点顺。”我和弟弟也跟着附和:饺子马上就熟,你再等会儿吧。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站在高岗上,朱军和李思思在电视里提醒,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让我们在新年开始之前许下自己的愿望……
“爸,你也许个愿吧。”弟弟的眼色并没能制止住海芸,“我的新年愿望是,一家人都能快快乐乐的,最想做的事是,去云南旅游。”“得了吧,我还想去西藏呢,”弟弟拉拉她的衣袖,“油里是你酱里也是你,就你的事多。”“我怎么事多了,我又说错什么啦!”海芸甩开弟弟的手,“哥,你说,我让咱爸说他新年的愿望算话多吗?我不是,想让大家高兴,让气氛好一点吗?在家里你就这不让那不让,我活跃一下气氛又不对啦?”
对对对,好好好。父亲打了个嗝,他的脸已经变得更红,呼吸也更粗重起来:你得让我想想,一个瘫子能有什么愿望。
“爸,新的一年,你最想做的事是什么?我们帮你实现。”
“嗯……”父亲沉吟一下,这时,厨房里的母亲和我妻子已经打开了锅盖,饺子熟了,热热的气带着饺子的香传进鼻孔,“我想,”父亲说,他孩子似的,伸开两只手,做了个鸟类扇动翅膀的动作:
“我想飞。这样的日子,我实在是,实在是过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