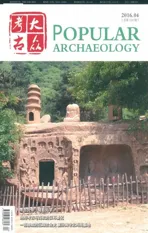儒家世界中的“教堂”与基督世界中的“宝塔”
2016-11-12戈畅
文 图/戈畅
儒家世界中的“教堂”与基督世界中的“宝塔”
文 图/戈畅
明清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沟通中国与世界贸易的重要航线,同时也是中国与欧洲文明得以相互沟通的媒介。晚明时期,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在华传教,标志着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开始在华传播,从此中国出现了“教堂”。随后,欧洲的园林中也出现了中国的“宝塔”,甚至弥勒佛成为家庭摆设……这种异国文化符号的交流互动,都以海上丝绸之路开展的贸易活动为基础。

圆明园西洋楼之远瀛观
温州博物馆副馆长伍显军先生在《论温州在“海上丝绸之路”史上的重要地位》一文中指出,“海上丝绸之路”是相对于“陆上丝绸之路”而言的抽象空间概念,实际上并不单指某条海上路线,而是对所有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科技、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的统称。晚明“隆庆开关”以后,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不仅增加了中国的对外贸易量,也使中国与异域文化频繁交流成为可能。同时期,新航路的开辟使欧洲人主动地加入与中国的贸易与文化交流之中,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先后建立。欧、亚两大陆之间的交往与日俱增,彼此隔绝的状态逐渐被打破,世界开始形成一个整体。在这个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宝塔和教堂分别作为中国和欧洲的标志建筑,是各自文明特征的缩影。中欧两地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来自异域的“教堂”和“宝塔”,这种文化符号的错位交融是因海上丝绸之路的连接而产生,是中欧贸易的历史成果。
传教士与“中国热”
新航路的开辟给欧洲人创造了了解中国的绝好条件,也激发了天主教会向远东传播福音的热情。早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就有对中国的详细描述,并由此引发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强烈好奇。但是让欧洲人看到真实中国的文字表述,源自传教士们的书信著录。
冯国荣和侯德彤的《中学西渐的历史线索及相关研究课题》中说道:“传教士东来的本意是传播宗教,但许多传教士来到东土后发现中国文化的昌明成熟,自觉不自觉地担任了中学西渐的桥梁。”明清时期,来华的传教士们多隶属天主教会的各系修会,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由圣依那爵·罗耀拉于1534年创立的耶稣会。在华期间,他们不仅传播着来自欧洲的宗教信念、文化、艺术、科学等令中国人耳目一新的新鲜事物,也将他们在华的所见所闻著成书录寄回欧洲,成为欧洲人了解中国风情的重要渠道。
18世纪,源源不断销往欧洲的中国物品再加上传教士们的在华文字描述,给欧洲人现实和虚幻的世界中渲染出一个神秘、富裕、和谐的世外桃源,最终使得欧洲兴起了“中国热”,其表现就是欧洲人对中国物品的狂热迷恋、对中国风格的执着追求,因此“中国风格”(chinoiserie)风靡欧洲,皇室贵族以拥有中国瓷器为荣,庭院中出现了中国风格的亭台楼阁,甚至还有宝塔。
传教士东来的本意是扩大本国教会的影响力,而结果却与他们的初衷大有区别——天主教和西学没有顺利地在中国广泛传播,反倒是他们的对华传教过程,加快了中国文明在欧洲广泛流传,使欧洲人狂热地追逐起“中国风格”。同样,渴望把宝塔盖到欧洲去的想法,也是出于欧洲人自己的意愿。

澳门大三巴牌坊

北京西什库教堂外景
建立异乡的“教堂”和“宝塔”
教堂和宝塔既是欧洲与中国各自的典型宗教建筑,也是两地的文化符号,自利玛窦开创了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先例之后,中国人的信仰世界中出现了一位新的神——上帝,此后欧洲风格的教堂建筑开始在中国建立。
天主教在华传播,带来的不仅有关于救赎的宗教信念,伴随其中的欧洲文化与艺术风格也随同进入中国,所以这些教堂建筑往往带有强烈的欧洲风格:
澳门的大三巴牌坊是始建于1637年的圣保禄教堂的遗迹。“三巴”是“圣保禄”的粤语音译。晚明时期,由于官方施行海禁,来华的传教士不能直接进入中国,而葡萄牙人拥有在澳门的居住权,所以澳门就成为怀有“中国梦”的传教士们的第一站。1835年的一场大火使教堂仅存今日所见的正门大墙,这座大理石建筑具有欧洲巴洛克的艺术风格,墙体的雕塑体现出与《圣经》相关的内容。尽管大三巴牌坊的装饰元素中出现了汉字以及石狮,但它整体上是一个欧式风格的建筑。

邱园宝塔
随着传教活动的深入,传教士们的活动范围也就不再局限于澳门,开始向内陆发展,甚至到了皇城北京,例如始建于1693年北京的西什库天主教堂,就是传教范围不断扩大的结果。 它是典型的哥特建筑——这种起源于法国13世纪的建筑风格被完整地移植到东方。
传播教义固然是传教士们的首要工作,但也不仅仅局限于此,西方的科学、历法、医学等西方文明也通过传教士们被带进了中国,传教士还曾承担起皇家园林的设计和施工。圆明园的西洋楼建筑群就是在郎世宁、蒋友仁等耶稣会传教士的共同参与下完成的。
传教士们在华的福音传播并非为欧洲文明传递至中国的单向运动,欧洲人也正是通过他们了解到更加生动、真实的中国,甚至中国佛教寺庙中的宝塔被欧洲人模仿进了他们的园林中,这要归功于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节纽浩夫(Johan Nieuhoff)。他在《中国出使记》中所详尽描绘的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使宝塔成为中国建筑的典型式样。
1761年,英国人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通过瑞典东印度公司到达广州,期间收集了大量与中国建筑、园林有关的资料,并于1761年在伦敦的邱园(Kew Garden)建造了一座十层宝塔,成为欧洲的第一座中国塔,其正是以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为摹本仿造。
以南京大报恩寺塔为摹本进行仿造,以表达对中国元素的渴求,并非英国邱园的孤例,邱园只是这个仿造热潮中,仿造得最到位的。
“南京塔”的缩影在欧洲其他国家的宫殿或公园中也能找到,尽管它们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相似。例如,由瑞典国王阿尔道夫·福雷德里克于1753年下令秘密建造的中国宫,它的外形和宝塔实在难以相提并论,但瑞典的史料却称中国宫的建筑灵感源于南京的宝塔。
在德国的慕尼黑,也有一座类似宝塔的建筑,与“南京塔”相比,它不仅层数上缩减很多,造型也变化很大,而这类的形变中渗透着当时欧洲人对神秘东方文明的无比向往。
在波茨坦的无忧宫内,拥有一个具有“中国风格”的“中国楼”,这是从未离开过欧洲的腓特烈二世凭借自己对中国符号的想象和向往,凭空臆造出来的,除了勉强与蒙古包相似之外,它并不是那么的具有“中国趣味”。尤其是大帝为了营造更加浓郁的东方情调,在建筑的门柱下安置的镀金“中国人”塑像,他们看起来完全是戴着草帽的欧洲人而已。

大报恩寺琉璃塔

现代大报恩寺遗址公园
大报恩寺位于南京市秦淮区中华门街道雨花路东侧。此区域东吴时建有阿育王寺,又名长干寺,宋为天禧寺,元改为慈恩旌忠寺,元末毁于战火。明成祖朱棣修大报恩寺,寺内天王殿、大雄宝殿、佛殿、观音殿、祖师堂、法堂等。在大雄宝殿后的大报恩寺塔,被当时西方人视为代表中国的标志性建筑。塔高110米,九层八面,每层的覆瓦和拱门都用五色琉璃砌成,拱门上塑有飞天、飞羊、狮子和象等五色琉璃构件。清咸丰六年(1856),寺、塔毁于兵燹。今地面存香水河桥、北宝塔根井、永乐二十二年(1424)立大报恩寺碑的龟趺、宣德三年(1428)立的大报恩寺碑和三藏殿等。2008年开始,考古工作者从大报恩寺遗址宋代长干寺地宫清理出土了一枚“佛顶真骨”、“感应舍利”、“诸圣舍利”以及“七宝阿育王塔”等一大批佛教文物,入选“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3年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底大报恩寺遗址公园建成开放。

斯德哥尔摩中国宫
除了宝塔以外,佛教中的弥勒佛也在欧洲人的生活中出现,在法国画家弗朗索瓦·布歇(Francois Boucher)的作品《早餐》中,来自中国的弥勒佛憨态可掬地端坐在靠墙的架子上。
尽管带有中国佛教色彩的宝塔和弥勒佛能在笃信一神论的欧洲基督教世界传播开来,但它们并不意味着欧洲人皈依了佛教,事实上他们完全不知道佛教的存在,其原因离不开传教士的刻意为之。清华大学历史学系张国刚教授在《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中认为:“耶稣会士在他们的作品中也都繁简不一地提到中国的道教和佛教,但口气都是轻蔑不屑的,认为它们根本不能成为真正的宗教。”他们需要的是强调中国人具有纯洁的天性以及接受基督纯正信仰的根基,以此证明耶稣会具有实行适应性传教的依据。

慕尼黑中国塔

中国楼门柱的“中国人”

波茨坦无忧宫内的中国楼

布歇《早餐》
张国刚教授还写到:“如果太突出佛教和在佛教下沉沦的道教,当代儒教对中国人的影响,那么耶稣会士所树立的中国人的纯洁天性就难以成立,进而其传教策略也失去基石。所以,对佛教与道教轻描淡写也是有意为之,意在让欧洲的读者们不要太注意它们,忽略它们在中国社会的力量。其实耶稣会士李明(Louis Le Comte)的长篇大论根本没有说明佛教的教义,还不及曾德昭(Alvaro Semedo)说的清楚。佛教教派是和尚们领导的传播迷信、招摇撞骗、混淆视听的宣扬偶像崇拜的危险团体,虽然蒙蔽了许多无知者,但中国的有识之士并不承认它。而这也正是李明和大多耶稣会士所希望读者产生的印象,他们不需要欧洲读者对佛教有太多兴趣,或者他们自身也并非都清楚佛教是什么。”正是这个原因,欧洲人并未完全明白宝塔和佛教之间的真正关系——欧洲的宝塔往往在公园、庭院或喷泉中出现,都不是凝聚信仰的宗教场所。在“中国热”流行的18世纪,中国的宝塔可以作为欧洲庭院中最为靓丽的装点。清华大学建筑系陈志华教授《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影响》一文中说到:“高耸的塔点染风光的能力很强,何况,塔的异国情调最浓,同现实生活相去最远,最能投合浪漫主义思潮。”陈志华教授还提到:“宝塔和教堂分别代表中国和欧洲的文明符号,它们最终在另一个国度出现。这两种文明能够得以顺利传播,它既是明清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原因,也是在其形成作用之下的结果。”从外在形式来看,中国和欧洲各自吸取了对方文明的元素,并在各自的土地上生长,但是由于各国思维方式的不同,对彼岸文明的认知能力和程度也存在巨大差别。
(作者为南京博物院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