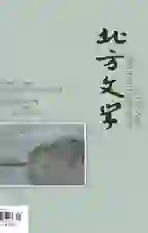憾溢盈圆,是为美
2016-11-10蔡云
蔡云
摘要:“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在《红楼梦》的审美长卷中,充满了无可奈何、人生空幻的“辛酸泪”,充盈了艺术再造的无缺之“缺”和无梦之“梦”。曹雪芹在“梦”中高唱“好”“了”之歌,以“情美”之“缺”来“用心”和“运思”,将喜、怒、哀、乐、爱、恶、惧真实的展现在了文本之中,以“心镜”映照出“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的幻灭,用“痴人说梦”般的“诗性智慧”道出了生命崇高的真实——人生如梦,万境归空,生命本真的回归回溯写满了缺憾之美。
关键词:《红楼梦》;曹雪芹;缺憾美;真;情;梦
在《红楼梦》的审美长卷中,无处不充盈着世界之幻化,人生之百态。无疑,红楼世界自身已幻成了一个完满的生命体,其“向死而生”,一步步走向毁灭,写满了缺憾,时时吟唱着动人的生命挽歌。生命是“灵魂”与“肉体”的自然之“化”,既是形而上纯净之美的象征,又是形而下剽悍之美的载体。《红楼梦》从生命的本情出发,勾勒出美美与共的“群芳髓”,衍生出“千红一窟”、“万艳同杯”的哀伤,使其圆融的生命体位“上”“下”归“一”。一个作家,一缕情思;一部作品,一种真实;一位读者,一场梦;一方世界,万种情。
一、缺缘于情
《红楼梦》作为一部“世情作趣”、“大旨谈情”的“痴”书,它“厚地高天,堪古今情不尽”,凝神于“情”而钟于“情”。在《红楼梦》中,脂批慨叹宝玉虽然悬崖撒手,到底“跳不出情榜”去,可以说曹雪芹是看透了“情”中的破处、缺处,方才“研泪为墨,滴血成字”,憾此人生,以情写书。而人生、命运不过是个体身上一层轻薄的架纱,人本身,才是这场缺憾的终极指向。《红楼梦》中曹雪芹让“缺憾”同人物之心齐跳,让“他者”替古人担忧,为熟悉的陌生人掬泪。
就爱情而言,《红楼梦》为我们谱写了一曲令人心驰神往的华章,然而这其中跳跃的音符却是“嘈嘈切切错杂弹”——有无尽的缺陋交叉跑动。以宝黛的爱情为例,他们的知己之爱或显或隐的闪烁着平等、独立、自由的光芒,因此,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部“才子佳人”小说的感情分量。“林妹妹不说这些混账话;要说这话,我早和他生分了!”宝玉早已挑明了他的态度。所以,宝、黛二人因共同叛逆着、因心心相印、因思想信仰上的一致而成为挚友、成为知音、成为至爱。这是多数前辈所论及过的,然而,某些细枝末节的特殊感情信息、一些爱情之微小的“不忠”“不专一”之处也即一些缺陋之处,亦更增添了宝、黛爱情的光泽。不同于张生和崔莺莺的“郎才女貌”,宝玉视那些个齐家治国的高姿态的人生理想为钓名沽誉、聚财敛货的龌龊的个人私欲,却在大观园里流连忘返,他“爱红”、“偷着吃人嘴上擦的胭脂”,曹雪芹以大而化的笔意熔铸了小而细的生活常态,写出了宝玉的“痴”“真”,这些都是不为当时那个时代所接受的诟病和残缺。而黛玉虽有一身的才华,却“态生两屠之愁,娇袭一身之病”、“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相比之下,宝钗却“生得肌骨莹润,举止娴雅;肌肤丰泽,胳搏雪白;脸若银盆,眼同水杏;唇不点而含丹,眉不画而横翠”,以至于宝玉的情感总是徘徊在“专注”和“走神”的矛盾状态之中,他常常“见了姐姐”就“忘了妹妹”,常常在下意识中被薛宝钗“杨妃”式的丰采,以及温文尔雅的气派所吸引,有一回竟忘形得如同“呆雁”!他常常在钗、黛双峰对峙时无所适从,这是贾宝玉一个不大不小的“毛病”,是小小的“不忠”。然而正是这样的缺陋,这样的“意淫”式的痴情,反而透露出宝玉性情的真、纯、热诚和执着,也真切的击中了少男少女青春期的情思——容貌在初恋男女之间,是一个相当敏感的因素,写出了真的“情”。同时,由于共同志向在爱情生活中的主导作用,宝、黛的爱情在才、貌、情趣等因素之间发生抵触之时,如此有缺陋而又完满的“情”的因子则往往会微妙的行使自己的“否定权”。这样,就产生了情感和理智的矛盾,迫使主人公在反复权衡之后做出合乎逻辑的抉择,更加真切的表现了这种细枝末节之处由于缺陋而导致的爱情的痛苦和点点滴滴密麻的折磨。
红楼世界中的亲情、友情、悲情和其他人情世情也皆是如此,得缘于“情”而又皆是在缺憾之中使“情”更加圆满,呈现出溢美之光华。
二、憾显于真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悟吟志,莫非自然”,《红楼梦》中无处不跳跃着“情”之因子,跳跃着喜、怒、哀、乐、爱、恶、惧。在红楼世界中,各种情绪情感因缺憾的填充、因生命的灌注而更加真实、愈发自然。“艺术用感性形式表现最崇高的东西,因此,使最崇高的东西更接近自然现象,更接近我们的感觉和情感。”[1]曹雪芹以缺写情,进而以憾显真,通过完整严密的生活现象,把握事物的精神、灵魂和特征,一步步吸引着读者去接近那“最崇高的东西”,去触碰他所想要表达的“真实”。
晴雯,便是红楼世界里这样一个动人的女儿,是曹雪芹所塑造的“心比天高,身为下贱”却像芙蓉一样晴朗、芬芳、高洁的反抗之奴。曹雪芹以她的生命个体,隐约表达着对封建皇权官僚体系下的思想奴化、不自由的愤怒和对人生幻灭无奈的悲哀。所以她撕扇子作千金一笑,敢于蔑视森严的封建秩序,公然向主子表示自己的不满;她指责秋纹被主子的“恩典”弄昏了头,高呼“一样屋里的人,难道谁又比谁高贵些”;她病补孔雀裘,一针针,一线线,力尽神危的补到了黎明,显示了善良、纯真、重感情、见义勇为和心灵手巧的动人风采;她临危不惧,面对抄检大观园的狂风暴雨,始终保持着进攻姿态,把为虎作伥的王善保家的痛斥了一顿;她抱着屈辱夭折于所谓的“风流”,在生命的终点上,用强烈得不能再强烈的方式,向一个高贵的公子表露了火一般的爱情……这些生活现象无疑贴切的表达了他想要表达的信仰和愤怒,然而他的笔墨却不止步于此,曹雪芹没有采取“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多智而近妖”的笔法,而是让高洁的芙蓉女儿沾染了一些“污泥”,表现出一些不那么雅观又令人迷惑的缺陷:她赌钱,豪饮,猜拳,闲逛,似乎过着“游手好闲”的“二层主子”的生活;她动不动就支使小丫头们干活,声称:“等你们都去尽了我再动不迟。有你们一日,我且受用一日”;她常常责骂做粗活的奴婢,一会儿叫嚷“揭你们的皮”,一会儿扬言“拿针戳你两下子”,分明觉得自己比这些小丫头们高贵些;她为了坠儿偷虾须镯的事,甚至取了“一丈青”向坠儿手上乱戳,最后还自说自话的把坠儿撵了出去!她是如此的凶辣和不近人情……反观之,又正是这些缺陋之处映衬着晴雯这个小生命体的真实性,它包含了一个小个体全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从而使得“最崇高的东西更接近自然现象”而不至于失真。
然而,“霁月难逢,彩云易散”,这样一个完满灵动的小生命体晴雯最后却落得个“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诽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的下场,令人读之断人肠,大憾也!曹雪芹在红楼世界中多次以此“缺陋”之处勾连起我们的怜悯和哀挽之情,以“更接近我们的感觉和情感”的如椽巨笔,让人感觉缺憾之血充盈了整个心脏!那缺憾的点滴凝结而成血色之美也因此而更加的光鲜亮丽!
三、美幻于梦
刘长卿诗云:“心镜万象生。”红楼一梦“真”的如诗般梦幻,那“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无不灿然于其中矣,那“梦”的“幻”,幻出了“真”的“情”,“真境逼而情境生”。“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红楼一“梦”谜于“痴、凝于“情”而显于“真”,“真”“情”之中处处洋溢着“美”的颂歌,而每一曲歌唱的旋律和音符都迷濛的涤荡在“梦”之中,曹雪芹正是用如此“痴人说梦”般的“诗性智慧”道出了生命崇高的真实,唱出了生命“美”的真谛。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将眼中的所见所闻,心中的所思所感都幻化成了一股股与心意相通的“意象”,他心中有一座“红楼”,有一处“太虚幻境”。“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那红楼是“花柳繁华地”、“富贵温柔乡”,每个生命个体都会在那“红尘”“潇潇洒洒”走一遭,然而终究会回到“大荒山”回到“无稽崖”回到“青埂峰”之下,回到“彼岸”的“太虚幻境”,画完生命的圆圈。那圆的圈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人生舞台,可以展示亲情、爱情、友情,可以展示真、善和美,它能大能小,能简能繁,能动能静,能冷能热……然而圆圈滚来滚去,却终究找不到真正的立足之境,弄不清“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枉入红尘若许年”,身前身后依旧有如一片云烟一场梦。
梦是完满的,也是残缺的——“好便是了,了便是好”。它亦真亦假,虚虚实实,充满了幻象,曹雪芹寓意“情”的境地终为虚幻之境,而整个红楼世界也终不过是虚幻世界大梦一场,同于开篇回目所言的“梦幻”之境。他用假语村言将真事隐去,同时,他又将读者引入一个关于真假有无的哲理思辨的环状怪圈,既以迷宫式的深邃获得了美学无限,又在哲学上触及到纯粹的思辨层次,同时掩饰且提示了往返于真假中的创作真实。他旨在说明人生如梦,万境归空,历世的石头要回归大荒山,而做梦作小说的人最终要归于生命的消逝无痕,智性的诗篇终是指向消亡,生命个体终将死亡。因为有它的终极限定,而使得生命之内的所有探讨追寻都变得如同梦幻而没有意义。这是生命本真的回归,是“人”的终极缺憾之美。
缺而不缺,是为圆。《红楼梦》中所浸渍的“辛酸泪”旨在说明人生如梦,万境归空,这是生命本真回归回溯的终极缺憾之美,然而本真的生命始自“向死而生”又终将死,自始至终都充盈着缺憾,是以缺憾所画的圆圈作为句点,盈聚起一个圆。憾溢盈圆,是为美。红楼世界中无处不在的缺憾渗透在了丝丝血络的经脉中,流淌在“情”的血泊里,驶向圆透的心脏,画出了“真”实的“心”“情”,笔落至成荒唐之言——“好、了”“好、了”,然,“美则美矣,了则未了”,缺憾美,如是也。
参考文献:
[1]黑格尔.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