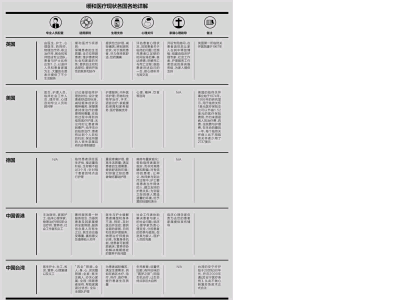对生命的努力与放手
2016-10-11
邓郁+李珊珊+邱苑婷
“缓和医疗是肿瘤内科大夫必须了解的一个重要内容,老年内科、心内科、肾内科,甚至所有的医生、护士和老百姓,都需要了解缓和医疗是什么。那就是生命的有限性,医疗是干什么的,医疗不是永远治愈,也治愈不了。但缓和医疗可以给你更好的生活质量。”
——协和医院老年科 宁晓红
生命由谁做主?
两年了,刘靖始终不能释然。

罗点点,“选择与尊严”网站创始人,推广传播生前预嘱
2012年春,99岁的父亲患上肺炎。家人立刻把他送进医院。因为老人有陈旧性肺气肿,医生立即把家属招到办公室征询:“要不要上呼吸机?”
“选择与尊严”网站、“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志愿者刘靖,无论如何不愿开口说放弃。“我怎能看着医院不做任何努力就让父亲走了呢,就像面对生离死别的至亲,我紧紧抓住不肯放手。姐妹也一致要求抢救。”
口腔呼吸机戴不成了,只好退到气切(切开气管),否则老人吸痰不利,一口痰堵住便有生命危险。从气切那一刻起,刘靖就永远听不到父亲洪亮、慈爱的声音了。看着老人一天十几次忍受惨不忍睹吸痰的痛苦,她和姐妹心如刀绞。
最后的日子里,他经常向刘靖姐妹们摇头。刘靖猜,那摇头里有无奈也有放弃。“谁也没正式问过他,是想放弃治疗吗,我们不忍心。”刘靖在回忆文章里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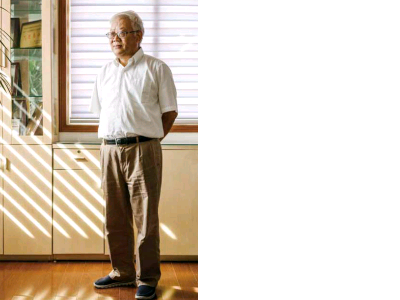
中国生命关怀不协会常务理事施永兴
老人不能表达,只能点头与摇头。最初刘靖的妹妹给他买了个书写用白板,老人能很吃力地写下几个字表达意思。大家只有猜他的意思再说出来,他用点头摇头来确认。多数情况这种“打哑谜”没有结果。刘靖清楚记得父亲最后一次给她写下的是“去吃碗肉丝面”。
即便饱受煎熬,老人的头脑一直清楚,“可见他的忍耐力和承受力超乎寻常”。刘靖相信,父亲曾满怀信心地期盼、等待着病愈,一如他在50年代被审查、“文革”时期被迫害没有灰心丧气一样,他认为自己能渡过难关,奇迹一定会发生。
直到2013年底的一天,父亲的心律高达160左右,医生用了强心剂并招呼至亲们来医院看望老人。意识到最后的时间来了,刘靖和家人终于一致同意不做电击、心脏按压等无谓的抢救,让饱受折磨的父亲安静地走。

北京军区总医院前肿瘤科主任刘端祺教授说,“缓和医疗不等同于临终关怀,而是涵盖了临终关怀的概念,是对于老年病、慢性病和危重病人从确诊开始的全程照护和对症治疗”
2014年1月9日,命若游丝般的老人在坚持了20天后,走了。
刘靖明明白白地看到,父亲一辈子经受的苦难都不如他辗转病榻这1年零8个月。那种苦难是无助、无望的,他自己也无法表达接受与拒绝。“如果父亲之前有过对生命末期的表示,我们也许会遵从他的意愿,可是他没有。”
“怪他老人家没有先见之明、没有交待?怪我们优柔寡断措施不力?抑或怪上苍无情无义?”刘靖冥思苦想没有答案。谁不愿意自己的至亲走得从容、平顺、安详呢?然而生命里没有如果。
刘靖在“选择与尊严”网站和“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担任志愿者,她的日常工作其实正是要让更多人了解到何谓“尊严死”,在意识尚清醒时作出自己的抉择。
10年前,这个网站由大将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和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共同创办。一开始,罗点点只是和朋友们半开玩笑地说,弄一个“不插管俱乐部”,“临终时不过度抢救,不搞插管、心肺复苏这些”,后来却办成了一件正经事。

宁晓红原来在协和肿瘤内科,因为老年科主任刘晓红力邀,来到老年科充分实践自己的缓和医疗理念
两人都经历过至亲的生离死别,临终时却情形迥异。
陈小鲁在《看见》节目中提到,去世前,71岁的陈毅被癌症折磨得不成人形,只能靠呼吸机、输液、打强心针勉强维持。在外人看来,这些都是对陈毅生命的延续。“但延续的后果是什么呢?”陈小鲁坦言,“他痛苦,大家也痛苦,也是对国家资源的浪费。”
中年陈小鲁曾问过301的医生,能不能不抢救了,让父亲平静离去?医生的两句诘问让他难以忘却:“抢救不抢救,你说了算吗?我们敢吗?”
2004年,罗点点的婆婆患病入院。因为依稀记得婆婆说过,不希望自己病重时切开喉咙,插上管子。关键时刻罗点点作出了停用呼吸机的决定。然而抱着婆婆,罗点点忽然感觉到老人身上的体温,看到了她合上的眼皮里眼睛在转动,她的决心骤然崩溃。“我有什么权利去决定他人的命运,我怎么知道自己做的是不是她想要的呢?”还好,几天后她在家里书中发现了一张婆婆留下的纸条,上面清楚地写着不希望过度抢救的要求,她还委托学医出身的罗点点对自己做善终处理。
在心惊肉跳和后怕之后,罗点点更加意识到,如果人们能在意识清醒时便有那么一纸文件,写明希望如何离开,如何度过生前的最后时光,岂不是为这个困境提供了一条出路?
1976年,美国加州通过了《自然死亡法案》(Natural Death Act),允许患者依照自己的意愿,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延长临终过程,自然死亡。而在中国,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家属来做关乎手术、治疗和生命的决定。

北大教授王一方在医学院开设了医学哲学课
2012年底,罗点点创立了北京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生前预嘱(Living will)的概念来自西方,指人们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签署的、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文件。它不是传统的法律意义上的遗嘱,不违反绝大多数国家现行的任何法律。
“选择与尊严”网站以美国的相关文件为蓝本,根据中国的法律环境和使用者的特点修订出了预嘱的文本《我的五个愿望》:
我要或者不要什么医疗服务;
我希望使用或者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
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
我想让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么;
我希望谁帮助我。
文本中还有这样的提示:
无论您如何选择都是对的。没人能在伦理道德上批评您。
如您改变主意,文件中所有已填写的内容可随时修改和撤销。
采访时,罗点点用平静柔和的语气强调,只要是基于理性的自我选择,都值得尊重。“生前预嘱,以及我们所讨论的各种各样的尊严死的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我们并不是说只有放弃过度抢救、追求有尊严和无痛苦的死亡,才是合理和正确的,没人有权利说这种话。如果你和家人决定,就是要尽一切金钱和能力,坚持到最后一秒,那也是值得尊重的决定。”她还为协会的志愿者规定了“第一时间缄默”原则:“我不会拉着你说,你信吧,类似于某种传教。只有自己能把自己的愿望说出来,这才是正确的。”

2016年9月某天,普贤莲社的居士们为北京松堂关怀医院的往生者进行助念,他们相信这将有助于离世者在肉体生命结束后,前往另一个美好的世界。在港台和英美的缓和医疗、临终关怀理念里,“灵性关怀”通常由牧师、修女和佛教法师等宗教人士承担。无论是何种专业人士,灵性关怀都致力于让病人与自己的核心连结,发现或重塑人生最后的存在意义。1987年成立的松堂医院是北京最早的民营临终关怀医院,也是惟一建有佛堂的此类医院。至今已有2万多人在松堂住院辞世(往生),临终助念1600人以上
但这样的推广和获得理解显然还需要时日。即便身为网站志愿者的刘靖,感觉父亲“不大理解也不愿意了解孩子们在做什么”,“我想他对我们的理念和工作有很多误解。我们把罗点点等人出的书《我的死亡谁做主》拿回家,父亲问妹妹,拿来这书干什么?可见他排斥。”
刘靖没有对父亲做任何解释。“点点说得对,选择自己的死亡方式没有对错,只要你认为对就好。我只是为他老人家走得如此艰难、悲惨而深深地难过、痛楚……”
截至发稿时止,已经有21314人通过“选择与尊严”网站填写了生前预嘱。罗点点说,出于隐私保护的考虑,他们从未公开过填写者的性别、年龄和其他数据。但她告诉我,张爱萍将军的夫人李又兰在读过《我的死亡谁做主》之后,填写了“我的五个愿望”,申明放弃临终(过度)抢救。“李又兰阿姨或许是我们生前预嘱帮到的第一人。”
从前看病是看不到人的
在面临“生死抉择”时,希望不做过度抢救的人,能够收获怎样的余生呢?罗点点表示,“不再以治愈疾病为目的,而是让他在临终时尽可能安稳,尽量没有痛苦,走向他生命的终点——这就是缓和医疗。”
缓和医疗,又称姑息或舒缓治疗、安宁疗护,由英国圣公会护士桑德斯医师提出,源自英文Palliative Care,后转化为Supportive Care。“它不等同于临终关怀,而是涵盖了临终关怀的概念,是对于老年病、慢性病和危重病人,从确诊开始的全程照护和对症治疗”。北京军区总医院前肿瘤科主任刘端祺教授说。

北京德胜社区临终关怀科副主任金琳(右)在安慰病人和家属
缓和医疗在中国起步并不晚,但步伐很慢。早在1988年,天津医学院便建立了专门收治晚期肿瘤患者的姑息治疗病房。90年代后期,昆明第三医院的马克和上海的施永兴分别在各自的领域开始了探索。但真正在从事肿瘤和老年治疗的医学界对此形成部分共识,来自2012年初的几次赴台之旅。
当时,刘端祺组织了13名在北京从事肿瘤治疗的优秀医生,去亚洲排名第一的台湾参观当地的安宁疗护。海淀医院肿瘤血液科的秦苑、中关村医院肿瘤科的王甦在参观花莲慈济医院、马偕医院和荣民总医院后,“受到极大的震撼”。
“第一是洗澡机。病人能使用号称上百万新台币的超声波全自动洗澡机,人躺在里面,出来就全身都清洁了。去他们的安宁病房,他们的编制可能是20张病床,但是他只开了十几张床,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们护士照顾不够。按他们的管理规则,你要开安宁病房,病患和护士的配比是1:1,到不了这个配置的话就不能开。”
社工和志愿者一见到病人抵达,便以专业态度引导对方,告知就诊流程。病房每张病床都铺有家居感觉的床品,装上有隐私考虑的门帘。不同宗教信仰的几家医院还特别开辟了祈祷室或“蓬莱阁”,给予信徒与自己对话或与亲人交流的私密空间。秦苑说那也是团员们的一次“灵性复苏之旅”。
“我和我的同学,美国一个资深的神经内科大夫讨论这个的时候,他非常不客气地说,‘你们从前说的对身体的照顾都还不是很准确,准确来说只是照顾一个器官。那时我才知道自己以前只是一个看病的大夫,去了台湾才真正看到怎样去照顾一个生病的人,在我以往的工作模式中其实是看不到人的。”
WHO在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缓和医疗的原则:“维护生命,把濒死认作正常过程”;“不加速也不拖延死亡”;“提供疼痛的缓解服务”;“提供支持系统以帮助家属处理丧事并进行抚慰”。2002年,WHO对缓和医学的定义进行了修订,特别考虑到“躯体、精神心理、社会和灵魂”(简称为“身、心、社、灵”)的需求。

2008年,以汶川地震心理援助志愿者身份回到上海后,王莹和搭档黄卫平创立了上海浦东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为癌症患者的社区自助、舒缓疗护提供志愿支持。正是在王莹、黄卫平等许多民间力量的推动下,上海在“死之尊严”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
目前,受条件约束,国内的借鉴和实践多集中在身、心的层面。“你疼痛,给你止痛,呕吐的话给你止吐,吃不下我们给你营养支持。”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综合科的赵苇苇介绍,对于癌症终末期的病人,很多三级医院不愿做“抽腹水”的治疗。“他们觉得已经很晚期了,抽腹水是治标不治本的。缓解症状只是暂时性的,但是今天放掉这么多,明天一定会有,有可能过一周两周三周,还会再长出来,(他们)就不想做。”
“有些病人肚子比10月怀胎还要大,肚脐眼也凸出来。病人很痛苦,腹水大了以后,它会压迫输尿管泌尿系统,导致肾坏死。但放胸腹水,又不能放太快,因为病人得同时补充白蛋白,白蛋白丢失,又会增加胸腹水产生的量,因此会产生一个恶性循环。我们给他们做了处理,症状就好多了。”
话术的魅力
美国纽约东北部的撒拉纳克湖畔,镌刻着医生特鲁多的名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这句话,成为无数中外医师刻入心扉的行业指导。在缓和医疗里,“话疗”对病人和家属都发挥着极大的作用。而“告知坏消息”则是非常重要的功课。
比如他突然肚子疼来看病,检查时发现肚子里有什么问题,他的症状一点一点加重,你让他回忆就是帮助他整理这个过程,每次他讲到加重的时候,你就让他停下来,说:“噢,我听到你说又出现了一个什么什么症状,是吗?”病人就会说:“是啊。”在这样的一问一答中,就让他感觉到自己的病情是一点一点加重了,这是一个铺垫。讲到最后,就说出现了什么问题,这样就可以谈了,“那您看了那么长时间的病,前面的大夫都是怎么说的呢?”在沟通中一点一点地将坏消息暗示给他,他也一点点接受。如果突然告诉他,就有一种落体跳崖的感觉,这和一步一步往下走不一样。我会试探地问:“我大概知道您的情况了,您到这儿来之后我们还会做一些检查,您自己怎么想呢?您愿意了解您的检查结果吗?”
这是秦苑现在接诊病人的流程。“这些很细的东西和我以前工作的理念完全不一样。以前我们是征求家属的意见。我不会苦口婆心地和家属说为什么要让病人有权利让自己做决定。现在的做法沟通成本非常高,但和病人的链接深度非常不一样。我以前只会看病的那点事儿,和病人就是鸡同鸭讲,两个人都不在一个层面上。”
比如说家人都死于癌症,自己又有一个独子,他的恐惧就会出来,他知道自己要不久于人世了,他儿子已经结婚了,就会考虑要不要他儿子要孩子,他会害怕儿子生的孩子也是癌症。在这里我学到的就是,我们并不能给他答案,但是你只要诱导他把担心和恐惧的问题说出来,他的压力就会减轻很多,让他受到一个真诚的支持,有人愿意陪伴他一起去面对这些困境。我们是不可能帮他做选择的,只要表达这样的意向,对病人就是莫大的支持。
宁晓红原来在协和肿瘤内科,因为老年科主任刘晓红力邀,来到老年科充分实践自己的缓和医疗理念。她和我们说话时语速很快,绝无多言。但和病人交流时则循循善诱,运用各种方法来保障病人和家属的知情权、选择决定权,满足病人“并非不可能实现的愿望”。
我们的缓和医疗培训里有一个演练特别有意思,有人扮演护士,去照顾一个50多岁的、腹腔肿瘤转换转移的病人。病人说:“唉,我想去看我的一个哥哥,他在天津,但是我能不能去啊?”(演练中的)护士没有搭茬,因为不知道怎么搭。换我,我就会说:“你哥哥是怎么回事啊?”就跟他聊家常。接着我会说:“我觉得可以去。我跟你老伴说,我们一起商量商量,这事很重要。但是以你现在的情况坐火车、坐汽车,我觉得你够呛。如果你非去不可,我有个主意,救护车你觉得行吗?”我就是个建议者,首先我尊重他想要看哥哥的愿望,非常理解,而且我是从心里非常积极地想要达成。我提出这个的时候,患者就说:“行啊,救护车行。”
这个演练给出的例子就是,我们不知道在病人心目中什么最重要,但是我们要去探究。不去探究你就什么也不知道。
有个病人是外阴肿瘤转移到腹股沟,腹股沟整个都烂了,都能看得到洞。病人她倒不害怕,她是痛,要止痛药。她是一个大学教授,虽然不是学医的,但知道她那块儿有支动脉,就问了我一个问题:“我这儿会破吗?”我认为她非常严肃地问了我这个问题,我现在就不能告诉她不要瞎想,让她去逃避。我告诉她,有可能,肿瘤确实有可能把动脉侵蚀破了的,一下子就破了。动脉一出来,那血一下子就多了。我接着说,如果真的破了的话,那是你的造化,因为那样会很快。有一天我给同学们讲课,讲到这个例子,他们就笑。我说你们笑什么?是我说得不对,还是我说的方式你们接受不了?我把我的反馈告诉你们吧:我把这些告诉病人以后,病人就说,“嗯,我知道了。”非常平静。再后来,过了两三个月,病人去世了,她女儿告诉我,“我妈走了。我妈得病之后受了非常非常多的苦,但我觉得,她真的是一个非常有造化的人。因为正如你所说,她真的是那儿出血了,然后没有任何痛苦,非常平静就走了。”所以我说,我们给病人的这些关于死亡的知识,真的是那个时候他们非常需要的。你干嘛不告诉她?如果你有,就告诉她。
很早我就跟她的女儿说,说你妈的这样走是有可能的。那到那个时候你要做什么?我说你就准备几样颜色比较深的东西,因为医院里的床单都比较浅,那个时候如果到处鲜红,不管家人还是病人看见了都特别恐惧。一旦真的出血,你用深色毛巾去覆盖一下,看上去不那么刺眼。这样可能会好一些。
这让63岁的北师大教授陆晓娅分外唏嘘。1987年那个炎热的夏日,她和妹妹把肝癌晚期的父亲送到医院,没有病房,父亲躺在过道中,直到单位领导出面,才进了急诊室。没多久,父亲开始吐血。陆晓娅找到医生,焦虑地问,该怎么办?得到的回答是,“你们难道没有准备吗?”不知如何应对的她和妹妹在悲伤中慌乱地一次次为父亲擦去血迹,等母亲赶到时,他已经停止呼吸。“一切都是那么匆忙,好像只是为了尽快腾出一个床位……”
在台湾参观时,秦苑和宁晓红看到医生、护士、心理师、社工等整个接诊团队在跟进的过程中,除了有病人的病史、病历,紧接着病人的家庭系统图就出来了。“这个人是什么状态?谁在主要照顾他?谁是他的经济支持者?家庭关系?经济关系?性格特征?原来是什么样的经历和背景?包括情绪的评估,一整套全都出来了。于是社工包括心理师开始介入。你就会发现特别不一样,高度个体化就体现在这儿。”有医生和护士想不通,干嘛要了解和介入人家的家事?但在缓和医疗的倡导者看来,病人的症状、情绪和家庭关系密不可分,医者要做的不是干预,而是了解和疏导。
由布达佩斯医生巴林特创立发明的巴林特小组,组员一般8到十多名,会定期碰头。由志愿者通过前段时间的经历讲述一段医患关系案例,组员们分析、讨论,从而改善医生对病人的处理和医患关系。这一方式目前在国内很多大医院都得到了采用。
大连中心医院关爱病房主任桂冰告诉我,她在一次巴林特小组会上,听到护士描述一位40多岁的乳腺癌病人比较敏感、多疑。每次护士给她换药,都要问“你这是什么药,什么作用,到底几支?”护士们感觉自尊受到很大影响,都不喜欢她。病人的责任医生讲了她的成长故事:出自农村教师家庭,父亲对她管教严厉。一次父亲因为她没考好打她,母亲在旁拿起刀对父亲说,你就拿刀砍死她算了。后来她考上大学,离开家,和心仪的男孩相爱、结婚,结果小孩一岁多她就得了癌症,非常不甘心。“她抗争了10年,所有地方都转移了。病人对爱的需求特别强烈,坚决要活,因为感觉到命运不公平,脾气也有些古怪。这样大家就对病人的表现非常自然地理解,也能更好地照顾她了。”
9月的某个周一下午,宁晓红预约了自己的十来个病人。其中一半是病人的儿女帮父母来问诊。一位癌症晚期患者的儿子(以下简称“男”)对父亲的病情了如指掌,对着手机上的症状记录细致入微地咨询过宁晓红后,略带迟疑地提出了下面的问题:
男:我感觉最近父亲也在抓紧时间……逮着我,就问家里的衣服、钥匙、存折搁哪儿了。以前交待过,现在又让我记下来。
宁:我想你父亲可能想知道,你是不是真的上心,真都记住了。你可以问他,“都搁在这里,这里,我都记下了,你看我说得对不对?”
男:嗯,是的。有一天他突然气哼哼地拉住我,咱们家有笔理财是不是都到期两天了?我说是,都办好了呀。他说,那你得跟我说啊!
宁:他可能有点恨得慌,觉得自己做不了什么的那种感觉。
男:宁大夫,还有一件事,我感觉我想错了。原本我以为,我父亲能挺到今年11、12月,没什么问题,甚至能到元旦。但现在看到癌细胞发展这么快,我想问您,会不会很快……
宁:那我想问问你,你为什么要问到这个“快”的问题?
男(哽咽):您说过我爸的病情,我也跟他交底了,也跟我妈说了。我以为自己不会慌张,以为后面就没事了。可我发现……
宁:你还是很舍不得。
男:我挺怕这一天的,我更怕他突然昏迷、咳血,走得很突然……
宁:嗯,如果让我给一个明确的数字,这很难。但我宁愿把这个时间想得短一点,如果明天是最后一天,那咱们今天怎么过?这样我们会赢得很多天,而不是每天惶惶不可终日。我们不去猜测。今天你去看了他,明天你去倾听他,多陪陪他就行,这样不会遗憾。你的不舍,是很正常的。不用害怕。你妈妈现在怎么样?
男:我妈,还好。但我觉得我爸好像对我妈的照顾有点不信任,老是冲她嚷嚷。我妈本来身体也不太好,已经尽了她最大的努力。
宁:你妈是不是你爸爸一直以来最安全的一个发泄对象?
男:是的。
宁:那你也需要安慰下你妈妈。她本来就不舍,再加上委屈,那就更不舒服了。
这样有针对性和提示的心理辅导,在当下的中国医疗求诊环境里,不易得见。秦苑在海淀肿瘤血液科推行缓和医疗以来,整个团队走向的核心就是所有人都看到病人自己的意愿,无形的工夫都花在“劳心”这部分。“在科室里推缓和医疗,大家一听就会觉得好累啊,我每一个步骤、每一个人都要不停地沟通,所有的医疗措施、方案制订、下一步要怎么走都要沟通,一直是在动态沟通的过程中完成。他们就想按照原有的模式和流程走嘛,其实不是的,那是个死的东西,你怎么去照顾一个人?人是活的啊,他上午和下午的情绪都会不一样。”
刘端祺说,缓和医疗在医院系统进展缓慢,第一是上面不拨款,第二是科研不批。“有的老百姓也是一听就变脸了,你们都是应该救活病人的,谁要听‘死得舒服?其实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做心理按摩和复苏,这是很不显山露水的工作。”复旦肿瘤医院综合科主任成文武叹气,手下医生都觉得做这行没有成就感。“人总是要走的,没有那种抢救的成就感,别的科室晋升顺利,我们要文章难有文章要课题难有课题……”
罗点点曾经去过一家北京的三甲医院推广生前预嘱和缓和医疗。“医院院长就明着跟我们讲,我们这要做手术的人还来不及,要救的还救不过来,还谈缓和治疗,那我的医院怎么经营啊,有病吧?!这是他的潜台词。”
昆明第三医院的马克在关怀科从中青年做到了头发斑白。“在中国,人一生的医疗费用,70%用在最后3个月。其中又有70%是花在最后的28天。过去的理念强调放开抢救,没有姑息学科的建设。我曾经问过一个检察长,能否放弃无意义的抢救?他说,见死不救,是犯罪。我们的法律和医疗管理有时是冲突的。从事缓和医疗和临终关怀的医生,应该是个哲学思考者,而不是技术的工匠。”
社区样板的夜间3小时
采访时,北大肿瘤医院姑息中心主任刘巍等人都认为,缓和医疗未来的出路在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样的一级医疗机构。事实又如何呢?
9月21日夜里21点32分,北京二环的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德胜)大门已经落锁,4楼的生命关怀病房走廊却灯火通明。护士刘蕊刚处理完一个癌症晚期病人的突发状况。“有点喘不上气,刚才输了液”。
这是一幢外表并不起眼的4层建筑,里边却倍觉整洁。诊室、病房的常规配备,走廊里的水晶吊灯、欧式沙发椅,楼梯上挂着的“静以修身”字画镜框,恍惚间形成了一种“舒适型酒店+医院”的即视感。
桌上摆着的两个塑料袋是发给值班护士的“夜宵”:值“小夜”(前半夜)的可以吃到馒头和粥,值“大夜”(后半夜)的能“享用”两块饼干、一个苹果和一袋牛奶。
白天,刘蕊和同事做得最多的是“对症处理”。很多病人经过大面积放疗以后,身体变形,加上细菌感染,导致身上出现不同程度的溃变。前不久刚去世的一位患下颌癌的病人,下颌全部溃烂成深紫红的腐肉,中间已经成了一个“漏斗”。“喝水,水就直接流下来”。刘蕊每次都要花20来分钟,用棉签粘上聚维酮碘清理创面,接着拿镊子把里头的脓弄出来。“病人一推到楼道里,整个一层都臭,特别没尊严,家人拒他于千里之外,他的女儿戴着好几层的纱布手绢”。但对刘蕊们来说,这一切都稀松平常。
夜里偶尔也有病人出现“爆发性疼痛”——是那种白天定时打过吗啡后,更高级别的、无法忍受的疼痛。
碰到这种情况,需要护士加大止痛药的使用量。如果“爆发性疼痛”频繁出现,则表明常规的吗啡用量不够准确。医护们会尽量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
在大夜班的10个小时里,刘蕊每半小时要巡视一下所有的病房。除了症状处理,怕的还有夜里病人的自杀倾向。“夜间自杀几率略高,因为病人的不舒适感较白天更多,又不像白天会有一些外界的干扰。他们的精力全都集中在了身体痛苦和无尽的烦恼上。”
在德胜,病人和护工的洗澡间是分开的。病人视身体状况,可以在护士的帮助和看管下淋浴,或坐着洗澡。几天前,一位许久没有洗澡的病人,忽然独自去了护工的洗澡间,这让正巧路过的刘蕊吓了一跳。“危重病人洗澡一定要事先征得家属同意和签字。那位病人经常需要吸氧,他可能嫌手续麻烦,又很想洗,就自己溜进(护工洗澡间)了。我们和他老伴儿解释,家属理解,但病人就不高兴,后来开了开玩笑,也算过去了。想起来还是有点后怕。”
那是刘蕊3年的德胜工作经历里碰到最棘手的一次,却不是最揪心的。揪心,永远发生在病人离世的时刻。
两个月前,急救车送来了一位43岁的病人党女士。病人的疼痛评分很高。“院子里路不平,她稍微颠了一下,我就看到她的表情特别痛苦,她一直闭着眼睛,说不出话,而且阴道和直肠都漏穿了,从阴道里流大便,这么痛苦还是为了看到孩子考上大学而活着。在我们这儿住了两个月,两周前去世了。医生和护士的心天天都难免受到影响。”21日夜班前几小时,我在301医院的缓和医疗峰会上见到德胜主任韩琤琤,说起这些她眼眶微微发红。
10年前,出于“分级诊疗更加明晰”的初衷,北京市卫生部门要求所有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撤消病房。位于积水潭的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却顶着压力,保留了22张病床——西城区惟一一家。韩琤琤说,那时只想做康复病房,后来却成了康复和临终关怀的宝贵火种。
身处癌症终末期、没有治疗机会的病人会来这里“走完人生的最后一公里”。在其他医院,住院病人通常会面临病床周转期这样的难题。为了杜绝并不严重的病人占用医疗资源,三甲医院的病人通常住14天到一个月就被要求出院。但在德胜,最长的病人住了3年。虽然中间仍会有90天“出院再进”的不得已措施,但已经比大医院少了很多折腾。
就在临终关怀病房刚成立一年左右,护士长金琳的父亲得了胆管癌。一开始金琳没有把病情告诉他。有一天,父亲“不知怎么”翻看起女儿带回家的文件箱,看到了临终病人目录上自己的名字。
父亲主动对她说,“如果我病情变坏了,不要让我痛苦地维持生命,那样太难受没必要,到时候把中山装给我穿上,咱老北京人就喜欢这身行头。”金琳的眼泪涌上眼眶,却不敢落下。要在最亲的人身上诠释“不以延长生存时间为目的,而要提高临终生命质量为宗旨”的生命理念,原来是那么的痛。
数日后的夜晚,医生说父亲不行了,要金琳作出抉择。她亲手给爸爸测完最后一次血压,拉完最后一张心电图。爸爸大口喘着气,眼睛直直地盯着她,似乎还有话想说。金琳俯身在他耳边:“爸,您不用担心,以后家里还有我,您就放心吧。”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如今从一线转到行政岗位的金琳对我背起泰戈尔的这句诗,她说自己并不是文学爱好者。在父亲离世的那夜过后,她对于缓和医疗和临终关怀有了比以往更切身的理解,“碰到每个病人都会想,能不能让他们少一点遗憾和痛苦?”
道孤路远
看过纪录片《人间世》的观众,都对其中的上海临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印象深刻。本篇的外地受访者都表示,政府支持和重视是上海做到全国前列的最直接因素。
原本,上海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基本保留了病房。2012年初,上海一名患者家属秦岭给当时的市委书记俞正声写信,讲述了他陪肺癌晚期的父亲艰难入院治疗的经过。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其父因为病情严重,无法手术和放化疗,医院为了优先给急症病人提供医疗资源,不愿意让这位患者入院,病人所遭受的癌痛苦难令家人心碎。在此之后,上海市在17个区县的18家医疗机构开设共计180张临终关怀的床位。”
截至2014年底,上海在缓和医疗项目上投入4000余万元,已有76家市级试点单位,890张床位,减少无效医疗6000余万元。《上海观察》专栏作者王潇写道,试点机构“所有费用可以通过医保支付,由市、区两级政府出资,市自然基金会、市红十字会慈善机构给予资助,每收治一名病人给予2000元医疗补助,居家宁养提供1000元补贴医疗费用,并为癌症晚期患者免费提供止痛药。”
为什么上海能做到如今的规模,在北京,惟有德胜一家撑到今天?
“上海在市政府的重视下,这项事业有医政、医保、财政、红十字等8个部门牵头,德胜也算做出成绩来才享受了可以在卫计委备案的特殊待遇。但北京(做缓和医疗和临终关怀)多半都没有编制,怎么复制?”金琳摇头。
韩琤琤算了一下账。在德胜,对临终关怀病人很少用高额药品,最大部分的花费大概是自费的护工费。除去1300元的住院起付金,每位来临终关怀科病房住院的病人,自费医药部分只要3%到10%。其实是一项利民举措。
但对多数医院而言,没有编制就没有经费。无论是德胜临终关怀病房这种受到关注和肯定的试点,还是海淀医院血液肿瘤科这种自发探索的部门,像疼痛评估、哀伤抚慰和心理诊疗等,都没有收费标准,目前都是医护义务承担。
而且,并非有了上级指令就能带来期望的局面。社区医院恢复病房势必带来运行成本提高和压力的加大:“需要医生、护士值夜班,得准备一日三餐、夜里要留电梯,夜间也要有暖气,包括护工、保洁、洗涤、餐饮以及风险——万一病人要抢救、死亡,整个病人的管理远比不设病房复杂。”
到今天,德胜成了国家领导人都来参观的典型,风光的背后掩不住医护们的职业难题。
“有一个大夫,也不算是新毕业了。一次值夜班的时候,(遇到病人死亡)他就一直守在那里,在楼道里不停地徘徊。有时候一个病人去世,一宿都不敢关灯。虽然都知道这是无药可治了,家属也不闹,但医生的那种责任感,加上年轻医生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尤其像我们做临终关怀、晚期(癌症)的这些人,就觉得人的归宿都是一样的,这种恐惧就一直围绕。曾经有个副主任告诉我,一晚上年轻大夫给他家里打了11个电话,高度紧张。”韩琤琤说,他们也会请心理医生来给医生护士们做辅导,但最终所有的问题还是必须自己消化。
社区特别需要的全科医生,职业发展前景并不乐观。“毕业之后有的当校医,比如去了皇城根小学。学校就说你如果来,你的孩子在我们小学一直上到对面的四中,直升高中,所有的赞助费免,人立马就去了。干嘛不去?在基层,待遇低。他的心态是跟二级、三级医院比,我为什么8年的受教育背景只挣他们二分之一、三分之一的工资?”10年里,她时常需要面对医生护士提出“换科、换岗(不上夜班)”的要求。“如果不换岗,那么能够想象(医生)跳楼就是不可控的。”
二十多年过去,国内目前仅有两百多家临终关怀机构。同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这一数字远远不够。2011年,美国有近44.6%的人是在临终关怀项目中去世,接受临终关怀的人达165万。那一年,美国的临终关怀项目/机构达到5300个,覆盖美国全部的50个州。
金琳很佩服上海社区临终关怀的领路人施永兴。“他不急功近利,也不轻言放弃。为了做临终关怀,头发都白了。我记得他说过:坚持,一定会有结果。因为他就是这么过来的。”
凌晨1点,德外大街上的车辆少了许多。金琳将我送出门,转身再度扎进了4层小楼。说真的,能拥有这样现代而具人性关怀的社区医院,我对这里的居民颇有几分羡慕。金琳叉着兜,撇撇嘴,“还不够大呢,想想,我们要承担十多万人的医养关怀,应该再大一些……”
(参考资料:选择与尊严网站《告诉我们你的故事》《看见》《我希望我爱的人能更有尊严地离开》,感谢所有受访者。实习记者张宇欣、孟依依、李驰、胡宏培、刘玥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