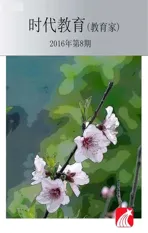春醪和鸡汤
2016-09-22杨军
文_杨军
春醪和鸡汤
文_杨军
一
本期推荐梁遇春的散文。梁氏早逝,只活了27岁(1906-1932),除了翻译,身后还留下几十篇散文,都编在《春醪集》和《泪与笑》里。因此得了“散文家”的名头。但是,在这个“散文阅读”盛行的时代,他的“名气”最终也散了。和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大约相似,因为属于“负能量”过多的人,在中学语文教材鲜见身影。偶尔可在阅读材料中看见一两篇,如《春雨》《吻火》《途中》一类,被要求分析作者的“表达技巧和作用”。而梁遇春不被重视,大概也由于此。
中学语文教学重视散文,很大程度因为作文考试。考试,总是技术大于其所宣称要求的真情实感。几十分钟写一篇800字作文,给出材料或主题,除诗歌外文体不限。说明文太死,记叙文难写,议论文其次,最后只剩那个难以定义、“不伦不类”的散文。
散文被当作神器,大概因为“形散而神不散”。所谓神,在教学话语里被等价于中心思想。文章不论怎么写,只要服从中心思想,再多些好词好句,就差不多了。而且也不能完全“形散”,要稍微有型。如一句话点题(另外题目长点也无关系,专业说法叫“题目是观点的形象化表述”),首尾呼应,结构整齐(这里的整齐是指文章中段多以对称或排比形式出现)等等。秘籍口诀人们已耳熟能详。这就是许多人所谓“高考体作文”或者散文化作文。
语文改革多年,不断有人抨击这种文体,但至今盛行不衰。究其原因,有人认为是评价机制。作文要有足够量化的标准,才可让评卷老师在短时间内估算分值。也有人认为是社会功利化影响,如看看现在的新闻报道,公文,网络流行的标题党,深度好文,不转不是中国人,或各类广告文案,其写作方式和高考体作文如出一辙,可见社会对这类文章其实需求旺盛。学生作文如此,并不偶然。
在“网络时代”(无论事实是否如此),散文被称为一种“美文”。下意识地,人们的精力每天被无穷的信息分散,除了工作报告和媒体宣传外,那些功能性较强的文章外,总要寻一些“美好”的刺激,诸如“岁月静好,不忘初心”。这就是所谓“美文”,一种被认为没有实用目的包含审美价值和精神寄托的文章。甚至不必是文章,一个有趣的段子,一段名人名言足矣。唯一的定义是唯美。至于何为唯美,则从来含混不清。大约是,总有一段修辞可以打动你。等同于那句由村上春树发明的流行语“小确幸”。
于是,越唯美似乎越“实用”。一切不忘初心、一片岁月静好,华丽空洞的文笔大量复制,逐渐代替了审慎思考。有人批评为“心灵鸡汤”。仅此而已吗?又不尽然。
人们可能忽视了一个背景,我们如今被批判的年轻读者们,正是在一代又一代高考作文大全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在学生时代,他们就被要求收集名人名言,摘抄好词好句。鸡汤的批判实在毫无意义。专业人士可能早就发现,在这个普遍缺乏完整阅读和表达能力的时代,无论讲多么“高大上”的东西,一定要写得够鸡汤才有人看。
鸡汤的存在,不过是表达贫乏的背景而已。有时正如某些人指责的汉语粗俗化一样,它也正好代表了这个时代的“冗余”。在一种僵化的话语体系之下,人们还有机会选择另一种表达方式——尽管后者可能同样“僵化”。
讽刺的是,在历史上,梁遇春的散文正是被归为“美文”一类,尽管含义多么古怪。
二
美文一词,是法国舶来语,原意为纯文学,泛指一切文学诗歌和艺术的总和。在新文化运动引入中国后,因周作人等倡导,一度专指叙事抒情散文,成为“独立文体”,与杂文相对(实际并未流行,最后还是借了一个古词曰小品文)。梁遇春正好处于这时代。
那时,在新文学阵营中,作为“匕首”的杂文和作为“个人的文学的尖端”的美文曾一度论战。不过,因为早逝,在那些后来“开出一片新土地”的美文之间,梁遇春似乎总有点尴尬。
和前辈周作人相比,他缺乏一种人生阅历丰富的“闲适”,似乎浑身都是少年“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反叛,一切成见都要举出反例。人们谈论人生观时,他要写《人死观》。别人说gentleman和君子时,他写流浪汉,赞美“真正的流浪汉无人无我的境地”;人们热爱春光,他偏要“爱凝恨也似的缠绵春雨”,说“满眼春风百事非这般就是这般”。人们提倡早起,他又要赞美迟起,一副“懒汉”论调。他甚至还揶揄教书匠们是知识贩卖所的伙计——没错,他大概正是指我们现在正在传播高考作文大法等知识的老师们……
但如果这样,那这个人可能刻板得无趣,偏偏他又从他译介的英国作家那里找到某种滑稽来调和,如杰罗姆的《三人同舟》。在《春朝一刻值千金》中,他借杰罗姆的话头“懒惰汉的懒惰想头”说:“春宵一刻值千金这句老话,是谁也知道的,我觉得换一个字,就可以做我的题目。连小小二句题目,都要东抄西袭凑合成的,不肯费心机自己去做一个,这也可以见我的懒惰了。 在副题目底下加了“之一”两字,自然是指明我还要继续写些这类无聊的小品文字,但是什么时候会写第二篇,那是连上帝都不敢预言的……”
而终于他也不是要把文章来做“匕首”。有时,他似乎要投出一把匕首了,但最后却刺向自己:

三人同舟插画

梁遇春翻译查理斯·兰姆,也深受其影响,被朋友称为中国的伊利亚。伊利亚为兰姆笔名
“若使我们睁大眼睛,我们可以看出世界是给猫狗平分了。现实的黑暗和灵魂的堕落霸占了一切。我愿意这片大地是个绝无人烟的荒凉世界,我又愿意我从来就未曾来到世界过。这当然只是个黄金的幻梦。”
当然是个黄金的幻梦。他有限的生命大多在平静的助教生涯和图书馆度过,和他同龄的大多五四青年们迥异。如果没这些文章留下,或许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他想如何“溶入生命里的狂潮”去写作,如何用一种“悲剧的幽默”(梁的老师叶公超评语)来支撑他对世事无常的幻灭感了。
废话到此,这里只选一篇他《春醪集》的序言。在这篇短序里,他借着春醪的典故,说了一个他所谓“心力克”(即Cynic,犬儒)的天真的人生态度。犬儒,这个曾充满道德意味的词,现在早已成了绝对贬义。世事变迁如此。所谓“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他才不管。结尾他说,“我面前还有大半杯未喝进去的春醪”,几十年后的事情“我现在是不想知道的”。
当然,几十年后,他并没有活到。只剩下他那些不再喝春醪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