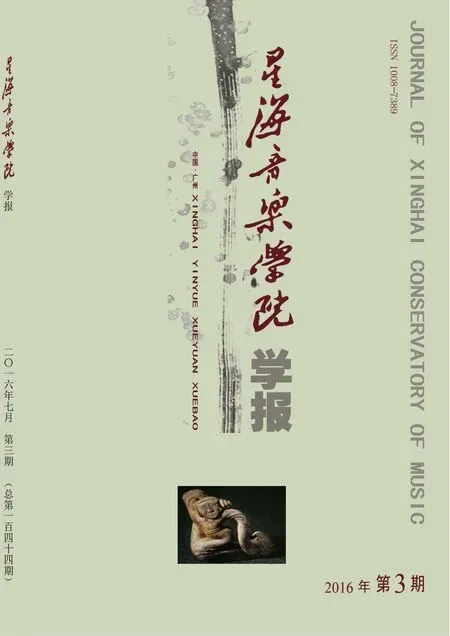西方音乐阐释理论的历史梳理
2016-09-18宋瑾
宋 瑾
(中央音乐学院 音乐学系,北京 100031)
·西方音乐史·
西方音乐阐释理论的历史梳理
宋瑾
(中央音乐学院 音乐学系,北京 100031)
西方音乐阐释理论大致可分为中心主义和多元主义两类。前者主要分布在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后者基本上分布在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后现代主义及其“之后”的时段。前者对音乐的释义,经历了作者中心、作品中心和读者中心的移动。相应的理论有历史释义学、结构主义和接受美学。后者则出现了从结果到过程、从作品到文本、从确定到随机、从中心到多元,以及从单一到多样的演变,涉及解构主义、多元对话理论、生态哲学美学等后现代主义及之后的理论。各种音乐意义的阐释理论或观点都有各自的历史语境,亦有各自的逻辑结构;从关系实在论哲学观点看,这些阐释理论或观点都具有自洽的合理性。时间先后并非进化,仅为历史分布。
音乐作品;文本;意义阐释;释义学;结构主义;接受美学;后现代主义
于润洋教授在《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第三章中对西方音乐释义学的历史作了梳理和研究。涉及词源、各历史阶段的表现;涉及重要人物如维柯、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克莱茨施玛尔、伽达默尔、姚斯等人,在第一章中还涉及相关学派,如俄国形式主义、美国新批评派、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1]194-237,45-108朱立元在其主编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导论中提到西方文论的研究重点的“两次转移”,即从作家到作品,从作品到读者;“两次转向”,谈到认识论转向和语言论转向,涉及解释学的关键问题。[2]4-9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作一些梳理和联系,重点在释义的“转移/转向”,期望中国音乐界更多关注后现代主义的阐释理论,如巴赫金的“多元对话”、德里达的“焚化”、罗兰·巴特的“文本”、哈桑的“不确定性”等。参照丹尼尔·贝尔对西方近现代历史的划分——后现代主义造成“传统言路的断裂”,使之区别于从传统到现代主义的哲学美学,出现了“后哲学”“反美学”。本文认为西方音乐释义学的历史亦可以此“断裂”大致划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中心主义时期,一个是多元主义时期。前一个时期的变化表现在释义具有中心性,尽管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心不同,后一个时期的变化则表现在多个方面,如下所述。
一、释义中心论及其转移的时期
20世纪中叶以前,西方音乐释义学以本质主义哲学为基础,表现在以下认识:意义是确定的;存在着意义阐释的中心。从18世纪到20世纪,释义中心依先后分别为作者(作曲家)、作品(乐谱或音响)和读者(听者)。
1.作者中心
历史释义学。19世纪西方人认为音乐由作曲家创作,所以对音乐意义的追问必须到作曲家那里寻找答案,此为作者中心论的释义学。追溯历史,对音乐意义的阐释,主要指对音乐作品所包含或关联的意义的解读或理解。马丁·路德对宗教经典《圣经》的重新解读造就了“新教伦理”,导致西方人精神世界的变化,造就了丹尼尔·贝尔所谓的“现代新人”,进而促成社会的变革,从神学笼罩的封建社会过渡到科学理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充分看到意义阐释的重要性。西方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对此有深刻阐述,受到贝尔的大力赞扬。18世纪的维柯在《新科学》中提出了释义的历史主义原则,认为对事物的意义的阐释,不应加入阐释者的主观因素。这种历史主义阐释观在施莱尔马赫那里得到继承,他提出回到过去,重建作品的真实的释义学思想。随后,以狄尔泰为代表的历史释义学虽然指出艺术文本的意义有待于人去阐释,但是阐释过程是一种“同化”过程,读者阐释的“第二精神世界”应尽量靠拢作者创作的“第一精神世界”,这仍然是一种重建历史的思路。其实,历史释义学中已经埋下了中心转移的种子——重心逐渐指向读者,尽管在当时强调作者和意义的客观性。例如狄尔泰始终没有否认阐释的主观因素,认为那是很难排除的。这样就为中心移动埋下了伏笔。
西方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实证主义都是产生作者中心论释义学的基础。在它们的影响下,音乐释义强调作曲家和作品所处社会时代的研究,特别是对作曲家的研究,包括他的生平、创作环境、创作动机或意图的研究。
2.作品中心
结构主义。到了20世纪上叶,结构主义盛行。在释义领域,出现了作品中心论,典型者即俄国的形式主义文论和美国的新批评派。它们的主要观点是,作品一旦创作完成,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如同出生了的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人们的审美经验似乎也表明了这一点:不了解作曲家,并不妨碍对音乐的审美。文学艺术界的情况都如此。不了解作家,照样能阅读小说和诗歌;不了解画家,依然能欣赏美术作品。艺术作品作为客观存在,作为自足的世界,作为结构,其意义是作品自身各要素的关系确定的;解释活动就是依照作品的结构要素所形成的既定关系,去理解作品的意义。在象征主义文论那里,“结构”还包括延伸到作品之外的世界部分,即作品形式所连接的他律性内容。例如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1913-2005)认为,释义学的任务就是从作品的象征形式的研究入手,具体分析其象征结构,从而揭示出多种意义。[2]273尽管如此,意义仍然是这种结构中存在的、由结构相关因素的关系确定的存在;释义就是对这种存在的把握。此外还有符号学(Semiotics或Semiology)、阐释人类学等。传统符号学认为作品的能指和所指的结构关系是确定的,释义就是对这种关系的把握和揭示。苏珊·朗格虽然认为艺术符号有别于一般符号,是一种抽象情感的符号,涉及外在事物,但作为一种特殊符号体系,艺术的意义是在作品之中供人体验的。这种观点体现了自律美学和唯美主义的倾向。后者如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寓言等的象征结构进行分析,以此来揭示它们所蕴含的意义。芬兰的塔拉斯蒂(Eero Tarasti)出版了不少音乐符号学方面的著作,如《音乐符号学理论》(1994)、《音乐的意义:符号理论与音乐分析文集》(1995)、《音乐符号学的发展》(1996)等。他从音乐结构整体的张弛流动探讨音乐的意义。用这种理论,塔拉斯蒂研究了瓦格纳、西贝柳斯、斯特拉文斯基、肖邦等作曲家作品中的意义,以及音乐与神话的联系。显然这种意义是客观的,不是主观构造出来的。与此相似的是语义学(Semantics),研究语言逻辑系统的意义。东欧的沙夫将它引进音乐意义的阐释中,强调音乐作为“指号”的特点及其交际功能。[1]307
后结构主义看到了读者对作品意义生成的作用,因此向追求客观意义的结构主义注入了主观因素。详见后述。
3.读者中心
接受美学。以德国学者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1920-)为代表的接受美学理论认为,作品只提供意义的可能性,而读者通过审美活动,才使作品的意义转变为现实性。从价值角度看,作曲家创作音乐作品,目的在于被听者感受、理解;有效的意义只能是听者所把握到的东西。因此,释义学的任务在于分析听者所接收到的意义。姚斯针对以往的三种研究范式,即古典主义-人文主义(以古典作品为范本来衡量后来的作品并构筑文艺史)、历史主义-实证主义(将文艺史看作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纳入整个社会历史)和审美形式主义(与社会历史分离的自律历史)范式,指出它们割裂了文艺与历史、历史方法与美学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希望建立一种将三者统一起来的方法论,即命名为“接受美学”。[2]287他将作品研究变换为作品存在方式的研究,进而为作品存在史的研究。作品的存在史也是作品与接受互动的历史。姚斯认为读者参与了作品的存在,甚至决定着作品的存在。[3]按照姚斯的看法,听者的音乐审美经验和生活经验构成期待视域,这种期待视域是理解的基础;对作品的理解过程就是这种期待视域对象化的过程。显然这跟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相通,他也确实受到伽达默尔的影响。但是对姚斯而言,愉悦是审美经验的基本事实,审美判断毕竟是听者的判断,因此,听者才是作品意义的最终确定者,虽然听通俗音乐与听先锋音乐情况不同,亦虽然作品是作曲家和听者共同创造的产物。
另一位接受美学代表人物沃夫尔冈·伊瑟尔(Wolfang Iser,1926-)提出“两极理论”,他认为作品是一种交流形式,作品存在于文本与聆听之间,不同于乐谱,也不同于音响。这里可见茵加尔顿的影响。他从“文本召唤结构”转为“文本的隐在读者”,以此来探讨相关问题。伊瑟尔赞成茵加尔顿关于作品的可能性或“空缺”由欣赏者转变为现实性或“填补”的观点,进一步指出欣赏对文本构成具有内在性。他认为实际的欣赏只实现了文本的某一种可能性,“隐性读者”才是理想的欣赏者。可见,“隐性读者”对应的是文本的所有可能性。[4]当然,“隐性读者”仅仅是理论上的存在,这无非还是回到接受美学的基点,即作品充满各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是为接受者设计的,并等待接受者去实现;具体的一次审美接受,是作品意义的一个可能性的实现。
接受美学看到听者之间的差异,打破了以往确定、客观的意义的看法和释义理论,但是它仍然具有中心性,只不过将意义阐释中心由作者、作品转移到读者。
二、释义去中心的时期及其哲学基础
20世纪中下叶以来,西方逐渐兴起后现代主义思潮,音乐界则稍晚,大约在世纪后期。与释义学有关的理论或思想观念,确实具有“传统沿路断裂”的特征。[5]在后现代语境中,“作品”概念和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释义对象和行为也随之发生重大改变。
1.从方法论到本体论
哲学释义学。虽然哲学释义学在先,接受美学在后,但是前者是去中心的释义学开端,而且是释义学由方法论转为本体论的典型。伽达默尔认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根本不是方法论的差别,而只是认识目标的差异。……我们是在探究:理解怎样得以可能?这是一个先于主体性的一切规则的问题。……理解不属于主体的行为方式,而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包括此在的全部世界经验。”[6]5-6伽达默尔认为艺术对哲学释义学而言最具有典型性,因此他以艺术经验作为事例展开研究。他说:“在任何情况下,每一个对艺术作品具有经验的人无疑都把这种经验整个地纳入到他自身中,也就是说,纳入到他的整个自我理解中,只有在这种自我理解中,这种经验才对他有某种意义。”[6]7这段话表明,对艺术作品的理解就是对自我的理解,这也是哲学释义学的本体论旨趣所在。伽达默尔指出,“作者的思想决不是衡量一部艺术作品的意义的可能尺度。”这一观点将作者从释义活动中剔除出去了,仅此而言与结构主义和接受美学有相同之处。但他进一步又指出,“理解(Verstehen)从来就不是一种对某个被给定的‘对象’的主观行为,而是属于效果历史(Wirkungsgeschichte),这就是说,理解是属于被理解东西的存在(Sein)。”[6]8这里强调了对“作品”的释义不是对给定对象的主观阐释,而是在一种“关系”中的实在的理解行为。“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6]385最后,伽达默尔用“视域融合”来概括哲学释义学的要义。[6]393所谓视域融合,即历史视域和理解者当下视域的融合。这里又将作品中心和读者中心剔除出去了。他指出审美者总是在自己的“前理解”基础上对艺术作品作出释义的。如果说现象学追求的是“面向事物本身”,希望通过现象学还原(排除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先入之见,洗刷掉认识的底色)让本质存在的事物在人的意向性中本真地显现自身(即所谓“绝对被给予”),那么视域融合则不认为前理解能够洗刷掉,对象不可能按其本色呈现;理解或阐释得到的“颜色”是认识的底色和对象的原色混合的结果。一方面它不是作品客观存在的自身,另一方面它也不是读者主观映射之物,而是二者结合的产物。这样,作品的意义就像一个矿藏,可以不断开采;每一次的艺术体验活动,都是一次视域融合提取意义的行为。由于读者的经验不断改变,因此他的认识或心灵的“底色”也不断改变,视域融合的结果——对作品意义的理解也不断改变。显而易见,“视域融合”是非中心性的,它顾及作品和读者、历史和当下、客观和主观双方,而不以某一方为中心。
2.从结果到过程
德里达的“焚化”理论,是行为艺术的观念表达。在德里达看来,艺术是一种过程,而不是过程的结果。过去看重的“作品”,是创作行为的结果。它被当作审美对象,与欣赏者分离,构成“主体-对象”二元关系。在作品被当作审美对象的同时,也被当作了意义的载体,成为理解对象、释义对象。这也正是多年来音乐分析、阐释所面对的对象,意向性对象所关联的存在,当然也是分析美学论域中的囊中之物。德里达指出真正有价值的是艺术过程,而不是结果。对于这样的过程,他曾经用“沙漠的旅行”来说明,认为旅行过程就是意义所在之处,旅行过后只剩下“足迹”或“踪迹”,那不是艺术意义之所在。后来他又用“焚化”来说明这样的产生意义的过程,并相应用“灰烬”来表示结果。在德里达看来,艺术意义在于焚烧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有一种天赐(in the gift),赋予焚烧的过程无限美妙的意义。[7]这样的过程充满即兴性、不确定性,而不是按照既定设计(例如乐谱)走套路的活动(按照乐谱的表演)。从结果到过程,传统意义的“作品”被解构了。
相应的创作现象是行为化的音乐。作曲家只需要用文字表述为表演提供指示,而表演者根据提示来“演奏”。甚至可以由作曲家本人来表演。前者例如斯托克豪森的《来自七天》最后一个乐章《金粉》,表演者根据作曲家的文字谱进行表演。
四天内完全单独生活/没有食物/绝对安静,不要有很多活动/睡得少到必要的程度/尽可能少思索/四天后,深夜里/事先不要与人交谈/演奏一些单音/不要想你在演奏什么/闭上你的眼睛/只是听。[8]
后者如约翰·凯奇的《0分00秒》(或《4分33秒》第二号),作曲家自己在台上做各种表演,发出各种声音。对这些“作品”的释义,显然应该聚焦过程,而不是作为结果的“乐谱”。实际上它们本来就没有传统意义的乐谱可分析;真正的作品只存在于过程中。在“东方后现代”(不彻底的后现代,整合了现代主义的后现代)视野下,谭盾的《地图》实际上由结果和过程两部分组成。前者即传统概念的乐章,后者则是其DVD后半段展示的整个创作过程,包括寻找表演场所和实施的过程。释义应该兼顾二者。
这样的过程性的“作品”充满了即兴性,甚至由听众来表演,例如《4分33秒》,观众席发出的任何声音也即作品中的声音。这些过程中的声音都是随机发生的,它们没有确定结构,更不是预设的结构,如奏鸣曲式之类。当听众和表演者混为一谈的时候,舞台中心也就被消解了。流行文化的广场音乐现场也具有“焚化”过程特征:在巨大的声光电笼罩下,台上台下同吼共扭;在巨大的体能输出的同时,昨天和明天都不在场,而此在,则是“集体精神吸毒”状态,或者“主体零散化”[9]。
至于我们要从传统概念的作品中寻找的意义,德里达认为它是永远不在场之物;作品仅仅是能指链,所指就像《等待戈多》戏剧中就要到来却始终没有到场的“戈多先生”。这样的能指链是一种延异系统,无始无终。以语言为例,被书写或言说之物都不在场;体验到的东西是无法言说的,审美体验如此,宗教体验如此,日常生活中情感体验或感性体验皆如此。如果要言说,那么只能是从能指到能指,形成一种换喻的关系。当然,不可言说之物亦为存在之物;能够被感受到的东西,亦有意义。德里达说的是言说本身的意义不在场。这里需要深入思考的是:感性意义与理性意义的区别,作品包含的意义与行为的意义的区别。
在德里达看来,体验过程才是最有价值的。体验过程充满随机性,就像民间狂欢节一样,没有传统意义的导演和预演,整个过程充满偶然性,因而具有非中心性。这样,焚烧的体验既是艺术过程,亦是艺术意义阐释过程。
3.从作品到文本
罗兰·巴特的“文本”观。巴特从结构主义走向后结构主义,将“作品”替代为“文本”。其“文本”不同于传统意义的文本。传统意义的文本基本上等同于作品,在历史释义学主导的年代,作品是有主人的,即作曲家;作品的意义是确定的,社会历史文化及音乐相关思潮通过作曲家,汇同他的创作动机,将确定的意义注入到作品中。结构主义时期,作品的主人被抛开了,但是作品的意义依然被看作是确定的,就在结构要素的关系之中。而在接受美学那里,虽然音乐的意义随欣赏者的不同而不同,但是意义依然具有归属中心。巴特的文本观,继承了前说,又摒弃了中心论调:首先,文本是没有主人的,因此不必从作者那里寻找意义;其次,文本只具有一个可能性的场域,而不是锁闭着确定意义的确定结构;再次,读者每一次进入文本空间/可能性场域,可以获得某种可能性,从而生成某种意义,这种意义既不是文本的唯一意义,也不是它的全部意义。“评述者一旦摆脱任何整体性观念,他的工作便恰恰在于虐待文本和切割言语。不过,被否定的并不是(在此为无可比拟的)文本的品质,而是其‘本性’。”[10]这段话有两点需要关注,一是否定整体性观念,二是否定传统文本的本性。“整体性”是西方传统本质主义哲学的特点之一,它跟确定性、普遍性等相关。作为普遍性真理体系,传统哲学追求完满性,体现出整体性特征。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是向整体性开战的著名斗士,美国后哲学文化、新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也从反本质主义入手反对整体性。所有整体论都是本质主义的;所有本质主义都是中心论的。正是这样的反对,在释义领域才出现了非中心的阐释观念和行为。“文本”就是一个开放的、未完成的可能性场域,而读者本身也没有一个本质主义的中心,也在不断变化或处于各种关系之中,处于各种状态之中;两个非中心的事物(文本与读者)在某一次释义过程中产生某一意义析取,即巴特的“虐待文本”的行为。文本的传统“本性”在这里受到否定。
4.从确定到随机
哈桑在其代表作《后现代转折》(1987)中用“不确定性内在性”来概括后现代主义的审美特征。“不确定性”意味着中心的消失,还有本体论的消失。不确定性针对以往的确定性,还衍生出各种特征。从哈桑对照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表格[11]118-119中,可以看出这些特征。

表1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比
哈桑在该书的第八章还另行概括出后现代主义的十一个特征:不确定性、零乱性、非原则化(decanonization)、无我性和无深度性、卑琐性和不可表现性、行动和参与、构成主义、内在性。[11]125-132
从哲学上看,西方传统哲学本体论有三个假设:其一,世界是确定的,有一个本质;其二,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可以认识到世界的本质;其三,语言表达能力是无限的,可以表达出认识捕捉到的世界的本质。在这里,世界的本质、认识到的本质和语言表达的本质,三者可以打等号。只有确定,才有本质。一个不确定的存在,还未构成某个实体,也就无所谓本质。可见确定性是西方本体论哲学的基础。而在此基础上建构的美学、艺术理论,包括释义学,以及艺术作品,便都具有中心性。打破确定性,也就打破了中心性。哈桑概括道:“所谓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我指由下面这些各种不同概念所共同勾勒的一个复杂范畴:模糊性、间断性、多元性、散漫性、反叛、倒错、变形。仅变形一项就统摄了当今许多自我消解的术语,如反创造、分解、解构、消解中心、移置、间断性、分裂、消隐、消解定义、非神话化、零散化,反正统化——还不用说反讽、断裂、无言这些专门术语。”[11]119-120对于后现代音乐现象,哈桑的“不确定性”是释义的重要参照。
“内在性”(immanences),对应的是“超越性”。后者一直是西方传统和现代主义哲学美学所追求的。形而上学真理体系具有抽象性,它超越于具体世界。而内在性,则是内在于人的东西。哈桑指出:“我使用的这个词并无宗教的回音,它只用来指心灵的能力——在符号中概括自身,愈来愈多地参预自然,并通过它自己的抽象性概括而作用于自身的能力,它因而逐渐地、直接地成为了其自身的环境。”哈桑提到一些相关词,如发散、传播、推进、相互作用、交流、相互依赖,作为语言动物的人类,“通过他们自己创造的符号构成他们的世界”。[11]120联系后现代词汇中的文本间性(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和主体间性(互为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也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以说明内在性的含义。只有内在性,才有这些性质。这种性质内在于事物中,而不是超越存在于事物之外或之上。
人类创造了艺术,这个感性和理性交织的世界也是内在于人类自身的。正如上述伽达默尔所言,艺术是内在于人的整个经验的。但是这种内在性并非整体性,也非确定性,而是充满模糊性、认识之谜,“它趋向开放(时间与结构或空间上的开放)、游戏、祈愿、暂时、分裂,或不确定的形式,趋向反讽和断片的话语,缺席和断裂的‘苍白的意识形态’、以及分解的渴求和对复杂的、表现思想的无声的创新”。[11]122这些词无论指谓是否明晰,都构成了一个释义的迷宫。如同德里达焚化的体验,是内在于体验者的,所有内在性都充满随机、偶然、暂时等特点。这些都颠覆了中心性释义理论。
5.从中心到多元
巴赫金“多元对话”理论,是典型的非中心性理论。巴赫金是前苏联的文学理论家、思想家,他虽然不是后现代主义者,甚至不知道何谓后现代主义,但是,他的理论为后现代主义提供了思想资源。他提出的“复调小说”,即若干主题的情节同时存在于一个小说之中,但彼此并无关联,体现出多元性和断裂性,或无机组合性。“复调”显然借自音乐,但是多元混杂的文学作品却不似复调音乐那样具有有机性。所谓“多元对话”,即针对作者中心、作品中心和读者中心,巴赫金指出整个文学艺术活动的意义是相关主体之间相互交流产生的。例如小说的意义,是作者、作品中的人物、读者相互交流产生的。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已经跟小说里的人物进行了对话;小说中的人物之间本来就处于对话状态;读者在阅读时,跟小说里的人物进行对话,并且间接跟作者对话。意义就在这样的多元对话中出现。
生态哲学。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21世纪以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进一步拓展思想疆域,将早时引入的生态学观念提升到哲学层面。美国哲学家罗尔斯顿是生态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的许多著述中,探讨了生态伦理和哲学问题。如《环境的哲学问题》(1974)、《生态伦理是否存在》(1975)、《我们能否和应否遵循自然?》(1979)、《哲学走向荒野》(1986)、《环境伦理学》(1988)、《保护自然价值》(1994)、《全球环境伦理》(1995)、《自然、文化与环境伦理学》(1996)、《被管理的地球与自然的终结?》(1999)、《生物多样性与精神》(2000)、《论可持续性发展:一项持续的伦理研究》(2002)等。“生态”显然来自自然科学,如环境科学和生物科学。生态哲学借助生态学研究成果,探究生态系统的持续存在根由。“生态”和“环境”表面上相似,实质上二者有重大区别。前者是非中心的,后者则是中心论的。前者将所有相关者联系起来,但并没有一个权力中心;后者则以人类为中心,视其他相关者为围绕中心的隶属物。“我们要尽可能广义地理解生态学这个概念,要把它理解为研究关联的学说。”[12]虽然生态哲学主要研究的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地球生态问题,提出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提倡维护生态整体的伦理思想,但是从哲学上看,反中心论体现了后现代精神;“生态观”是一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甚至有学者认为,已经来临的时代是人类生态学时代,“‘后现代’是生态学时代”。[13]
在一个没有中心的生态系统中,是什么因素维持着系统的存在?自然规律。什么规律?“自组织”。美国的埃里克·詹奇在《自组织的宇宙观》一书中指出,自组织是“自然系统的动力学”模式,即“自然系统的建模”,是一种新的统一范式,即“自组织范式”,涉及物理化学系统、生物系统、社会生物系统、生态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14]自组织理论中的核心词“随机涨落”,表明生态系统的无序状态;“对称性破缺”,表明从无序走向有序的开始(条件);“耗散结构”,表明消耗能量的动态有序结构。这些自然科学哲学思想被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所采纳,引起了人文社会科学本身包括释义学的变化。音乐出身的美国著名学者、罗马俱乐部成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顾问或专家队伍的灵魂人物E.拉兹洛就是应用自然科学哲学的典型。在其专著《进化——广义综合理论》的基本概念中,就有“自创生”“吸引子”“突变、混沌和分叉”等。[15]显然拉兹洛采取了社会生态观来看待全球社会问题,并依此提出个人的解决方案。这在他的其他著作如《决定命运的选择》(1992)[16],以及他主编的广义进化论丛书如《多种文化的星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的报告》(1993)[17]等中,都能明确展现。拉兹洛的核心观点是:生态系统中各因素是相互关联的;差异的存在并不影响整体的有序;冲突并不导致各方离散或消灭,而可能在更高层次上统一起来;系统中各个单元都有责任维护生态平衡。拉兹洛据此提出“星球意识”,即“多种文化的星球”的思想观念。
伴随生态哲学的发展,出现了生态美学、景观美学等,如美国的史蒂文·布拉萨的《景观美学》[18]等。不赘述。
生态哲学美学作为新兴的、影响广泛的思想资源,对现代释义学的启示很大。这种启示的核心是反中心论与多样性关联或广泛关联,以及不确定性和自组织性或自创生性。巴赫金的“多元对话”理论就具有这样的生态哲学美学特征。
6.从单一到多样
后现代主义的“多元”观念。首先,针对本质主义哲学的大一统本质观,后现代主义关注差异的存在,认为差异是不能抹除的。以往的哲学希望建立普遍性真理体系,因此采取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抹除现象的差异,抽取本质的统一,以此建构形而上学。后现代主义打破这种思维方式,强调差异,因而强调多元存在。上述生态哲学美学就是在这种差异观、多元论基础之上构建的。
“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15年美国学者霍拉斯·卡伦的《民主与熔炉》一文。这个词的含义不同于“文化多元主义”,前者是非中心的,后者则是中心性的,它维护一种普遍性的文化,只不过容忍少数族群文化的存在。[19]12-13多元文化主义源自二战结束之后,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新格局的出现,以及伴随的相关思潮的出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州政府和军队等,都分别建立了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英国、德国、法国、荷兰等欧洲国家,也都不同程度制定了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或掀起学术思想讨论热潮。[19]15-22迄今“多元文化”的思想已经在全球传播,甚至成为共识。当然也引发很多争议。有些西方学者指出,多元文化主义“远非一种方法论,而更接近于一种意识形态”。“多元文化主义是某种政治手段、战略、道德实践和思路的文本总和”。当然,它仍然具有文化意义。“多元文化主义确实涉及社会文化领域,因为它成了一个口号,鼓励了各种文化表达与文化实践,使得人类学意义上的不同的文化传承(音乐、造型艺术、教育、烹饪、文学)相互交融,彼此渗透,或仅仅共存。在所有以上领域,多元文化主义几乎就是文化杂交、双语主义、文化混血,以及文化混合的同义词。但是,更普遍地说,它的作用在于强调了各种文化和种族实践的共存是必要的,必须在一个不应被质疑的整体中相邻而共存。”[20]127-128巴柔认为用“文化间性”比用“多元文化主义”更有利于阐明他的观点。因为“文化间性意味着文化之间相互开放,开展永恒的对话。”对文化间性的思考,就必须质疑文化同一性或同质性的观念,也必须质疑各种思想与文化实践在全球的“整平化”,即所谓全球化或世界化。[20]129这种思想要求在对特定文化中的音乐进行意义阐释时,要考虑到“他者”的存在。这种释义方法与文化比较的方法相通,但仍然不同。比较是被比较的双方或多方都在“明处”,在同等的、可比的限定中探讨各自之间的异同。而在他者参照下的文化阐释,他文化作为参照,在阐释过程若隐若现,被阐释者占据阐释中心。巴柔指出,在这样的多元文化阐释中,在对多元文化关系造成的特殊文学艺术样式的阐释中,作者是中介。“我们就是要用这种文化间性以及‘之间’这个词缀去对照一种多形性的现实;各种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媒介,作家被看作是‘中介人’。”[20]130文化间性理论强调差异,认为只有差异才有各自的特点,也才有对话的条件和相互理解的前提。这一点是后现代主义真谛所在。
在后现代多元文化语境中,还出现了很多相关理论,如后殖民批评理论、社会性别理论等,都对传统释义学提出新的挑战。这种多元论要求人们转变观念,“认识到关于一个既定主题,不只一种‘正确的’或‘真实的’论点。这样理解的话,多元论就是对旧的哲学信仰的挑战,因为那种信仰认为,关于存在的东西,构成知识的东西和道德涉及的东西的问题,只有一种正确的答案。多元论的世界画面迫使我们承认,可以有许多不同的不一致的概念的和道德的框架,有许多信仰体系和终极价值,并不存在一个决定何为‘真理’的压倒一切的标准”。[21]按照这种多元论哲学观点,对一部艺术作品的解释,或对一个艺术现象的阐释及评价,可以有不同的“正确的”的看法,也可以有不同的“真实的”事实描述。其实,在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那里,已经可以看到这种多元论的阐述。相反,按照历史释义学的观点,一部作品拥有一个确定的意义,对它的理解或解释,即对这个确定意义的还原;即便不能还原,也应该逼近,不断解释是因为需要不断逼近。而其他中心论释义学,如作品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释义也都依赖一个中心,当然,作品中心论中,意义是确定的、唯一的,解释者应该排除主观因素;读者中心论中,解释的主观性受到合法化和合理化,意义也因此具有多样性,但毕竟还要依赖读者这个中心。巴赫金的“多元对话理论”,意义不仅是历史视域和当下视域的融合,而且还有围绕作品的多类主体的对话,这样的意义不是“一”,而是“多”,是“多”中之多。
以上这些释义学转向的相关理论,都对音乐释义产生深刻影响。
三、西方释义学转变在音乐释义领域的表现
释义学转变在音乐学领域主要体现在“新音乐学”理论及其释义的学术实践。虽然新音乐学主要出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但是就像后现代主义一样,在随后的年代并没有消失,而是体现在具体的社会文化实践中,体现在具体的音乐意义阐释中。
1.挑战音乐学
克尔曼将西方音乐释义相关思路划分为“音乐学”“音乐理论”和“民族音乐学”。前者主要研究西方历史中的艺术音乐,中者主要研究西方的现代艺术音乐,后者则主要研究非西方的或含西方在内的民族文化中的音乐。克尔曼指出,艺术音乐体现的是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因此属于精英音乐,受到来自中产阶级的音乐学家的关注。到了20世纪,19世纪甚至更早的时期的艺术音乐仍然受到音乐学家的关注。因此,克尔曼联系西方过去不同时代的情况,得出一个确定看法:这样的“传统”是培育学者能够联系或认同的传统,“这些传统,如前所述,可能受到阶级以及民族和宗教意识形态的控制。”[22]24-25作者提到哈里森的一个看法:对于审美者而言,音乐是哪个时期的并不重要。这一点颠覆了音乐学家的历史观。当然,20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音乐另当别论。“20世纪音乐学的意识形态是反现代主义和‘精英化’的”。[22]27这里显然指的是后现代主义。这是后话。回到多数音乐学家的学术兴趣,他们坚持研究历史中的艺术音乐,“展示早期音乐文本及其事实和人物,而不是去解读它们,这被视作音乐学最突出的成就。不只是实际上不准进行批评性的解读——这里解读即试图将所有收集资料用于审美评价或阐释。甚至连历史解读都加以限制。在这个领域,大多数活动都是将音乐史事件(被认为是自律现象),安排成简单化的进化格局……。很少注意音乐史与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的互动。也很少试图将音乐理解为一般文化的一个方面及同其的联系”。[22]30另一方面,音乐理论主要关注作品分析。比如申克分析法,受到普遍关注和应用。在对纯音乐对象的分析中,音乐意义就是作品结构的意义,是客观存在于结构中的,和人的主观因素无关。克尔曼指出“申克体系体现的主要是一种结构主义者的审美观”,似乎很有逻辑,很精确,却把所有的调性音乐都看作一种复杂繁琐的结构形式。[22]70申克力图寻找所有调性音乐的共同精髓,即不变的抽象的范型或基本结构,忽视具体音乐的无限多样性或丰富性,显然是本质主义的思路。十二音作曲法本身就是一种从“基本形式”(Grundgestalt)出发,应用“发展变奏”的手法创作乐曲的。逆过来,对十二音作品的结构主义的分析,就是寻找基本形式和发展变奏手法的过程;音乐意义即基本形式所蕴含的音关系。整体序列主义音乐作品的意义也一样,只不过基本形式除了音高原型序列之外,还有时值、力度和音色安排的序列。随后的音集分析理论也如此,追踪作品的“基本结构”(Urssatz)。这些分析理论“只对结构进行了阐述,而且把其作为一个纯粹的、脱离了任何历史语境的部分”。“在20世纪50年代的实证主义氛围中,固守逻辑——而非价值观,成了无人不谈的话题”。先锋派与学院派最终合二为一,体现了一种作曲与教学的守护“抽象思维”的联盟。[22]75,83,86这种抽象思维,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逐渐形成的理性中心主义在20世纪的延续。这也是后现代主义所反思的。因此克尔曼的批评,体现了新音乐学释义观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基础。实证主义的分析法、释义观,将音乐释义活动引向“本真性”或“真实性”,讲究“证据和解释”,就象自然科学那样。克尔曼认为,以19世纪为例,人们完全可以直接去研究打动他们的作品,并认识到“分析是形式主义思维的产物,并对批评有很大的局限”。当然,他也指出分析的价值所在,即有利于“再现珍贵的曲目”。在他看来,新的、更全面的分析应该朝着“批评的方法论”方向前进。[22]126-127显然批评与价值判断相关,与主观世界相通。克尔曼非常赞赏查尔斯·罗森(Charles Rosen)在其《古典风格》一书中的做法,称其为“近年论音乐最好的、最重要的著述之一”,尽管从传统理论立场看它属于异端。该书的做法就是分析加批评,既探究作曲家如何操纵音乐语言,又对结构进行价值判断。克尔曼指出罗森甚至在专业性容许的范围里运用了感情语汇。当然,感情语汇是用来做价值评判的。
1950年孔斯特创立了“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名称,替代此前的“比较音乐学”。在这个领域,克尔曼特别提到查尔斯·路易斯·西格(Charles Louis Seeger,1886-)。克尔曼看中西格论述中的两个主题,一个和认知有关,一个和价值有关。西格将认知分为音乐的言语认知和音乐的音乐认知,二者都属于“描述”范畴。而判断和批评则是跟描述相对的“价值”范畴。西格希望将这两个范畴统合起来阐述音乐的意义。[22]138-139克尔曼赞赏的就是这种释义路子,还有民族音乐学对中产阶级精英传统的对抗。克尔曼还提到其他知名民族音乐学家,如布莱金、梅里亚姆等。
通常学界将音乐表演当作音乐作品的阐释。但是这种表演的阐释多追求对作品本真性的揭示,表演者被要求“符合习惯”“符合风格”,遵循历史规范。克尔曼指出,像本雅明所说的机械复制那样的音乐表演,是糟糕的表演。也就是说,“本真性”不能保证表演质量,因此这个术语是有害的。克尔曼认为表演是一种批评,因此应该有表演者的独特的音乐阐释。他列举了珍妮特·贝克的演唱,钢琴家霍洛维茨的演奏的事例。他们的表演都不符合惯例和风尚,但在克尔曼看来,却都具有批评品格和阐释力量。克尔曼认为如果将分析作为表演的指南,那么这样的表演就没有阐释。表演家按直觉阐释音乐,并不需要分析家操心。表演的直觉,包括良好的趣味、想象力和诠释的敏感性。克尔曼指出,提高音乐诠释水准,是批评家的追求,也是表演家、音乐学家努力的方向。[22]169-171,185,193
最后,克尔曼还贬低音乐辞典和乐谱之类出版物的价值。他说:“一部辞典,即使是最好的辞典,基本上也只是实证主义的又一个胜利纪念品。它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是一个不可移动的东西,而非一支不可抵御的力量。辞典的特征是大纲性、歌颂性、回顾性,且枯燥无味,它储存,但不是产生、变化、启发、发展。作为仓库,它所提供的自然是实证主义的茎秆,而非解释的花瓣。”[22]201这段话是克尔曼的经典语录,是他挑战音乐学的檄文中闪光的一段文字。从中可以提炼出克尔曼的音乐释义思想——只有走向批评的音乐阐释才具有产生、变化、启发、发展的动态。
遗憾的是,克尔曼在赞赏民族音乐学的释义方法的同时,表明自己对非西方文化的音乐兴趣不大,并表明自己认可的是西格的音乐学家身份而不是民族音乐学家。此外,他的“挑战”资源仅限于音乐学界,并没有看到他对音乐之外的学界资源的引用。
戈尔的《音乐作品的想象博物馆》也有类似的挑战。她的着力点是解构传统概念的“音乐作品”,指出“作品概念的用法越全面地泛指化、普遍化和中性化,便越缺乏具体性甚至历史性。……以例如纯粹本体论同一性的名义将一切音乐现象统统纳入宽泛的作品概念,往往同时使不同类型的音乐之间,本来有充分理由加以保持的差异边缘化,甚至消除这些差异。在此,本然化的不只是作品概念,而且是作曲家的标准。”[23]10这段话有三个要点:一个是“作品”概念被超越历史地泛化;一个是本质主义的“作品”概念消除了不同文化中的音乐现象的差异;最后一个是“作曲家”也随着“作品”的概念而建立了某种标准,这种标准确立了本质主义“大师”概念。这种看法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基础。戈尔明确表示自己的学术目标就是“揭穿声称全然泛指、中性或无所不包的本体论学说的谎言”,打破“言必称作品的思考方式”,追问“没有作品概念的音乐实践意味着什么”,“消解某种业已过分僵化的概念的陈规”。[23]12-13正由于在1800年前后出现了“作品”概念,音乐释义也就明确追求忠实性和本真性,“忠实原作这个词首先进入音乐话语,而后进入其他表演艺术”。总之,从作品概念确定开始,西方音乐界形成一种音乐创作和诠释的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音乐体制和实践。例如该书开头描述的音乐厅制度。对此,戈尔给予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这种反思和批判显示了反本质主义的释义立场。戈尔在初版前言里强调音乐的历史性,意味着强调音乐在历史中的变化。为此她反对分析美学的阐释方法,明确指出它具有局限性,即亦然追求本质性、普遍性释义结果。
2.社会性别理论的音乐阐释
新音乐学的一个分支是从社会性别角度来阐释音乐,包括女性主义释义和更广泛的社会性别(包括同性恋等各种不同的性取向)的释义。这种角度的释义在学界及社会引起很大反响。“社会性别”(gender)有别于“自然性别”(sex)。这个领域的学者指出,自然性别被社会化之后,出现了很多变化。雄雌动物之间在体态和行为上的差异,没有男女人类之间的差异那么大,有的甚至难以区分。《木兰辞》用诗句表达了这一点:“双兔伴地走,焉能辨我是雄雌”。人类文明发展以来,很多民族文化都强调男性的阳刚和女性的温柔。男女在发型、服饰等外观上,在内在的观念上,在日常行为上,都显示出明显差异,最终出现了文化习俗的禁忌和社会规训与惩罚。“伪娘”和“女汉子”受到社会排斥,在找对象、找工作等方面都遭遇困难。传统社会在强调刚柔二元对立的同时,排斥其他性别类型及其关系的合法性,如同性恋至今未受到普遍接受。20世纪西方女性主义的出现,针对的是男性中心主义,看到的是男女之间的差异。随后的后女性主义,进一步看到女性内部的差异。但是,以上都还建立在男女二元对立基础之上。在同性恋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化理论“酷儿理论”(queer theory)则打破了这种二元对立。“酷儿”不分男女,但是仍然划分出“酷”的程度,如“一般酷儿”“较酷儿”“最酷儿”(gueer, queerer, queerest)[24]11等等。酷儿理论的重要思想:向异性恋和同性恋的二分结构、社会“常态”挑战;向男女二分结构及一切严格分类挑战,进而批判西方传统二元对立思维方法;对传统的同性恋文化挑战,彻底破除性别身份和性身份,包括异性恋身份和同性恋身份;使所有边缘群体联合起来,共同行动,否定传统性别主流文化,也否定本质主义的身份建构;以后现代主义为基础,向所有传统价值挑战,开创新的人际关系格局和新的生活方式。酷儿理论提出多重主体论(multiple subjectivities),如男女同性恋者、超性别者、异性者、双性恋者等,这些主体身份不仅跟社会和种族的历史背景相关,而且“抛开单一的、永久的和连续性的‘自我’,……它是表演性的,可变的,不连续的和过程性的,是由不断的重复和不断为它赋予新形式的行为建构而成的”。[24]7
麦克拉蕊(Susan McClary)对西方男性作曲家创作的作品进行性别角度的释义,同时关注女性作曲家或表演者的创作,阐释其中的“阴性”表现。在《阴性终止:音乐学的女性主义批评》(FeminineEndings:Music,GenderandSexuality. 1991)一书中,作者探讨了被男性作曲家“再现于音乐中的女人”,如歌剧女主人公“波佩亚”“卡门”“疯女人”等,也探讨了一度创作和二度创作中的“女性再现音乐”。非同凡响的是,该书还专题讨论了同性恋、异性恋在音乐领域的表现,虽然篇幅不大,例如柴科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舒伯特的创作等。作者本人概括自己的研究目标是音乐中的“社会性别(gender)与性欲特质(sexuality)的问题、歌剧中女性与男性的文化再现、不同历史时刻的音乐如何建构欲望与快感,以及音乐论述普遍充斥的性别化隐喻”。[25]19作者提到自律论音乐美学的问题,如汉斯力克和斯特拉文斯基,指出这种强调音乐自主的思想是为了避免受到任何文化阐释,它影响到后来的音乐形式主义分析。此外,作者指出,一直到20世纪末,音乐生活仍然处处体现了作者理论指向的事实。如歌剧中出现的依然是社会性别化的角色,听众听音乐仅仅满足于感官刺激,而音乐理论家和批评者依然习惯于依赖男女二元对立的文化模式来思考音乐问题。麦克拉蕊同样提倡文化理解、文化批评对音乐释义的价值。为此提到阿多诺的社会学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模式,认为人类学模式的文化分析,提供了多种方式去理解音乐,“我认为《阴性终止》所运用的诠释架构,是将人类学、社会学与文化研究常见的议题拿来检视‘我们自己的’音乐。……将文化批评导入音乐学领域的工作多半落在女性主义理论学者的肩膀上”。考察西方各时期的艺术音乐,以及现代流行音乐比如蓝调乐手的表演等,麦克拉蕊说:“音乐学能研究什么,不再取决于一组精英层级的美学价值。取而代之的,与文化形塑相关的议题——不同音乐如何影响自我模塑、如何演现社会互动的模式——已移至核心位置。”[25] 21,23这样,对音乐意义的阐释,就出现多种方式,包括女性主义批评或社会性别释义的方式。反对精英文化的姿态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姿态,反主流文化,关注被社会文化边缘化的群体,如女性、同性恋者、有色人种、少数民族、成长于殖民或后殖民环境的人。麦克拉蕊指出,这些人被西方文化影响,却又被西方文化当做他者(Other)而生存于边缘。“随着女性主义、同志解放(即同性恋解放——引者注)和后殖民批评的兴起,除了社会性别和性态特质,种族、民族、身体、情感和主体性也遭到质疑。”[25]28但是主流文化的质疑并不能阻挡新音乐学阐释力量的兴起,并最终如火如荼地展开。麦克拉蕊将音乐意义阐释的女性主义和其他新兴文化批评理论联系了起来,构成一幅当代新音乐学阐释的学术景观。
男女二元对立的模式通过长期社会规训建构起来,男性-阳刚,女性-阴柔,这种模式或观念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影响着人们的音乐实践。例如大卫·勒温(David Lewin)认为音乐与社会的普遍文化联系是将旋律与阴柔气质相连,而和声则与阳刚气质相关。长期以来人们多关注阳刚气质,直接影响了接受舒伯特和肖邦的方式,也不能全面阐释多变的瓦格纳的思想和创作。这种二元对立模式早在女性主义兴起之前就存在,只不过女性主义或社会性别理论将它纳入研究视野。在西方历史上,不少学者言说音乐常常采用性别隐喻方式。例如奏鸣曲式,人们常将阳刚和主题联系,将阴柔和副题联系。而再现部的“解决”,则是将副题隐匿到主题之中,或者自我消解,以便突出主题的主调。女性主义批评这种隐喻充满了男权中心论调。因为阳刚往往和理性、客观相联系。强调阳刚、理性、客观,是和西方历史上音乐人往往被社会贬斥为“娘娘腔”密切相关的。这种强调,是对社会贬斥的抵抗。女性主义音乐批评恰恰要从音乐角度阐释音乐意义,强调阴性,就是强调非理性、主观性。消解男女二元对立模式,就是消解理性与非理性、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模式,此即后现代主义去中心的旨趣所在。见后述。
澳大利亚的女性主义音乐美学学者莎莉·麦克阿瑟(Sally Macarthur)则采用比较方法,比较同一内容男性作曲家和女性作曲家创作的乐曲之间的差异。在其专著《音乐中的女性主义美学》(FeministAestheticsinMusic,Westport,Connecticut and London;Greenwood Press.2002)中,她列举了许多事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麦克·阿瑟认为男女性经验对其创作具有重要影响,并能体现在他们的作品特征中。男性性经验中通常只有一个高潮,在性行为过程的后半段,结尾具有收束性。女性性经验中则有多个高点,结尾具有开放性。例如马勒的妻子与她的男性音乐教师选择同一诗歌作为歌词,分别创作了歌曲。通过形式结构分析可以看出,男性作品具有一个高潮和收束性结尾,而女性作品则有多个高点分布和开放性结尾,尽管男性诗人创作的诗作本身的结尾是收束性的。阿瑟再三强调自己的举例是“小型叙事”,并不具有普遍性。[26]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第一次女性主义音乐批评浪潮,进行女性音乐史建构,到20世纪中叶第二次浪潮的女性主义音乐批评的理性反思,相关学者着力于解构男性-理性中心。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后现代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后女性主义音乐阐释思想,进一步深入剖析社会性别差异在音乐领域的多样表现及其社会文化和历史根源。后女性主义不仅看到女性与男性的差异,还看到女性内部的差异,进而看到更多的性取向及其在音乐领域中的表现。如露丝·索利(Ruth Solie)于1993年编辑出版的MusicologyandDifference:GenderandSexualityinMusicScholarship(中文版《音乐学与差异:音乐研究中的社会性别与性征》于2011年由谢锺浩翻译,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汇编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16篇论文,集中讨论了女性“本质论”、女音乐家的社会性别表现以及音乐家的同性恋现象等几个焦点问题,是后女性主义音乐批评的代表作品。菲利普·布莱特(Philip Brett)、伊莉莎白·伍德(Elizabeth Wood)编辑的QueeringthePitch:TheNewGayandLesbianMusicology(《酷儿音调:新同性恋音乐学》,1994)是音乐领域酷儿理论的奠基性著作,探讨了音乐家、理论家的同性恋倾向对其音乐创作的影响,并用同性恋视角探讨音乐作品中的性欲表现以及一些音乐家如亨德尔、布里顿以及舒伯特的性倾向对其音乐创作的影响。其他关于酷儿理论的研究还有约翰·基尔(John Gill)的QueerNoises:MaleandFemaleHomosexualityinTwentieth-CenturyMusic(《酷儿噪音:20世纪音乐中的同性恋》,1995)、韦恩·克斯坦鲍姆(Wayne Koestenbaum)的TheQueen’sThroat:Opera,Homosexuality,andtheMysteryofDesire(《皇后的咽喉:歌剧、同性恋和欲望的秘密》,1996)。进入21世纪,由贝弗利·戴蒙德(Beverley Diamond )和皮尔·莫伊萨拉(Pirkko Moisala) 编的论文集MusicandGender(《音乐和社会性别》,2000;中译本由谢锺浩翻译,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2012)通过编辑相关的音乐成果,论述社会性别、音乐与表演的关系。玛丽·安·斯玛特(Mary Ann Smart)主编出版的SirenSongs:RepresentationsofGenderandSexualityinOpera(《塞壬之歌:歌剧中社会性别与性征的表现》,2000)对歌剧展开了深入的性别解读。其他相关论著还有简·伯恩斯坦(Jane Bernstein)编辑出版的Women’sVoicesAcrossMusicalWorlds(《世界音乐中的女性声音》,2004)。简·帕斯勒(Jann Pasler)的WritingthroughMusic:EssayonMusic,Culture,andPolitics(《音乐中的写作:论音乐、文化和政治》,2008)。[26]
性别这一释义的切入点,其合理性不可能从传统哲学基础的释义学理论那里获得,而只能从“后哲学文化”(理查德·罗蒂语)的释义理论中获得。因为无论是作曲家还是表演家,很多人很多作品恐怕在创作时都没有表现性征的意图,除了莫扎特的《唐璜》、韦伯恩的《沃采克》之类,但表现爱情的作品的释义需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爱情与性相关,却不等于性。历史释义学、结构主义释义理论都以本质主义、实证主义为基础,以作曲意图考掘、作品结构分析作为阐释音乐意义的证据。因此它们不可能为社会性别的音乐释义提供合理性依据。而后现代主义文本观和释义思想,则认为只要从人与音乐的交流(对话)中发现某种可能,就可以对它进行阐释。
结 语
每一种音乐释义理论都有其社会历史因缘。应该放弃“学术进化论”的误区,认识到释义理论并非越新越好。研究者必须弄清楚自己所欲或目的、所处的关系、所采取的释义立场,才能选择合适的释义方法,实现有效的意义阐释。
后现代关系实在论哲学为上述非进化论的多元释义学提供了合理性证明。它破除了物质实体观,提出新的存有观,即首先确定关系,然后确定存在。无论是中心主义释义学还是多元主义释义学,在各自的关系中都具有合理性。虽然历史碎片无法全部搜集齐全,历史无法再现,但是追求作曲家、作品和音乐事件的历史真实仍然是有意义的。因此,历史释义学的方法依然可以根据某些学术需要而采纳。结构主义对于人们了解音乐作品的形式意义,对作曲技术的研究和作曲理论的发展具有特殊的价值。接受美学对音乐审美意义的阐释具有重要贡献,因此,在审美关系下进行音乐意义阐释,仍然可以借助它。后现代主义各种释义理论,首先能够阐释20世纪以来的新的音乐现象,其次它们拓展了音乐阐释空间,也开掘了更多新意义的可能性。因此在后现代各种语境-关系中,上述释义理论各有各的价值。
[1]于润洋. 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2]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3]姚斯.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4][德]伊瑟尔. 阅读行为:中译版序言[M]. 鑫惠敏,张云鹏,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5][美]丹尼尔·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 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9:134.
[6][德]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M]. 洪汉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5-6.
[7][法]包亚明. 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M]. 何佩群,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5-16.[8]钟子林,编. 西方现代音乐概述[M].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1:164-165.
[9][美]F. 杰姆逊.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 唐亚兵,译. 西安:陕西师大出版社,1987:156.
[10][法]罗兰·巴特. 罗兰·巴特随笔选[M]. 怀宇,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166.
[11][美]伊哈布·哈桑. 后现代主义转折:第四章[M]//王岳川,尚水. 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2][德]汉斯·萨克塞. 生态哲学[M]. 文韬,佩云,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2-3.
[13]鲁枢元. 生态文艺学[M].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169.
[14][美]埃里克·詹奇. 自组织的宇宙观[M]. 曾国屏,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68-86.
[15][美]E.拉兹洛. 进化:广义综和理论[M]. 闵家胤,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45-51.[16][美]E.拉兹洛. 决定命运的选择[M]. 李吟波,张武军,王志康,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7.
[17][美]E.拉兹洛. 多种文化的星球[M]. 戴侃,辛未,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8][美]史蒂文·布拉萨. 景观美学[M]. 彭峰,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9]常士闫. 异中求和:当代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想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13.
[20][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 多元文化主义与文化间性:从形象学到媒介[M]//乐黛云,孟华. 多元之美.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1][爱尔兰]玛丽亚·巴格拉米安,埃克拉克塔·英格拉姆. 多元论:差异性哲学和政治学[M]. 张峰,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1.
[22][美]克尔曼. 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M]. 朱丹丹,汤亚汀,译.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8.
[23][英]利迪娅·戈尔. 音乐作品的想象博物馆[M]. 罗东晖,译;杨燕迪,审校. 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
[24][美]葛尔·罗宾等. 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M]. 李银河,译. 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
[25][美]苏珊·麦克拉蕊. 阴性终止:音乐学的女性主义批评[M]. 张馨涛,译. 台北:商周出版社,2003.
[26]邓婕. 论莎莉·麦克阿瑟的女性主义音乐美学思想[D]. 北京:中央音乐学院,2013.
【责任编辑:吴志武】
The historical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theoryin western music
Song Jin
(Musicology Department, Central Conservatory of Music, Beijing, 100031)
The music interpretation theory in Western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centrality and pluralism. The centrality was mainly popular from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middle of the 20th century,and the pluralism which includedhistorical hermeneutics, structuralism, aesthetics of reception, was used after the second half of the century,especially in the postmodernism and later period. In pluralism, the characterof culture from result to process, form work to text, form certainty to random, from center to multielement, and from single to diversity. The analysis refers to many postmodernism methods, including structuralism,theory of multiple dialogue and ecological aesthetics. All kinds of method for meaning explanation, which have no evolutionary relationships, have particular historicalcontext, logical structure and rationality under concept of realism on relations.
Musical Work; Text; Meaning Interpretation; Hermeneutics;Structuralism; Aesthetics of Reception;Postmodernism
2016-06-06
宋瑾(1956-),男,福建宁德人,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副所长、音乐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音乐美学研究。
10.3969/j.issn.1008-7389.2016.03.002
J614.3
A
1008-7389(2016)03-00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