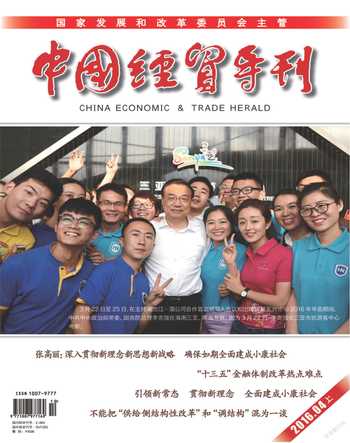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世界意义
2016-09-10左传长
左传长
一、与世界经济互惠共荣的“强国福民”探索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民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虽然随着外部经济环境和内部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和前景依然看好,有望克服拉美一些国家所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在不远的将来做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一,并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实现“强国福民”,即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
根据世界历史发展经验,经济中心的转移必然带来相应学术中心的转移,这是不仅是因为经济中心会成为广受关注的研究对象和实践场所,而且新兴经济中心的本土学者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会逐渐上升。20世纪的美国伴随形成全球经济霸权而确立其世界学术中心地位的历史就是鲜活的例子。本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经济和学术的世界影响力也日益增强。关于曾宣称历史终结的所谓“华盛顿共识”的式微和近年来对中国模式的热议,就是国际专家学者关注的宏大历史叙事。
不可否认,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基于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学习借鉴国际理论和经验,积极融入全球经济的历史性探索,并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即在先农村后城市的分步推进、先“特区”试点示范后逐步复制推广以及价格改革的“双轨制”过渡体制等改革政策实践,逐步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提高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的比重和效率,在较短时间内减少了改革的摩擦阻力和经济成本、实现了整体经济效率的帕累托改进;另外通过“增量式”的市场体系构建和相应激励约束机制的不断完善,极大激发了经济要素的创新创造活力,使经济的价值创造效率和效益空前提高。这些改革发展举措都是对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实践是创造性丰富和发展。当然,也不可避免存在制度经济学上的“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在某些方面和领域形成后续改革的阻力,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改革的成效。与此相伴,中国的对外开放事业也通过采取区域性“优先发展”和产业领域的渐次开放策略,不断发挥我国要素禀赋等的比较优势和有关区域的区位优势,并逐步实现市场空间和产业领域在时序上的渐次开放,采取优势资源优先聚集发展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策略,逐步演进到均衡发展的新局面,拓展了参与国际资源配置的市场空间,通过经贸往来和投资合作,构成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毋容置疑,中国是改革开放的收益者,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和政策实践的探讨将也必将日趋具有世界意义。
当然,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伴随着特定的发展阶段,在积极推进经济市场化、国际化的同时,成功推进经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结构性转型,逐步实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空间结构优化,使经济发展的优势不断累积、经济增长的潜力不断释放。当前,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力人口比重下降,支撑国内经济转型发展和基于劳动力要素比较优势的人口红利趋于下降。与此同时,土地资源的相对有限性和生态环境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日益增强,以要素市场化和投入量增加为标志的要素驱动型改革发展难以为继,因而必须转向创新驱动型发展新阶段,在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在更高基数下趋于下降,而对包括生态环境、精神文化、民生幸福等元素在内的经济增长的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
当前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就是我国面对发展新形势、新阶段、新情况、新常态,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并借鉴国内外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引领我国“十三五”乃至今后相当一段时间改革发展事业的新希望、新要求、新思想。所以,中国的改革发展的理论和政策实践既具有世界意义,也立足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实践,并与时俱进、动态创新发展。如为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发展,曾提出新型工业化的概念,基于经济空间优化和人口空间分布调整、体现生态(环境)、人文(教育)、智慧(信息)特征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概念。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充分体现了国际借鉴与中国国情的有机结合,体现了干中学引发的后发优势,和消化引进吸收并结合中国特色的再创新,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无疑是国际理论政策和经济全球化的收益者。
二、逐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前景”创想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引领的新阶段。一方面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引发的深度经济结构调整尚未结束,中国经济运行必须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而相应调整发展模式,而外部可以借鉴的理论政策和实践案例资源趋于枯竭,进入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中国经济自身亟需进行理论和政策创新;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增强,中国经济政策实践的示范意义和“溢出”效应扩大,国际社会期待中国智慧,希望从中国的理论创新和政策实践中获益,这就对我们政策理论研究的同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是我国大力加强中国特色智库建设的原因所在。
可以说,世界经济已步入需要中国引领的新一轮“再全球化”新阶段,中国的理论创新既充满希望、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也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再生创新提供了新的契机,正如当年欧洲文艺复兴中的“美第奇”效应一样,需要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外来先进文化交叉融合再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人类未来提供中国智慧创新“解决方案”,而且这种解决方案不仅要立足自身发展,破解发展瓶颈和难题,而且要放眼全球,直面人类全球化、现代化发展所面临的共同挑战,着力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冷战结束后的日裔美国学者傅山提出的宣告西方模式大获全胜“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曾预言的“文明冲突论”,到国际新儒学代表人物、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基于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对话理性”理论而倡导的“文明对话论”,再到中国学者提出的“文明互鉴论”,进而提出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要求,无疑是中国智慧对人类发展思想的创造性贡献。
当前,国内外经济正在经历结构性大调整、历史性大变革。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提出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试图转嫁危机走出困境,不仅面临使美元因面临“升降两难”的“特里芬”之谜的困境而国际霸权地位下降,而且也暴露出其民主制度本身存在的内在缺陷导致政府“财政断崖”风险危机;日本以邻为壑以求自保的所谓安倍经济学,所释放出的货币宽松至负利率的“毒箭”,也未能使其经济起色好转;在欧洲不仅几经折腾的欧元区内发展不平衡的不同国家曾惊现退出欧元区的危机,现如今作为金融大国的英国也面临脱离欧盟的公投,失去向心力的“双速欧洲”可谓若隐若现;作为新兴经济体代表金砖国家也遭受资源价格波动下跌严重冲击;中东石油国家不仅面临资源价格下跌、石油美元回流美国的压力,个别国家还饱受内乱和战火之苦,引发的难民危机还殃及欧洲等地;气候反常变化,国际疫情频发等等。人类社会正面临各种前所未有的挑战。
面对世界经济的新挑战和国内创新驱动发展新阶段新要求,适应经济新常态,应对长期依赖凯恩斯学派需求管理的宏观经济政策所积累的结构性产能过剩等负面效应,借鉴西方“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和美国经济学家拉弗等供给学派的思想理念,提出宏观微观相结合中国特色结构性“供给侧”经济政策改革方向,即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供给模式,谋求改革和创新红利,主要包括:通过差异化财税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调整和优化升级,改革商事制度,复制推广自贸区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改善营商环境和服务体系,激发微观市场主体活力,利用互联网+技术手段开拓市场空间,重塑市场经济生态。当前的关键还在于打造与趋于强化的约束条件相对应的激励机制,使市场创新活力竞相迸发。这些政策措施必将推升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新境界,跨界融合创新的局面已经展露曙光,文化创意、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和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和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业态也呈现蓬勃发展新气象。着眼于“富余”产能国际转移合作的“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也已初见成效,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高铁和核能已经走出国门,不断落户。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合作中也要着重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些理念不仅在国内发展中需要坚持,在中国引领新一轮全球化的今天更应反映在国际经济“互联互通”和“互利共赢”的合作发展中。与此同时,还要注重国内不同地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文脉历史渊源,促进国内外统筹协调发展,按照生态经济模式,循环高节约利用国内外资源,参照我国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与新兴工业化相结合的发展思路,促进国际产能合作伙伴国家健康永续发展,同时注重将产能转移合作与开拓新兴产业国际发展空间相结合,而不能只是将传统富余产能简单转移,而且还要注意尊重合作伙伴特色文化和生态多样性、善于发现并吸取他人优点,促进和谐协调、共荣互惠发展,为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好家园而不懈努力。
三、寻求经济学研究突破的“理论创新”尝试
在经济理论创新方面,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也不甘落后,呈现积极创新的昂扬面貌。北京大学教授、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提出了强调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促进产业升级演化的《新结构经济学》。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教授着眼金融行业发展新趋势曾提出《大金融》学说。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财政部科研所原所长贾康研究员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群体力图创建的中国特色《新供给经济学派》,并为我国推出“供给侧”改革政策做出有益贡献。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学家突破性创新的大胆尝试,对中国学者进行理论创新具有标志性示范意义。与此同时,海外知名学者,如曾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傅山教授开始反思美国模式、华盛顿共识中的忽视政府作用一些弊端,从而对中国政府在创造经济奇迹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予以肯定。法国学者皮凯蒂在其享誉世界的名著《21世纪资本论》中更是揭示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所蕴含的资本和劳动深层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内在矛盾,而国际学界对拉美“中等收入陷阱”和德国及北欧其它国家在面临国际金融危机中的不俗表现也对社会福利政策予以更多的关注和思考。有基于此,本人作为国家首批高端宏观经济智库试点单位的一员,结合自己的观察思考,在此不揣冒昧,提出本人认为值得关注和持续研究、初步设想包括下述创新要点在内的“新宏观经济论”学术命题,供各位学界先辈和同仁批评指正。
(一)造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GDP”概念
在经济学通行的国内生产总值“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ION)概念基础上,以中国新近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中国引领新一轮“再”全球化的宗旨,迎接“人类共同体”的未来,倡导“新GDP”发展概念框架,即“全球发展推动(GLOBAL DEVELOPMENT PROMOTION)”,并将五大发展理念核心要素融入到“新GDP”经济核算体系之中。
(二)基于政府社会市场协同的“新PPP”模式
当前中国政府包括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借鉴国外理论和实践推行的政府与市场协同的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发展概念,局限于具体投资项目的公共资本和社会资本结合,而国资委倡导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也仅限于微观市场主体企业层面的不同性质的股权合作关系。我们不妨从经济学界关注的更加宏观的经济模式框架诉求出发,将PPP概念扩展到政府社会市场协同的“新PPP(PUBLIC-PROFITABLE –PHILANTHROPIC)”模式框架,其中PUBLIC公共部门代表政府,PROFITABLE代表盈利部门的市场,包含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国有企业,比单纯的PRIVATE更加符合中国实际,含义更为贴切,而用公益PHILANTHROPIC置换PARTNERSHIP,将突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二元思维,进而拓展到涵盖由PHILANTHROPIC延伸的非政府、非盈利的社会公益机构等,在国内外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进行的大量研究基础上,如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有机结合的同时,更加注重政府对包括社会保障、公益慈善、文化教育等在内的社会事业的发展的政策扶持,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更加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以及培育更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企业等,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有机联系、良性互动协同发展的新模式。
(三)适应新型产业形态的“新金融”理论
我国分业经营和监管的金融体系面临混业跨界经营和联合监管的新挑战,各种改革方案也在酝酿探讨之中。与此同时,作为改革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工具的财政和金融交互作用值得更多关注和研讨,在学术文献中“财政和金融”有时通用英文“FINANCE”一词,在政策实践方面,国家发改委承担的财政金融协调职能颇具中国特色、值得重视和总结提高。在互联网+等新型产业形态下,金融元素与其他产业广泛融合发展,实体经济与金融产业的良性互动也是时代的新要求,突破消费与投资界限的数字货币等新金融值得关注。在国际金融大调整中亟需协调国内外金融货币政策,尤其当前结合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和外部环境变动,应促进人民币“内贬外升”,既有效化解国内通过紧缩趋势、也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同时要未雨绸缪、积极谋划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有效应对“独立有效的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汇率稳定三者”不可兼得的“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困境,并前瞻探讨人民币如愿成为国际货币之后我国货币政策的国际溢出效应,避免当前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所面临的“升降两难”的特里芬之谜效应,至少要追求形成无损国际伙伴帕累托改进效果,着力推进我国有效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并以“互惠共荣”为目标造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
(作者为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所博士、清华大学科研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