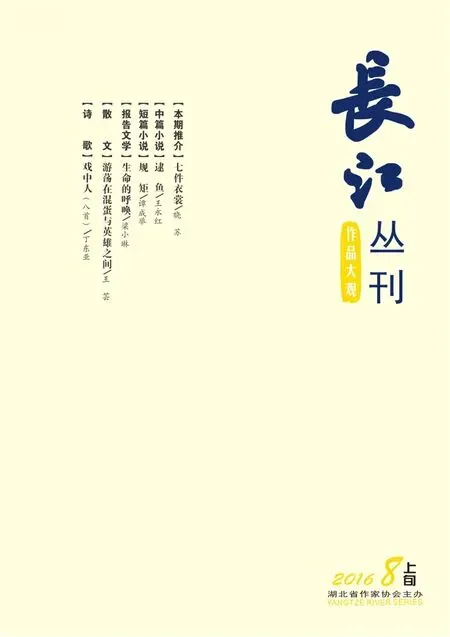游荡在混蛋与英雄之间
2016-09-08王芸
王 芸
游荡在混蛋与英雄之间
王芸

王芸,女, 中国作协会员,生于湖北,现为南昌市文学艺术院专业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江风烈》,小说集《与孔雀说话》,散文集《穿越历史的楚风》《接近风的深情表达》《经历着异常美丽》《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倾城张爱玲》《纯净与斑斓》等。在《小说选刊》《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新华文摘》等刊物发表小说、散文逾200万字。作品被收入30余种选本。
说影片《无耻混蛋》之前,必须说说导演其人,昆汀·塔伦蒂诺。
昆汀的电影充满了关于坏人与好人、混蛋与英雄的辨证。一个又一个混蛋在邪恶与正义间荡着秋千,他们发出肆无忌惮、痛快酣畅的大笑,用力地跃动身躯摇荡秋千,时而奔赴这端时而奔赴那端,在真理的天空划出缭乱不堪、却又清晰深刻的印迹。非学院派出身的电影导演昆汀追求的就是这种效果,清晰而又缭乱,鲜明而又混沌,简单而又复杂,低俗而又神圣。他似乎迷恋混蛋,迷恋血腥,又迷恋英雄,迷恋神圣,以非常态的路径融合两者——用戏谑的方式消解神圣,又让神圣来解救低俗;用血腥戳戮正义,又让正义浸染血腥。他让它们交混在一起,搅拌,打烂,血肉模糊地成为一体。
在他的影片中,那一个又一个让你过目难忘的混蛋,让你不齿让你嘲笑让你愤恨,却又在某些时刻让你情不自禁地牵挂、同情、尊重,恨不能为他们去伸张正义。说到底,昆汀的电影里没有一个完美的好人,也没有一个彻底的坏人;没有一个完美的英雄,也没有一个彻底的混蛋。
他喜欢在电影里大段大段地进行论证,他也喜欢在电影里运用小说的结构方式,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乐此不疲,耐心地为之命名。在那些角色喋喋不休展开论证的环节里,你仿佛看见昆汀那冷静严肃而又暗隐了一丝戏谑的表情。有时他那么克制而不动声色地完成残忍,有时他那么泼洒地英武气十足地完成复仇,有时他那么肆无忌惮地血腥泛滥,有时他那么不正经地进行宏大叙事,有时他那么混蛋却又那么英雄……但你得承认,他的电影总是热气腾腾,在不知不觉中感染你,攫住你,让你边看边感叹,“昆汀这小子!”看完,还要情不自禁地回味、咂摸一下。仿佛用舌头卷过嘴角残留的一抹血腥。
据说,导演昆汀用十年时间来创作、修改《无耻混蛋》的剧本。有过中长篇小说创作经历的人大约知道,十年的时间跨度可能带给一部作品颠覆性的变化,让最初的构思一再转折,改变方向。最终呈现给我们的影片《无耻混蛋》由五个章节构成,沿两个线头行进,情节之弦紧绷,意外频现,直至影片尾端,两条线索交汇,轰轰烈烈地实现臆想中对希特勒的完美刺杀。
影片开头,杀机在田园牧歌似的景象中突然而至。砍入树桩的斧头,退进小屋的三个女儿,竭力用井水泼面镇定自己的父亲,他即将面临一场势必折磨他余生的审问。
昆汀的镜头语言简洁、克制。杀机的逼近淡近无痕,却在漫长耐心的铺垫之后,以极其残忍暴虐的方式抵达杀戮。
德国党卫军汉斯·兰达上校有彬彬有礼的举止,一丝不苟的作风,略带讥讽的笑容,隐而不发的锋利,含而不露的凶残。这位伪装起来的混蛋,被法国人喻为“犹太人猎手”的德国军官,以追杀藏匿起来的犹太人为职责,并为自己的无往不胜而自傲。他不慌不忙,近乎饶舌地一步一步引导对话,四两拨千斤地攻破了这位父亲的心理防线,迫使他供认出了正躲藏在他家地板下的邻居索莎娜及其家人。士兵蹑足而入,枪弹蜂拥而出,击穿地板,木屑飞溅,看不见的鲜血迸射。
索莎娜的家人都被残杀,只有她逃向了田野,带着满脸血痕、惊惶、悲怆和刻骨的仇恨。
影片的第二个线头,是九个空降到法国的美国士兵,他们都是犹太人,怀着对纳粹的刻骨仇恨,在法国的山野间开展游击战,唯一的任务是“屠杀纳粹兵”,以尽可能凶残的方式,让纳粹兵闻风丧胆。奥尔多·雷恩中尉是他们的首领。这个脖颈上残留着一圈疤痕的军人,开场白痛快直接,“纳粹没有人性,他们的头儿是一个憎恨犹太人、杀人如麻的疯子,他们必须被消灭,所以我们见到的每一个穿纳粹军装的混蛋,都得去死。”
这样一群自称混蛋的军人,立誓要极其冷血地对待大洋彼岸的那群纳粹混蛋。他们说到做到,剥掉每一个纳粹兵的头皮,将每一具尸体开膛破肚,肢解毁容,他们让自己成功地成为了德国士兵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偶尔,他们放掉一个纳粹兵,不是大发慈悲,而是为了让他回去描绘同伴被虐杀的场景,让他回去展示额头永难消除的纳粹标志,将恐怖酿造得更加恐怖。
在昆汀臆造的世界里,他们是一群痛快淋漓的复仇者,一群满身英雄气的混蛋,他们让希特勒束手无策,暴跳如雷。昆汀故意将威武的希特勒画像和气急败坏的希特勒置于同一画面,实现无声的解构和嘲讽。即使是残忍至极的画面,昆汀也习惯幽默顽皮地加以解构,填入昆汀式的戏谑。
四年后再度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索莎娜,已经拥有了另外的名字、另外的身份。她是一家电影院的继承人,她暗暗策划着一场复仇行动。似乎是为了成全她的复仇,昆汀让一个德国英雄佐勒列兵爱上了她。他曾独自守卫一座钟楼,射杀了两百多个敌人,被德国人奉为战斗英雄,他的事迹被拍摄成电影《国家骄傲》,而他在影片中扮演自己。佐勒列兵极力说服德国宣传部长将《国家骄傲》的首映式,放在索莎娜的电影院举办。这无疑是天赐的良机,但走在复仇之路上的索莎娜还要闯过重重关卡。
在餐厅,她与“犹太人猎手”兰达上校再次狭路相逢。这位有着惊人嗅觉的“犹太人猎手”保持着他的警惕与怀疑,他用奶油来试探索莎娜,用言语刺探索莎娜,索莎娜已不是四年前那个惊惶无措的少女,想必四年来她已被刻骨的仇恨磨砺成了一把锋利内敛的箭,只待需要射出的那一刻到来。可是,她毕竟不是钢铁,不是机器,她不得不极力掩饰自己呼吸不畅的本能反应,竭尽全力冷静以对。终于,在经历漫长的“猎手”的逼视和试探之后,兰达起身离开,索莎娜再也控制不住,一瞬间,痛苦的表情侵漫而上,吞没了她的面容。这表情,代表了一个民族曾经的共同表情。
索莎娜的计划逐渐成型,她要在电影院举办“德国之夜”,在《国家骄傲》的首映式上来一场痛痛快快的复仇。与此同时,在索莎娜看不见的地方,一场针对德国最高首领的刺杀计划“影院行动”也在进行中。与索莎娜微弱的个人力量不同,这计划惊动了英国和美国军方,惊动了雷恩中尉和他带领的那班混蛋们。这一端的较量,更加惊心动魄。
在整个计划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是作为间谍的德国演员布里奇特·冯·海姆斯马克与英国派出的阿齐·西科格斯中尉接上头,将他带入德国人为《国家骄傲》举办的首映式——“基本上所有的臭蛋都在一个篮子里了”,只要炸掉这个“篮子”,就可望早日结束战争。万军丛中取其首,这是军方的战略。
西科格斯中尉在战前是个电影评论员,熟悉德国电影,成为这项任务的最佳人选。接头地点选在一个偏僻乡村的地下室小酒馆里,最终,除了海姆斯马克,没有一个人活着出来。
导演昆汀善于拿捏节奏,营造紧张气氛,也不吝啬残酷和血腥。其代表作《杀死比尔》之一、之二,同样是关于复仇的大戏,铿锵激越。在《无耻混蛋》中,小酒馆接头的一场戏同样被渲染得扣人心弦,跌宕起伏。
几个在此聚会游戏的德国士兵、三个乔装打扮的英国和美国士兵、一个充当间谍的德国女演员、一个坐在暗处嗅闻可疑气息的盖世太保,在空间狭小的酒馆里狭路相逢。试探,掩饰,化解,冲突,剑拔弩张,乱枪横飞,情势快速扭转……最终得以活着离开的,只有腿部受伤的海姆斯马克。混乱中,她遗落在现场的高跟鞋,让“犹太人猎手”兰达上校捕捉到了危险的信号。
看起来,一个筹备多时、精心酝酿的“影院行动”即将告吹。可即使是在一根钢丝上也要继续走动,雷恩中尉不肯放弃这大好机会,打算铤而走险。他带着被德国人以惊恐的心情称为“杂种”的游击队队员,跟着腿上裹缚石膏的海姆斯马克,衣着光鲜地出现在电影首映式上。已经知晓兰达惊人嗅觉和手段的我们,暗暗为他们捏一把汗。
两根线索在盛大的电影首映式交汇,却又保持各自的节奏平行向前,若即若离。两根线索在行进中都遇到阻碍,佐勒列兵突然闯入放映室,与索莎娜先于结局双双仆倒在血泊中;海姆斯马克被兰达暴虐地掐死,雷恩中尉被逮捕。这一切都在公众的视线之外,悄然发生。影院里,电影如常放映,银幕上的佐勒完成着他射杀两百多敌人的壮举,他的每一次射击都激起观众的一阵欢腾,而银幕的背后,堆置着即将置观众于烈火的硝酸胶片。
兰达,一个看起来那么忠心耿耿、尽忠尽责的德国军官,在千钧一发之时,却与被捕的雷恩中尉玩起了谈判的艺术。原来,这是一个正为自己寻找未来命运出口的投机者,他以自己的敏锐眺望到了战败的结局,冀望以自己的智慧和狡黠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英雄”,一个终结纳粹罪恶的“英雄”。只是雷恩,断不肯将这个彻头彻尾的混蛋成全为一个“英雄”,他以混蛋的手段完成了对这个纳粹混蛋的审判与惩罚。一个无法抹除的象征耻辱的标记,被他用尖刀刻在了兰达的额头。
复仇在戏剧性的转折中实现,被锁闭的电影院内,索莎娜出现在银幕,她面带嘲弄的微笑,“你们就要死了,好好看着我的脸,我就是杀死你们的犹太人。”伴随她的笑声,烈火喷涌而出。
她终于实现了复仇,在年轻短暂的生命之外。
映衬着烈火奔腾的背景,两名“杂种”游击队队员冲着惊惶逃窜的德国军官们疯狂射击,轰轰烈烈。昆汀在他创造的世界里,帮千千万万的犹太人实现了他们的复仇,以混蛋加英雄的方式。轰轰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