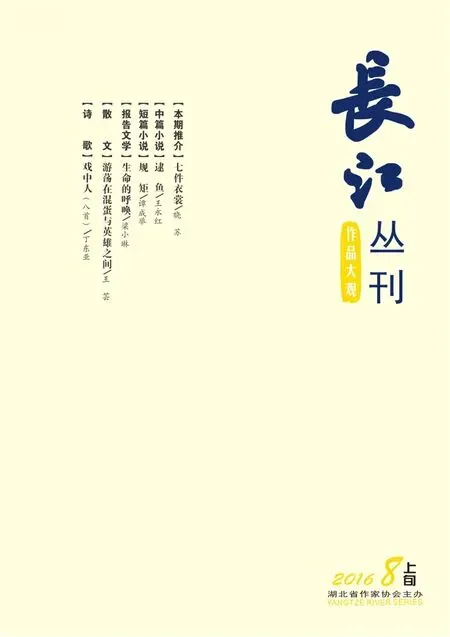七件衣裳
2016-09-08■晓苏
■晓 苏
七件衣裳
■晓苏
1
在我的老家油菜坡,人们都习惯于把衣服称为衣裳。与衣服比起来,衣裳不仅说起来悦耳动听,而且还给人一种柔软温馨的感觉。我在老家生活了十七年,在那十七年中,我已记不清穿过多少件衣裳,但有七件,我却至今难以忘怀,并且还经常在梦中与它们重逢。
我是从小学三年级那年开始注意自己的穿着的。在那以前,我似乎没有关心过我的衣裳,父母给我缝什么衣裳,我就穿什么衣裳,无论是大还是小,无论是新还是旧,无论是白还是黑,我都往身上穿,从来不管它是否合适,是否好看。但是,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突然对穿着产生了兴趣。
说句笑人的话,我那时对穿着产生兴趣与一个女同学有关。那个女同学姓宗,与我坐一张桌子,是我们班主任的侄女。她长得很漂亮,穿得很干净,学习也好,特别会唱歌。有一次上体育课,老师教我们玩一个游戏。那个游戏是两个人一组,并且是一个男同学和一个女同学自由组合。开始我以为姓宗的女同学会主动跟我一组,因为她毕竟与我同桌。可她却没有选我,她只看了我一眼就把目光投向了一个姓刘的男孩,很快与他组合到一块儿了。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我于是就想,她为什么选择别人而不选择我呢?我很快想出了原因,原来姓刘的男孩穿的比我好,他穿着一件灯芯绒褂子,而我身上的褂子却是用土布染的。这是一个重要发现,就是这个发现,使我开始注意自己的穿着了。

晓苏,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先后在《收获》《人民文学》《作家》《花城》《十月》《中国作家》《大家》《上海文学》等刊发表小说五百万字。出版长篇小说《五里铺》《大学故事》《成长记》《苦笑记》《求爱记》5部,中篇小说集《重上娘山》《路边店》2部,短篇小说集《山里人山外人》《黑灯》《狗戏》《麦地上的女人》《中国爱情》《金米》《吊带衫》《麦芽糖》《我们的隐私》《暗恋者》《花被窝》《松毛床》12种。另有理论专著《名家名作研习录》《文学写作系统论》《当代小说与民间叙事》等3部。作品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刋》《新华文摘》《中华文学选刊》等刊转载40余篇,并有作品被译成英文和法文。曾获湖北省第四届“文艺明星”奖、首届蒲松龄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二届林斤澜短篇小说奖、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湖北文学奖、第六届屈原文艺奖。《花被窝》《酒疯子》《三个乞丐》分别进入2011年度、2013年度和201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
那时候,我是多么想我也有一件灯芯绒衣裳穿啊!但那个想法不切实际,只能在心里想一想。当时,我们家非常困难,兄弟多,劳力少,父亲虽然在镇上工作,但每月只有三十七块五角钱,母亲一个人在农村劳动,每年都要给生产队交一百多块钱的口粮款。在那个岁月里,我们兄弟能穿上土蓝布衣裳已经很不容易了,哪里还能奢望穿灯芯绒衣裳啊!
不过没过多久,母亲给我缝了一条黑布裤子。在那之前,我每天放学后都上山挖黄姜,一连挖了半个月。半个月后,母亲把我挖的一背篓黄姜背到供销社卖了。也许母亲想奖赏我一下吧,她在用卖黄姜的钱买了盐和煤油之后,便用剩下的钱买了一块黑布,给我缝了一条裤子。
开始把那条裤子穿到身上时,我并没有感到它有什么特别。那是一条很普通的裤子,用卡叽布缝的,无论是颜色还是样子,都很普通。
但是穿到了学校里,那个姓宗的女同学却睁着圆圆的眼睛把我的黑裤子看了好半天,她还说,你穿这条黑裤子真好看!我一听就激动了,浑身上下麻酥酥的。课间操的时候,那个姓宗的女同学还偷偷地给了我一把红枣。就这么,我深深地喜欢上了那条黑裤子。后来一连好多天,我都舍不得脱掉它,差不多天天穿着它去上学。母亲说,你怎么天天穿这条黑裤子?也该换下来洗一洗了。星期天,我总算把那条黑裤子脱下来让母亲洗了。但到了第二天,我又把它穿到了学校。
大概是穿得太多的缘故吧,我那条心爱的黑裤子不到两个月就破了。最先破的是膝盖头那里,破了一条小口子,接着屁股上也破了一个洞。黑裤子破了,我伤心极了,还流了许多眼泪。
2
到了过年,父亲手头再紧也是要给我们兄弟缝一套新衣裳的,用父亲的话说,叫一年一个新头儿。我的老家油菜坡,长期流传着这样两句话,大人盼种田,小孩盼过年。小孩盼过年,无非就是盼吃盼穿,过年可以吃腊肉和米花糖,可以穿新衣裳。父亲当时在单位上很忙,差不多每年都是在大年三十的头一天晚上才能回家。父亲在一年当中至少也要回十几次家,但他这一次回家是最受我们欢迎的,因为他进门不久,便要打开提包,从中拿出他为我们过年缝的新衣裳。父亲开提包时,我们的眼睛都睁得有鸡蛋那么大,一眨不眨地看着父亲的那双手。父亲的动作很慢很慢,他一点一点地扯着拉链,像是要故意吊我们的胃口。当他打开提包掏出新衣裳的那一刹那,我们都会禁不住哗地惊叫一声,然后像鸡子展翅一样,张开双手朝新衣裳跑了过去。
长期以来,父亲过年时给我们兄弟缝的新衣裳都是一样的布料,要么都是黑的,要么都是蓝的,要么都是灰的,我们兄弟穿着新衣裳站成一排,就像是一个部队的。然而,在我读五年级的那一年,父亲却给我缝了一件与几个弟弟不大相同的褂子。几个弟弟的褂子都是用灰布缝的,那灰布的颜色很不正,看上去新不新旧不旧的样子,并且也很薄,摸在手上像皮纸。而我的那一件,却是板栗色的,一看就赏心悦目,而且布料也厚实,摸起来特别舒服。开始我并不知道我的褂子与几个弟弟的不一样,父亲要我们穿着试一下大小,等我们都穿上新衣裳站在一起的时候,我才猛然发现我的与众不同。我顿时一愣,用异样的目光看着父亲。父亲这时走过来,摸着我的头笑着说,你已经长大了,应该穿得好一点儿!听了父亲的话,我心头陡然一热,一股温暖的泉水很快涌遍我的全身。而我的几个弟弟,却有些不高兴了,一个个翘起小嘴巴,用怪怪的眼神看着我。母亲这时用手把他们揽在怀里,说,等你们长大了,爸爸也给你们缝板栗色的衣裳。
当时在我们油菜坡,有一个过年给军属送对联的习俗。一到大年三十的早晨,生产队就要组织一群人,敲锣打鼓将大红的对联送到军属的门口,先扭一阵秧歌,然后再把对联贴在军属的大门上。给军属送对联,每家每户必须去一个人,这是政治任务。以往给军属送对联,我们家都是母亲去。而在我父亲给我缝板栗色褂子的那一年,父亲却让我去了。父亲对我说,你已经长大了,替你妈去给军属送对联吧。我一听就跳起来,差点儿高兴得发了疯。说实话,好几年前我就盼着加入那个给军属送对联的队伍了。
毫无疑问,我那天是穿着那件板栗色的褂子去给军属送对联的。送对联的队伍有半里路长,我穿着那件板栗色的衣裳,在队伍里穿来穿去,跑前跑后,像一只发了情的小公狗。我发现,我的那件板栗色衣裳在那条队伍中是最好看的,好多人都用羡慕的目光看着我。也许正是因为穿了那件板栗色衣裳的缘故,在往军属门口贴对联的时候,民兵队长特地派我去刷了浆糊。
3
小时候,我的裤子破得最早的往往都是两个膝盖头。一是我们那个地方山路多,走山路就要不住地弯膝盖头,一弯膝盖头就要磨裤子上的那一块。二是我喜欢跪在田里扯猪草,跪着扯猪草又快又省力,但却非常费裤子,尤其是裤子的膝盖头那里。因为家里穷,裤子破了还要接着穿。好在母亲很勤劳,又特别尽职尽责,每当我裤子的膝盖头破了,她都要及时找来一块旧布将那破处补起来。在一条裤子的两条裤腿上,左边的那个膝盖头常常又是先破,因为我用左腿跪地的时候偏多。母亲补裤子,当然是什么地方破了就补什么地方,比如左边的膝盖头破了就补左边的膝盖头,她不可能把右边的那个膝盖头也同时补上。虽然过不了多久右边的膝盖也会破,但那也只能等它破了以后再补。
在一条裤子右边的膝盖头还没破而左边的膝盖头上已经出现补疤的时候,我是很不情愿穿着这条裤子去上学的。因为那样子太难看,一边有补疤,一边没有,就像是一只眼睛睁着,一只眼睛闭着,越看越像一个独眼龙。但是,这条裤子你不情愿穿也得穿,当时我基本上只有两条裤子换着穿,换着洗,当那一条裤子洗了,你不穿这条独眼龙裤子穿什么呢?总不能光着屁股去上学吧?每当穿着这条裤子到学校,我都觉得非常自卑,见人就脸红,脖子发粗,抬不起头来,下课了也不敢出教室去玩,一心只想着把两条腿子藏在桌子下面。
我们初中的老师,一般是没有谁穿补疤衣裳的。但有一天,我却发现代我们初一年级体育课的刘老师的裤子上出现了两个补疤,左边膝盖头上一个,右边膝盖头上一个。因为两边都有补疤,所以看上去并不难看,好像还别有一种味道。下课后,我斗胆问刘老师,你的两个膝盖头都破了吗?刘老师说,只破了一个。我马上问,那你为什么两个膝盖头上都补了疤呢?刘老师说,为了对称嘛!刘老师的话,像是在我面前划然了一根火柴,我两眼顿时豁然一亮。
那天我穿的是一条蓝布裤子,左边的膝盖头上补着一块刺眼的补疤,而右边的膝盖头上还是好好的。傍晚放学回到家里,我一进门就换了一条裤子,然后找来一把剪子,咔嚓一声就把那条蓝裤子右边的膝盖头剪了一个洞。天黑后母亲从生产队收工回来,她一进门我就对她说,蓝裤子的另一个膝盖头也破了,你给我补一下吧。母亲说,吃了晚饭补。晚饭后,母亲一收拾好碗筷就进了她放针线的那间屋。没过多久,母亲突然喊了我一声,让我快去。我马上去了。我刚一进门,母亲便一手把我按在了地上,接着就用一只拳头拼命地打我的屁股,她一边打一边骂,你这孩子真是个败家子,好好的裤子剪一个洞干什么?那晚,母亲真是气坏了。她一口气把我打了好半天,疼得我杀猪似地乱叫。不过她打了我一顿之后,气也消了,接着就在那条蓝裤子的右边膝盖头上补了一个疤。
第二天,当我穿着那条两个膝盖头上都有补疤的裤子上学的时候,我突然感到这条蓝布裤子比以前好看多了。这时,我怎么也回忆不起来头天晚上挨打时的那种疼痛的感觉了。
4
在缺衣少食的少年时代,我最崇拜的有两种人,一是厨师,再就是裁缝。粗糙的米到了厨师手里,就会变成香喷喷的饭,毫无形状的布料到了裁缝手里,就会变成漂亮的衣裳,他们真是心灵手巧,我非常崇拜他们。当时我还想,我长大后要么就当一名厨师,要么就当一名裁缝。在我记忆的屏幕上,我认识的第一位裁缝叫石膏儿,她住在一条小河边上,缝衣裳的那间房子正好临河,她可以一边踩着缝纫机一边倾听水声,如果抬头从窗口看出去,就可以看见清清的河水以及漂在水上的那群白色的鸭子。石膏儿长得很白很嫩,脸和脖子,还有那双手,都像是用豆腐捏成的。我当时想,石膏儿天生就是一个当裁缝的。
我是在读初二那一年的夏天认识石膏儿的。一个慢长的春天过去后,当我脱下那件穿了几个月的黑夹衣的时候,母亲突然说我长高了。我的确长高了,母亲找出我头一年穿过的那件灰衬衣,我怎么也穿不得了。母亲面对长高的我,显得既惊喜又忧愁。后来她终于咬咬牙对我说,走,我们到供销社去。母亲那天是提着一篮子鸡蛋去供销社的。在供销社卖了鸡蛋后,母亲就去扯了一块灰布,然后就把我带到了石膏儿那里。
母亲把那块灰布放在石膏儿的缝纫机上,对她说,给我儿子缝一件衬衣吧。石膏儿草草地看了那块灰布一眼,很快就把眼睛转到了我身上,她的眼睛很亮,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了好久,然后,她又扭头朝那块灰布扫了一眼。母亲以为石膏儿是怕那块灰布的尺寸不够,就说,布不会少的。石膏儿说,布肯定不会少,我是觉得这块布料不适合你儿子穿。母亲问,为什么?石膏儿说,你儿子皮肤这么白,应该穿一件白衬衣。那块灰布太老气了。石膏儿说着,又扭过头来看着我,并且还对我笑了一下。她的牙齿也很白,笑起来特别好看。母亲这时说,他一直穿灰布衬衣的,白衬衣难洗。我突然说,难洗我自己洗!石膏儿听我这么说,又对我笑了一下,然后劝母亲说,那你就给你儿子缝一件白衬衣吧。母亲犹豫了一会儿说,灰布已经买了,再说……石膏儿不等母亲说完便说,灰布买了不要紧,我带你们去供销社退掉,再换一段白布,供销社的经理跟我很熟的。听石膏儿这么一说,母亲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只好点头同意。
供销社的经理果然与石膏儿很熟,我们一去就换了布。那段白布比那块灰布要贵几毛钱,石膏儿要经理免了,经理真的就没要。这让我母亲对石膏儿充满感激,我当然更是感激不尽。
从石膏儿家到供销社有好几里路,一去一来花了一个小时。石膏儿生得白皮嫩肉,但她并不娇气,一回到家里就开始给我量尺寸。她两手捏着一条皮尺,一会儿量我的肩,一会儿量我的膀子,一会儿又量我的胸脯,动作十分娴熟。我闻到石膏儿身上有一股淡淡的香气,像百合花的味道。在给我量胸脯的时候,石膏儿的手指头无意中按了我一下,我顿时有些紧张,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朵。
石膏儿当时就把那件白衬衣给我缝好了,并亲自给我穿在了身上。那件白衬衣真不愧是比着我做的,穿在身上要多合身有多合身。母亲看着穿上白衬衣的我,嘴笑得差点合不拢了。石膏儿这时对母亲说,怎么样,你儿子穿白衬衣好看吧?接下来她又摸了一下我的头说,看,简直像个小新郎了!
说一句难为情的话,那件白衬衣差不多让我激动了大半年,每当穿着它,我就显得特别有精神,无论是在学校读书,还是回家里干活,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儿。我穿得也非常珍惜,生怕弄脏了它。那件白衬衣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动手洗,每次都是轻轻地搓,轻轻地揉,轻轻地抖,像是害怕弄疼了它。
5
我读初三的时候,油菜坡来了好几个支农干部,有的来自镇上,有的来自县城。这些干部很特别,他们在村里走动时,你一看就知道他们不是油菜坡的人,一看就知道他们是从外面来的,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干部。这不光是因为他们戴着手表,也不单是因为他们挨家挨户吃派饭,还因为他们每人都穿着一种很潇洒的裤子。那裤子是咖啡色的,很薄,走起路来一荡一荡的,没有风吹也荡,乡亲们都称这种裤子叫荡荡裤。他们由于穿着这种荡荡裤,走到哪里都受到人们的尊敬,大家忙着给他们让座,忙着给他们递烟递茶,忙着给他们做好吃的。我是非常羡慕那些干部的荡荡裤的,每当他们穿着荡荡裤从我面前走过时,我会睁圆眼睛看他们的腿子,并且转着身子跟着看,他们走远了,我的眼睛还久久收不回来。不光我羡慕那些干部的荡荡裤,就连我们油菜坡的队长和会计也羡慕得要命。他们虽然也是干部,但穿的都是与油菜坡一般农民没有什么区别的布裤子,看起来就显得土里土气,根本不能和那些外面来的干部相比。我曾经注意过队长和会计的眼神,他们一看到外面那些干部的荡荡裤就目光发花,恨不得扑上去将别人的荡荡裤扒下来穿在自己的身上。
队长说起来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虽然脸上有一块火烧疤,头上没有几根毛,但他的两颗绿豆小眼一转就是一个点子。当时,我们油菜坡已经开始使用化肥了。化肥是按计划供应的,大部分是县城化肥厂生产的碳酸氢氨,也有少量的日本尿素。日本尿素是用一种小口袋装的,那口袋很薄,摸起来光滑如水。队长很快把这种装尿素的口袋与那些干部的荡荡裤联系起来了。他于是就用几个口袋缝了一条裤子,又买回几包咖啡色的染料,将那裤子染成了咖啡的颜色。队长刚开始把那种裤子穿出来的时候,乡亲们一下子都傻了眼,差点儿把他当成了外面来的干部,一看他脸上的火烧疤,才发现他就是本村的。队长用尿素口袋缝的这种裤子,初看上去与外面那些干部的荡荡裤没有多大区别,走路也是一荡一荡的,只是将眼睛贴拢去看时,才会发现裤子的前后都有字,前面两个字是日本,后面两个字是尿素。但这并不要紧,谁经常把眼睛贴到那裤子上去看呢?队长穿上荡荡裤不久,会计也穿上了一条,后来就没有谁穿了。生产队里的日本尿素都是队长和会计管着,其他的人去哪里弄那种口袋呢?所以大家只能眼巴巴地望着队长和会计穿。
我当时做梦都想穿荡荡裤,哪怕是用日本尿素口袋缝的我也想。有一次,父亲从镇上回来时,我终于向他开了口,求他在镇上碰到了日本尿素口袋后给我弄两条。父亲很快明白了我的意思,答应将这事放在心上。约摸过了半个月,父亲突然回了油菜坡,他说这回是专门为我回家的。父亲说着就从包里掏出一条荡荡裤。这是一条半新不旧的荡荡裤,父亲说是镇上的一个化肥仓库保管员为他儿子缝的,可他儿子皮肤不好,穿了这种裤子两腿发痒,于是就不穿了。我接过荡荡裤喜出望外,差点叫了一声毛主席万岁。父亲有些担心地说,但愿你穿上腿上不痒。我说,绝对不会痒的,我的腿子绊了漆树都不痒。
第二天我就把荡荡裤穿出去了,村里人见了我都像看一个天外来客。有人问我,你是不是当上队长了?我说,没有。那人就说,那你肯定是当上了会计!我还把荡荡裤穿到了学校,一下课就在校园里荡来荡去,好多女同学都对我刮目相看,一时间我觉得我简直成了全校最风光的人。
然而母亲却对我穿荡荡裤不以为然,她认为裤子应该穿得稳重才好,说荡荡裤荡来荡去十分轻浮。她希望我以后少穿这条裤子出门。但我没有听母亲的,我把她的话当成了耳边风。后来一连好多天,我照样穿着荡荡裤出门,并且专门朝人多的地方跑。母亲见我这样非常不满,看见我就板着脸。
有一天我把荡荡裤脱下来洗了,晒在门口的竹杆上。等我晚上放学回家时,那条荡荡裤却怎么也找不到了。我问母亲,母亲威严地对我说,我用剪子把它剪了!
6
我至今忘不了那个名叫云朵的女人,她也是个裁缝。云朵是镇上的人,家住街头第一家。云朵在当时是全镇最有名的裁缝,据说垄断了大半个镇的缝纫生意。说来也怪,当年镇上三个最有名的手艺人都住在街头那里。除了裁缝云朵,还有剃头佬老曹和铁匠刘麻子。云朵那时候四十出头,脸长长的,瘦瘦的,短发齐耳。她见人话不多,但总是笑笑的,两只眼睛挺漂亮。
我是读高一那年住到镇上去的,高中设在镇上,我在学校住读,每周回一趟油菜坡。父亲就在这个镇上工作,他工作的单位离街头不远。记得就是在我读高一的那一年,父亲把我带到了云朵的缝纫店。
那是高一下学期刚开学的时候,学校团委书记突然在全校大会上宣布说,学校要成立一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愿意参加的同学可以报名,但报名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有一件胸前有两个口袋的黄军装。事实上我们班上有不少同学早已穿上黄军装了,黄军装是当时最时尚的服装,穿上它雄纠纠气昂昂,高人一等。拥有黄军装的同学大都是家里有人在部队当兵,要么就是有人在武装部工作。我家一没当兵的,二没人在武装部,所以我一直穿不上黄军装。其实我是非常想穿一件黄军装的,作为一个十四五岁的青春少年谁不希望自己英姿飒爽呢?但我没有门路,只好心甘情愿穿我的百姓布衣。然而,一听说要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的心就热血沸腾了。这时候我想,我一定要想方设法弄一件黄军装,然后加入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首先找到我们班的体育委员,听说他哥哥在部队当连长,他已经穿过好几件黄军装了。但体育委员没有给我这个面子。他的学习很差,只会打篮球,而我的学习很好,还当着班上的学习委员。我对体育委员说,你帮我弄一件黄军装,我每天帮你做作业。我以为我这个主意不错,没想到恰恰伤了体育委员的自尊心。这样事情就没弄成。接下来我找到了我们的生活委员,他舅舅是武装部的副部长,每年负责征兵工作,手中捏了不少黄军装。但生活委员很贪婪,他说帮我弄一件黄军装可以,但必须给他十块钱。作为一个穷学生,我到哪里偷钱去?事情于是又泡了汤。后来没有办法,我只好去了父亲的单位,苦苦哀求他买段黄布给我缝一件。不到过年,父亲平时是从来不肯花钱为我缝衣裳的,他每月就是那么三十七块五角钱,必须一分一分数着用,不然日子就过不下去。那次我去求父亲,开始他怎么都不同意,后来我流泪了,他的心才软了下来,答应拿出五块钱,给我买段黄布缝一件。
父亲买了黄布带我去云朵那里时,正是傍晚时分,太阳刚落,红霞满天,云朵的缝纫店也被晚霞染红了,云朵的脸上像是打了胭脂。父亲把黄布交给云朵,请她为我量一下身体。而云朵没有量我的身体,只是睁大眼睛将我前前后后打量了好半天。她倒是量了那段黄布。量完黄布,我发现她好看的眉头突然皱了一下。父亲也发现云朵皱了眉头,便问怎么啦?云朵说,这段布不够!父亲说,你还没量我儿子的身体呢,怎么知道布不够?云朵说,谁说我没量他的身体?我的眼睛比尺子还准。父亲说,这布应该是够的呀!云朵说,如果做学生装当然够,但要做军装的样子就不够了,学生装只有一个口袋,而军装有两个口袋,并且还有口袋盖。父亲想了想说,那就做学生装吧,他本来就是学生嘛!我这时突然急了,赶紧说,不,我要军装!父亲顿时有些生气,黑着脸说,要军装干什么?你又不是当兵的!他说着就拉着我的手,将我扯出了缝纫店。走出店门后,父亲回头对云朵说,就做学生装,他明天来拿。我这时候忍不住哭了,我哭着回头朝缝纫店看了一眼,发现那里的晚霞都变成黑的了。
第二天我没去云朵那里,我觉得那件只有一个口袋的学生装对我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然而在我上晚自习的时候,父亲却突然来到了教室门口。他递给我一个纸包说,这是你要的黄军装,云朵师傅自己买布给你做了两个口袋。我顿时欣喜异常,立刻打开了纸包,看见那件黄衣裳上面果然有两个口袋。当天晚上,我就穿着云朵为我缝的黄军装去团委书记那里报了名。第二天,我加入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7
高二那年我从镇中转入了县城一中。
县城里那时候正流行一种的确良黄裤子。无论在大街上,还是在小巷里,你到处都可以看到那些穿的确良黄裤子的人,他们有的骑着自行车在马路中间飞奔,有的沿着街道旁边的人行道款款而行,由于他们都穿着的确良黄裤子,所以一个个都显得很高贵,神气得不得了。在县城里,除了城里人,也会有一些来自乡下的人。这些人你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当然是没有的确良黄裤子穿的,大都穿着皱巴巴的布裤子,有的还一条裤腿卷着,另一条裤腿吊着。这些人到城里来,说到底就是给城里人当陪衬的。
我们学校也有许多穿的确良黄裤子的人,他们大都是县城的学生。一中的学生大部分家住县城,来自乡下的很少很少。比如我们班上,四十个人中只有六个人从乡下来。谁是城里的,谁是乡下的,只要看看他的裤子就知道了。城里的学生差不多每人都有一条的确良黄裤子,而我们几个乡下的学生,几乎穿着清一色的布裤。
说句心里话,我是很欣赏的确良黄裤子的。它颜色纯正,而且布纹细腻,一看就有档次,实在是一种好衣裳,我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当然也希望自己能有一条的确良黄裤子穿一穿。我想,造的确良的人又不是专为城里人造的,乡下人为什么不能穿呢?不过我知道暂时是穿不上的,我想等我有钱了一定缝一条穿在身上。当然,那段时间我也没有过多地去考虑穿着问题,很快就要参加高考了,我必须把精力放到学习上。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春天就过去了。春天一过,天气便热了起来,这时候县城里穿的确良黄裤子的人就越发多起来了。大家都知道,的确良黄裤子布料很薄,穿在身上轻快而凉爽。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犯愁了,因为入夏以后我身上还一直穿着那条厚厚的灰布裤,闷热时刻袭击着我,有时候我不得不合拢手中的书本,把裤脚高高地挽起来,透透风,散散热。每当这时,我就特别羡慕那些穿的确良黄裤子的城里学生,我想,他们的腿子装在的确良黄裤子里面该是多么舒服啊!
父亲正是在这个时候来到县城的。他到县城一方面是因为单位的差使,一方面是为了给我送粮票,算是公私兼顾。父亲在校园里找到我已是黄昏了,但光线还很明亮。在黄昏的天光下,我一眼看见父亲穿着一条的确良黄裤子。一发现这条的确良黄裤子,我的眼睛就不动了,像是钉在了那条的确良黄裤子上。父亲很快发觉了我神情不对,便伸手在我的灰布裤上摸了一把。父亲问,这条裤子穿着是不是很热?我想了一下说,还好,不是太热。父亲本来打算在校园里看看我就和我分手的,但这会儿他却改变了主意。父亲对我说,跟我到旅社去一趟吧。
开始我以为父亲只是让我送送他,好让父子俩多说几句话,到了旅社以后,我才发现父亲是有重要事情要做。父亲一到旅社就打开了他的提包,从中找出一条半新的布裤,接着就把身上的那条的确良黄裤子换下来了。我看着父亲的举动,正感到疑惑时,他把脱下来的的确良黄裤子送到了我手里。父亲说,天气太热了,这条裤子给你穿吧!我捧着父亲的的确良黄裤子,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
后来的两个月,我差不多每天都穿着父亲的那条的确良黄裤子,复习非常认真,可以说是把全部身心都扑在了学习上。七月,我参加了高考。九月,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十月,我穿着父亲的那条的确良黄裤子,从油菜坡出发,经过镇上,经过县城,上了省城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