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缘的馈赠
2016-08-17郭彦
郭彦
当老友吕澎嘱我为他新近作品《血缘的历史——1996年之前的张晓刚》写一篇评论的时候,直白地说,我是无感的。首先,我不是艺术圈中人,对当代艺术界的现状和话语体系无甚了解。其次,看了书而为一本书写评论实在是劳神费力的一件事情。

2006年,张晓刚、吕澎于韩国
但看完这本书却很快提笔,这基于两个原因。

草原组画:暴雨将至,重庆,1981年10月,纸本油画,83cm×110cm
第一个原因,这本书的写作动机、出发点与我最近的写作有一定程度的关联。前一本书完稿后,我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了另一本的写作,它是有关中国古代文人生活空间和精神结构的一些思考。我试图花一点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和梳理时空如何作用于一个个体文人,也即是试图去探索过往历史(时间)的叠加和社会现实(空间)的状态如何合谋作用于某些特殊的个体。它涉及到古代文人的价值取向和世界观,也涉及到族群、他者、地域和流徙,当然,绝不可能回避政治、社会、家族等一些绕不开的空间和时间指涉对文人思想、生活和创作的高度介入。而吕澎的这本《血缘的历史》是对当代杰出艺术家张晓刚所做的精神、艺术历程的个案书写。在这一点上,他的写作甚合我意。

充满色彩的幽灵:向边缘移动,昆明,1984年3月,纸本油画,55×80cm
吕澎在后记说,“对于那些试图了解大家庭系列的观众来说,他们希望了解为什么艺术家会在这个时候创作出这样一类让人能够感受到一个国家的历史的特殊样式?他们希望了解大家庭背后的精神世界与历史原因”。所以,他“试图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艺术史、个人经历等不同的角度描述这位艺术家以及他艺术实践的历史”。我相信,这是一种严肃而有意义的努力,尤其是当代艺术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仍然只是不断增加的市场数据,是一些以为可以抛开艺术家的精神探索而能被简单模仿的毫无技术含量的东西的时候,从个案的角度去探索一个艺术家在一个特殊时代的思想和精神历程尤显重要和必需。

除夕夜,重庆,1990年,布面油画、拼贴,130×97cm
该书是一种力求客观而没有太多文学情感介入的写作。虽然写作者吕澎几十年来和张晓刚保持了十分亲密的关系,但在本书的书写中吕澎尽量做到了“不在场”,或不带太多个人的参与性和亲历感。相反,他用更多的笔墨呈现了一种广泛、深入的社会和思想背景,展开了极其复杂而丰富的现实和历史空间,也暗含了一种奇特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展示了艺术家在一个特殊时代接纳、认识、抵抗并试图超越的挣扎和努力。尤其是在阅读本书前面部分的章节时,有一种感受特别强烈,它几乎在刚刚展开对张晓刚个人生活描述的同时,就将笔锋一转,转到了时代所发生的一些大事件上面去了。这种不在具体日常生活细节上停留并展开的写作,是吕澎多年来的书写和行为习惯使然,也是他拥有的历史纵深感和偏好宏大叙事的惯性作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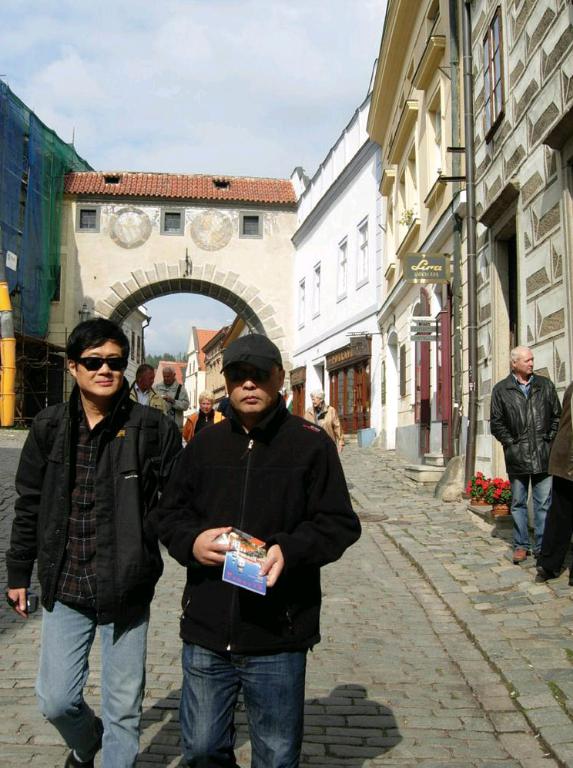
2008年,张晓刚、吕澎于布拉格
吕澎在后记中把自己的写作目的做了一个说明,“我在书中省略了大量关于艺术家的生活习惯以及个人特殊感情历程的叙述”,是因为“基于本书的任务是向读者概括性地介绍一位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艺术经历,并且尽可能条理清晰地保留这个介绍的叙述线索以便阻止读者朝着过分猎奇的方向去理解一位本来就是在这个国家的历史大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艺术家”。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既可以将该书看成是一个个案书写文本,也可将其视为吕澎连续几本宏大的中国艺术史写作的一种延续。他不过是通过对个案深度写作的方式展开了又一幅历史画卷,这既是张晓刚这个具体的艺术家血缘的历史、精神的历史、艺术的历史,也是一个时代或一个国家的血缘的历史、精神的历史、艺术的历史。

2009年,张晓刚、吕澎于苏洲
他说,“艺术家的个案是历史大厦必不可少的砖头,离开这些砖头,艺术史是难以成立的,何况有些艺术家就代表或者象征着一个时代 ——不是时代的辉煌而是时代的疾病”。而张晓刚的作品、尤其是大家庭系列作品所显示的特殊的图示、符号和形制,体现出强烈的被修饰和被创造的国家历史印记和个人痕迹,太容易唤起人们从中寻找群体和个体记忆的冲动。换一句话说,如果要回顾一个民族、一代人记忆中的国家历史和个人历史,张晓刚的作品简直太适合担当这一角色。

血缘-大家庭:全家福1号,重庆,1994年,布面油画,150×180cm
第二个原因,是本书所写的主人公张晓刚也是我所熟悉的一个人物,甚至在早些年,还是相当熟悉的一个人物,这在该书中有一段简单的描写:

血缘-大家庭3号,重庆,1995年,布面油画,180×230cm
张晓刚和唐蕾的家安在成都走马街邮局宿舍。婚后,时间和经费允许,张晓刚便尽可能地将他的生活与创作放在成都。成都有同学何多苓、周春芽和牟恒等川美老同学,加上他与唐蕾住的地方正好位于吕澎家的背后、川大教授易丹家的前面,大家经常串门,来了外地的朋友,就在某一个人的家里聚会喝酒,聊天,讨论哲学,倾听音乐。那是一个几乎还没有咖啡馆和小酒馆的岁月,有无数个夜晚,那些来自不同地方的艺术家和文艺圈的朋友都住在那些有音乐但空间十分狭小的家里:喝酒、讨论哲学、音乐以及与艺术有关的中国问题。

血缘大家庭:同志与红色婴儿,重庆,1995年,布面油画,150×180cm,昆士兰美术馆藏
这里所说应该是1985年至1991年张晓刚去德国以前的一段时间。这段生活我是熟悉的,因为我就是那个住在张晓刚走马街的家前面的易丹家里的女人。当时张晓刚家在走马街,吕澎家在红星路四段(紧靠督院街),我们家在学道街。稍微熟悉成都地图的人会知道我们实在是住得太近了,走路也就几分钟时间。那个时代,大多数家庭都没有电话,也就自然没有电话提前预约的事情发生。通常的情况是,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吕澎两口子,或张晓刚两口子。当然,还有时候会是一群人,或单独一人,比如张晓刚突兀地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瓶劣质白酒,用他迷茫的眼神和慢吞吞的语调表达一种十足的礼貌;还有的时候,打开门,是张晓刚两口子,唐蕾手上高举一包东西,一如既往地快言快语,我们带来了云南火腿,今晚有下酒菜了!

母与子2号,昆明,1993年,布面油画,150×180cm,福冈亚洲美术馆藏
现在无法想象,没有电话的时代一群人怎么可能走动得如此频繁,但到底是怎样一种预约方式又实在想不起了,但一定是有某种预约吧,要不然一群人,也不晓得咋个就从这一家窜到了另一家,而且有时候人还越来越多,沙发上、凳子上坐不下了,就直接坐地下,喝酒、吃饭、听音乐、打扑克、看录像,折腾下来通常很晚才回家,有时候也就干脆睡在了别人的家里,打地铺也不是一回两回的事情。
每次张晓刚从云南或重庆回到“腐朽的成都”(张晓刚总是把成都称为腐朽的成都),我们会发现他又把那个十分狭小的家狠狠折腾了一次,床和沙发搬过来又搬过去,一二三再而三,没完没了,让我们在一旁看的人都感觉精疲力尽,说你不嫌累嗦。这个时候,张晓刚就嘿嘿笑两声,显得相当有成就感。

血缘大家庭10号,成都,1997年,布面油画,158×188cm希克收藏
他们一群人十分迷恋音乐,常常一起出门买磁带。大家手里都没钱,就约好了互相不买重复的,然后互相交换,也就是互相翻录,封套也会拿出去复印,然后折叠好,整齐地放在翻录好的磁带盒子里。记得,放得最多的音乐是斯特拉文斯基、肖斯塔科维奇、拉赫曼尼诺夫,还有勋伯格,屋里总会持续充斥着一种无端的悲壮和崇高气息,这个时候,其中一人就会突然冒出来说,来一段肤浅的吧。童安格、王杰、齐秦、苏芮之类的就来了。如果没记错的话,“肤浅”这个词最初是从张晓刚嘴里出来的,也是他说得最多,后来大家都用这个词来指代一种特定的、大众的、流行的东西,好像达到了短暂参与简单快乐的目的,也使自己对外部世界保持足够的警惕和清醒。
后来,还有一些词汇,比如“焦虑”、“得逞”、“生效”、“进入历史”、“成功”、“老哥萨克”等一些词汇也具有了某种特定的含义。
大多时候,张晓刚的谦逊、自持和善解人意让他一直在群体中保持有谦谦君子的形象,而他极其强烈的忧郁、悲观气质又总是在各种场合暴露无遗。直到现在,我还能清晰地记忆起,无数个夜晚,酒后的饭桌前张晓刚痛苦的陈述和执拗的追问。
写这些的目的,其实是想说,并不完全是作为张晓刚某段生活的旁观者,而是作为一个阅读者,我是一定会欢迎书中出现更多日常生活的细节的。我相信,任何气质性的东西一定会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得到他人的感知和印证。
我从来不喜欢传记中过度的文学渲染和情绪介入。这种所谓的文学性试图通过对主人公进行某种设想或妄想,以达到所谓生动描述的目的,它牵引读者朝向一种他所设置的氛围和情绪去认识和理解人物,有意无意低估了读者的智商,并成功阻止了读者的判断能力,极有可能造成读者的误读。事实上,张晓刚就曾经谈到过他被《梵高传》误导的一段经历。所以,在传记阅读中,我从来更信任一种适度专业、理性、冷静的写作,这也是吕澎在写作中已经呈现给我们的。从个人阅读经验来说,这是一本让我一口气读完的书,也是甚和我阅读口味的一次阅读。这是吕澎游刃有余地把握历史和具体人物之间关系的结果,也是其多年深度介入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视野和高度所决定的,同时也是他小心翼翼褪去个人主观色彩的一次努力。
但细节,却并不一定是和文学性直接勾连的,更不是人们印象中单纯的生动描写、修辞和渲染,相反,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把细节看做是客观性的一部分,更是气质性和精神性表现的一个绝佳注脚。
所以,尽管吕澎已经毫不含糊地申明了日常细节有可能遮蔽现实真相的极度危险性,但我还是情愿把一些生活细节看成是张晓刚作品中那些貌似随意选择或摆放的物件,比如沙发、匕首、灯泡或电视机。它们或许如吕澎所说,只是一种经过了感觉变形和肢解的回忆,但,它的存在又是如此必然,以至于我们一定会去追问,张晓刚为什么会选择这些物件——而不是其他物件——将其抛掷在画面中?绝对真实的细节构成并不必然指向一种绝对的真实,相反,它可能构成一种巨大的荒诞甚至虚无,这兴许就是细节的迷人和诡异之处。如是,我设想,如果更多一点日常生活的细节加入,兴许有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更深入了解张晓刚的奇特角度——这个一直以来以低调、克制出名的艺术家极度敏感、神秘的个人特质。
当一盆历史的大雨浇泼在芸芸众生的身上,对每个人而言,都是一个被洗礼、被毁灭也是被塑造的过程,也可能是一个抵抗、博弈并最终胜出或失败的过程。很长一段时间,张晓刚沉陷在孤独和痛苦之中,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也在享受和利用这种孤独和痛苦,并一直暗自把自己置于超越的位置,最终,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为我们留下了一代人的精神记忆。时代已经远去,吕澎的书写已然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艺术史甚至一个国家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一部个人精神史。血缘,既是家族的馈赠,也是历史的馈赠,有人尝试超越了,就可能使其成为又一种精神的血缘,静静流淌,并最终成为后人可能接受的馈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