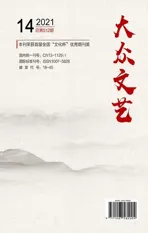权力叙事视阈下的《城堡》
2016-07-12刘尚琪吉林师范大学130000
刘尚琪 (吉林师范大学 130000)
权力叙事视阈下的《城堡》
刘尚琪(吉林师范大学130000)
《城堡》是卡夫卡的经典之作,它凝聚了卡夫卡有关世界与权力图景的构想,本文将从权力叙事来解读小说中暗含的真相,以此来窥见特殊时代人们对权力的理解与包容。
《城堡》;卡夫卡;权力叙事
弗朗茨•卡夫卡(德文:Franz Kafka,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是二十世纪文学界“谜”一样的伟大作家,他视写作为生命,不惜牺牲一切地付出。他的小说有着独特怪谲的想象,令人捉摸不透的结局,神圣般的未完成性。他的经典之作《城堡》始终弥漫着权力的意味,充斥着各种权力的矛盾,小说看似如湖面般平静,卡夫卡却赋予小说权力的历史背景,设置了在权力外游走的K。捷克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说:“按照卡夫卡,世界是某种官僚化的体系,办公室不仅是普遍存在地社会现象之一,而且是这个世界的本质。”
《城堡》讲一个土地测量员K到城堡赴任。首先我们来看故事发生的地点:城堡。城堡所处的周围环境使神秘的,厚厚的积雪将人们进出城堡的痕迹销毁干净,让K找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浓雾和黑暗笼罩着城堡,给人一种不能强烈的疏离感。K站在城堡外,很迷惘,感觉不到城堡存在的方向。城堡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包围着,没有一点光亮能看到城堡的具体位置。它高高在上,给人一种不可接近之感。而K迷茫地站在村口,似乎没有任何希望进入城堡。城堡的虚无缥缈与K努力想要接近城堡但城堡离它越来越远是相对应的,城堡里有着各种这样的权利,而像K这样的外来人是没有权利进入城堡的。
K想要进入城堡,他想尽各种办法,联系各种与克拉姆有关系的人:信使巴纳巴斯、情妇弗丽达、前情妇老板娘、不明下属村长老师、秘书助手艾朗格,目标就是见到城堡的老爷克拉姆。而克拉姆始终都没有露面,他是一个十分神秘的人物,但他的权威却无处不在,没有人不敬畏他。见不到克拉姆,他想尽各种办法,先是企图让信使巴纳巴斯带他回城堡,却被他带回巴纳巴斯的家里;K想要和克拉姆的情妇弗丽达建立恋爱关系甚至结婚,然后从她口里探出有关克拉姆的消息,弗丽达要和克拉姆分手,这样一来,K就又一次失去接触克拉姆的机会;
卡夫卡通过反复叙事来强调K是游走在权力之外的人员,尽管他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找到城堡的主人。反复叙事是一种不断重复的叙事,在《城堡》中,K的每一个行动都难以实现。他想在城堡中寻一份工作,进而在城堡山稳定下来。虽然拜访村长求得工作,在学校工作后却与教师发生矛盾,以至致工作难以继续。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在城堡山上,各种规则和要求的不合理,使得权力得以施展而无从监督。福柯认为:在规训机构中,有关职能场所的规则将逐渐把建筑学通常认为可以有几种不同用途的空间加以分类。某些特殊空间被规定为不仅可以用于满足监督和割断有害联系的需要,而且也可用于创造一个有益的空间。
卡夫卡在《城堡》中巧妙地将语言渐变为“权力”。K的目的自始至终只有一个:见到城堡的主人。中间经过各种纠葛,通过客店老板的转述,我们得知城堡里所有的人都是有威望的,非常高贵的人。这样的转述数不胜数,还包括老板娘等人物的语言。总而言之,正是这些城堡最普通不过的人们阻碍了K去城堡的路。也就是所谓的语言让城堡变成一个不能被了解的“权力”的符号。城堡注定是抵达不了的远方。这种语言的力量胜过一千次的行动,它们将K 的耐心和决心耗费殆尽,失去进入城堡的意义。
如在《城堡》第4章,K与老板娘的对话解除了前3章中K行动的意义。老板娘在得知K想见克拉姆的时候,这样说:“土地测量员先生在问我话,我就得回答他提的问题,不然他怎么会明白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是说克拉姆老爷决不会同他谈话,我刚说什么来着?‘不会’,不,是‘不能’,您听清楚了,土地测量员先生!卡拉姆老爷是城堡的人,即便撇开克拉姆担任的职务不说,仅仅这一点本事,是城堡的人这一点,就是一个很高很高的级别了,可是您究竟是什么人呢?我们居然还在这里低三下四地求您同意同弗丽达结婚!您一不是城堡的人,二不是村里的人。您什么也不是,但是可惜的是您又确实是个人,您是个外乡人,一个多余的人,一个在这里处处碍事的人,一个不断给人找麻烦的人。”由此可见,K想要通过同侍女弗丽达结婚来达到见克拉姆的目的,但现实是残酷的,这一点通过老板娘之口说了出来,说K根本就无法看到克拉姆,而且实际上他也没有见到克拉姆,这就否定了K来城堡工作的实际意义。
《城堡》后17章将这种语言的力量发挥到极致,各种小人物,像村长、老板娘、弗丽达等,他们看起来很普通,但一与K交涉就变成长于言辞的人,他们对K形成了一种包围的态势。在小说中刚开始还有些许情节,到后面,从没完没了的对话里,行动已经完全被淹没。行为失去了它最实际的意义,《城堡》中的人物仿佛除了说话别无所长。德国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认为小说中这种荒谬的权力与卡夫卡父子之间的关系联系紧密。他始终与自己的父亲有着隔阂,永远无法沟通,甚至是活在父亲的阴影下。
卡夫卡的卓越是世界有目共睹的,他的视角总是很独特,让后代的学者研究了几百年。卡夫卡是出生在奥匈帝国时期、居住在布拉格、说德语的犹太人,这种身份的特殊身份使卡夫卡离我们很远;但卡夫卡对生活中痛苦的体验和领悟,对世界性图景的洞察,使得他离我们很近。卡夫卡在《城堡》将权力描写得淋漓尽致,从《城堡》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权力不仅是一种有形的存在,而且无形存在于人的意识形态里。与其说卡夫卡对权力的卓越的感受力带我们走进权力的世界,不如说,窥见权力的世界也就窥见了卡夫卡的世界。
[1]米兰•昆德拉,唐晓渡,刘晓东译.《小说的艺术》.作家出版社,1992.
[2]弗兰茨•卡夫卡,叶廷芳译.《卡夫卡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3]米歇尔•福柯,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4]瓦尔特•本雅明,王炳均,杨劲译.《经验与贫乏》.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5]曾艳兵.《卡夫卡的眼睛》.商务印书馆,2012.
[6]马克斯•布罗德,唐永宽译.《卡夫卡传》.漓江出版社,1999.
[7]卡夫卡,郑法清等(编),叶廷芳等译.《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刘尚琪,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欧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