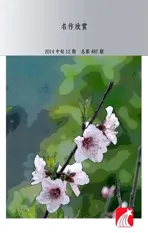追随别样的魏晋风度
——应璩作品简析
2016-07-12郝倩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山西临汾041004
⊙ 郝倩[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山西临汾041004]
追随别样的魏晋风度
——应璩作品简析
⊙ 郝倩[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山西临汾041004]
应璩作为曹魏文学家之一,具有不可忽视的独特意义。考察其一生际遇,可以看出应璩儒道风雅并存的思想、积极为民的为官之道、诙谐自我解嘲的态度和珍视自然之美的情怀。应璩在处世方面呈现出一种不同于全力入仕和佯狂避世的风格,构成他别样的魏晋风度。
应璩 人生际遇 别样风度
一、引言
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历史上的一段繁荣期,期间完成了文学的自觉,也涌现出了诸如三曹、七子、竹林七贤等一系列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应璩作为众多作家中的一员,虽然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仍具有不可忽视的独特意义。
二、应璩简介
1.生平
应璩(190—252),字休琏,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县)人,三国曹魏时期文学家,建安七子中应之弟。他生于汉献帝初平元年,卒于魏齐王曹芳嘉平四年。在《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王粲传》注中,裴松之曾引《文章叙录》说:“璩字休琏,博学好属文,善为书记。文、明帝世,历官散骑常侍。齐王即位,稍迁侍中、大将军长史。曹爽秉政,多违法度,璩为诗以讽焉。其言虽颇谐和,多切时要,世共传之。”①
2.历史上对应璩的评价
对于应璩的作品,历来评价不一。上面提到他“博学好属文,善为书记”,强调他在书信文写作方面很擅长。的确,应璩书信文成就很高,独树一帜。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中说“休琏好书,留意词翰”②,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应德琏、应休琏集》题辞中亦称“休琏书最多,俱秀绝时表”③,都给予了应璩书信文很高的评价。这与《昭明文选》大量选录其书信作品的审美取向是一致的。
应璩诗歌也有较高成就,尤以《百一诗》著称。锺嵘在《诗品》中将应璩列为中品,称其诗“善为古语,指事殷勤,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④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评价道:“若乃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⑤李充《翰林论》说:“应休琏五言诗百数十篇,以风规治道,盖有诗人之旨焉。”⑥
可以看出,应璩在历代评论家心目中还是有一定地位的。但由于其作品大都散佚,时至今日,应璩的价值不能得到恰如其分的认识,不免令人叹惋。但我们仍能够沿着他现存作品里的线索,慢慢追随那已远逝的、别样的魏晋风度。
三、应璩风度之别样
(一)应璩的人生际遇
应璩历仕魏文帝、明帝、少帝三朝,其文学生命横跨建安、正始两个时期。正因如此,他自身也经历了从建安到正始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年代间的一系列变故。应璩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建安年间度过。汉末,应璩饱尝了流离之苦、兵祸之灾,故在作品中充分体现出心系苍生、悲天悯人的情怀,表达自己渴望建功立业、匡时救世的理想。前者如“丧侧食不饱,酒肉纷狼藉”,后者如“丈夫要雄戟,更来宿紫庭。今者宅四海,谁复有不”。这同所有建安诗人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是相一致的。曹操于邺城建都后,政治环境得以改善,文化环境也较为明朗。在曹氏父子重视文学,将文学看作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大环境下,作为以文致仕的应氏家族成员,应璩也同当时所有文人一样,得到了崭露头角、抒发抱负的机会。
应璩的主要创作期在曹魏后期。他辅佐明帝曹睿,任少帝曹芳大将军长史职务,仕途上似为得志,实际也经历过隳官而去的波折。同时,应璩的物质生活也颇清苦,“谷籴惊踊,告求周邻;日获数斗,犹复无薪,可以熟之”。
应璩晚年时,司马懿篡权夺势的行径甚嚣尘上。正始十年爆发高平陵事变,曹爽、何晏等人均被诛灭,实际政权落入司马氏手中。他们实行高压统治,残杀异己,使得“魏晋名士少有全者”。
面对这种局势,应璩选择了适时地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回归到田野乡间安度余年。《三国志·魏志·朱建平传》
中有记载:“(朱建平)谓应璩曰:
‘君六十二,位为常伯,而当有厄,先此一年,当独见一白狗,而旁人不见也’……璩六十一为侍中,直省内,见白狗,问之众人,悉无见者。于是数聚会,并急游观田里,饮宴自娱,过期一年,六十三卒。”
荒诞的白狗之说使得身为曹魏旧臣的他能够避身远害,不受司马政权的牵制和迫害。这一方面得益于应璩先前与曹爽、何晏等浮华之人界限分明,因此能不被牵连其中,另一方面就是应璩自己的处世原则。生于仕宦家族的他对篡权的司马氏极为不齿,根本不可能甘心受任于其下。所以他选择“急游观田里”“饮宴自娱”,在政治侵袭不到的纯净空间里度过最后的岁月。
(二)应璩的处世之道
考察应璩的人生际遇,可以看出他面对政治等大事的处世智慧。这是应璩留给后人永不会消逝的珍宝。
1.儒道风雅并存的思想。应璩的思想由于经历了正始玄风的浸染,在原本建安盛世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基础上,加入了清玄的道家思想,有了玄道的影子。他曾在《与刘文达书》中写道:“仆顷倦游谈之事,欲修无为之术,不能与足下齐镳骋辔、争千里之表也。”可见,应璩是有意向道教的清玄无为思想靠拢的。这使得应璩从思想上区别于其他活跃于建安早期的文人,既有着建功立业的志向和关心民生疾苦的胸怀,还同时向往老庄的清静无为。
应璩的玄道思想由于具有复杂的过渡性,是较为平和冲淡的,不似当时玄学名士那样狂热。对于某些名士过分于放诞的表现,应璩持批评态度。《与崔玄书》中他就表达了这种看法:“岂有乱首抗巾,以入都城,衣不在体,而以适人乎?昔戴叔鸾箕坐见边文礼,此皆衰世之慢行也。”将玄谈时放任的“衣不在体”看作衰世之慢行加以批评,可见,应璩思想仍以中庸的儒家为主。
2.积极为民的为官之道。不论应璩如何看待为官之事,他在任时都是积极地尽其所能,关注现实并为民谋利的。这从《百一诗》讽谏为主的性质就能窥其一二,现摘出其中一首。
室广致凝阴,台高来积阳。奈何季世人,侈靡在宫墙。饰巧无穷极,土木被朱光。征求倾四海,雅意犹未康。
这首诗作于青龙三年(235),当时魏明帝曹睿大修宫馆,使得被调集来修筑宫殿的百姓们无暇务农,错失农时。当时一些大臣们纷纷进谏,高堂隆就曾上书:“广开宫室,高为台榭,以妨民务,此害农之甚者也。”他还告诫明帝“不夙夜敬止,允恭恤民,而乃自暇自逸,惟宫台是侈是饰,必有颠覆危亡之祸”⑦。上述应诗所表达的同高堂隆之意是一致的,他们都对魏明帝大兴土木、罔顾民生疾苦的行为予以了批评和劝诫。
应璩不仅谏在位者,他对地方官员也有建议。
在《与广川长岑文瑜书》中,应璩对解决当地炎旱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彼时草木焦黄、沙砾横飞,人们筑土龙、泥人等求雨,历经数旬仍无成效,而情形已是“处凉台而有郁蒸之烦,浴寒水而有灼烂之惨”般刻不容缓。应璩明确地告诉岑文瑜“劝教之术,非致雨之备”,婉劝他学习夏禹、殷汤等古代圣贤,躬自暴露,以感动上苍求得降雨,抛却个人利益为一方百姓谋福祉。
虽在今看来,信中的思想仍然无法避免地带有些许封建色彩,但应璩关心黎民苍生、体恤民生疾苦的入世情怀和他儒家的仁义观念都已在信中展露无遗。
3.诙谐自我解嘲的态度。张影洁在其论文《〈百一诗〉与应璩的诙谐》中说道: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歌在古代文学传统中占据的位置实在重要,诗人创作的时候也不免秉持严肃、庄重的艺术态度,很少能以“游戏”的心态进行创作。汉魏以来,应璩的《百一诗》是少有的兼具“严肃”与“诙谐”的作品。⑧
诙谐作为应璩乐观解嘲生活态度的一部分,在他的作品中表现了出来。
先看其《百一诗》中的自嘲诗:
诗中应璩将年老后的自己描述成一个丑陋粗鄙之人,落拓不修边幅。酒醉之后酒巾帻掉落,秃顶的头状似壶瓢。这个形象与他留给我们风流倜傥的印象全然不同。身为舞文弄墨的文人士子,大概很少有人像应璩这样“自毁形象”吧。略显粗俗的文风,自我嘲笑的描述,个中辛酸先不予论断,单就诗中所流露出的豁达与幽默,也当是应璩一个独特的标签了。
在《与侍郎曹长思书》中,应璩对自己怀才不遇的心境进行了剖露:“德非陈平,门无结驷之迹;学非扬雄,堂无好事之客;才劣仲舒,无下帷之思;家贫孟公,无置酒之乐。”从德行、学养、才华、家世四个方面与历史名人作对比,谦逊又略带落寞地讲述自己的情况,对朋友“陈其苦怀”。能够看出,在面对生活中不能改变的窘困时,应璩是坦然相对的。相比很多文人们自恃清高、不可一世的态度,这种敢于自嘲的生活态度,并非当时人人皆有的。
4.珍视自然之美的情怀。应璩珍视自然之美的情怀,也在其一系列清新如洗的景物描绘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
在给友人的书信《与满公琰书》中,他写下这样令人备感清新的句子:“夫漳渠西有伯阳之馆,北有旷野之望,高树翳朝云,文禽蔽绿水,沙场夷敞,清风肃穆也。”视野开阔的画面里,葱茏的树木掩映着白云,绿色的水面栖息着禽鸟,沙场平坦而开阔,且有阵阵清风拂面吹过,全然一番动人心弦的景色,令人心向往之。
《与从弟君苗君胄书》中,所描绘的美更加沁人心脾:“间者北游,喜欢无量,登芒济河,旷若发,风伯扫
途,雨师洒道,按辔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凉过大夏;扶寸肴修,味逾方丈。逍遥陂塘之上,吟咏菀柳之下;结春芳以崇佩,折若华以翳日。弋下高云之鸟,饵出深渊之鱼。蒲且赞善,便称妙,何其乐哉。”北游路上,作者抛开世俗繁杂尽情亲近自然,一切感官都如同获得新生,舒畅自如。土壤微微潮湿,凉风吹来阵阵清新,驻马四望,周围天地瞬间广阔无垠。尝过可口的佳肴,住过敞亮的房子,芳草编成饰物戴在身上,明媚的春光里,射下高空的飞鸟,钓起水中的游鱼,满载而归。这样的人间美景乐事,吟咏间便可醉人。
(三)别样的风度
《魏晋风度二十讲》一书中这样定义魏晋风度——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精神的统一体。依此考察,应璩独特的魏晋风度已经得到了体现。
从风骨为主的曹魏过渡到玄学弥漫的两晋,应璩将两段时期的主导思想融为一体,在处世风格上呈现出一种不同于全力入仕和佯狂避世的第三种态度。
曹魏时期文人皆满怀济世豪情,力图在盛世中贡献出自己的光热,从而名垂千古,得到自我满足的同时光宗耀祖。他们作品中除去抒发宏韬伟略,还表现出深重的忧患意识。以建安七子中的王粲为例,其表现个人雄心和忧患的《登楼赋》就是表达自己在荆州不得刘表重用,渴望回归北方中原故土一展身手的愿望。滞留荆州十余年,王粲的客居心理在失意不得用的心境下越演越烈,发出“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的感叹。失意的现实与还归的强烈意志使得他内心充满无限的惆怅,“夜参半而不寐兮,怅盘桓以反侧”。相比之下,应璩就冷静很多:“下流不可处,君子慎厥初。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诬。前者隳官去,有人适我闾。田家无所有,酌醴焚枯鱼。问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庐。”这样的诗句显示了应璩对于功名的淡泊,能够隳官而去,安适于田家清贫的生活,仅将为官看作是一生中的功德之事,这种态度于浮华的魏晋中实属不易。
两晋时期由于政治环境的险恶,朝政危机四伏,使得有志之士们将原本打算有所作为的政坛看作了畏途。一种“由积极向消极,由进取向退避,由乐观向悲观”的态度笼罩了整个文化环境。竹林七贤退避世事,不与司马朝政为伍的玄学士流风气开始形成。其中最为激烈的当属嵇康。他敢于当面奚落司马昭的心腹钟会,大胆地抨击礼法的虚伪,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自述“七不堪”和“甚不可者二”,更成为借此公然与司马政权决裂的声明书。李贽评价“此书实峻绝可畏,千载之下,犹可想见其人”。但正是这种尖锐决绝的态度,给嵇康招来杀身之祸,一曲《广陵散》也终成绝唱。应璩的处世态度比之于嵇康,就显示出了玄学外由于儒家思想深渗而恪守的中庸平和。同样向往自然,不愿被尘世喧嚣烦扰,应璩在《与从弟君苗君胄书》中只是温和地表示“营宅滨洛,困于尘嚣,思乐汶上,发于寤寐”,并以伊尹辍耕和致恽投竿的典故,表达出自己意欲“秉耒耜于山阳,沉钩缗于丹水”的态度。乱世的统治时代往往容纳不下嵇康那样的理想主义者,因此,应璩这种兼具儒家中庸又携玄学潇散的态度,使他在纷乱的年代里享以终年。
四、结语
从作品中,我们看到一个鲜活的应璩。有抱负有才华,关切现实又富于生存智慧,在乱世中极力保存真实的自我,不背叛本心。他珍视亲情友情,懂得欣赏世间美好,同时恪守儒家中庸之道。面对仕途的不得志,他能够自己进行开解,转而投入到力所能及的事业中,为黎民百姓谋求出路。面对丑恶虚伪,他能够洁身自好地退离官场,心境恬淡地回归到简朴的生活当中。他也为文人士子们树立了一个正直豁达、耿介温厚的典范,展示了属于他的别样的魏晋风度。
①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01页。
②郭晋稀:《文心雕龙注译》,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234页。
③孟殷伦:《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87页。
④陈延杰:《文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35页。
⑤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7页。
⑥萧统:《昭明文选》(卷二十三),李善注引文,京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
⑦陈寿:《三国志·魏志》(二十五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84页。
⑧张影洁:《〈百一诗〉与应璩的诙谐——兼谈易代之际士人的困境与抉择》,《名作欣赏》2012年第2期。
[1]孟殷伦.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2]徐公持.魏晋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3]萧统.昭明文选[C].北京:京华出版社,2000.
[4]穆克宏.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述略[M].北京:中华书局, 1997.
[5]张影洁《.百一诗》与应璩的诙谐——兼谈易代之际士人的困境与抉择[J].名作欣赏,2012(32).
[6]王利锁.应璩书信文简论[J].河南大学学报,2010(53).
作者:郝倩,文学硕士,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编辑:康慧E-mail: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