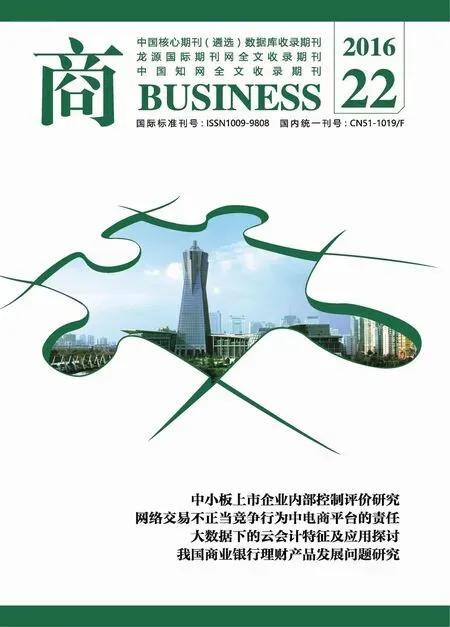民事执行和解若干问题探析
2016-07-08张驰
张 驰
民事执行和解若干问题探析
张驰
摘要: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在执行程序中,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后,原执行程序可能因当事人的申请中止或终结,但法律并未规定在当事人没有做出明确意思表示时,原执行程序应处于何种状态,这也在实践中造成了混乱。为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解协议成立后,当事人选择执行程序状态前,或者当事人未做任何意思表示时,原执行程序的状态应作中止处理;若当事人选择因执行和解协议而终结执行程序,要重新开启执行程序,则需再次申请,同时要受到两年的执行时效和受理执行申请条件限制。此外,执行和解协议的履行情况应由法院采取被动的形式审查才能原终结执行程序。
关键词:民事执行和解;中止执行;终结执行
一、民事执行和解制度的立法困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解释》)第466条规定:“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后请求中止执行或者撤回执行申请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中止执行或者终结执行。”可见,在执行和解的过程中,对于原执行程序状态的变化,有三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一是和解协议成立时;二当事人请求中止执行或者撤回执行申请时;三是法院裁定中止执行或者撤回执行申请时。由此产生一系列的疑问是,和解协议达成后,当事人未对原执行程序状态作出意思表示时,原执行程序状态如何确定;当事人申请撤回执行申请后,和解协议未得到实际履行如何救济;以及和解协议履行状况如何审查。
二、完善民事执行和解机制
要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必须从执行和解协议本身出发,对整个执行和解的过程进行一以贯之的系统化规制。
(一)当事人自主选择原执行程序的状态
执行和解协议是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自行协商,对生效法律文书已经确认的权利义务关系重新处分的合意。这表明了当事人试图摆脱公权力自行解决纠纷的意思,但正如上文分析,实践中,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当事人可能并不会在权利没有确定被实现的情况下完全脱离法院的权威。比如在和解协议生效后根据履行的情况,再作出对原执行程序状态的选择。“诸多当事人不选择在诉讼中达成和解,而选择在判决生效后甚至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方才和解”至少的一个原因,“是当事人即使有和解的意向,但由于权利之有无及其数量尚未经判决予以最终确认,缺乏确定的权利和利益参照系,对和解方案的具体内容难以权衡、决策,需待判决确定之后,方才决定达成何种和解方案。”①因此,在和解协议履行过程中,原执行程序的状态可能是不确定的,依然会存在当事人之间对相关权利的取舍和博弈。
(二)区分原执行程序状态的救济
“中止执行”和“撤回执行申请”不同。如前所述,《民诉法》第256条规定的中止执行的情形和效果表明,中止执行只是因为发生某些特定的事项阻碍了执行程序进行,而暂停了正在进行的执行程序,中止事由消失后执行程序可以继续恢复执行。而撤回执行申请,按照法律用语的习惯来看,诸如“撤回起诉”在民事诉讼法上视为原告从未起诉,那么撤回执行申请是否可推定为申请执行人从未申请执行,实质上也是执行程序不再进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民诉解释》第466条将申请执行人撤回执行申请的法律效果规定为“终结执行”也是可以理解的。而终结执行也就意味着原执行程序已经结束,如果申请执行人有需要再次通过执行程序获得救济的情形,应该重新开启执行程序,并不是像中止执行那样可以随即恢复执行程序中止前的状态。因此,对于原执行程序“中止执行”和“撤回执行申请”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和解协议的救济方式应该是不同的,不应一律按《民诉解释》第467条的“恢复执行”来处理。终结执行后,申请执行人又试图启动执行程序的,应重新申请执行。与此同时,终结执行程序后要再次开启执行程序,需要申请执行人的再次申请也意味着,再次申请启动执行程序,要受到两年的执行时效和受理执行申请条件限制。
(三)法院被动审查和解协议的履行状况
《执行规定》第87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合法有效并已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作执行结案处理。”以及第108条,将“当事人之间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已履行完毕”作为执行结案的情形之一,这些法律规定都表明,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框架内,法院要将执行和解的案件结案是需要审查执行和解协议的履行状况的。“民事执行和解的效力来源于执行法院对执行和解的司法审查。”但“民事执行和解司法审查的前提是当事人享有意思自治的权利。”②一方面,法院不应过多干涉和解协议的履行。在实体法上,既然执行和解协议是当事人对自己民事权益的处分,自然应尊重当事人自己的意思,执行和解协议的履行与否也正是当事人的处分权范围,法院作为公权力载体不应过多的干涉;在程序上,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协议已经将其争议从公权力控制下的执行程序剥离,法院再主动干涉和解协议的履行势必逾越了公法私法之间的界限。但另一方面,当当事人要使公权力主导下的程序状态发生改变,或者当事人自己不能通过私力途径实现自己的权利,需要借助公权力的力量时,需要向法院表明自己的请求,必要时还应作出相应的证明,法院只做形式审查即可。因此,在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终结执行程序前,和解协议的履行情况应由当事人向法院说明,法院形式审查后即可做出相应裁定;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在原执行程序终结后,再向法院申请启动执行程序的,无需再由法院审查执行和解协议的履行情况。
但在另一种可能鲜有的情况下,即执行程序已经终结,且被执行人一方已完全履行和解协议,申请执行人再次申请启动执行程序的。若允许申请人的执行申请势必不利于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也会降低司法效率,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甚至破坏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所以,不应准许此情形下,应申请执行人的申请而再次启动执行程序。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在申请执行人再次申请启动执行程序时,法院似乎也有必要审查之前和解协议的履行情况。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申请或移送执行的法律文书已经生效;2、申请执行人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3、申请执行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申请;4、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有给付内容,且执行标的和被执行人明确;5、义务人在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未履行义务;6、属于受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管辖。”可见,法律规定的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的条件内不包含审查和解协议的履行情况。(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法学院)
注解:
①雷运龙:《民事执行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载《政法论坛》2010年11月第6期。
②陈群峰、雷运龙:《论民事执行和解司法审查的本质、功能与效力》,载《法学家》2013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雷运龙:《民事执行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载《政法论坛》2010年11月第6期。
[2]陈群峰、雷运龙:《论民事执行和解司法审查的本质、功能与效力》,载《法学家》2013年第6期。
[3]隋彭生:《诉讼外和解协议的生效与解除——对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2号>的实体法解释》,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4]肖建国、赵晋山:《民事执行若干疑难问题探讨》,载《法律适用》2005年第6期。
[5]雷运龙:《论民事执行调解制度》,载《法律适用》2009年第4期。
[6]黄金龙:《不履行执行协议中的和解协议的救济程序》,载《人民司法》2005年第11期。
作者简介:张驰(1991-),男,汉族,河南泌阳人,河南大学法学院,14级法律硕士,研究方向: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