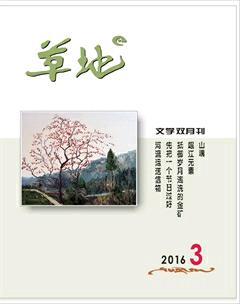抵御岁月淘洗的金矿
2016-07-06刘德远
刘德远
这是一本厚厚的笔记本,封皮是黄色和褐色组成的图案,褐色部分是不规则的点状纹,黄色部分是规则的竖条纹,半月形状,覆盖在褐色之上,英文“NOTEBOOK”这个单词清晰地印在上面,告诉人们它的用途和潜在的价值。
这是我精心挑选的笔记本,记录了首届汉语非虚构写作“长白山高峰论坛”的真知灼见。“非虚构写作”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写作方法,它着眼于日益丰富的现实生活细节,以田野考察为观察手段,以跨文体写作为表现手法,在传统散文表现手法力不从心之处阐幽发微,还原、呈现生活与文学的真相。这次高峰论坛名家荟萃,思想交流碰撞,我相对完整地记录大师们思想的火花。现在,这个笔记本里留下了一串名字和思想的痕迹。蒋蓝、高维生、黑陶、吴佳俊、杨晓华、尉迟克冰、袁炳发、纪洪平、于德北等先生对非虚构写作的思考,已经成为这个笔记本抵御岁月淘洗的金矿,等待着我这个淘金者挖掘和发现。
作为首届汉语非虚构写作高峰论坛的主讲嘉宾,蒋蓝先生在文学上的建树可谓富甲八方,作为当代先锋诗人、思想随笔作家,已出版《诗歌笔记》《词锋片断》《黑水晶法则》《寂寞中的自我指认》《人迹霜语录》《爱与欲望》《身体政治》《哲学兽》《玄学兽》《身体传奇》《思想存档》《鞋的风化史》等20多部个人著作。在继续诗歌写作的同时,“以深入黑暗中心的思想随笔开启了非非主义写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我的记录中,蒋蓝先生对于非虚构写作与踪迹史的思考堪称富矿。闲暇的时候,我会把品名蒋蓝的矿石放在桌子上,仔细地鉴赏和品味,从文字的矿脉中寻找到思想的结晶体,像一个寻宝的孩子,任它在我的眼睛里闪闪发光。
作品的生命力是作家安身立命的资本,生命力越恒久,作家才更有价值。如何评价一个作家的价值呢?蒋蓝先生说:“敝帚自珍是个人行为,作品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散文和随笔的体系梳理,是蒋蓝先生的开题之课。先生认为,西方出现散文要晚于随笔,中世纪欧洲的演讲辞就是随笔,由于没有预设话题,而是激辩过程中思想火花的碰撞而产生。谈到散文和随笔的区别,先生认为随笔服务于思想空间,散文服务于文学。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先生打了一个比喻:“面对一棵苹果树,一个散文家可以做很多描述,而一个随笔作家会直接摘下果实,吃上一口,告诉你果实的味道”。比喻恰如其分,让先生的思想愈加生动活泼。
蒋蓝先生关注当下中国散文创作,但他认为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一是个人情绪化叙述严重,小感情散文成为主流。二是预设问题写作大行其道,缺乏个性创作。先生认为,散文是个性化创作,要有文本指标、生活拷问和思想的指射,体现精神性力量,为当下进行造像。
近几年来,非虚构写作悄然兴起,越来越受到散文界的关注。作为非虚构写作的翘楚,蒋蓝先生颇有心得。听先生讲课之前,我先入为主地读了美国著名报人杰克.哈特的《故事技巧》一书,这本书是一本系统讲述叙事性非虚构文学创作方法与技巧的作品。译者叶青和曾轶峰在《译者序》中写到,简单来说,文学作品可以用“虚构”与“非虚构”两分。当我们乘着想象的翅膀遨游了一圈,回到现实生活中,遗憾地发现,我们终究是生活在“非虚构”的世界。所以我们需要“非虚构”文学来帮助我们更清醒地面对现实,更勇敢地过好自己的人生。非虚构故事的力量到底源于什么?杰克.哈特给出的答案是源于真实。非虚构作家把这个真实世界中的真实故事记录下来并深入到故事背后,挖掘出可供我们参考借鉴启发深思的普遍真理,并假以高超的叙事技巧,写成一个个愿意读、敢于读的故事。
在谈到非虚构写作与踪迹史的时候,先生坦诚自己的观点。我记录的文字不能窥其全貌,但阅读了先生《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一书的序言,对先生的踪迹史观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在《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这本书里,我所关注的唐友耕一个人的“踪迹史”,也可以说首先是引我步入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从而带出有关四川晚清时节的官场史、黑暗史、军事史、廉政史、民俗史、风物史等等。
历史即是“人迹”铺成。但重大的往事才成为了“史迹”,而在个体生命与连续流动的历史关系中,探寻历史运行过程中个体生命的“踪迹”,自然成为了我的着手点。尽管汲深绠短,我当勉力为之。
如同发生的事情即是事实一样,凡是发生的踪迹都是轨迹。但唯有那些能够说明历史轨迹的人格踪迹,才构成一种强力的个案踪迹。
表面上看,踪迹存留于历史的缝隙,我们一旦将某个人的踪迹钩沉而出,将历史碎片铺开,历史中不可解释的部分往往就只剩下心灵的部分。所以,一个人的踪迹史是把一个又一个的空间串联并敞开,宛如我的书案上狂乱的笔触,构成了一道插满蒺藜与玻璃的山墙。我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技术,才能安然通过。
当然了,回到对历史的书写,也并非一味在永续开放的变异中仅仅着眼于无规则沉淀。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确实导致历史的杂乱踪迹,导致碎片化的历史活动弥散在各个角落,但不可否认的是,总有一些基本的活动及其价值以规则性和周期性而信然存立。踪迹纵然有丰富的活动和作用空间,但必定会通过观念、知识以及相当的机制反映、制约和调节社会运行和历史运动。虽然表面上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进行历史活动,但他们的活动只能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进行,而这就是历史规律性的根源。
很清楚,我在这里谈论的踪迹,与德里达的“踪迹论”南辕北辙。我所谈论的踪迹是形而下的,是肉身化的,不可能遁形而知天命,去关乎“在场”与否。本文所言的踪迹接近刑事案件的侦破术,这些踪迹忠实地纪录着暴力曾经的“在场”。踪迹在此既是进入事件主体过程的物质线索,同时也是衡定历史的物证。
十分欣赏蒋蓝先生的话:最锋利的刃,总是砺自墓碑。锈迹与石屑交替而下,个中更有无数幽魂,以沙粒的精光凝视你!
2013年6月20日上午,在长白山脚下的二道白河镇的长白山大厦三楼会议室,儒雅博学的蒋蓝先生为首届汉语非虚构写作高峰论坛主讲。由于我就坐在先生的右下首,得以最近距离地观察先生和聆听教诲。一台笔记本电脑摆放在眼前,打开的文档上密密麻麻的文字,看来先生做足了功课。但先生根本就没有注视它的存在,而是慢条斯理地给我们讲课,不时轻轻地靠在椅背上,用目光和叙述引领我们进入他的内心世界和创作心路。在这里,先生谈起《褴褛时代的火焰凌霄》的创作心路。
《褴褛时代的火焰凌霄》的主人公凌君如,是刘文彩的三姨太,蒋蓝先生最初对她的了解仅仅是大邑刘文彩庄园里两张老照片。很多次陪同客人参观,先生只是简单介绍,发黄的黑白照片和庄园一样,到处都是刘文彩的烙印。2005年夏天,蒋蓝先生陪同北京作家祝勇参观庄园,站在凌君如的几幅老照片前,祝勇停留了很长时间。作为“新散文”写作的倡导者,长期触摸历史文化形成的敏锐嗅觉,使祝勇对凌君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为照片的背后有故事。蒋蓝先生决定挖掘和还原这个小人物。蒋蓝先生先后查阅了17种史料书籍以及内部档案,采访过程持续了5个多月,从两个小故事入手,先后8次探访宜宾和大邑,通过对敬老院老人、生产队队长、大量村民的走访,剥茧抽丝般不断地寻找新的线索,还原凌君如坎坷而传奇的人生,最终使凌君如在历史的风尘中慢慢清晰,成为有血有肉有思想有灵魂有爱恨情仇的女人。同时,在4万多字的文章中,还涉及到刘氏家族发家史、四川捐税史、袍哥史,满纸活生生的宜宾和大邑的风土人情。
蒋蓝先生如痴如醉的述说,让我产生一个幻觉,凌君如在历史的某一个空间注视着这个房间,她为自己不再是匆匆过客而嫣然一笑。从这个意义上说,凌君如应该感谢蒋蓝先生记录了这段湮没的历史。
从长白山回来以后,我在网络上搜到这篇文章,略显吃力地读完这篇文章,有一段文字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到达宜宾宗场镇大棬子村的凌家时,凌君如的年龄大约在11岁左右。那个年代的人总是成熟得过早、过快,艰辛成为了生活的常态,可以让人成为易耗品,就像投之入水的一幅美轮美奂的绵竹年画,春花秋月的纸上遣兴,迅即化为了纤维的丑陋和褴褛。这段文字,我认为是凌君如一生的写照。正如一位评论者指出:“蒋蓝写的人物传记的最大特点是,他写人物的遭际和内心的苦痛,给人一种被撕裂的疼痛感,带着硬物划过玻璃的刺响,让读者与书中的人物感同身受,给读者带来震撼,他的文字有火的灼热,刀剑的锋利和硬度。”读《褴褛时代的火焰凌霄》,我深有同感。
蒋蓝先生继续着讲座,工笔性描写正细腻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我开始注意到先生的衣着有一个细微的变化,先生衣着随意,一件从领口由老绿渐为浅绿的T恤,轻松地穿在身上,米色的休闲裤整洁干净。我觉得先生的衣着比较符合今天的气场和氛围,儒雅而坦诚。但是前两天却不同,甚至有些超出我的想象。6月18日,各位老师从长春出发,中午抵达我的家乡吉林省敦化市。在金鼎宾馆一楼的见面宴会上,高维生老师特意介绍我和蒋蓝老师认识。蒋蓝老师的儒雅、沉稳和睿智吸引了我,更吸引我的是他的T恤上黑色的虎头图案。我对四川的印象是大熊猫,一直觉得老虎属于东北。当儒雅遇到老虎,我确定是王者归来。蒋蓝先生以独特的方式,加深了我对他的印象。
禅心听佛语,佛度有缘人。我一直相信,万物聚散皆有缘分。长白山首届汉语非虚构写作高峰论坛,使我有缘结识蒋蓝先生,也圆了我一个梦。第一次知道蒋蓝先生的名字是六七年前从诗人姜英文那里。作为延边的文化名人和文学活动家,英文工作生活在长吉图开发开放的前沿珲春市,这里地处中、俄、朝边境,是个一眼望三国的好地方。得益于地缘优势,珲春市与韩国束草的文学交流比较频繁。束草文学总会编辑出版中韩文学作品集,在姜英文先生的推荐下,蒋蓝的诗歌《三轮车夫与李白的瀑布》、高维生的诗歌《我回忆梦的情景》、古筝的诗歌《快乐》、王川的诗歌《初夏的傍晚》和我的诗歌《开花的石头》被译成韩文收录其中。读蒋蓝先生的诗歌,进而了解到先生是先锋诗人、思想随笔作家,让我只能望其项背。
机缘巧合,我再一次对蒋蓝先生产生神往,源于高维生老师。2012年5月22日,高维生老师到敦化采风,我们几个文朋诗友略尽地主之谊。交谈中,高维生老师挂在嘴边的就是非虚构写作和蒋蓝先生。不怕您笑话,高维生老师在我心目中俨然是大家,而他对蒋蓝先生的评价之高,使我感到不能错过和蒋蓝先生相识的机缘。尤其是蒋蓝先生在《独立文丛》总序中的一句话:“高维生宛如一架抗起白山黑水的虎骨,把那些消匿于历史风尘的往事,用一个翻身绽放出来”。我认为把高维生老师写活了,令我心生神往。听说高维生老师正筹备非虚构写作高峰论坛,我就唐突地提出是否可以列席论坛旁听。在高维生老师的极力推荐下,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在首届汉语非虚构写作高峰论坛上见到蒋蓝先生,并且首先领略了先生诗人的风采。
首届汉语非虚构写作高峰论坛的序幕在第二松花江源头的敦化和平林场拉开帷幕。18日下午和19日上午,敦化市作家协会举办了一个小型活动,包括《雁鸣湖》杂志笔会、考察松花江源头、举办篝火晚会、登草原山和松花江源头漂流等项目,文朋诗友和各位名家寄情于山水之间,领略自然之美、和谐之美,一颗颗因为文学而激情澎湃的心,在沟通和交流中释放着人性之美。在跳跃的篝火面前,蒋蓝先生和美女作家蔚克冰一起朗诵了自己的诗歌,用诗人的激情沸腾了篝火旁一颗颗驿动的心。
蒋蓝先生年长我3岁,但先生的博学、睿智、厚重和热情,一直令我望而生畏,几天里很少主动沟通。6月21日,我们一行人同登长白山。蒋蓝先生古道热心,为我们拍了很多照片,不时地和我们交流着摄影技巧。为我们摄影的时候,他会精益求精,丝毫没有松懈。但我们在给他留影的时候,他会很温和大度地说,拍的不错,有个留影就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探访地下森林的时候,走到一条溪水积潭的地方,清清的浅底有几十枚硬币,肯定是一些虔诚的游客许愿时投在这里的。我是一个相信万物皆有生灵的人,也就萌生了许愿的念头。但衣袋里没有硬币,我只好一甩手怏怏地走了。可就是这一甩手,却碰到了蒋蓝先生的鼻子,弄得我十分不好意思,一个劲地赔礼道歉。蒋蓝先生若无其事地说,没什么,没什么,脸上没有一丝愠态。蒋蓝先生的平和,使我的心轻松许多。
晚饭以后,我请蒋蓝先生到文友的房间,再一次向他请教非虚构写作的技巧。为了和蒋蓝先生沟通交流,我提前两个月在网上订购了美国作家杰克.哈特的《故事技巧—叙事性非虚构文学写作指南》,并认真地阅读。就书中和实际创作中的一些问题,我向蒋蓝先生进行请教。尹卓铃、王玉欣和李淑杰也都提出了她们关心的问题。从8点到10点,蒋蓝先生给我们单独吃了小灶,使我们受益颇多。这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两个小时的解难答疑,我们听得很解渴,但却忘了给蒋蓝续水,想起来也是够粗心的。先生没有责怪的意思,反而高兴地对高维生老师说:“他们对文学很虔诚,让我很感动”。听到这样的评价,我们又岂是简单的感动。我对蒋蓝先生的博学很是钦佩,先生则说,要多读书,读经典著作。要跨学科阅读,丰富知识储备。我每个月都要购买很多书籍,并坚持大量阅读。你们应该养成读书的习惯,最少一个月读三本书,三年下来一定会有所收获,有很大提高。听到这里,我真的有些汗颜了。我也读书,但仅限于浏览,由于喜爱诗歌,读诗相对多些,对其他领域的书就很少问津了。本来想请先生给开个书单,但由于时间太晚了,加之心虚,也就没有提出这个要求。我决定还是先把家里现存的一千多册书籍好好读一读。
6月22日9点30分,我们和各位老师在敦化市翰章广场依依惜别。这次聚会虽然短暂,但给我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为了参加首届汉语非虚构写作高峰论坛,我休假一周,提前安排好工作,免得工作打扰。我对参加文学笔会一直感觉很神圣,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参加过数次《天池》杂志举办的笔会,虽然地点不同,但我是怀着一颗朝圣的心把仰慕变为敬重,然后不断地提升自己。这次高峰论坛,应该说比我参加的笔会层次更高,收获也更多。把蒋蓝先生比作一个富矿,因为先生的博学多识。先生的藏书有五万多册,相当于一个小图书馆的藏书量,可见先生的阅读量之丰富。在先生面前,我就是一个淘金者,只有努力挖掘,勤奋创作,才可以找到文学的矿脉,把亮晶晶的矿石据为己有。
责任编校:周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