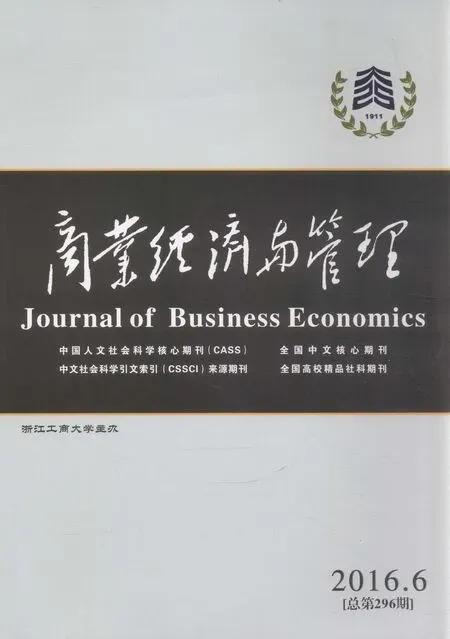旅游减贫效应的门槛特征分析及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2016-07-05郭鲁芳李如友
郭鲁芳,李如友
(浙江工商大学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旅游减贫效应的门槛特征分析及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郭鲁芳,李如友
(浙江工商大学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文章利用中国2000-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对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其它变量的条件下,中国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作用以积极影响为主,同时呈现显著的门槛特征。具体而言,中国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促进作用表现为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重门槛特征、基于旅游资源禀赋的三重门槛特征以及基于交通便利程度的单一门槛特征,随着门槛变量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旅游发展并非总对贫困减缓产生实质贡献。为此,文章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在思想观念上,客观认识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正确指导旅游减贫开发实践;在发展路径上,贫困地区应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旅游减贫精准性;在发展政策上,实现由统一指令性政策向灵活协调性政策转变;发展保障上,政府部门应积极发挥主导作用,为旅游减贫创造有利条件。
关键词:旅游减贫效应;门槛效应;面板门槛回归模型
一、 引言
反贫困一直是全人类共同面对且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旅游业因其投资少、见效快以及就业门槛低、产业关联广等特点,被认为是贫困国家和地区减贫增收的有效工具,在世界反贫困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就已经开始了旅游减贫开发实践,一些旅游资源丰富的老、少、边、穷地区通过发展旅游业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尤其是近年来国际社会提出“有助于贫困人口的旅游”(Pro-Poor Tourism,PPT)和“消除贫困的可持续旅游”(Sustainable Tourism-Eliminating Poverty,ST-EP)战略之后,政府部门和相关组织积极探索并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以环境保护为原则、以特色资源为依托、以居民受益为目的的旅游减贫开发模式,涌现出了许多益贫式发展的成功案例。
旅游减贫活动在世界范围内如火如荼开展的同时,研究者们也对旅游发展的减贫效应展开了争论。传统的观点认为,旅游业在减贫方面有着其它产业所无可比拟的优势,因此,将旅游开发与贫困地区发展有机结合是消除贫困的有效途径[2-4]。但是,随着旅游减贫实践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开始质疑旅游业对贫困国家和地区的减贫作用。有学者认为,旅游漏损与旅游乘数同根同生,巨大的经济漏损可能造成贫困的进一步加剧[5],换言之,旅游流量与贫困减缓之间存在负向关联的可能[6]50。由此可见,旅游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远比想象的更为复杂,那么,现阶段在经济落后地区发展旅游业是否对贫困减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如果是,旅游减贫效应到底有多大?在经济水平、旅游资源禀赋和交通便利程度等发展条件不同的地区,旅游减贫效应是否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特征?这些都已成为影响经济落后地区发展战略决策和旅游产业地位的重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即是本文研究目的所在。
二、 文献综述
关于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影响,国内外学者通过大量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形成了三种迥然不同的观点,即旅游减贫有效论、旅游减贫无效论和环境决定论。
持旅游减贫有效论观点的学者认为,旅游发展对经济落后地区的贫困减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Ashley和Boyd(2000)认为,旅游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且就业门槛低,发展旅游业能够为贫困人口创造就业和收入机会,从而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7]。特别是旅游工艺品和纪念品不仅可以向旅游者直接销售,还可出口销售,此类技术要求不高的就业岗位为处于更加劣势地位的人(如妇女和残疾人)提供收入机会[8]。不仅如此,Shah和Gupta(2000)通过研究发现,贫困人口除了通过就业直接从旅游业中获利外,还可以通过旅游收入的“渗透作用”获益[9]。旅游业具有产业关联广的特点,发展旅游业能够带动其它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从而进一步地扩大劳动就业和增加居民收入。Ashley和Mitchell(2006)在对非洲旅游减贫的研究中计算了旅游乘数效应,发现游客的直接旅游消费能够带来60~120%的间接影响,即游客每消费1美元,当地人将获得1.60~2.20美元的总收入[10]。这两位学者的后续研究表明,旅游减贫的效应越来越明显地发生在旅游业之外,且并不限于旅游地区域,还通过产业链影响到旅游地区域之外[11]。旅游发展对贫困地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非经济影响对于减缓贫困来说同样重要。Reeder和Brown(2005)认为,旅游业发展可以带来旅游目的地的贫困率和其它社会条件的改善,如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健康等,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加强了边缘地区与其它地区在资金、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交流,从而有利于减缓贫困[12]。此外,赵磊(2011)发现,旅游发展对农村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但与城镇地区经济增长并不存在显著关系,发展旅游业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从而对减缓贫困产生积极影响[13]21。
持旅游减贫无效论观点的学者认为,旅游发展对于贫困减缓并无积极作用。Lewis等(2003)认为,由于旅游业的就业门槛较低,在旅游行业就业的人通常素质不高且技能低下,从而导致薪水普遍低于工业和高新技术行业,因而这些人被称为“穷忙族”(Burger-flippers)[14]。Walpole和Goodwin(2000)认为,由于贫困地区经济基础差,旅游市场容易受外来资本控制,旅游漏损问题严重,当地居民从旅游发展中获得的经济利益有限[15]。类似地,Taylor(2001)在对库克岛(Cook Islands)旅游发展进行研究时发现,由于当地的社会经济过度依赖旅游业,造成旅游替代产业失去了生存空间,特别是旅游业易被外来机构和组织控制,经济漏损严重,当地居民并未从旅游发展中获益[16]。此外,Wattanakuljarus和Coxhead(2008)利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研究了泰国旅游发展的减贫效应,结果表明,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提高了泰国居民的家庭收入,但削弱了贸易领域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就业人员的收入[17]。
近年来,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由于许多区域性和地方性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决定着旅游业发展及其在地区贫困减缓中的角色和潜力,旅游减贫的效果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存在明显差别,于是形成了第三类观点——环境决定论。旅游业是高度综合性行业,涉及食、住、行、游、购、娱等各个方面,经济基础、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区域发展战略都是旅游发展不可回避的制约因素,这些因素的区域差异造成了旅游减贫效应的空间异质性。例如,Deller(2000)应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研究了美国乡村贫困与旅游及娱乐活动之间的关系,得出二者关系在空间上存在显著差异的结论,同时发现高尔夫、网球和游泳等娱乐活动有助于降低旅游地的贫困率,但其它形式的旅游和娱乐则对贫困率的变化没有影响,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18]。Muchapondwa和Stage(2013)通过对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和南非这三个国家旅游减贫效应的研究发现,由于旅游者在三国的消费水平存在一定差异,造成当地居民从旅游业获得的收益也存在较大差别[19]。Thomas(2014)认为,旅游地的地理区位、吸引力等因素同样影响旅游从业人员的工资水平。例如,2009年琅勃拉邦的游客量是多贡的6倍,与之相对应地,前者旅游从业人员的平均收入比后者高出2倍,随着当地旅游业的持续发展,从业人员的技能更加熟练和专业,工资水平也会不断提高[20]。于是,Scheyvens(2011)认为,许多对旅游减贫效应持否定观点的学者忽略了旅游发展条件的合意性,旅游业只是为一些其它因素引发的问题承担罪名的“替罪羊”[21]。
已有研究成果从不同方面展示了旅游发展与减缓贫困之间的复杂关系,为本文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是,本文认为还需从以下方面做出补充和完善:(1)从研究内容来看,考察视角大多基于跨国数据或国别个案宏观层面,忽略了各种因素在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同一国家不同地区之间呈现的异质性以及由此导致的旅游发展减贫效应的区域差异,并且来自中国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关系的经验研究还相对缺乏。(2)从研究假设来看,既有文献多在线性模型框架下展开,忽略了旅游发展与贫困缓解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即不同经济水平、资源禀赋或交通便利程度条件下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差别效应。(3)从贫困测度方法来看,现有研究通常采用贫困发生率来衡量贫困水平,而此种以贫困线为基准来衡量贫困状况的方法可能在统计上掩盖了部分旅游减贫效应,正如Blake和Arbache(2008)所言,尽管巴西的最低收入群组家庭从旅游发展受益较少(远低于高收入群组家庭),但并不能否认旅游发展对所有群组家庭收入的影响是积极的[22]。基于此,本文尝试在非线性模型框架下探讨中国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及其特征,以便为深入认识中国实施已久的旅游减贫政策的有效性提供现实解释,并为不同地区旅游减贫政策转向提供参考依据。
三、 模型设定、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一) 模型设定
为了分析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的关系,本文首先构建如下面板数据模型:
POVit=μi+β1TOURit+δXit+εit
(1)
POVit=μi+β1TOURit+β2TOUR2it+δXit+εit
(2)
式中,i和t分别表示个体和时间,POVit为贫困水平,TOURit为旅游业发展水平,TOUR2it为旅游业发展水平的二次项,Xit为其它控制变量,μit为地区间差异的分观测效应,εit~iid(0,σ2)为随机扰动项。
如前文所述,旅游减贫效应的发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不同条件下,旅游减贫效应可能存在差异,其机制和效果的转变可能需要跨越一定的门槛。而经济基础、旅游资源禀赋和交通便利程度作为影响旅游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发挥旅游减贫效应无法摆脱的羁绊,在一定条件下形成旅游减贫效应的门槛条件。门槛效应的检验方法主要有分组检验模型和交叉项模型。前者先验地选择分割点将样本分为若干组,在每一组内进行线性关系检验,但分割点的选择具有随机性,且无法对回归结果的差异性进行显著性检验。后者通过建立包含交叉项的线性模型来考察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尽管能够估计出门槛值,但交叉项的形式难以确定,同样也无法对门槛效应进行显著性验证。Hansen于1999年提出的门槛面板回归模型能够弥补上述检验方法的缺陷,该方法的特点是通过内生方式对样本进行分组,分别估计不同样本中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能够反映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否在某一或某些时刻发生了结构性突变[23]246。基于此,本文根据Hansen(1999)[23]250提出的门槛回归模型的思想,将面板数据模型扩展为分别以经济发展水平(EGDP)、旅游资源禀赋(RES)和交通便利程度(TRA)为门槛变量的多重门槛面板回归模型:
POVit=μi+β11TOURitI(EGDPit≤γ1)+β12TOURitI(γ1 +…+β1,nTOURitI(γn-1 (3) POVit=μi+β21TOURitI(RESit≤γ1)+β22TOURitI(γ1 +…+β2,nTOURitI(γn-1 (4) POVit=μi+β31TOURitI(TRAit≤γ1)+β32TOURitI(γ1 +…+β3,nTOURitI(γn-1 (5) 式中,EGDPit、RESit和TRAit为门槛变量,γ1、γ2、…、γn-1、γn为n+1个门槛区间下的门槛值,β11、β12、…、β3,n-1和β3,n为不同门槛区间下的估计系数,I(·)为指标函数,若门槛变量满足条件则该指标函数值为1,否则为0,εit~iid(0,σ2)。控制变量(Xit)具体包括产业结构(IND)、城镇化水平(URB)、贸易开放度(OPEN)和教育水平(EDU)等。 (二) 变量选取 1.因变量。贫困水平(POV)。常用的贫困测度指标有贫困发生率、贫困距、Sen指数和可分解FGT指数等,这些测度指标都以贫困线为基准进行贫困程度的评价,对中国的适用性不强。其原因是,中国对贫困线的划定无统一标准,不同时期的贫困线有所不同,致使指标值对贫困线的选择非常敏感。贫困具体反映在个体的健康、教育、技能以及公共品的可获得性等方面,所以应被视为“基本能力的剥夺”[24]。许多学者依据获取有价值的功能性活动的能力来评估贫困水平,收入或支出是常用的测度指标。郭熙保和罗知(2008)[25]18、杨霞和刘晓鹰(2013)[6]49利用20%最低收入人群的平均收入来估算贫困水平,张冰和冉光和(2013)则用人均消费水平指标来反映各地区的贫困程度[26]。本文从收入的角度对贫困状况进行测度,出于如下考虑使用人均收入作为衡量各地区贫困水平的依据:(1)部分地区统计数据缺失或不连续,考虑到分析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比性,统计相对完整的人均收入水平指标是可靠之选;*由于中国省级及以下层面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分组统计数据缺失,郭熙保和罗知(2008)文中的贫困人口收入水平实际上是城镇贫困人口收入水平。杨霞和刘晓鹰(2013)综合考虑了城镇和农村地区人口收入,但在计算中,城镇数据使用按收入等级分组时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而农村数据则使用未分组的农民人均纯收入。(2)郭熙保和罗知(2008)[25]18等学者建议使用20%最低收入人群的平均收入估算贫困水平有其合理性,作为参照,本文对2000-2013年全国城镇人均总收入与其20%低收入组进行相关分析,得到Pearson相关系数为0.993,在0.1%的水平(双侧)上显著;类似地,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其20%低收入组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998,同样在0.1%的水平(双侧)上显著,所以,人均收入也可以视为20%最低收入人群的平均收入的替代变量。因此,本文衡量贫困水平的计算公式为:POV=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村人口占比+城镇人均总收入×城镇人口占比。 2.核心解释变量。旅游发展水平(TOUR):参照Adamou和Clerides(2010)[27]、Fayissa等(2011)[28]和赵磊(2011)[13]的做法,采用旅游专业化(Tourism Specialization)作为旅游发展的代理变量,其度量方式为地区旅游总收入与GDP之比。 3.门槛变量。理论和实证研究都已证明,旅游业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经济基础、旅游资源禀赋和交通条件的作用最为突出[29]。首先,经济基础决定区域内的旅游供给能力和旅游消费水平。旅游业的高产业关联特征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旅游业有助于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其它相关行业的发展水平对旅游业产生影响和制约。经济发达往往意味着合理的产业结构、丰裕的财政收入和合理的制度安排,这些都为交通条件的改善和旅游市场的繁荣提供原动力;同时,经济发达地区的居民往往拥有更高的可自由支配收入和参与旅游活动的可能性,形成的现实旅游需求及较强的消费能力能够促进当地旅游业更快发展。其次,旅游资源禀赋客观上决定了旅游业的发展方式和发展程度。旅游资源越丰富,市场需求将越大;类型越齐全,则旅游活动更趋于多样化;品位越高、垄断性越强,对外地游客的吸引力越大。最后,交通条件是旅游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产生空间相互作用、旅游者实现空间位移的基础性条件,并对游客结构及其停留时间产生重要影响。可见,经济基础、旅游资源禀赋和交通条件是旅游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一点已毋庸置疑,那么这些因素是否更为深入地对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其作用方式是否通过影响地方公共政策、旅游者构成及停留时间而呈现非线性特征,还需做针对性研究进行判断。因此,本文分别采用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和交通便利程度作为门槛变量,对中国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的非线性关系进行检验。 (1) 经济发展水平(EGDP):用人均GDP表示,并利用GDP平减指数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折算得到实际值。 (3) 交通便利程度(TRA):采用交通密度来衡量,其计算公式为:TRA=Li/Ai,式中,Li为地区交通线长度,Ai为地区国土面积。考虑铁路、公路和内河航道等不同交通方式对旅游发展的作用不同,本文参考赵东喜(2008)的方法[33],利用赋分法计算获得交通线长度代替值,即:Li=(RAIL×5+ROAD×3+RIVER×1)/9,式中RAIL、ROAD和RIVER分别为铁路里程数、公路长度和内河航运里程数。 4.控制变量。选择产业结构(IND)、城镇化水平(URB)、贸易开放度(OPEN)和教育水平(EDU)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产业结构(IND)用地区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来衡量;城镇化水平(URB)即为人口城镇化水平,用非农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来衡量;贸易开放度(OPEN)用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来表示;教育水平(EDU)用每万人口中在校高中生的比例衡量。经济发展水平(EGDP)和交通便利程度(TRA)对地区贫困水平产生直接影响,因此也将之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 (三)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实证检验的样本为2000-2013年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数据资料,未包括港、澳、台地区。关于数据的获取与处理,有以下几点说明:(1)旅游总收入由旅游外汇收入与国内旅游收入汇总得到,旅游外汇收入按照当年平均汇率计算;(2)为了消除统计数据中价格因素的影响,旅游总收入和人均GDP等绝对指标值都用GDP平减指数(以2000年为100)进行了折算;(3)本文所使用旅游收入统计数据来源于各期《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及其副本,A级景区数据来源于国家旅游局网站发布的统计信息以及各省级单位的统计年鉴,其它统计数据均来源于各期《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4)为了避免量纲和异方差的影响,本文采用自然对数对所使用的数据进行处理。 四、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弱外生性检验 前文分析已经说明旅游发展是贫困减缓重要影响因素,同时还应注意,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贫困地区居民外出旅游的欲望增强,这能够促进本地及周边地区旅游业的发展,于是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Engle等(1983)定义了弱外生性概念,认为在研究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关系时,解释变量需具备弱外生性,这是保证模型统计推断有效的必要前提[34]。基于此,本文利用Johansen(1992)[35]提出的弱外生性检验方法对旅游发展水平(TOUR)进行检验,以确保模型估计方法选择的合理性。*伍德里奇(2003)建议用相同的方法进行变量的内生性检验[36]。首先用被怀疑的内生变量对原模型中所有其它解释变量和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并提取其残差。然后把残差加入到原模型作为一个新解释变量继续回归,如果其系数显著,则说明怀疑对象确实是一个内生变量。反之,则无法拒绝怀疑对象为外生的原假设。首先用旅游发展水平(TOUR)作为被解释变量,用其它控制变量以及旅游发展水平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进行OLS估计;然后将估计残差作为新的解释变量加入到模型(1)中进行再估计,如果其系数显著异于零,则拒绝“旅游发展水平是弱外生变量”的假设。按照上述方法,本文得到估计残差作为解释变量时的t统计量为0.32,p值为0.748,从而说明旅游发展水平(TOUR)具有弱外生性。 (二) 门槛效应检验 根据Hansen(1999)的研究思路,本文首先对模型的门槛效应进行检验。分别以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和交通便利程度为门槛变量,依次对存在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的原假设下对模型(3)-(4)进行估计,得到F统计量和采用bootstrap方法得出的p值,如表1所示。结果显示,以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时,旅游减贫的单一门槛效应和双重门槛效应均在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三重门槛效应未通过水平为10%的显著性检验;以旅游资源禀赋作为门槛变量时,旅游减贫的单一门槛效应、双重门槛效应和三重门槛效应都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以交通便利程度作为门槛变量时,旅游减贫的单一门槛效应在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双重门槛效应未通过水平为10%的显著性显著。因此,对于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和交通便利程度这三个门槛变量,后文将分别基于双重门槛模型、三重门槛模型和单一门槛模型进行旅游减贫效应的门槛特征分析。 注:表格内数值为门槛检验对应的F统计量,括号内是p值,为采用bootstrap方法反复抽样300次得到的结果;*、**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进一步地,对分别采用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和交通便利程度作为门槛变量的双重、三重和单一门槛模型的门槛值进行识别。表2报告了门槛的估计值及其对应的95%置信区间,图2的似然比函数图可以更为清晰地理解门槛值的估计和置信区的构造过程,图中虚线为LR值在10%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虚线以下的区域构成门槛值的90%置信区间。如图1所示,当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时,LR统计量在90%渐进有效置信区间[9.008,9.159]和[9.889,9.889]内接近于零,检验结果无法拒绝门槛估计值为其真实值一致估计量的原假设,由此可断定模型估计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两个门槛估计值分别为9.047和9.889;类似地,分别得到当旅游资源禀赋为门槛变量时的三个门槛估计值分别为4.159、5.620和6.410,以及当交通便利程度为门槛变量时的单个门槛估计值为1.402。 (三) 门槛估计结果分析 如前文所述,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与交通便利程度三个门槛变量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均拒绝了线性关系的原假设,且分别在双重、三重和单一门槛模型下的门槛效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由此可以判断,在上述三个门槛变量影响下,中国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换言之,中国旅游减贫效应存在门槛特征。门槛回归模型实质上是根据门槛估计值将样本分成多个区制,分别考察每个区制内部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作用,并通过比较回归系数的差异来检验门槛效应是否显著。根据三个门槛变量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和门槛估计值,分别考察在不同的区制内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结果如表3所示。此外,为了对比总体水平上与不同区制内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作用,表3同时报告了线性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模型(1)中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2)中加入了旅游发展水平的二次项(TOUR2),其系数的估计值显著为负,这也说明了中国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非线性关系的显著存在。 注:括号内为t值,*、**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中国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作用呈现出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阶段性响应的双重门槛特征。该特征具体表现为:当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值低于门槛值9.047时,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当经济发展水平值进入门槛值9.047与9.889之间时,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具有显著积极影响,影响系数为0.151;当经济发展水平值跨越门槛值9.889时,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作用又重新变为不显著。概言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旅游减贫效应不明显;经济发展中等水平地区,发展旅游业将有助于贫困减缓;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同样无显著促进作用。究其原因在于旅游业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其突出的综合带动作用的另一面是其对其他行业的多重依赖性,容易受到国家政策、宏观环境及其它相关产业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低往往意味着落后的基础设施、守旧的思想观念或沉闷的地方政策,市场活力相对不足,这都将成为制约旅游发展及其减贫效应发挥的掣肘,因此,经济发展落后地区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促进作用并不突出。随着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及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旅游业获得良好的发展环境,其投入少、见效快、带动性强的优势逐渐体现,所带来的财政税收增加也为政府部分针对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提供资金支持,此时,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发挥积极作用。然而,旅游业就业门槛低,专业技术性不强,这决定了从事该行业的社会劳动收入低于许多知识型或技术型行业。经济发达地区拥有良好的资源条件、合理的产业结构和成熟的市场体系,若过于重视旅游业,必然对其它产业的发展产生“挤出效应”,使一些“富民”作用更为突出的产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受到抑制,在此条件下,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作用具有不确定性。 以旅游资源禀赋为门槛变量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中国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作用呈现出基于旅游资源禀赋的逐步提升趋势的三重门槛特征。该特征具体表现为:当一个地区旅游资源禀赋低于门槛值4.190时,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影响作用未通过水平为10%的显著性检验;当旅游资源禀赋进入门槛值4.159与5.620之间时,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具有显著积极影响,影响系数为0.081;当旅游资源禀赋进入门槛值5.620与6.410之间时,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产生显著积极影响,影响系数升为0.184;当旅游资源禀赋跨越门槛值6.410时,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同样产生显著积极影响,影响系数升至0.274。由此可见,旅游资源禀赋较差的地区,发展旅游业并非一定能够减缓贫困;对于旅游资源禀赋较好的地区,发展旅游业却有助于贫困减缓,且随着旅游资源禀赋的不断提升,旅游减贫效应愈加明显。究其原因,旅游资源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旅游业的先决条件,是吸引旅游者前来旅游的核心要素。旅游资源越丰富、品级越高、垄断性越强,其吸引力越大,市场覆盖面越广。旅游资源贫瘠地区对旅游者的吸引力较弱,旅游业发展潜力不足,无论是对当地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是对其它相关行业的带动都十分有限,此时,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无法表现出积极的促进作用。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能够吸引大规模旅游者前来观光和消费,旅游业发展潜力大,行业带动作用强,在当地产业结构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在政府的政策支持和社区广泛参与的情况下,旅游发展为当地居民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为重要的是,以旅游者为载体的外来文化打破了落后地区传统思想的禁锢,先进思想观念的涉入能够激励当地居民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积极寻求发展,提高生活水平。因此,随着旅游资源禀赋的提升,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促进作用呈阶梯状增强的趋势。 以交通便利程度为门槛变量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中国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作用则呈现出基于交通便利程度的跨越式提升的单一门槛特征。该特征具体表现为:当一个地区交通便利程度低于门槛值1.402时,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具有显著积极影响,影响系数为0.134;当交通便利程度跨越门槛值1.402时,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积极影响则更为明显,影响系数升至0.247,提升率达84.33%。由此可见,旅游业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促进作用受到交通便利程度的影响,随着交通便利程度的不断提升,旅游减贫效应愈发突出。究其原因,旅游活动是一种典型的地理现象,在空间上表现为旅游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迁移过程,旅游交通是沟通旅游需求与旅游供给的桥梁,是旅游活动得以实现和促进目的地旅游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在旅游系统中担任旅游要素流动通道和系统润滑剂的角色,决定和影响旅游者旅游动机的产生和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一方面,便利的交通条件提高了区域可进入性,加强了旅游目的地与客源市场及周边其它旅游目的地之间的联系,通过“时空压缩”使旅游活动变得更为便捷、经济,从而提升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使旅游者规模及其停留时间、消费水平得以提高,增加当地旅游企业和旅游从业人员的收入。另一方面,交通不仅是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区域格局演变的驱动力,显著地影响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37]。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可以降低运输成本、吸引投资,加快生产要素的流动,促进其他行业的快速发展。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旅游业的发展及其减贫作用的发挥都有赖于其它产业尤其是零售、餐饮、娱乐等第三产业的支持,交通运输条件通过集聚效应和对其它要素的协同效应,为旅游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从而使旅游减贫作用更为有效地发挥。因此,随着交通便利程度的不断改善,旅游减贫效应逐步增强。 各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EGDP)同贫困水平呈显著相关,这符合区域发展实际,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人们可以面临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劳动收入,贫困水平明显低于经济落后地区;交通便利程度(TRA)与贫困水平呈显著相关,区域可进入性对于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的影响是根本性的,“要想富,先修路”这一普遍认识在中国减贫政策制定和减贫开发实践中都得到充分体现;教育水平(EDU)与贫困水平关系显著,教育水平越高的地区,其贫困水平越低,反之亦然;产业结构(IND)和城市化水平(URB)的提高对贫困减缓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贸易开放度(OPEN)对贫困水平的影响作用显著为负。可能的原因是,贸易开放对贫困减缓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贸易开放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等途径来减缓贫困;另一方面,贸易自由化又会影响到进口竞争部门的生产与就业,同时造成一国或地区经济在外部冲击的影响下变得不稳定,从而不利于贫困减缓。因此,贸易开放对贫困减缓的影响作用具有不确定性。此外,贸易开放对贫困的影响取决于劳动力要素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部门再分配,劳动力要素充分流动的条件下,贸易开放将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和减少贫困,但如果劳动力要素不能充分流动,则贸易开放将拉大收入差距和加深贫困[38]。中国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从而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和贫困程度的加深。于是,理应成为贫困减缓助推剂的贸易开放却成为了加深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2000-2013年中国大陆31个省级单位的面板数据,运用Hansen(1999)[23]提出的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分别以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和交通便利程度为门槛变量,检验了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在上述三个门槛变量的影响下,中国旅游减贫效应存在显著的门槛特征。具体表现为:(1)当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时,中国旅游减贫效应呈现双重门槛特征。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旅游减贫效应并不明显;经济发展水平中等地区,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但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旅游减贫效应重新变为不显著。(2)当旅游资源禀赋为门槛变量时,中国旅游减贫效应呈现三重门槛特征。旅游资源贫瘠地区,旅游减贫效应不显著;旅游资源丰富地区,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随着旅游资源禀赋水平的提高,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积极促进作用呈阶梯状增强趋势。(3)当交通便利程度为门槛变量时,中国旅游减贫效应具有单一门槛特征。在交通便利程度的第一区制内,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具有积极影响;在交通便利程度的第二区制内,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同样具有积极促进作用,但影响系数大幅提高。该结论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关系的认识,对学者们关于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关系这一问题的观点互为矛盾的现象,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同时为一些地区盲目进行旅游减贫开发实践敲响了警钟。 (二)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的建议是:(1)思想观念上,客观认识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正确指导旅游减贫开发实践。在诸多影响因素的作用下,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传统的线性模型研究框架已无法准确地表达这一点,而要用系统和发展的观念更为全面地认识在不同条件和环境下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影响,只有这样,以此为借鉴进行的旅游减贫开发实践才不至于误入歧途。(2)发展路径上,贫困地区应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旅游减贫精准性。中国疆域辽阔,旅游资源分布的空间差异十分明显,旅游资源丰富地区可对之加以有效利用,通过旅游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旅游资源贫瘠地区应考量区位、经济、市场等条件,挖掘或开发创意型旅游资源,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主题公园旅游以及购物旅游等方式提高旅游减贫开发的扶持对象精准性、项目安排精准性和脱贫成效精准性。(3)发展政策上,实现由统一指令性政策向灵活协调性政策转变。旅游减贫作用的发挥需要一定的环境和条件,旅游减贫开发政策的制定不能一刀切,即应考虑在经济落后地区,通过税收和金融服务等优惠政策鼓励发展乡村旅游,使农特产品成为附加值更大的旅游商品,从而实现脱贫致富,还应考虑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旅游业就业层次不高造成的“富民”作用的局限性,根据不同地区的环境和条件制定灵活性政策,最大限度地释放政策红利。此外,经济落后地区“小农本位”的生产观、“固守田园”的乡土观以及传统的思维方式根深蒂固,地方政府应加大教育投入,增强贫困地区居民的发展意识,使旅游减贫从自发走向自觉。(4)发展保障上,政府部门应积极发挥主导作用,为旅游减贫创造有利条件。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旅游发展的重要条件,对旅游减贫作用的发挥具有积极影响,地区发展规划中应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区域交通、土地利用和公共服务体系等规划都应充分考虑旅游业目前和未来的发展需要,各部门要强化协调、指导、服务职能,形成行之有效的管理和服务机制,为旅游业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1]AREF F. Tourism industry for poverty reduction in Iran[J].African Journal of Business Management,2011,5(11):4191-4195. [2]高舜礼.旅游开发扶贫的经验、问题及对策[J].旅游学刊,1997(4):8-10. [3]马忠玉.论旅游开发与消除贫困[J].中国软科学,2001(1):4-8. [4]周歆红.关注旅游扶贫的核心问题[J].旅游学刊,2002(1):17-21. [5]林红.对“旅游扶贫”论的思考——兼议西部旅游开发[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5):49-53. [6]杨霞,刘晓鹰.旅游流量、旅游构成与西部地区贫困减缓[J].旅游学刊,2013(6):47-55. [7]ASHLEY C, BOYD C, GOODWIN H. Pro-poor Tourism: Putting Poverty at the Heart of the Tourism Agenda[R].Natural Resource Perspectives, 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ODI),2000:4-5. [8]WHITE A, SPENCELEY A, WILLIAMS E. UCOTA: The Uganda Community Tourism Association: A Comparison with NACOBTA[R].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e(ODI),2001:5-16. [9]SHAH K, GUPTA V. Tourism, the Poor and Other Stakeholders:Experience in Asia[R].ODI Fair-trade in Tourism Paper, 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ODI),2000:27-31. [10]ASHLEY C, MITCHELL J. Can Tourism Help Reduce Poverty in Africa?[R].ODI Briefing Paper, 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ODI),2006:1-5. [11]MITCHELL J, ASHLEY C. Tourism and Poverty Reduction: Pathways to Prosperity[M].London: Earthscan,2010:120-126. [12]REEDER R J, BROWN D M. Recreation, Tourism, and Rural Well-being[D].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2005:14-18. [13]赵磊.旅游发展能否减小城乡收入差距?——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旅游学刊,2011(12):15-25. [14]LEWIS D J, HUNT G L, Plantinga A J. Does Public Lands Policy Affect Local Wage Growth?[J].Growth and Change,2003,34(1):64-86. [15]WALPOLE M J, GOODWIN H J. Local Economic Impacts of Dragon Tourism in Indonesia[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0,27(3):559-576. [16]TAYLOR J E. Tourism to the Cook Islands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J].The Cornell Hotel and Restaurant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2001,42(2):70-81. [17]WATTANAKULJARUS A, COXHEAD I. Is Tourism-based Development Good for the Poor?: A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for Thailand[J].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2008,30(6):929-955. [18]DELLER S. Rural Poverty, Tourism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10,37(1):180-205. [19]MUCHAPONDWA E, STAGE J.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Tourism in Botswana, Namibia and South Africa: Is Poverty Subsiding?[J].Natural Resources Forum,2013,37(2):80-89. [20]THOMAS F. Addressing the Measurement of Tourism in Terms of Poverty Reduction: Tourism Value Chain Analysis in Lao PDR and Mali[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2014,16(4):368-376. [21]SCHEYVENS R. Tourism and Poverty[M].London: Routledge,2011:73. [22]BLAKE A, ARBACHE J S. Tourism and Poverty Relief[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8,35(1):107-126. [23]HANSEN B E. 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 Estimation, Testing, and Inference[J].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9,93(2):345-368. [24]SEN A. Development As Freedom[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87-92. [25]郭熙保,罗知.贸易自由化、经济增长与减轻贫困——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经验研究[J].管理世界,2008(2):15-24. [26]张冰,冉光和.金融发展视角下外商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分析[J].管理世界,2013(12):176-177. [27]ADAMOU A, CLERIDES S. Prospects and Limits of Tourism-led Growth: The International Evidence[J].Review of Economic Analysis,2010,2(3):287-303. [28]FAYISSA B, NSIAH C, TADESSE B. Research Note: Tourism and Economic Growth in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Further Empirical Evidence[J].Tourism Economics,2011,17(6):1365-1373. [29]郝俊卿,曹明明.基于时空尺度下陕西省旅游经济差异及形成机制研究[J].旅游科学,2009(6):35-39. [30]敖荣军,韦燕生.中国区域旅游发展差异影响因素研究——来自1990~2003年的经验数据检验[J].财经研究,2006(3):32-43. [31]左冰.中国旅游经济增长因素及其贡献度分析[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1(10):82-90. [32]王淑新,何元庆,王学定.中国旅游经济的区域发展特征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1(4):89-96. [33]赵东喜.中国省际入境旅游发展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分省面板数据分析[J].旅游学刊,2008(12):41-45. [34]ENGLE R F, HENDRY D F, RICHARD J F. Exogeneity[J].Econometrica,1983,51(2):277-304. [35]JOHANSEN S. Testing Weak Exogeneity and the Order of Cointegration in UK Money Demand Data[J].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1992,14(3):313-334. [36]J.M.伍德里奇.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M].费剑平,林相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468-469. [37]殷平.高速铁路与区域旅游新格局构建——以郑西高铁为例[J].旅游学刊,2012(12):47-53. [38]TOPALOVA P. Factor Immobility and Regional Impact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Evidence on Poverty from India[J].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2010,2(4):1-41. (责任编辑傅凌燕) Analysis on the Threshold Effe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levant Empirical Test:Based on the Province Panel Data in China GUO Lu-fang, LI Ru-you (SchoolofTourismandUrbanManagement,ZhejiangGongsh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18,China) Key words:effe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poverty alleviation; threshold effect; panel threshold regression model Abstract: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13, this paper established the panel threshold regression model in order to test the threshold effect of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on poverty alleviation. Estimation result showed that there was dual threshold effe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poverty alleviation when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was used for the threshold variable. However, with tourism resource and traffic condition for the threshold variable, the nonlinear relation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presented a triple threshold effect and single threshold effect respectively. As the threshold variables changed in different stages, tourism development did not always contribute to poverty alleviation. Finally, some advices were put forward in terms of ideological concept, development path, policy, and safeguard measures on poverty alleviation by tourism development. 收稿日期:2015-1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我国旅游业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机制与政策研究”(14CGL023) 作者简介:郭鲁芳,女,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旅游管理与休闲经济研究;李如友,男,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旅游经济与管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F5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54(2016)06-008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