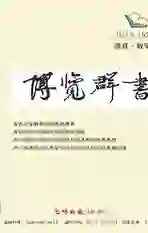《聊斋志异》中的女子报恩现象
2016-07-04高亚萍
高亚萍
摘 要:蒲松龄吸收了儒家文化中的德报思想和佛教的果报观念,创作出了一批重报恩,有情义的女子形象。蒲松龄对女子报恩的描摹,一方面,反映了他对当世时风的不满,希望通过报恩故事能警醒世人;另一方面,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男女交往上升到精神层面,实质上反映了蒲松龄对知己的渴求。
关键词:《聊斋志异》;女子报恩;教化;知己之托
《聊斋志异》是古代文言小说的一座丰碑,在近五百个故事中,塑造了丰富多样的人物形象,而在这人物画廊中,作者创作了一批知恩图报,有情有义的女子形象,本文试从女子以婚姻报恩的角度,分析《聊斋志异》中女子报恩现象,进而探讨恩报主题下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一、蒲松龄对报恩思想的接受
因果报应是佛教的根本教义,佛教认为人死之后,会根据生前的善恶分别进入六道,而人的三生也有因果联系。在《大般涅槃经·僑陈如品》中就有具体的论述:“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三世因果,循环不失。”蒲松龄生长在佛教滋养的环境中,很容易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在《聊斋志异·自志》中记载了蒲松龄出生时候的情形“松悬弧时,先大人梦一病瘠瞿昙,偏袒入室,药膏如钱,圆粘乳际,寤而松生,果符墨志.”(《自志》)临生托梦的故事在古代很常见,但大多是托梦于圣贤或预示才华的事物,蒲松龄却是病僧投生,受佛教的影响不言而喻。此外,蒲松龄生活的淄川附近就有大小神庙十几个,附近的村民集资修庙,供奉佛祖,在这样一个佛教文化浓郁的环境中,自然会受到佛教因果报应思想的熏陶,因而在《聊斋志异》中,不仅有地狱鬼神的神秘,也有佛教果报思想渗透其中。
儒家文化强调“来而不往非礼也”,这是谦谦君子在道德上的自律。孔子为了维护统治秩序而提倡“以德报德”,并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影响着民间,成为封建社会君臣、父子、夫妻、朋友间的一种伦理原则。 蒲松龄是封建末世的落魄文人,他的一生都在做两件事,科举考试和坐倌教学。“惨淡经营,冀博一第,而终困于场屋,至五十余尚希进取”(蒲箬《柳泉公行述》)从十九岁应童子试,到71岁按例补为贡生,蒲松龄一生都在忙于同科举考试作斗争,在考试与落榜中不断挣扎,却无力改变一个下层寒士的悲惨命运。经济上的窘迫使得蒲松龄不得不找个工作应付全家人的生计,于是,设帐坐倌便成了蒲松龄维持生计的途径。无论是科举考试,还是坐倌都与儒家文化有着化不开的浓密关系。蒲松龄强烈的儒家道德伦理观念正得益于此。《聊斋志异》中许多篇目都极力赞扬“知恩图报”的美德。
二、《聊斋志异》女子报恩故事的不同类型
在各种人际关系中,蒲松龄强调各种人物关系之间的恩报关系,并积极将其融入婚姻爱情关系中,而女子作为封建社会传统中的弱势群体,因而常常作为受恩一方。《聊斋志异》中有关报恩的篇目一共有47篇,其中关于女子报恩的有27篇,具体情形如下表:
由上图可见,《聊斋志异》收录的女子报恩故事,从报恩的原因来分,可分为救助类、情义类和知己类;从报恩的主体来看,可细分为,人类报恩、精怪报恩、鬼神报恩;从报恩的方式来看,可分为婚姻报恩和救助报恩。《聊斋志异》中的女子报恩,大多是以男性的救助或者痴情守候开始,以婚姻关系结束。本文主要从报恩酬情的原因对《聊斋志异》中女子报恩现象作进一步分析。
首先,救助型的报恩故事在《聊斋志异》的女子恩报故事中占了很大比例,这一类故事往往不是单独的救助,常常伴随着男子的痴情守候,和男女间的知己之交。《聂小倩》《青凤》《连锁》《侠女》《花姑子》《荷花三娘子》《神女》等都属此类。在这一类故事中,男性在女子或其亲人遭遇困难或者危险时,进行了有意或无意的帮助,结局大多是女子以身相许来报答恩情。《聂小倩》中宁采臣在小倩遭遇妖物胁迫时,帮助她迁骨改葬,小倩主动要求做其妾婢,侍奉公婆;《青凤》中耿生从凶狠大狗口下救下无路可逃的青凤,青凤遂以身相许;《侠女》篇中米生帮助侠女奉养年老的母亲,侠女感其恩情,为其诞下子嗣,延续香火;《小翠》中的狐妇无意得到王太常的庇护而免遭雷霆之劫,将自己的女儿小翠嫁给王太常的傻儿子元丰,并多次巧妙地帮助王家躲过劫难。
其次是痴情类的报恩故事。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记中言:“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可谓一日倾心,终身不改。在《聊斋志异》中亦是如此,爱情不仅可以超越人鬼的边界,亦能穿越生死的界限,《阿宝》、《香玉》、《连锁》、《鲁公女》等故事中的男男女女出生入死皆为了一个“情”字。《阿宝》一篇中,孙子楚爱上了美丽的少女阿宝,为了能得到心上人,不惜折断自己的枝指,飘飘然魂随阿宝;后又魂附鹦鹉,追随阿宝,只为能与阿宝朝夕相处,阿宝感其深情,发誓说“君能复为人,当誓死相从”(《聊斋志异·阿宝》),孙子楚这才回魂。当孙子楚病故,阿宝亦准备殉情而去,其节义感动地狱阎王,于是双双还魂。但明伦评论说:“如此情种,自宜以死报之”(《聊斋志异新评》)。
再次,知己类的报恩故事是救助类和痴情类的升华,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和震撼人心的力量。《乔娜》、《宦娘》、《乔女》、《黄英》、《香玉》等均写书生与狐鬼神灵神交的故事,其关系甚至超越了爱情和婚姻,蒲松龄对两性之间的这种知己之情极为赞赏。在《乔娜》一篇末,蒲松龄甚至说“余于孔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也。观其容可以忘饥,听其声可以解颐。”(《乔娜》)《宦娘》中,宦娘生前“少喜琴筝”,听了温如春弹琴后,便心驰神往,暗中撮合温如春和良工的婚姻。虽然故事中宦娘与温如春的交集不多,但以琴知音,正是一段高山流水的佳话。《乔女》中的乔女不同与《聊斋志异》中的其他美丽女子,不仅又黑又丑,还豁着鼻子,瘸着腿,但正是这样丑陋的寡妇却得到孟生的倾慕,孟生死后,乔女为了报答他的知己之恩,不仅帮他夺回家业,还抚养其子长大成人,却不沾其家业分毫。蒲松龄评价说“知己之感,许之以身,此烈男子之所为也。彼女子何知,而奇伟如是?”(《乔女》)赞赏之情,溢于言表。
三、女子报恩故事的文化内涵
《聊斋志异》是一部“孤愤之书”,是蒲松龄内心“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的呼喊。作者并不仅仅是为了创作一部流芳百世的小说,更重要的是为了抒怀言志,表达怀才不遇的愤懑,世无知己的无奈,以及对现实世界的不满。
蒲松龄对知恩图报的大力倡导,源于当时世风日下的现实。蒲松龄希望通过《聊斋志异》中的故事来警醒世人,恢复淳朴古风。“盖以振励斯文,事关名教,表彰盛迹,责在儒生”蒲松龄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虽然他的兼济天下的愿望因不断落榜而消逝,但他内心仍然有一个儒生扶世的心愿,他把他的这种愿望沉浸在他的诗中,融进他的文中,寄托在小说中。这既是一部“孤愤”之书,也是一部醒世之作。蒲松龄的朋友也证实了他在这方面的意愿,唐梦赉为其做的序言中说“今观留仙所著,其论断大义,皆本于赏善罚淫与安义命之旨,足以开物而成务,正如杨云法言,桓谭谓其必传矣。”充分肯定其教化作用。但明伦在点评时也说“……取是书随笔加点,载以臆说,置行筐中。为友人王菱堂,钱辰田两侍读,许信臣、朱桐轩两学使见而许之,谓不独揭其根抵,于人心风化,实有裨益。”这说明《聊斋志异》实际上也起到了道德开化的作用。
花妖狐魅的虚幻世界,成为蒲松龄消除心中块垒的一种方式,托妖写志,以狐类人,似在谈鬼,实则说人。通过鬼狐妖怪的世界来描摹蒲松龄的理想国,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创造一个恩怨分明,赏罚有道的世界。蒲松龄常常感叹在道德上人不如兽,人不如物,“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此非定论也。蒙恩衔结,至于没齿,则人有惭于禽兽者矣。”( 《花姑子》)“一狐也,以无心之德,而犹思所报; 而身受再造之福者,顾失声于破甑,何其鄙哉!”( 《小翠》)通过有情有义之鬼怪与无情无义之人的鲜明对比,衬托出世风日下的现实,这是一个有良知的儒生发出的呐喊。一方面他希望通过“知恩图报”典型来挽救颓风,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一个底层知识分子的无奈。
知己之情是中国传统文人一生的追求,“士为知己者死”不仅体现了传统士人的一种价值观,更是一种精神寄托。蒲松龄科场上屡屡失败,生活上也是潦倒落魄。物质与精神上双重失意,使得蒲松龄更加渴求一个能在心灵上给予其慰藉的知己,对知己之情的追求愈加强烈而理想化。蒲松龄在悼念故友毕际有曾写诗曰“此生所恨无知己,纵不成名未足哀”(《偶感》),足见其对知己的渴求。
蒲松龄把对知己的渴诉诸笔端,在《聊斋志异》中创作了一批娇俏可爱,知书达理,重恩图报的女性形象,那些从蒲松龄笔尖幻化出来的窈窕女子,或是感于男子的情深义重而托付终身,或与书生赋诗填词,往来唱和,或与文人秉烛夜读,解除其青灯黄卷的孤寂。这些曼妙佳人不以世俗的价值观来评判,她们看中的是精神上的交流,是男子内在的才华与品性。知己之爱使得那些在生活中百无一用的书生们显现出独特的魅力,他们“腹有诗书气自华”,其自我价值得到充分肯定。在这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婚姻,是一种双向的精神交流,男女不仅彼此爱慕,还相互欣赏和理解,肯定彼此的人生价值,这种婚姻关系摆脱了传统婚姻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限制,上升到精神层面的结合,这正是蒲松龄内心所向往的理想世界,一个理解他,肯定他的乌托邦世界。
清代社会主流的结合方式是聘娶婚,也是男婚女嫁的最主要的方式,封建家长在男女婚姻上拥有绝对的权威,只有在父母同意,媒人介绍的情况下,才能成为正式有效的婚姻。明清律令对于在婚姻中的妻子有着严酷的规定:“若妻背夫在逃者, 杖一百, 从夫价卖;因而改嫁者绞”。贞洁观成为女性价值观中最重要的一环,是封建社会给女性戴上的沉重的枷锁。但是在这种世俗环境中,《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却呈现出一种别样的风貌,为了冲破封建礼教的桎梏,蒲松龄笔下的女性在恩报关系中大多超越了生死边界,超越了物种的限制。女性为了报恩,往往是两性关系中更为主动的一方,常常无媒自嫁,大胆追求爱情生活,将“君子好逑”变成“淑女好逑”。爱情成为婚姻关系的前提和基础,这是蒲松龄婚姻观的进步。
参考文献:
[1]罢元谶译,宋先伟主编.大般涅盘经(卷四十).[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359.
[2]汤显祖.牡丹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1.
[3] 盛伟.蒲松龄全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1104.
[4] 朱一玄编.《聊斋志异》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474.
[5]朱一玄编.《聊斋志异》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321.
[6]【清】蒲松龄.聊斋志异.[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0.10.
[7] 【清】蒲松龄.蒲松龄全集[ M]. 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8:1307.
[8] 马瑞芳.聊斋志异创作论.[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
[9] 马瑞芳.鬼神狐妖的世界——— 聊斋志异人物论.[ M] .北京:中华书局, 2002.
[10] 叶春雷.论《聊斋志异》报恩型作品的两大范式及其文化内涵.[ D].华中师范大学.2004.
[11] 申瑞妮.《聊斋志异》“鬼报型”作品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09.
[12] 臧国书、任秀芹.论蒲松龄对传统婚恋观的继承与创新——以《聊斋志异》中女性形象的类化与解读为例.[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