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小学到剑桥大学
2016-06-28苗千
苗千
在30多岁的年纪回忆自己当年的小学教育,这份记忆恐怕已经不大值得信赖了吧。但是在20多年前小学里的一些场景、对话和心情,在我后来的生活中,仍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不断涌现出来,与当时所处的情景融合起来。从一所学校到另一所学校,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在我30多年的生命里,20多年在学校里度过,时间不断地向前,接受的教育程度逐渐攀升,但对于小学时的记忆和影响却始终不曾减弱,我意识到这已经成为我人生的底色之一。在升学考试时,在毕业答辩时,在中国大学的课堂上,在剑桥大学的实验室里——小学教育,尤其是小学教师,对我的影响始终挥之不去。
我开始把自己接受的小学教育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或是把自己与身边的同学进行比较。不同的城市之间,中英之间,在人启蒙之初的教育方式有何异同?基础教育又是怎样在塑造一个社会的文化,甚至是一个国家的形象?这样的反思和比较,可能正是我在多年之后努力寻找一份可能已经被扭曲和修饰过的回忆,并把它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意义。
上课第一天,有关坐姿:背手而坐
我出生在1月份,上小学一年级时还只有6岁半,尚未达到标准的入学年龄,为此当时我的父母还感到有些幸运,家里小我3个月的堂妹只能再等上一年才能入学,大我3岁半的表哥则高出我两级。入学那一天似乎是在闹哄哄中开始的,父母一起送我到离家并不远的那所小学的操场上,之后呢?我妈妈像是哭了,看着我依依不舍——不对,这是我17岁时父母送我去西安上学时的情景;我妈妈似乎是很高兴,在电话里说她肯定高兴得一晚上都睡不着了——也不对,这是我29岁那年通过博士答辩后给家里打电话时妈妈说的话。我6岁半时的那一天发生了什么呢?耳边又传来爸爸略显气急败坏的一声喊叫:“快点跑呀,跟上他们!”
即将进入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们几乎站满了学校不大的黄土操场,每个班的班主任都出来认领自己班里的学生,然后把小孩子们排成两排,迈向他们人生中的第一间教室。爸爸叫我快点跑,现在想来是希望我能跑到队伍的前排,以便在稍后排座位的时候能够尽量坐到前排,这样老师就能够给予我足够的“重视”,课堂提问或许能多叫到我,至于教室的后排,在他们的印象里大概是留给无可救药的后进生们的。
我不大情愿地跑了两步,跟上我人生中的第一班同学向教室走去——随后我被分配到教室的第四排,在这个60多人要坐上十几排的拥挤的班级里算是前排座位了,大概属于会被老师重视的区域。启蒙课程要到排了座次之后一天才正式开始,班主任是一位姓杨的女老师,在我印象里她是一位老太太,但现在想来她当时也只有四五十岁而已,我父母打听了这位老师在学校里的名声,听说她对学生很严——这是个叫人放心的好事。语文、数学、自然、音乐、美术、体育,还有课外活动课,这就是我在接下来的5年里要接受的全部教育,但是每门课的重要性显然有所不同——这样对于课程的划分在我后来的教育经历中成了常态。在小学里,语文、数学和自然是主课,学生在心里自然对每一门课程有权重。在以后的学习中,不被高考、考研涉及的学科都只是副科而已,只有体育和艺术特长生才去专攻那类课程,而我也几乎没有从课堂上得到过涉及美术和音乐的教育。这种教育的缺憾,现在已经转化为人生的遗憾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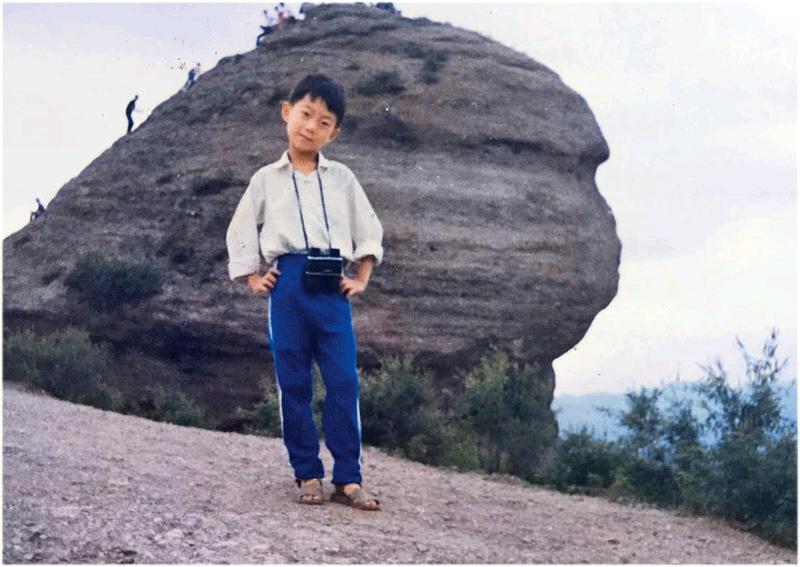
小学教室里的灯光不算明亮,第一天上学时我数过头顶上的日光灯管,一共有六个,在教室里三排两列地排列着,到了下午快放学时教室里会显得有些昏暗。这并不让我感到不舒服,一种更大的不适已经伴随了我一整天。从早上的第一节课开始,小学生们就被要求把双手背在身后听课,腰板要挺直。双手反剪背在身后听一整天课(维持这个动作的原因在于如果有学生敢于在老师讲课期间做小动作,老师可以及时地发现并喝止),对于小孩子来说并不是一件能容易办到的事情。以我在幼儿园时不多的课堂经验来说,坐在教室里听课时双手应该平放在膝盖上,但我身边的同学们坐在教室里都已经自动把手背在身后,整齐中显出了纪律的威严。后来我明白,这是因为我的同学们大多上过一年至两年的学前班(当时也叫育红班),这种针对五六岁学前儿童开设的学前课堂已经开始按照小学的标准进行管理,参加过学前班的同学自然已经提前适应了小学课堂。
这样的要求没有人觉得不妥。小孩子爱动,老师更要严格管理,但这种生硬的听讲姿势伴随着身体的僵硬感觉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国外的小学生是怎样听课的?直到我来到英国,和我的英国同学交流小学生活——英国的同学告诉我,在他们的小学教室里会有一个“den”(小窝),小学生在上课时如果情绪不好,就会自己跑进den里面休息一觉,里面还会有一些“fancy dress”(奇装异服),学生们大可穿着这些看上去夸张的衣服来上课,每周五学生们还可以带着自己心爱的玩具上学,英国同学还意犹未尽地对我回忆起小学时在老师腿上爬来爬去的课堂生活……这样的小学教育,不仅是我无法经历,甚至已经是我无法想象的了。
零分,哇哇大哭
我因为不了解小学课堂而给自己带来的麻烦远不止于不习惯双手背在身后听课,我远想不到自己6年多的人生中最大的挫败正在入学第一天的末尾等着我。下午第二节课的下课铃已经打响,我已经做好准备收拾书包回家,但此时班主任老师并未如我所愿地宣布下课,而是说出了另外两个字:“考试。”我的同学们又一次显示出了让我惊讶的适应能力,他们迅速从书包里掏出一个作业本和铅笔用来考试,而当我掏出书包,找到作业本时,杨老师已经开始念出了考题——考试内容并不复杂,考察的是当天的语文教学内容,也是当时我头脑里仅有的知识,四个拼音字母:B、P、M,还有F。默写这四个刚刚学过的拼音字母对我来说挑战不大,虽然拿出作业本的速度稍慢了一些,我仍然大约听到了考试内容,我在每行有四条横向虚线的作业本上用铅笔写下这四个拼音字母,然后把这一页纸撕下来,交给老师。
老师当堂判卷。大约10分钟之后,我得到了人生第一次考试的成绩,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零分。原因在于老师在考这四个字母时并未按照当时教学的顺序,而是把它打乱了。我因为那十几秒的延迟,想当然地按照上课时学习的顺序写下这四个字母。老师对全班同学宣布我抄袭,并且当堂给了我零分。在我23年的学生生涯完全结束之后,我已经可以坦白这20多年里我曾经抄袭过同学的作业,也曾经在考试中作弊,我为此并不感到庆幸或光荣,却也没有太多的自责或反省,我只是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把它当成学生生活中普通的一部分而已。但是在小学生活的第一天,我也可以以同样的坦白说,我当时尚且不知道抄袭的含义,我完全掌握了那四个拼音字母。如果我的老师能够稍有耐心查明情况,而不是急着给予我人生中的第一个零分,或许就不至于在一个小孩子心里留下难以磨灭的恶劣记忆,让我对于老师和考试报以长久的不信任。
之后的情节是我妈妈后来告诉我的。走出校门,妈妈等在学校门口接我下学,和我同行的一个同学见到,抢在我之前向我妈妈报告:“他零分!”我随即哇的一声大哭起来,现在当然已经记不起这大哭究竟是委屈,是羞耻,是胆怯,还是三者都有。学生时代第一天的经历让我永生难忘,时至今日,我仍然愿意把我人生的第一个零分看作是有某种带有启示性的信号。我后来升入中学、大学,出国留学直至读完所有的学位,心里始终带有某种委屈和不甘,考试对我来说总是意味着不公正,我从未有过令自己感到酣畅淋漓的考试,我的成绩也从未成为父母可以用来向邻居炫耀的谈资。这种对于考试的恐惧、对于老师的不信任贯穿了我的学生生涯,我不能理解以考试为乐的同学,更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可以和自己的老师成为朋友——如同老鼠和猫之间永远不可能存在友谊一样。在大学的课堂上,从未和自己的老师有过什么交流;在剑桥大学的实验室里,和导师的讨论过程中,我始终恭谨严肃,轻易不发一言,接下导师布置的任务就知道埋头苦干。我认为不多说话、不多发表自己的意见是“成熟”的表现,同时又希望导师能够“重视”自己,所以从不与导师相左。我追逐着学位,却又希望可以早日摆脱师生关系给我带来的局促和不安。
算术竞赛,看谁更快
小学生涯开始了。除了在开学第一天发生了意外之外,我的小学生活还算顺利。班主任老师严格的管教之下,教室里的秩序始终如军队一般井然有序,学生们在课堂上没有丝毫放肆的举动——这被认为是班主任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学生管教有方的证据,也使得学生们在之后的升学过程中可以毫无困难地接受军训。语文之外,数学和自然算是另外两门主课,在学校里已经可以听到“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样的顺口溜。从老师到学生,美术、音乐和体育这样的课程并不太重视,更谈不上有英国小学生要学习的“主课”之一:人文教育(Humanities)。这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也是无奈之举,学校操场不大,各年级的学生课间时在操场上疯跑已经足够拥挤,学校里当然不可能有塑胶跑道或是游泳池这样的奢侈品,正如没有足够的英语老师而无法开设英语课——更不可能组织学生像我未来的英国同学一样在学校的运动场上练习曲棍球,美术课上的蜡笔和水彩笔已经是很多学生家长一笔不小的开销。
小学生们被教师和家长精心地教育着,他们经常被明示或暗示,学好“文化”才是最重要的事,一个学生如果把过多的经历花在副科上,那他学习主课时就难免会分心,这当然是错误的。而一个学生如果过于热衷体育项目,那往往是最值得家长们担心的信号,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四肢发达”四个字后面毫无疑问都会跟随着“头脑简单”这句判断语句。数学被认为是和语文同等重要的科目,学习数学的重中之重则是速算。一张张油印的,或使用复写纸印出来的速算考题被学生们带回家里(有时学生家长们也要负责抄写这些速算考题),这是属于学生和学生家长们共同的课后作业,要学生在家长的监督和计时下完成各种速算题,从10以内的加减法,逐渐发展到100之内的加减乘除,完成之后,学生家长负责在作业上签字并且写下完成时间。这当然是一个全国性的风潮,当年培养一群孩子进行快速心算训练的史丰收可以在电视上率领学徒们进行表演,他们是真正的明星。
后来在我以物理学为专业的博士训练中有时也需要进行各种计算,做计算时我头脑里有时竟会回想起小学时在油印纸上进行速算的场景——同样是坐在桌子前面对数字,对人的训练和要求却截然不同:公式推导、数学演算是一种智力劳动,而简单的数字计算则可以用计算器来完成。数学能力和数学思想的培养实际上与小学生做速算练习那种类似于赛跑的竞技训练几乎没有任何关系,速算锻炼的是人的反应速度,与数学学习并无真正的联系。小孩子为家里的客人奉上水果,心里是在等待客人夸赞一句“小朋友真懂礼貌”——我的小学把数学学习替代为竞技项目的训练,正如把礼节教育转变为一种孔融让梨式的道德表演。
中国式师生关系,好学生开始成型
深冬时节,北方的早晨天还没完全变亮,一群群准备开始早自习的小学生已经汇集在校门口,除了背后的书包外,十有八九学生们手里还拿着一根不到1米长的圆筒,外面被报纸包裹着。有人一边走一边挥舞,也有朋友遇见,彼此拿这圆筒做金箍棒打起来。我手里也有一根,遇见同学,彼此心照不宣。“你拿的是什么呀?”总有一个人忍不住,先开口问道。“我拿的是个大炮仗,你呢?”“我拿的也是个大炮仗,哈哈哈!”——我们每个人手里拿的都是一本要送给班主任的新一年的挂历,前一晚被家长卷好后再用不起眼的报纸包上,即使被同学看到也不会显得过于有心计,但是家长们没有想到的是,几百人同时拿着被报纸包裹的挂历出现在校园里,便成为一个奇异的盛景。没有人提“挂历”这两个字,更不会有人问它的用途,它们被立在课桌旁,然后会在某节课后被默默地送给班主任,懂事的学生会说上一句“老师新年快乐”,更多的学生则是红着脸一言不发——这样一群小学生,和他们的祖国和文化一样过于早熟,他们在心里明白给班主任送挂历的意义,更懂得这不能和同学们直言的原因,而当送挂历成为所有学生都去履行的一套形式,这份礼物所承载的意义却又烟消云散了——没有人因为给班主任送了一个挂历而被照顾,似乎也没有人因为不给班主任送挂历而被忽视。但是在20多年里,这样奇异的场景总是在我的头脑里挥之不去,如同一个电影的开端,我甚至开始想象它的后续,老师收到几十个新年挂历,堆积在教研室里,只能在每天下班时辛勤地拿走几个,要十几天的时间才把这些挂历全都堆放到家里……
尽量讨好老师和领导,希望能够获得他们的欢心和重视,这样的观念从小就融入到了我的血液里。直到我出国,作为一个习惯,我也曾在机场寻觅,最后送给我的导师一个京剧脸谱作为礼物,导师有些局促地表示感谢后收下了。尽管如此,和系里秘书每学期一次的谈话却让我开始重新思考我对于师生关系的认识,秘书向我询问我和导师之间的联系:每周见几次、总共多长时间,我对于自己的导师和研究项目是否满意,有无任何其他不满的情况想要向系里汇报,是否考虑过要换导师……直到那时我终于意识到,师生关系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关系,而应该是一种受到监督的相互作用。
进入到小学三年级,班里换了另外一批老师,班主任依旧教语文。我大概算是班里的好学生,上课不顶嘴不插话,下课不打架,听讲时坐得笔直双手背在身后已经是自然而然天经地义的动作,大概能背下上百首的唐诗,100以内的加减乘除算得飞快,我写出来的拼音字母在四线本上从不越线,我写出来的方块字横平竖直简直和真的方块一模一样,三年级可以用钢笔了。
新班主任是一个心火旺盛的中年妇女,在学校里的名声比前一任班主任更加严厉,在课堂上羞辱谩骂起同学来也是全然的肆无忌惮。学生在课堂上背不出唐诗,就一直站着背下去,直到背出来为止,否则全班都别想下课;她看一个以“倩”为名的女同学不顺眼,又可以直抒胸臆:“你知道你为什么叫‘倩吗?你就是欠收拾!”她兴之所至也会在下课前给我们讲起她和我们的数学教师在教研室里对骂的场景,描述得生动又详细,让我在20多年之后仍然对那个场景如同亲身经历过一样熟悉。
这样一位严格的老师,表现又是如此火爆,现在想起来她大概对于自己只是在一个小城市里做小学教师心中有不平。每年市里的“人大”会议班主任总会参加,因而会缺席几天教学工作(这几天里学生们的心情可以想象),她也会英语,有时她会在黑板上写下几个英语单词,然后回头问我们:“这是英语,倒装句!你们懂吗?”说完后班主任的脸上又会流露出一种怅然若失的表情。我当然不懂,我当时还没上过英语课,一个单词也不认识,当时距离我后来参加GRE考试还有10年的时间。
好学生的使命:坏消息使者
小学的同班同学们大多住在同一个小区,往来方便,老师也会利用这种便利。对于一些需要家长签字的作业或是成绩单,班主任不放心一些学生瞒过自己的家长自己伪造签字,她别出心裁,命一个听话的学生充当老师的信使为同学家长送去成绩单,我便是她的信使之一。我主要负责为两个同学的家长传送一条条“自己儿子又考砸了”的噩耗。我送快递可以说是举手之劳,但是每一次的送信经历都让我难忘。
有一个同学考试成绩经常不理想,我仍记得他在小学二年级的数学课上,回答不出“1+1等于几”这个问题而被数学老师罚站了一整节课的情景。我去他家里送成绩单要家长签字的次数也就特别多,每次过去敲门,会是一个成年长者开门,我稍微介绍两句递上成绩单,对方接了谢过便关上门,从不会邀请我进去坐,而另一个同学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也经常去他家里,这样的关系让我去他家送成绩单时有了格外的为难。
因为我的任务是公开的,不得不充当老师的信使,我和那同学放了学会一起去他家,往往一路无话,走进家门后气氛便更加凝重,我们共同等待着他爸爸回家那一刻。有时要等半个小时,有时要等一两个小时,有时我们到时他爸爸已经在家,无论是哪种情况,我总要掏出在书包里装着的考卷递过去:“叔叔,这是我们班主任让我给你的,让你签字……”并不需要太过仔细地阅读那张考卷,只需要看一眼考卷上最醒目的猩红数字,我同学的爸爸便可以立时明白一切。在几秒钟之内,他会直接一个巴掌向我的同学抽过去,伴以同学的惨叫,之后便是在他家里长达十几分钟的追打。那段时间里没有人注意我,我也不好无声地不告而别,只能站在原地盯着某一个点翻来覆去地看。20多年之后,同学爸爸的样子我早就忘记了,同学的模样在我心里也变得恍惚,但是我始终记得他家里桌上摆的那盆粉红色的珊瑚很好看。那是真正的珊瑚,不是仿制品,同学爸爸在高兴的时候曾得意地对我介绍过的。
这样一遍遍充当老师的信使,使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老师信任的“心腹”,也让我和同学们之间的友谊蒙上阴影,我成为不时给自己的好朋友带去一顿毒打的那个人,我们之间的友谊既扭曲又沉重。这种状况延续了几年,我从未感觉过有任何的不妥,也从没有过一次,为了我的朋友能免去一顿毒打而欺骗老师,顺从老师被认为是好学生的标志之一。直到我大学毕业之后,才明白一个人的成绩理应属于隐私,老师无权命令我做她的信使,而不时毒打自己孩子的家长也早就触犯了法律。
对于强权的恐惧和顺从,是否天然地存在于我们的基因之中?而这种基因又是怎么样一代一代延续下来的呢?在我们的启蒙阶段,何曾有一个人教导我们,珍视自己的权利,勇敢地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尊严,而不是过早地学会面对长者、面对权威时,呈现出羔羊般的顺从?当自己或是同伴遇到困难或是不公平的对待,挺身而出对抗强权的勇气从何而来?在一种过度早熟的文明中,是否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位导师鼓励他的学生?对于教师的顺从,让我和同学之间的友谊过早掺杂进复杂的情感。
围棋、少年之间友谊,惩罚以及做好事
少年人之间的友谊真是奇怪,尽管我对于我的同学经常可以等同于厄运,但我们之间依然是朋友,我们仍然会在放学后一起回家,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在心里对我有没有恨。这个同学虽然学习不大用心,考试成绩不算太好,却是我在小学时代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之一,下围棋是全校冠军。
我们同在校内围棋班里学习围棋。这是学校推荐同时受到老师和家长们认可的课后学习项目,一位围棋教师自荐来学校开班,报名的学生在下午课后去一间教室里上围棋课。学习围棋安全、文雅,开发智力,既便宜又安全。学校里报了名的学生组成了一个60人左右的班级。围棋老师的讲解现在自然早都忘记了,只记得那个留着寸头的中年男老师在第一堂课上讲述他为什么在一个以西装为时髦的年代坚持穿中山装。我当时对于围棋的兴趣并不浓厚,只当是游戏,又嫌麻烦,从来没用心背过那些繁琐的围棋定式。后来学校里举办全校围棋比赛,我和围棋班里的同学依次对弈进行循环赛,最后获得第四名,我那位时常因为考试成绩差或不做作业被父亲痛打的朋友却轻松获得了冠军。有时在课外活动课上我们俩对弈,他分明没有太大的兴趣,一边和我下棋,手里总还要拿着本《乱马1/2》或是《北斗神拳》之类的漫画边下边看,仍可以轻松赢我。记得他在赢棋之后看我的眼神里有些轻蔑,大概这就是他对我这个还算得上朋友却反复给他带来厄运的人的唯一反抗了。
因为在学校围棋比赛里取得了不错的名次,我和另外几个同学一起被学校送到市体校学围棋,但我不记得体校的那两位围棋老师为我们上过哪怕一堂课,每个周日的下午我背着围棋和棋盘去体校,两位老师只是在那里安静地下棋,一群孩子在那里疯跑而已,直到有一天我妈妈去体校探班,看到我手拿扫帚在教室内外狂奔,于是把我领回家,从此再没去过。围棋可以放弃,学习绝不能疏忽。我是老师的信使,负责给其他人带去厄运,但我自己其实也无法幸免。
三年级的一天,我没写班主任前一晚留的作业,不巧又偏偏被查到,换来的是残酷的惩罚——所有没写作业的学生排成一个单排,大约有八九个人的样子,每个人手里拿着自己的语文书,逐个上前,让班主任依次横着撕掉,其他同学则坐在座位上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盛况。看到班主任面目狰狞地撕掉前排同学的课本固然可怕,但是站在队伍中手拿着一学期只有一本的语文书等着被撕掉则是更大的痛苦和恐惧,恐惧变成了事实,终于轮到我的语文书也被拦腰撕掉,我默默地收拾起书本的上下两截。整个过程井然有序,教室很安静。我拿着被撕断的语文书回家自然换来我妈妈的咒骂,她一边用胶布帮我把书重新粘成一本,一边骂我为什么不写作业,换来这样的惩罚——这样的小学记忆从此不再消退,学校和老师是带来恐惧的绝望的地方。让小学生过早地体会到恐惧和绝望,接触到社会现实,或许是教育的目的之一,但学生心里最活泼、最有创造力的一部分,也从此被扼杀了。当我听到英国同学对我讲述他们的小学老师坐在课桌上和学生嘻嘻哈哈,鼓励和称赞学生,我一方面会自然而然地觉得英国的小学老师太不正经,另一方面又会在心里感到深深的羡慕。
小学生的周日并不会闲着无事,有时除了作业之外还会有别的任务在身,学雷锋乃是应有之义。老师在周六下午按照学生们的家庭住址把全班同学分配成若干个学雷锋小组,安排每个小组在周日集合学雷锋做好事——好事的选择可以随心所欲,但班主任要求的是结果,每个学雷锋小组都必须带一封被我们帮助过的人的感谢信回来。于是,在某些周日,我和小组的成员们集合,商量去哪里学雷锋,一次是去一所中专学校的收发室里,不由分说走进去为收发员打扫房间,扫地,洒水。我们学了雷锋,走远之后才想起还没有要到感谢信,于是又跑回到那个收发室,要那个看门人写感谢信。我们依次报上自己的名字,要他写在信上,然后还要他在末尾写上对我们的班级、老师和小学表示感谢。那封写了半页纸的感谢信上多是连笔字,我看不懂,但是仍然满意地走了,在周一交给老师。
假期、标准答案与奥数
假期是天堂,但学校不会就此空虚下来,在这个旅游城市的暑假,小学利用自己的位置优势,变成了一家旅馆。在一个非到校日,我走进学校,发现教室里的桌椅不在了,换成了等间距摆放的床铺。而我见到我的班主任坐在一个桌子后面,成了这个临时旅馆的接待员。班主任见到我便叫我去旅馆房间里打扫卫生,直到我妈妈在外边等得焦急进来把我带走。
小学时家里订了《故事大王》《儿童漫画》《学与玩》和《童话大王》每月可以读来消遣,但在课堂上的阅读不但没有任何趣味,而且有着极大的压力和挑战。一首古诗或是一篇课文也好,在课堂上,在考试时,学生们总要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作者这样写表达了他怎样的思想感情?我不知道一个唐代诗人创作的初衷,也不可能知道一个已经故去的作家怀着怎样的心情写作,但老师有着标准答案。阅读中文课文并试图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这种阅读练习从小学开始,一直到高中完成我人生中最后一节语文课,始终一直深深地困扰着我,我知道这样的问题有技巧和套路可寻,却从来都猜不准,每次只能答对六七成,这或许是我的语言天赋所决定的。
多年以后,我写的一篇短文成了中国数十所高中期末考试或是高考模拟考试的阅读理解题目,随后这篇文章作为标准考题被发在网络上。我饶有兴趣地重读了一遍自己写的文章,试着去回答后面的三道考题,不出所料,题目问到了作者为什么要在某一段运用某种写法,表达了作者怎么样的用意……我努力回想,然后又试着回答,再和标准答案进行对照——和标准答案相比,我仍然差不多答对了六七成,与小学相比并没有长进。
阅读方式自然会影响写作手法。对小我一年级的堂妹介绍经验,我说写作文就是要胡编乱造——我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在长达300字、500字、800字的作文作业里,情节和人物的真实性是最不重要的,我的爷爷可以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奶奶可以做过地下工作,我无数次地在深夜里走过班主任家的楼下,总是抬头就能看见窗户里的班主任仍然在台灯下为我们批改作业,每一次我都感动得流出了眼泪……这些胡编乱造是为了能够在结尾提出主题思想,立志为一项事业奋斗终生,总是能得到一个还过得去的作文分数——这是我和我的同学们接受的文学启蒙,现在也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
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是聪明人的比赛。小学四年级,我被选拔参加学校的奥数培训。这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责任,每周有三天的时间,我需要在下午下学后换到另一间教室参加学校里的奥数培训。每个年级都有一个奥数班,都是由年级里数学成绩较好的学生组成,不同班级的学生组成一个班,彼此两两相望时眼神中都会流露出一种优越感。为我们授课的是一位更高年级的数学老师,他在课后和周末为我们讲解数学。这样的课堂里无需维持课堂秩序,学生们都知道自己是被选中的数学苗子,而坐在身边的同学都是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因此听课格外认真,做笔记。讲解的内容超出了课本,奥数老师为刚刚学习了一元一次方程的学生讲解二元一次方程和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在课间依然会打闹。当时市里午间的收音机里播放单田芳的评书《白眉大侠》,同学们便互相以《白眉大侠》中的人物给人起外号,我忘记了别人给我起的外号,却清晰记得一个女孩的外号,那是评书里一个女性的名字。为小学生提前讲解初中的数学课程,是为了考试。那一天到了,奥数班的学生集体到了市里另一所小学,与其他小学的总共几百名学生,一起参加数学奥林匹克比赛,如今只记得当时坐在那间陌生教室里的新奇感觉,题目是早就忘记了的,成绩下来,班里有同学拿了二、三等奖,我没拿到什么奖,奥数班从此解散了。
转学、小学快毕业了,要上一个不太差的中学
我转学了。在市区里为数不多的几所中学里,爸妈竭力想让我避开一所声名狼藉的中学,想让我去市里的重点中学,重点中学旁的一所普通中学也可以接受。小学毕业生分配上中学,由小学所在的学区决定。为此爸妈为我转到一所离家更远的学校,每天上下学要坐20分钟的公共汽车。问题还不止这些,市里的小学教育正处于转型期,九年义务教育有小学五年加初中四年和小学六年加初中三年两种,我上的五年制小学,在四年级之后转学到这所六年制小学的六年级,初中只要上三年,相当于省了一年,算是跳级了。这是我早半年上小学之后第二次为自己的教育省下了时间,这样让我在班级里始终是年纪比较小的学生,没有太多的朋友,难以寻觅友情,也更容易受到欺负;这也让我17岁半就上了大学,21岁出国留学,最后把这些省下来的时间荒废在英格兰。
转学到一个全新的学校,进入全新的班级,面对全新的老师,同学却不都是新的,我原来班级里的同学接二连三地转学过来,教室里很快就坐满了,有些原本供两个人分享的课桌要坐三个人才够用。新的班主任依然是语文老师。这是位年纪更大一些、大约50岁出头的妇女,这位老师一路把学生从一年级带到六年级,已经和班里的学生相处了5年多的时间,和许多学生情同母子。这也导致了她对班级的失控——学生们并不怕她,在上课时学生们有时会忽然哄堂大笑或闹起来,班主任对此无能为力,只能待哄笑结束,指着学生们说:“你们呀,哎!你们呀!”小学禁止学生骑自行车上学,但当时已经有学生偷偷骑自行车上下学了。班主任发现,把骑车的学生叫来质问,要他们改坐公共汽车,被质问的学生却满脸不在乎和滑稽的神气,否认班主任的指控,班主任依旧是无可奈何,只好说:“你走吧,以后注意安全!”数学老师是邻班的班主任,住在学校附近,听说邻班有很多学生都会在周末去班主任家里玩,我从来没去过,那更是一种我无法想象的境界。
忘记了在小学的最后一年学过什么课程,只记得当时的课堂总是闹哄哄的。最早的一批香港和台湾的流行歌曲开始传入大陆,最先流行的是台湾歌手郑智化,电视上反复播放他的《水手》和《星星点灯》,“小虎队”也出现了。报纸上有时会登出流行歌曲的歌词,我很小心地把这些歌词剪下来,贴在一个笔记本上。音乐课上老师不会让学生唱这些,新学校里音乐老师是一个神情欢快的老头,上课时他会背着一个手风琴进来,教我们唱日本民歌《北国之春》——教过的歌曲肯定不止这一首,但这一首是现在我头脑中仅存的音乐教育成果了。
我的小学生涯该结束了,最后面对的是小学生初中考试。考试只有语文、数学、自然三门,之后迎来人生中第一个没有任何作业的暑假。几天后收到考试成绩,我三门都在95分以上,其实这成绩并不算太突出,班里有好几个同学考了三个100分,判考卷的老师们在打分时想必都很慷慨。
小学生涯结束了,但升初中最关键的时刻还未到来,我爸妈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当时市教委意识到了很多学生为了避开那所名声不佳的中学而转学,这给他们划分初中的工作带来了麻烦,决定不仅通过小学的位置,也要通过学生的家庭住址来分配中学。一些小学毕业生的家长听到了风声,提早做了准备,提前准备了一个在重点中学附近的家庭住址等待检查——检查真的来了,一个没有任何自我介绍的电话打到我妈妈的单位,直接问她:“你家住在哪里?”我妈妈冷静地背出那个事先准备好的地址,对方无声无息地挂掉了电话。不知道这种世界上最为诡异的电话在那个夏天打过多少,结果还不算太坏,我没有被分配到那所重点中学,也避开了那所声名狼藉的中学,最终被分配到重点中学旁边的普通中学——这在当时是我爸妈所操心的事,而我正在享受一个无拘无束的暑假。
补习英语,小学结束了
初中要开始学英语了,我小学里没有学过英语,毕业时26个字母都认不全,有的小学在四五年级开了英语课,上了中学我要落后了。爷爷给我找了一个家教,那是个脸上总带着神秘表情的老头,他会英语,我表哥在两年前准备升初中时也找他补习过。表哥带我去那个老头家里,准备接受我人生中的第一节英语课。在路上表哥问我:“字母表你会不会背?”我说不会,表哥说:“这不行,你要是认不全字母,老师就看不起你,到时候该不好好教你了。”于是,在去英语老师家学习英语的路上,表哥叫我唱英文字母歌,那是“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的旋律,字母歌的最后有一两句英语,我是无论如何也记不下来,不过表哥说我背下来的已经足够了。不过等我到了老头家里,老头并没有问我认不认识英文字母,更没有给我机会让我演唱那首刚学会的英文字母歌,至于他教了些什么我早已忘记,但我清楚,我已经开始学英语了,这意味着我的小学生活结束了。
我的小学被拆掉了。在小学的原址上树立起了全市第一栋高层建筑,那是一个形状奇特、有着莫名其妙浅粉色外表、有二十几层的楼房,它占据了原来操场和教学楼的位置。高层建筑的地下一层、地面一层和二层变成了商场,冬天时,掀开厚厚的门帘走进商场,里面传来浓重的烤香肠味。小学生源逐年减少,学区里的几所小学相继消失,之后合并成为一所小学。随着高层住宅的涌现,我读书的初中和高中也相继搬离在市区内的位置,我接受初等教育的痕迹在家乡被一笔笔抹去,就像从来没存在过一样。我远赴外地上大学,继而出国,后来在剑桥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催促我不断取得学位的动力,除了对于知识的渴求,现在想来,其中也必定有一份因为对自己童年所受教育的不满而产生的补偿心理吧!
这是一份有关童年和小学的回忆,把它与我后来的成长经历和别国教育方式的对比,算得上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样本而具有特殊的意义。一个人被他的过去所塑造和定义,而小学教育正是一个人成长经历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需要注意的是,我所经历的小学教育,或者说中国整个“80后”群体所接受的小学教育,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教育方式,整个“80后”一代所成长的家庭和社会环境是极为特殊的。“80后”一代的父母和小学教师大多是同时代人,这一代经历了饥荒和罕见的社会动荡,在小城市或是村镇中,少有人能够接受哪怕是完整的初等教育,“80后”的上一代对于青春的回忆几乎没有课堂和教师,而大多是饥饿,对暴力的恐惧和体力劳动,他们的青春记忆难免会通过教育被移植到下一代人身上——尽管“80后”成长的社会环境与父辈已经截然不同。
时代会改变,学校的教育方式也会随之改变。现在的小学里更加提倡素质教育,网络社会的小学生们所接受的教育方式与上个世纪已经截然不同,师生关系也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追求高学位,追求名师和名校,期待自己被教育所改变,但我们始终需要意识到,一个人对于自己和社会最大的责任,就在于一生不断地对自己进行教育,无论与老师和学校之间有怎样感情,都需要意识到离开学校并不意味着教育的终结,时代与社会并不能完全定义自己,这种信念,或许才是一个人、一个国家前行的原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