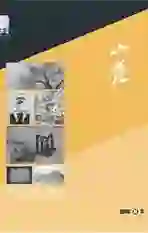和巴特勒先生见面
2016-06-16甫跃辉
甫跃辉
第一次见到巴特勒先生,是8月12日,思南公馆的讲座。我坐第二排,身后是乌泱乌泱的人群。那时,巴特勒先生唯一翻译成中文的小说集《奇山飘香》还没几个人看到,那么多人,大概是冲着“美国的创意写作课程”这个讲座题目来的吧?
在很大程度上,我也是冲着这题目来的。四年前,我从复旦大学首届文学写作专业毕业,不少媒体报道,很多都抱了质疑的态度。有一家媒体,时隔两年再采访我,仍然问,作家可以教吗?我有些生气,说这问题不是两年前就问过了吗?请问物理学家可以教吗?化学家可以教吗?这些“家”似乎都不是教出来的,但并不妨碍学校教物理教化学啊。同样的道理,作家不是教出来的,但并不妨碍学校教写作啊。后来,我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们谈到写作,那么抵触“教”?我们为什么把写作看得如此神秘莫测?
8月15日早上,我在华亭宾馆和巴特勒先生会面,一开始就和他聊到这个。
说来也巧,那天在宾馆里,很偶然地,遇到在二楼走道边沙发上休息的巴特勒先生。他一个人坐在那儿,望着楼下大厅来往的人。我愣了一下,还没到约定的时间,要不要上去跟他打招呼?最后,我还是硬着头皮走上去,和他聊了几句。他很惊讶,微笑着听我的半吊子英语,给我随身携带的《奇山飘香》签名,认真签下我的名字和日期。
有这铺垫,当翻译到来后,我们聊起来就很随意了。
关于创意写作课,他在讲座中就说过:“创意写作课程的确会教授写作方面的一些小技巧,但创意写作不能教出天才,而是教学生如何感受或者体会写作的过程,引导人们审视自己的内心,倾听自己的内心,选择正确的创作路径,尽量少走弯路。艺术来自你内心的真正想法,你可以拥有天赋,可以拥有写作技巧,但是如果不认真思考,你永远不会诞生伟大的作品,就像中国有句话叫做‘学而不思则罔’。”
在聊天中,巴特勒再次强调:智慧是不能够被教授的,它需要领悟,一样这个领悟,他作为写作学教授,只能教授一个人如何去领悟。而写作更重要的还在于,得有这个“智慧”,不然,空有领悟的办法,也只能徒呼奈何。
问题在于,有没有这个“智慧”是谁也不知道的,每个写作者所能做的,只能是努力去找到打开智慧阀门的钥匙。这把钥匙长什么样呢?通过和巴特勒先生聊天,我为这把神秘的“钥匙”归纳出这么几个特点:
首先,是看见,或者说观察。
巴特勒先生说,“观察细节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你读完一部小说以后,它应该像一部电影一样呈现在你脑袋之中。”这是他第二次到中国(第一次去的天津),第一次到上海,他说,一到上海,他就注意观察上海的行道树是什么。而这正是我长久以来的习惯。
巴特勒先生如此有意地观察细节,在越南时期就开始了。
《奇山飘香》这本小说集里的故事都是关于越南的。全书十七个小说,多数小说使用的都是第一人称叙述。每一个“我”都是不同的越南人。巴特勒先生说,他最初出版这本书的时候,书里没有他的照片的,之后的二十多年,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一个美国人,都以为他是越南人,人们知道他是美国人后,都非常非常吃惊。由此可见,他对越南人和越南生活的逼真、深刻的叙述。之所以有这样的效果,小说里展现出来的丰沛细节至关重要。
巴特勒先生告诉我,到越南之前,对他来说,越南的概念是非常模糊的。他对越南所有的了解,都来自战争。战争开始之前,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越南只是一个法国殖民地。在他去参加战争前,部队把他送去语言学校学了一年越南语,当他第一天来到越南,他已经可以说很流利的越南语了。在战争中,他做的最长时间的工作就是翻译,先是为美国的外交部做翻译,然后是到胡志明市。他尽可能地与越南当地的人打交道,想融入他们,了解他们。他发现,越南人是很热情好客的,他不仅学习到了越南的文化,也看到了越南人的内心。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他走上了写作的道路。
去越南之前,巴特勒读的是戏剧研究生。那时候,他只想做一个戏剧家。在他看来,戏剧的写作只是做一些人物的对话,让这一切呈现在戏剧的舞台上,而越南的这段经历,让他想把戏剧转化成小说,“因为小说是创造整个世界的,而戏剧只是在舞台上的表演。”
在越南期间,巴特勒就很有意地观察细节,并且做了很详细的笔记。越南战争结束后,他还曾四次回到越南。每一次,都会让他看到新的细节。
他把这些细节的记忆分成两大类,一个是“事实记忆”,一个是“感官记忆”。巴特勒认为,他写的多半是感官方面的记忆,他并不是很擅长于真正的事实上的记忆。
其次,是准确,或者说不带偏见。
我问巴特勒先生,他写作《奇山飘香》的时候有没有带有某种偏见呢?比如说政治偏见。这些会不会影响到《奇山飘香》的创作。巴特勒先生对这一问题没有回避,他认为,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并没带有任何偏见。但他似乎又不是那么肯定,他说,就算有偏见,这种偏见可能是来自于文章作者“我”本身的偏见,“这种偏见是作为一个人类的正常的偏见,比如说情感上的偏见,但它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就是人类体验的中心的偏见。”
或许,正是这种不带偏见的态度,让巴特勒得以融入越南社会,对越南有如此多的了解。越南不少地方有着东方式的鬼怪传说。《奇山飘香》中的《鬼故事》就很像《聊斋》中的某些篇目。谈及此,巴特勒先生给我讲了他在越南的一件真实遭际——他一再强调这事儿是真实的。他说,他在越南的时候,胡志明市的很多人都相信鬼的世界离他们是非常近的。他曾住在一间非常大的房子里面,那房子是1836年建的。每天晚上,都会有个鬼敲他的门。这不是您在做梦吧?我问他。巴特勒先生很认真地说,他把门打开了,看到屋里的东西在移动!这让我想到《奇山飘香》中与书名相同的那篇小说。
叙述者是个快要过世的老人,他不断看到早已过世的朋友胡志明来访。胡志明似乎是在梦中,又似乎是真实的。巴特勒先生说,他的很多鬼故事都是从越南人那听来的,而我所说的这篇小说中的胡志明是他的想象,他并不需要人们去判断这个鬼是不是真的,这个小说里面的主人公,他所学到的生活中的课程才是最重要的事。
进而,我问巴特勒先生,《奇山飘香》十七篇小说里的多数人物是越南人,多数都是第一人称叙述,您作为一个美国人,真的能确定“我”知道越南人是怎么想的吗?
巴特勒先生稍微犹豫了一下,说,当你了解得够多,写得够多,你最终会把这些经验输送到你的潜意识里面,当你的潜意识已经足够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你就可以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给它创造出来。此外,不管是关于性别也好、种族也好、信仰也好、文化也好、政治也好,都不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所有我们共同分享的意识,人类的意识。
最后,是遗忘,或者说贯通。
我在复旦读文学写作专业研究生时,上过美国写作学教授开的课。那位教授叫做约翰·舒尔茨,他是哥伦比亚艺术学院的教授,他是中国作家严歌苓的写作老师。我听他讲了十六节写作课,在他的指导下,我写了不少东西,当然,用的都是很简单的英语。课程结束后,我把其中一篇翻译并改写成了短篇小说《初岁》,后来,这小说收录进了我出版的第一本书《少年游》里。那段经历,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事实上,巴特勒先生强调的很多写作理念和舒尔茨教授所说的很像。我第一次读到理查德·耶茨的小说集《十一种孤独》,非常惊讶,觉得那个写作方式太像舒尔茨教授教的了。查了一下理查德·耶茨的简历,才知道他上过美国的写作课……这挺让我担心。
我把我的担忧告诉了巴特勒先生:这样一种写作方式,这样一种感知世界的方式,会不会让写作变得模式化呢?
巴特勒也认为,这是件危险的事,“因为在写作的这个课程里面,他们会创作一种像方程式然后让人去跟随它,但这背离了写作的初衷,写作应该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流露方式。”怎么解决呢?巴特勒先生,他在讲座里就提到过:小说家记忆力是最不好的。所以他觉得,写作学课程教给的方式是好的,但当你学到后,要把它忘记,然后把它丢到垃圾箱里,让所有技巧成为一个整体,把它彻底变成自己的东西,在写作中,让这一切自然而然地流露。
这正如庄子所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
一个半小时过去了,要和巴特勒先生告别了。很多年以后,我仍然会记得这次会面吧。它让我对写作有了更多的认知,有了更多的信心,我会记住巴特勒先生在讲座上讲过的一句话:“一个作家在写作时不应该过多担忧作品将来的命运,有多少销量,被多少人接受。假如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幸存的人,照样会写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