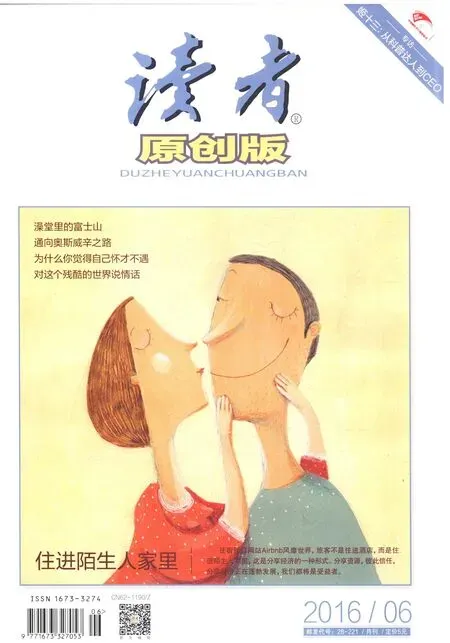我和我的七十二家房客
2016-06-14潘采夫
文_潘采夫
我和我的七十二家房客
文_潘采夫

从Airbnb上订的苏格兰农庄
现在想来,2012年可能是我人生的分水岭。2012年之前我在北京,北京像个大火锅,我是热汤中满头大汗的一根宽粉,膨胀、滑腻,翻来覆去,身不由己,不知如何终止这样的生活。2012年,我去了英国,一住两年,与以前的生活强行“熔断”,散步,爬山,旅行,去博物馆,整个人渐渐清爽了起来。
英国的家庭,无论穷富,一年总要出去旅行两回,把皮肤晒得黑黑的回来。有一次,一个英国大哥看到我,说看我晒黑了,饶有兴致地问我去哪个国家旅行了。我没好意思告诉他我是回了趟北京,跟哥们儿踢了几场球晒的。
周润发住进了房东家
2012年是伦敦奥运会,那两年,一个叫Airbnb的住宿预订网站开始风靡欧洲。订过房间后,旅客不是住进酒店,而是住在普通人家里——和房东同处一个屋檐下,或者住房东多余的房子。这种听上去很神奇的住宿形式,经济学家美其名曰“分享经济”。
我住在苏格兰,去欧洲大陆旅行基本都用Airbnb预订住宿。也怪了,我和家人选中的房东往往不是一般人。我们在阿姆斯特丹的房东是个剧院的经理,她男朋友看上去像个作家,文质彬彬,充满童心;柏林的房东是歌手兼DJ,从意大利跑到柏林学音乐,他租了一套房子,分租出去一间贴补生活;维也纳的房东是个不上班的奥地利青年,他的太太是个台湾姑娘,一个交响乐团的大提琴手。遇到的这些房东让我不住地感慨欧洲文明程度高,欧洲人真闲,有文化,会生活。
位于巴黎15区的房东是个全职奶爸,也是个港片迷,到他家的那天,我刚好梳了个大背头,房东见到我,大喊一声:“Chow Yun Fat!”说我长得酷似他的偶像周润发,手舞足蹈地跟我聊港片。阿姆斯特丹的那位女房东邀请我妻子和女儿去院子里聊天,她还亲手做各种糕点请我们吃。我们离开的那天,她儒雅的男朋友送我们走到公交车站,如老友一般挥手道别。
受那些房东们的鼓舞,我和妻子回到苏格兰后,也腾出次卧的上下铺,接待去苏格兰旅行的文艺青年和艺术家。爱丁堡是欧洲艺术之都,全世界艺术青年的圣地,所以订单不愁。不少房客身怀绝技,他们早上唱歌练声,晚上邀请我们去剧场看演出,或在家里跟我们一起吃着中餐聊着天儿,还送我女儿各个国家的小礼物。
美国歌唱家露丝·玛丽去爱丁堡艺术节演出,住的就是我们家的上下铺,她和我闺女江南聊音乐,后来她去伦敦开小型演唱会,还请我们去伦敦观看。
也有尴尬的时候,一对德国恋人住在我家,晚上他们去酒吧喝酒,回来后已是半醉。半夜,小伙子竟然迷路,跑进我们的卧室,还无助地喊着女朋友的名字。早上起来,发现这对青年早已整理好铺盖,悄悄地离开,留下满屋尴尬。
妻子和女儿的英文超好,而我是半瓶子醋,所以我就成了不需要跟房客交流的洗衣工,洗被罩、枕巾、毛巾、桌布。一个旅居异国的专栏作家,在风笛声处处的苏格兰,为房客洗洗涮涮而乐此不疲,这是什么样的精神?
谁家子弟谁家院
从苏格兰回国以后,我重操记者旧业,念念不忘的选题就是“Airbnb的中国学生”,想寻找一些与Airbnb类似的中国公司,看它们在中国遇到了什么困难,正在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在我看来,Airbnb这种到陌生人家里做客的分享模式,将会真实地呈现出中国与欧洲的诸多差异——欧洲人更有安全感,房主心态更开放,对陌生人更具善意,而国人最大的障碍,来自对安全问题的焦虑,对陌生人的提防。
我开始带着题目进行采访。直到联系上“小猪短租”,才觉得找到了Airbnb模式的“中国故事”。万万没想到的是,平生第一次做财经采访,结果竟然是我加入了这家公司。
公司的创始人陈驰是个“轴人”,这位曾经的妇科医生,从担任赶集网旗下的“蚂蚁短租”的总经理开始,就执着于Airbnb的分享理念。他所迷恋的,就是房东和房客之间交流的美好感觉。陈驰平生第一次出租自己的沙发,是租给一位到北京看病的大姐。最后,他让大姐住进卧室,自己在沙发上睡了一夜。这似乎就是Airbnb的中国化表达了吧,给开放、透明的短租模式,添加了温暖的中国式人情。
工作之余,我也做起了房东。我给家里的一间卧室放上大书架,把我喜欢的书放上,接待热爱读书的青年。这间卧室里放着单人床,床头的墙上挂着卡尔维诺和博尔赫斯这两位作家的海报,海报上还印着博尔赫斯的名言:“我暗暗猜想,也许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模样。”我希望给租客准备的卧室像一个小型图书馆。
果然,来我这里住的多是读书人,当然也有异类。前几天,一个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跟我联系,说他要拍一部学生作品,看中了我的卧室,因为很符合他影片中男主角的气质,问能不能住一晚拍电影。我接受了房款,164元,等他们上门。嚯!一下子进来近十个男生,还各有分工。他们一进门先叫盒饭上门,挺有片场的派头,场记还在卧室里贴满了动漫海报。我无意中推门进去时,男主角正沉浸在青春的迷惘中,导演说这是一部纯爱情片。
四个小时拍完,学生们迅速把家具恢复原状,垃圾收拾干净,很有礼貌地告别,他们对这种短租形式已经玩得很熟。我不在乎他们是谁家的子弟,他们也不在乎住的是谁家的院子,享用而不拥有,青年人最先懂得分享经济。

古清生的神农架原生态房源

前女排国手薛明的花房主题民宿
孤独的作家,温暖的书店
进入短租行业,我成了分享经济的“铁粉”。我拉着朋友作业本、王小山当房东,找前中国女排国手薛明当房东,招募青年人住进剧院、书店、图书馆、博物馆。
我有个朋友叫古清生,他是最早一批的北漂作家,曾与人合写《中国可以说不》,红极一时。后来古清生消失了,他去了神农架,写了一本《金丝猴部落》,还种起了茶叶,至今已在那里隐居近十年。
去年夏天,我去神农架看望古清生,想请他打开院门当房东,这样朋友们可以去看望他。老古院子的四周就是神农架的群山,那些山都绿得神秘莫测,在云雾中默立。古清生端着一个盘子,跨过院子里的小溪,走到房后高过人头的玫瑰花丛处,用浓浓的湖北普通话喊:“珍妮,大卫,你们在哪儿?”“珍妮”和“大卫”是他喂养的鸡的名字。不仅动物有名字,在老古这里,满院的玫瑰也各有讲究——门口那棵叫“自由精神”,鱼池边上的那棵叫“好运的渔夫”,还有一棵叫“爱丁堡公爵”。
神农架的生活太孤寂了,夏天还好,冬天封山,古清生几天不见一个人,他被称为“中国最孤独的作家”。在我的启发下,他当起了短租房的房东,还真有人从很远的地方跑去看他。每当此时,老古就给房客沏茶,亲手炒菜给他们吃,还带着他们去他的茶园劳动。
我喜欢逛书店,去巴黎旅行时还专门朝拜了莎士比亚书店,那个海明威睡过的地方如今依然放着一张单人床,四周堆放着书籍,让文学青年们流连不已。在书店里睡一觉并梦见海明威成了我的梦想,我幻想着书店老板打开门,安顿房客睡进书店一角的小床,房客随手拿起一本书阅读,城市夜空又多了一盏灯。
于是,我去拜访单向街书店的许知远,去扬州找边城书店,去泉州找风雅颂书局,联系翻译家文泽尔和他的私人图书馆,一共联络了十家书店开展短租业务,邀请爱书人住进书店里。“不能住宿的书店不是真正的24小时书店”,这是一位书店老板说的。
短短半年时间,加入“城市之光”计划的人文书店已近20家。在中国,当书店都能住宿的时候,我知道短租的潮流真的来了,这是趋势。
说了这么多,那什么是分享经济呢?在我的理解里,分享经济有几个要素,要有闲置的资源、接近于零的时间成本、很低的物质成本和个性化的体验。比如一间(或一套)闲置的房子,自由职业或不算太忙的房主,每一间房子和房东都有个性,这样就能在不消耗社会资源的情况下实现价值的增加,也实现了人和人的友好交往。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其中写道:“Uber、Airbnb、滴滴、小猪短租、在行,我好像赶上了什么大事,一场社会结构的重组浪潮?一场时间和空间的小革命?”这种兴奋又惶惑的心情,是我真实的内心感受,尤其在欧洲生活了两年之后,我对中国能赶上甚至引领新一波互联网浪潮,感到不可思议。分享经济是自带价值观属性的,它冲破的是各种壁垒,既有现实中的垄断,也有人们脑海中的桎梏,它将在实名制的基础上,搭建出完善的信用体系,有了安全的技术条件,就可以推动中国向互相信任的陌生人社会转型。
有人说未来是分享经济的时代,它将深刻地改变中国,我将注视着这一切如何发生,并满怀好奇。

“城市之光”合作书店:扬州边城书店

“城市之光”合作书店:北京单向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