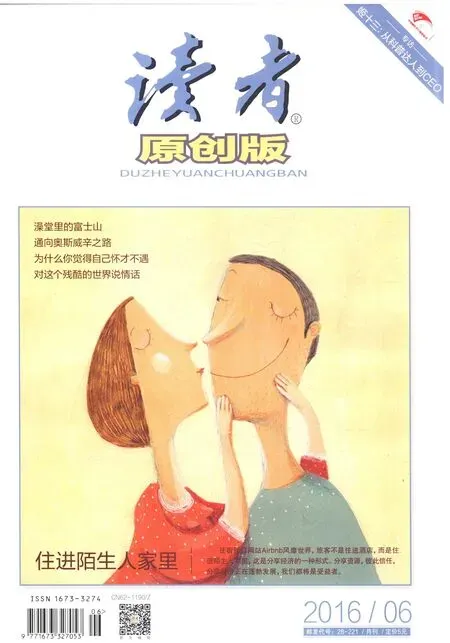做寿衣的父亲
2016-06-14文_寇研
文_寇 研
做寿衣的父亲
文_寇 研

一
老爸是镇上唯一会做寿衣的裁缝,这是他从祖父那儿继承来的技艺。祖父过完70岁生日不久,就穿着早为自己准备好的寿衣入土为安了,此后,远近需要做寿衣的人家,都会找老爸。
在我的记忆里,很多个寒冬或盛夏的深夜,在家里人全都睡下之后,整个小镇都笼罩在此起彼伏的鼾声里,会突然传来窸窸窣窣的脚步声,步履匆忙,由远及近,最后停在我家的小楼下。接着是说话声,像是在确认地址,然后有手电筒的光晃到我家楼上的窗户,楼下的卷闸门也被拍得哗啦啦响。老爸起床、开灯、下楼,把卷闸门哗的一声推上去,便拥进来几个裹挟着凉气且神色疲惫的男女——家里老人病危,急需置备寿衣,越快越好。
从老爸承接做寿衣的活计开始,就时常需要面对这种要连夜赶活的突发状况。通常,乡下的老人,比如祖父,会早早为自己和老伴准备好寿衣,以备不时之需。顶着夜色来找老爸的,往往是遭遇突然变故的家庭,老人还没来得及为自己备下寿衣。
浩荡而静谧的乡下小镇的夜色里,老爸一杯接一杯地喝浓茶,昏黄的灯光下,脚踏缝纫机的声响听来分外孤独。天亮时,寿衣已全部完工,包好,搁在货架上。等我们下楼吃饭、准备上学时,老爸已把他去附近乡镇赶集摆摊要带的货物在摩托车后座上捆好了。有一年,他照例熬夜赶活,天亮再去赶集,下午收摊回家的路上,摩托车冲到马路牙子外的石壁上,腿、胳膊、脸上全是细碎的伤口。那一个月或许是他这一辈子照镜子频率最高的一段时间,每天都要在穿衣镜前晃几回,还跟我妈反复确认:“是不是没有疤?真的没有?”临到做饭时间,又要去厨房反复叮嘱:“不能放姜,记得别放姜,吃姜留疤……”那是老爸少有的担心自己不再帅的时刻。
二
老爸老妈生了我们姐弟仨——一个合法,两个超生,谢天谢地第三个崽子终于是个儿子,这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式家庭构成。父母终日忙碌奔波,养家糊口,为孩子们挣学费。孩子们也按部就班,在镇上读了小学,再读初中,然后去县城读高中,幻想着有一天能去大城市上大学。这也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家庭的“中国梦”:父母本分地挣生活,孩子本分地挣成绩,都辛劳,都承受着各自的苦,却不懂得何谓沟通。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房檐下,各安本分,又各怀心事。这平静中孕育着风波,还未爆发,只因时候未到。
与老爸第一次发生重大分歧,几至决裂,发生在我20岁左右时。他强迫我与当时的男友分手,“战争”进行了三年,异常惨烈。他拿出连夜赶制寿衣的那份意志力,我呢,则继承了他的倔脾气。“战争”终于以我的恋爱失败收尾,我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他。以后的那些年里,他做他的寿衣,我上我的学,互相的沟通就剩最客气的问候,我打电话回家都是在估摸着母亲能接上的时间,要是他接了,也会立刻说:“我去叫你妈。”
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做了一个重大的人生决定:辞去工作,以写作为生。最初两年,收入很少,母亲难免会暗中接济,我自然知道,那些钱里有一部分是老爸熬夜挣出来的。老爸的“家门不幸”的苦恼都写在脸上。辛苦供我读完大学,我却不工作,躲在家里好吃懒做——这是他对我在家写作这件事的理解。就像没有人能阻止他要在天亮前赶制出别人订下的寿衣的决心,就像没有人能阻止他认定我的初恋男友是个“渣男”并必须出面干涉,我也无法阻止他认定我读书写作只是因为不想工作。那几年,我很少回家,不想面对他,我也约莫能懂他嘱咐母亲别忘了给我钱时,内心交织的愤怒与无奈。
三
几十年过去了,老爸已是镇上有名的寿衣裁缝,只要家有老人离世,人们会在第一时间找到我家。有时想想,竟也有些骄傲——他熬夜做了些新衣服,让老人们入土的那一刻体体面面。但我从未对他说起过这些,我们的沟通仍然只在最表面,叮嘱对方要吃饱穿暖、注意身体,诸如此类。近些年,我的境况逐年好转,写作,出书,老爸再不过问、干涉我的工作了。何况他也不懂,只说让我多吃一点儿,要劳逸结合,不要太辛苦。镇上若有人读了我的书、我的文章,夸了我,他会记得在母亲打电话给我时,让她转达这个信息。随着年龄渐长,我终于发现,自己努力了这么久,无非就是想成为老爸那样的手艺人,以写作为生。
关于我的感情问题,他也曾试探性地问过,每次都被我粗鲁地阻止,逐渐也就不问了。只是在我每次离家前,他会把我的箱子塞得满满的,好像今后一年没有这些东西我就得挨饿。我不耐烦地抱怨拿不动,他想想也是,转头又把箱子拆开重新打包,来回掂好几次,想象凭我的力气能够拎起来走多远。把我送到车上,隔着车窗玻璃,他招招手便立即转身走开,后来有一次通电话,他说:“看着你一个人……”我暴躁地打断他,以后他也不说了。有一年的大年三十中午,我弟终于从火车站接回了我,家里人都在等我吃饭,老爸尤其高兴——一个老人等到女儿回家的高兴。中午他多喝了两口,红着脸说笑着,突然就捂脸痛哭,他向我道歉,为多年前的那桩恋爱事件。我讨厌他给我道歉,我希望他还是霸道的、专制的,因为那代表他还是年轻的、固执的,不会伤感。
我想有一天,他也会穿着自己的寿衣离世,他会给自己准备好,就像当年的祖父。只是想一想这个世界可能有一天不再有他,都让人难以接受。但总是会有那么一天的,我希望当那一刻到来,他在回顾自己一生的艰辛时是安详的。我知道我们终会达成这样的默契:他的孩子虽然不太听话、倔强、任性,还不甘平淡地让自己的人生多有波折,但她,一直都非常非常爱他。
图/刘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