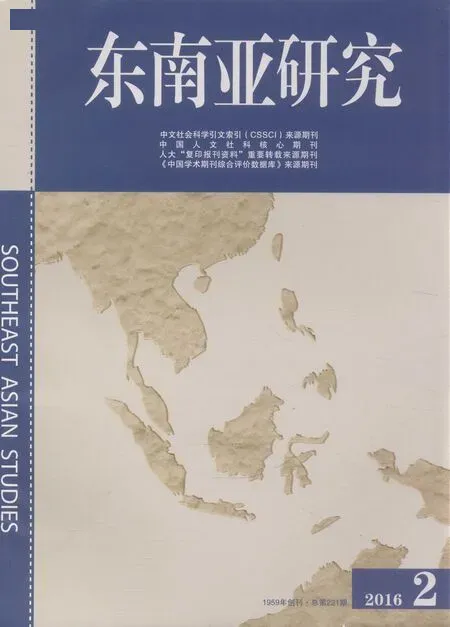婚姻的困境与突围
——基于缅甸抱村婚姻变迁的人类学考察
2016-06-13钟小鑫
钟小鑫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昆明 650091)
婚姻的困境与突围
——基于缅甸抱村婚姻变迁的人类学考察
钟小鑫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昆明 650091)
[关键词]缅甸;缅族;婚姻变迁;民族主义;佛教;互联网
[摘要]在缅族的传统文化中,婚恋自由、性别平等的观念一直被着重强调,也常被人类学家所称道。但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缅族的婚姻遭遇了许多困境,具体表现在婚姻结合越来越困难,适婚男女的独身率越来越高,并且由此引发出许多个人和社会问题。通过在缅甸抱村长期的田野调查,笔者发现这一困境与缅族民族主义复兴、佛教转向等原因有着密切的关联。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及移动设备在缅甸乡村社会的普及,基于网恋的新型婚姻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解决这一困境的途径。
Abstract: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Burmese, the conceptions of free marriage and gender equality have always been emphasized, while the stabl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marriage culture of the Burmese people has also been appreciated a lot by anthropologists. However, in the past twenty or thirty years, the Burmese marriage has encountered many predicaments, which specifically show in the increasing difficulty of marriage contracts and the increasing high rate of single marriageable people, which have led to many personal and social problems. Through long-term field work at Bao Village in Myanmar, I found that this predicament has close relations with the revival of Burmese ethnicity, Buddhism turn and so on. In recent years, as the prevalence of Internet and mobile devices in the rural society of Myanmar, a new marital pattern based on Internet dating has become in certain senses an effective way to solve this predicament.
引言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缅甸人的婚姻遭遇了重要转型,具体表现在婚龄被不断推迟,婚姻结合越来越困难,独身主义盛行,生育率下降等。这种转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人口学家葛文·琼斯(Gavin W. Jones)在2007年的一项研究中指出,1970年,在缅甸30-44岁的女性群体中,未婚率是15.5%,而2000年,这一数据已经蹿升至40.7%,25-34岁间的未婚男女比例达到33.1%[1]。与其他社会比较,缅甸在1970年的数据还处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但是到2000年时,未婚率已经远远超出了世界平均水平。针对这一现象,笔者于2013年12月开始在缅甸抱村从事田野工作,至今在抱村的实地考察已经累计超过一年。在此过程中,笔者曾有一个月的时间在抱村的寺庙中剃度为僧,还俗后便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习得了缅甸语。调查以参与观察为主要方式,也运用了非结构性访谈的方法。抱村隶属曼德勒省彬乌伦县宾撒镇,位于缅甸的中北部,是一个已有100多年历史的典型的缅族村落。根据2013年的抱村人口统计,全村有394人,共84户,除一户为克钦族,其余皆为缅族,普遍信奉南传佛教。全村17岁以上的男性未婚率为24.3%,女性则达32.7%*根据缅族文化,17岁的青年男女开始进入适婚期。。在与抱村村民共同生活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婚姻困境确实是村民们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对于这种现象,葛文·琼斯认为其原因主要在于缅甸经济的不景气,人们对于婚姻缺乏信心,加之信奉佛教的女性对于离婚的恐惧,使她们在婚姻面前犹豫不决;另外,最近二三十年以来,缅甸高等教育机会的增加也促进了独身主义的盛行[2]。笔者通过在抱村的田野调查发现,上述因素并非造成缅族婚姻困境的最深层次的原因。缅族女性在面对离婚时并没有太多的负担,许多注重性别平等的社会都表现出这样的情形。关于经济与婚姻以及教育与独身主义的观点,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在缅甸的乡村社会中,经济和教育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但独身主义却开始盛行的现象。本文认为,婚姻的困境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其与最近二三十年以来缅甸的民族主义复兴、佛教转向等因素密切相关。
一缅族传统婚恋模式
(一)公共活动——作为开展恋情的核心场所
缅族是一个普遍信奉南传佛教的民族,日常生活中充满了围绕佛教而展开的各种公共活动,几乎每个月都有一次重大的节庆,而且人们还会不定期举行各种大大小小的布施(缅语发音:a-hlu)活动。在类似于节庆、布施、婚礼、葬礼等公共性的活动中,未婚男女*一般是17岁及以上的未婚男女。需积极参与其中,并且有着特殊的任务。缅语称未婚男性为“卢骠”(lubyo),称未婚女性为“阿骠”(ahpyo)。村落中所有的卢骠组成一个未婚男性团体,相应地阿骠也组成一个未婚女性团体,这两个未婚的性别团体都设有一个头领,分别叫“卢骠纪”(lubyokyi:)和“阿骠纪”(ahpyokyi:)。在村落中的所有公共活动中,卢骠纪负责召集所有的未婚男青年,并给他们分配任务,阿骠纪则负责召集所有的未婚女青年,并给她们分配任务。卢骠团体最主要的任务是给公共活动中的来宾(包括本村的及外村的)提供点心,最常见的有拌茶叶、水果、米糕等;阿骠团体则主要给来宾倒茶水。每当有一个卢骠或阿骠要结婚,要离开他(她)自己的未婚团体时,他(她)就要向这一团体交纳一定数额的钱。在笔者所调查的抱村,这笔钱的数目是三万缅币(现在折合人民币约150元),这些钱由卢骠纪或阿骠纪管理,主要用于购买公共活动需要的水壶、茶杯、果盘等等。
美国人类学家朱恩·纳什(June Nash)和曼宁·纳什(Manning Nash)在他们的研究中提及缅族公共活动中的未婚团体现象,认为未婚男女在社会中有着特定的角色,在公共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单身并不受到歧视,从而认为这是缅族独身主义盛行的原因之一[3]。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是对这一现象的误读,德国人类学家谢尔曼夫妇(Lucian Scherman & Christine Scherman)在其20世纪初出版的关于缅族的民族志中明确指出,在缅甸广袤的乡村社会中,“单身是一种强烈违反习俗(strongly against customs)的另类行为,独身主义与嫖娼只被少数城里人所知道。”[4]单身并非像纳什所认为的那样不受到歧视,至少在乡村社会中是属于不正常的。笔者在抱村的调查表明,公共活动中的未婚团体的存在恰恰是为了使团体中的成员获得认识异性的机会,未婚团体设立的目的正是为了帮助未婚男女相互之间产生恋情,并最终走向婚姻和家庭。
每逢村落举行公共活动,卢骠和阿骠们都要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并精心打扮一番,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渲染节日的气氛,另一方面是尽可能地吸引异性的关注,而后者是更为主要的原因,因为在公共活动中,孩童和已婚人士并不总是这样注重衣着和装扮。装扮完成后,卢骠和阿骠分别去卢骠纪和阿骠纪的家里集合,领取果盘、水壶、茶杯等用具后便去往公共活动的场所。在活动过程中,别的村民往往是虔诚地坐在僧侣的前面诵经、叩拜、聆听教诲,而卢骠和阿骠们却并不参与其中,他们不时给来宾送去点心和茶水,更多的时候则是相互交谈或嬉戏,而对于自己心仪的异性,这时则要尽可能地引起对方的注意并且尽可能多地跟他(她)交流。而外村来的卢骠和阿骠也会参与到他们中间来,村内或村际间的恋情都往往起源于缅族社会中频繁的公共活动。当一个卢骠对于节日总是充满了迫切的期待,说明他已经爱上了某个女孩或者双方已经陷入恋情之中;而当一个卢骠总是热衷于参加某一个村的节日活动,则表明他心仪的女孩是来自于那个村。
特别是那些大型的布施,要延续三四天的时间,人们都放下劳动,全民进入到一种狂欢的状态,这时候对于卢骠和阿骠们来说,是发展恋情的最好时机。婚礼也是如此,依照南传佛教的习俗,每年的7、8、9三个月的夏安居时间不可以举行婚礼,所以,婚礼举行的时间相对比较集中,特别是每年的5、6月以及10、11月。社区生活的主旋律就是婚礼,而在婚礼期间,卢骠和阿骠们有大量的时间聚在一起工作、聊天,恋情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得到了发展。
在双方确立恋爱关系后,他们会寻找机会私下约会,但是最主要的约会时间仍旧是在村落公共活动中。当双方认为可以结婚并组建家庭时,他们便会将自己的恋情告知各自的父母,这时候,双方父母会根据两人的出生时间选择合适的提亲日期。提亲时一般是男子及其父母、亲戚,还有村长以及村里的长者一同去女方的家里。提亲的过程主要是商定婚礼举行的日期、地点以及婚后如何居住的问题,婚后从夫居和从妻居都被认为是合理的。笔者在抱村的田野调查过程中发现,这种在公共活动中结识、相恋最后结婚的模式是抱村村民婚恋的最主要方式。
(二)族内婚与族外婚
在传统的缅族婚恋观念中,青年男女对于爱情和婚姻有着非常大的自主权,这种自主权包括选择与何种民族相恋、结婚,族内婚和族外婚同样被接受。这与今天缅族的婚恋观念大相径庭。总体而言,族内婚是最常见的形式,佛教徒与佛教徒的结合被认为会给婚后的生活带来许多好处。传统村落社区的闭塞使族际间的交往并不频繁,这也是族内婚成为最主要形式的原因之一。但缅族并不排斥与其他民族以及信奉其他宗教的人结合。谢尔曼夫妇指出,按照缅族的观念,“一个缅人与印度人、华人以及欧洲人结婚都被认为是正常的、可接受的,而缅人与华人结婚则被认为是最优的结合。”[5]从这一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缅族对于族外婚的认可和接受。
在抱村,现在则完全以族内婚作为优先婚,族外婚已经长期不被接受。但是通过对一些老人进行访谈可以得知,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族外婚是被接受的,特别是缅族与掸族的结合非常常见,因为抱村离掸人的聚集区并不遥远,而且这两个民族有南传佛教作为共同的基础。华人则更受欢迎,因为“华人与缅人结合以后就会变成缅人”。而印度人也可以接受,但前提条件是他们是佛教徒或者印度教徒,而不能是穆斯林,因为“缅人与穆斯林结婚,最后往往是缅人被迫变成了穆斯林”。可见缅族在婚恋对象的选择上非常注重宗教背景,但是并不限定在南传佛教的范围内。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缅族传统的婚姻维系主要依靠他们婚恋观念中的自主性、开放性以及包容性。而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正是这些观念的消退导致了缅族的婚姻困境。
二缅族婚姻的困境
一些学者认为缅族的婚姻并不存在困境,因为他们的传统文化中就有独身主义的倾向[6]。这一观点已经被一些早期关于缅族的民族志所推翻,而更为关键的是,通过人口学数据统计,缅族独身主义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文化现象[7]。再来看抱村的情况,根据抱村现在最年长的村民吴明通(89岁)的回忆,“1942年日本进攻缅甸时,抱村在日军的轰炸下,只剩下8户人家,36人。”而至1980年,抱村人口已经增至312人,家户71户;1990年,抱村人口有367人,家户79户;到2013年,抱村人口为394人,家户84户(见表1)。

表1 缅甸抱村人口统计数据
资料来源:表格中1942年的数据来自村民的口述,其他数据来自抱村每年的人口统计表,村长处有存档,数据空缺表示未知。
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抱村的人口基数在1990年就已经基本奠定了,往后的20多年中并无实质性增长。而从适婚人群未婚率来看,1980年还保持在正常水平,而至2013年,全村17岁以上的251人中,有71人未婚,适婚人口的未婚率将近30%,离异和丧偶的情况还不包括在内。这足以证明抱村婚姻的困境确实存在,并且是近二三十年以来的现象。下面从不同角度来解释这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一) 民族主义复兴与通婚圈的萎缩
从1885年英国全面占领缅甸以来,缅甸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就一直高涨,如在20世纪30年代,缅甸国内爆发了“沙耶山农民起义”、由“我缅人协会”发起的“德钦运动”以及两次大规模反印运动,在20世纪40年代又爆发了大规模的“抗日运动”以及“抗英独立运动”,这些都是缅甸20世纪前半叶民族主义运动的典范。上述民族主义运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其目标的一致对外性,在总体上整合了缅甸国内的各方力量,并在《彬龙协议》的框架下促成了缅甸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团结。
缅甸独立后,其民族主义发生了深刻的转向,总体而言是在“一个种族(缅族)、一种语言(缅语)、一个宗教(佛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造成了缅族与其他民族的矛盾与对立[8]。诸多学者认为这种大缅族主义的民族主义倾向对于1988年以来缅甸的民主化进程而言是一种极大的障碍[9]。但是,民族主义与民主进程的另一个问题却较少被人关注。民主的前提是公民身份的平等,国内各族群都能享受到平等的权利,但正是在推进各族平等的过程中,大缅族主义运动进一步发展,坚决反对给罗兴亚人、印度人、华人等客籍公民、归化公民和侨民以完整的公民资格*依据1982年制定的《缅甸公民法》,缅甸国内公民分为完全公民、客籍公民、归化公民和侨民四等,公民权利依次递减。缅族以及其他7个原住民民族可享有完全公民的权利,华人和印度人一般被划分为客籍公民或归化公民,罗兴亚人一般是侨民和黑户。,同时又要尽力保持缅族在缅甸8个原住民民族中的优先地位。正是在这一股民族主义的复兴浪潮中,缅族的婚恋观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传统缅族对于婚恋对象的开放性正在新的民族主义浪潮中逐步消弥。以前对于印度人,缅族会区分他是穆斯林、佛教徒还是印度教徒,笔者通过在抱村的调查发现,现在村民们已经没有了这样的区分,所有的印度人都被认为是穆斯林,都被排除在婚恋对象之外。而华人在经济上的优势一再被夸大,并被逐步塑造成贪婪的资源掠夺者形象[10]。传统意义上视缅族与华人的结合为优先婚的观念已经不复存在。缅族与缅甸少数民族的隔阂也被进一步拉大。在抱村周围,分布着一些因为战争而迁徙至此的傈僳人村落,其中一些因为生存和适应的原因,开始弃基督教而改信佛教,但是缅族仍不与其来往。而传统意义上,缅人与掸人的结合是非常常见的,但现在掸邦地方军与政府的对立已经深刻影响了缅人的婚恋观念,掸人也被排除在缅族的通婚圈之外,他们被认为是国家分离主义者。
总之,在缅族民族主义复兴的过程中,一种族群化约主义正在缅族的观念中逐步形成,印度人被全民化约为穆斯林,华人被化约为经济掠夺者,少数民族被化约为国家分离主义者*关于化约论,详见〈英〉吉登斯著,郭忠华译《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1-17页。。正是这种族群化约主义将缅族的婚姻紧锁在族内婚的范畴之内,而无法向外拓展。
(二)佛教至上主义运动的影响
缅甸南传佛教参与政治以及渗透至其他世俗领域,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和传统,但是在缅甸民主化进程中的民族主义复兴的过程中,缅甸佛教中的一股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开始抬头,并且其参与政治的形式和影响都是以往的佛教运动无法比拟的。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缅甸僧人维拉图(Wirathu)发起的“969运动”*“969”对应的是“佛、法、僧”的意思,“969运动”旨在用最极端的形式阻止穆斯林在缅甸的生存与发展,维护佛教在缅甸的主导性宗教地位。。维拉图多次发起抵制穆斯林的游行示威活动,并呼吁民众抵制穆斯林的商业活动,禁止缅族与穆斯林通婚。2015年,该运动已经推动了缅甸“一夫一妻制”的立法成功,旨在阻止穆斯林人口在缅甸的增长。
目前,学界集中分析的是极端佛教运动所造成的缅甸佛教徒与穆斯林的对立,但是对于该运动的一些附加影响缺乏探讨。日本学者村主道美认为这一股极端的佛教民族主义浪潮的本质是“佛教至上主义运动”[12]。如果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一场佛教极端主义运动不仅仅是针对缅甸的穆斯林,而是试图确立佛教徒与其他一切人群的对立。目前虽然极端佛教民族主义运动只是缅甸佛教中的一小股力量,实际上许多民众、非极端主义的僧侣以及国家政要也都知道该运动已经偏离了佛教的教义,甚至已经走向了佛教的反面,但是他们一致选择了沉默,放任佛教极端主义持续影响缅甸局势[13]。
抱村寺庙的住持正是带有明显“969”倾向的僧侣,他极度推崇维拉图,并且对其主张和一系列行动表示赞许,这一点对抱村的婚姻情况造成了较为深刻的影响。在维拉图的主张中,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呼吁维护纯粹缅甸人的信仰与权利,而这种带有生物学意义的主张必须通过调节婚姻制度来实现[14]。在某种程度上,上文中提及的族群化约主义之所以可以在抱村这样一个最为基层的社区中生根发芽,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佛教精英的鼓吹与呼吁。民族主义复兴并不是瞬间席卷一切,其主张要渗透到最基层社会必须拥有一整套有效的传播机制,而宗教传播无疑是这种机制发挥作用的最佳途径。正是在频繁的村落宗教活动中,族群化约主义的思想在村民的头脑中慢慢形成,最后将族外婚的大门紧紧关上。
(三)族内婚的困境
在上文中,我们从民族主义复兴与佛教转向两个方面探讨了缅族族外婚所遭遇的困境,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缅族的族内婚出现了怎么样的问题。从抱村的情况出发,近二三十年以来的族外婚不再被认可和接受,长期的族内婚使村落整体成为一个亲属共同体,未婚男女在这一共同体中都结成了亲戚关系,从而无法成为彼此的婚恋对象。
缅族将第一代表亲和堂亲互相称之为“德旺贵”(t-wun:gwe:),将第二代表亲和堂亲互相称之为“内旺贵”(hnit-wun:gwe:),将第三代表亲和堂亲互相称之为“当旺贵”(tho:-wun:gwe:),而按照缅族的习俗,一个人是不可以与他(她)的德旺贵、内旺贵以及当旺贵结婚的,直到第四代的表亲和堂亲才可以结合[15]。抱村仍然延续了传统上公共活动中的卢骠团体和阿骠团体制度,但是这一制度再也无法满足未婚男女寻找婚恋对象的需求,因为整个村落都成了一个亲属共同体,未婚的男女都不再适合成为对方的婚恋对象,村内绝大多数卢骠和阿骠的关系都是德旺贵和内旺贵,他们只能是亲戚,而无法成为恋人。这是长时间族内婚带来的结果。
缅族对于爱情和婚姻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在今天除了跨族婚恋会受到干涉外,在其他方面仍旧延续了这种自主性。但是在婚姻面对困境时,婚恋的自主性不但没有缓解这种困境,反而使之加深了。婚恋的自主性意味着未婚男女有很大的自我选择的权利,但同时也意味着未婚男女能够得到来自他人(包括父母)的帮助是极为有限的。在中国,当一个“大龄青年”仍旧未婚时,他(她)的父母、亲戚及朋友都会积极地帮助他(她)物色婚恋的对象,缅族则缺少这样的机制,因为婚恋是自主的。所以,缅族未婚男女在寻找婚恋对象时,往往只能依靠自己特定的社会关系与网络,这使得未婚男女难以跨越村落建立更大的通婚圈。而村落又已经成为一个亲属共同体,这促使缅族婚姻的困境不断加深。
通过上述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很大程度上,近二三十年以来缅族中独身主义的盛行,其实质是一种“被独身主义”,是自主婚姻被政治挟持后的产物,既不代表人们的意愿,也非缅族文化的传统,正是在此意义上,它被称之为一种“困境”。
三互联网与缅族婚姻突围
对于大多数缅甸乡村而言,移动电话与互联网的普及是在2014年发生的。2014年之前,缅甸的电信行业一直被缅甸国企MPT所垄断,申请一个电话号码或手机号码的价格最贵时高达几千美元,即便到了2013年年末,价格仍旧维持在200美元左右。在缅甸广袤的乡村社会中,村民们往往具有购买手机的能力,却支付不起申请手机号码的费用。另外,许多乡村都处于信号不通的状态,即使拥有手机也没有办法使用。但是这一切都在2014年被彻底改变,2014年挪威电信公司Telenor以及卡塔尔电信公司Ooredoo同时入驻缅甸,申请手机号码的费用突然降至1.5美元。与此同时,两家公司在缅甸乡村建设了大量的信号发射站,使手机和互联网在缅甸乡村中迅速普及开来。
从抱村的情况来看,2014年缅甸互联网的普及对于缅族婚姻的影响同样是革命性的,村落中那些未婚男女几乎不约而同走进了全民网恋的时代。他(她)们主要依靠Facebook、Beetalk、Viber三款著名的社交软件对异性发起攻势,这三款软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的用户都是对陌生人开放的,这使得陌生人之间的连接畅通无阻,卢骠和阿骠们可以利用这些社交软件精确寻找适合自己的婚恋对象。网恋的效率非常高,2010至2013年这四年中,抱村每年成婚的次数分别是5次、3次、4次和3次,但是2014年,这一数字增至11次,其中有9次是基于网恋,2015年再增至18次,其中15次是源于网恋。毫不夸张地说,互联网改变了抱村的婚姻模式和结构,那些“被独身主义”的卢骠和阿骠们终于迎来了爱情与婚姻的“春天”。网恋成婚的高效率也进一步说明了抱村的婚姻困境绝非个案,而是缅族社会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普遍面临的问题,正是诸多类似于抱村这样的缅族村落之间的遥相呼应,才使这种新型的婚姻模式迅速流行起来。在互联网时代,各地的未婚者都可以轻松跨越他们现实生活中的亲属共同体,在全国范围内去寻找自己的另一半。互联网如此迅速并高效地使缅族的婚姻困境突出重围,还有如下几个方面原因:
首先,缅族的地方认同较弱,没有强烈的家乡观念。对于地方、家乡和故土的情感和认同往往来自于人们对于祖先的崇拜,正如费孝通所言,“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16]缅族没有姓氏,没有一套祭祀祖先的制度,也没有固定的继嗣制度。正是这些原因,使缅族文化中对于地方的认同是较弱的,家乡和故土的观念也不强烈。在缅甸,最经常听到的关于地方的划分是“上缅甸”和“下缅甸”的区分*缅甸人一般将曼德勒视为上缅甸和下缅甸的分界线,曼德勒以北为上缅甸,曼德勒以南为下缅甸。,但这一区分往往只具有地理学上的意义,而社会文化的意涵并不明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基于网恋的婚姻比较容易成功,因为双方都没有必要固守家乡,也不会对于家乡之外的地方感到陌生和难以适应。基于网恋的婚姻往往意味着远距离的婚姻,也就意味着有一方要奔赴至远离家乡的地方去生活,但这对于缅族而言并不是一个关键问题。
其次,缅族的婚后居住模式比较灵活。缅族并不过分强调婚后要固定执行哪一种居住模式,从夫居和从妻居都被认为是正常的、可接受的,父母很少与已婚的儿女生活在一起[17]。从抱村的情况来看,有超过1/3的家庭实行从妻居。这对于基于网恋的远距离婚姻而言,也是极为有利的条件,男女双方不必固定执行某一种特定的婚后居住模式,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协商和决定,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提升了网恋成婚的概率。
再者,基于网恋的婚姻模式符合缅族的隐秘性婚恋文化。缅族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在恋爱的过程中都十分注重恋情的隐秘性,只有双方决定结婚时,才将双方的关系告之父母,然后公之于众。这是一种对女性的保护措施,如果恋情以分手告终,也不会影响到女性后续的感情生活。网恋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进行的,隐秘性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保证,这也是网恋可以在缅族社会中迅速流行起来的重要原因。
总之,从现时的情况看来,互联网确实在很大程度解决了缅族的婚姻困境,使其在民族主义复兴和佛教转向的双重背景下实现跨地区婚恋对象调配。但是对于广袤的缅甸乡村社会而言,基于网恋的婚姻模式还是新生事物,其到底会朝着什么方向前进,并且会在社会文化方面产生哪些更为深远的影响,现在还难以预知。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基于互联网所产生的新型婚姻模式仍旧是在族内婚的结构内进行的,民族主义对于缅族婚姻的影响可能会进一步加深。民族主义的产生正是得益于新媒体的出现,而人类每一次传媒方式的革命也都伴随着民族主义复兴[18]。所以,民族主义与缅族婚姻很有可能在互联网时代拥抱得更为紧密。
结语
在缅族传统的婚恋文化中,基于社区共同体所开展的公共活动是未婚青年开始和发展恋情的重要场所。在婚恋对象的选择上,表现出对于不同族群的包容性,并且在爱情与婚姻中,强调个体自主以及两性平等。但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随着缅甸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缅族的民族主义思潮开始复兴,并且在缅甸佛教中引发了一股佛教至上主义的极端运动。在这一过程中,缅族的婚姻模式受到极大的影响,族群化约主义的盛行使缅族婚姻逐步固化在族内婚的结构中。许多缅族村落在长期执行族内婚以后变成亲属共同体,致使未婚男女的婚姻结合越来越困难,被迫采取独身主义的生活方式。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在缅甸乡村社会中的普及,基于网恋的新型婚姻模式开始盛行,缅族婚姻困境得到缓解。但这种新型婚姻模式到底会朝着什么方向前进,并且会在社会文化方面产生哪些更为深远的影响,现在还难以预知,值得持续观察与研究。
【注释】
[1] Gavin W. Jones,“Delayed Marriage and Very Low Fertility in Pacific Asia”,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Vol.33,2007,pp.455-457.
[2] Ibid.,pp.463-466.
[3] June Nash,Manning Nash,“Marriage,Family and Population Growth in Upper Burma”,SouthwesternJournalofAnthropology,Vol.19,No.3,1963,p.262.
[4] Lucian Scherman,Christine Scherman,Textiles,CraftsandCustomsofBurma’sWomenWorld,White Lotus Press,1910,p.19.
[5] Ibid.,p.20.
[6] June Nash,Manning Nash,op. cit.,pp.251-266.
[7] Gavin W. Jones,“The Flight From Marriage in South-East and East Asia”,JournalofComparativeFamilyStudies,Vol.36,No.1,2005,p.102.
[8] 刘稚:《缅甸民族问题的由来与发展》,《世界民族》1997年第2期。
[9] 焦佩:《族群冲突对缅甸民主转型的影响》,《东南亚研究》2014年第4期。
[10] 〈缅〉貌达著,曼德勒福庆学校译《文化古都中的龙的脚印》,《七日新闻周刊》2014年2月12日。
[12] 〈日〉村主道美著,刘务译《缅甸佛教徒与穆斯林冲突对其民主改革的影响》,《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4年第2期。
[13] 郭继光:《缅甸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宗教冲突探析》,《东南亚研究》2014年第6期。
[14] 同[12]。
[15] Robbins Burling,“Burmese Kinship Terminology”,AmericanAnthropologist,Vol.67,No.5,1965,pp.116-117.
[16] 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9页。
[17] 钟智翔、尹湘玲:《缅甸文化概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第154页。
[18]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8-46页。
【责任编辑:吴宏娟】
The Predicament and Breakout of Marriage: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n the Marital Change in Bao Village of Myanmar
Zhong Xiaoxin
(Centre for Studies of Chinese Southwest’s Borderland Ethic Minorities, 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091, China)
Keywords:Myanmar; Burmese; Marital Change; Ethnicity; Buddhism; Internet
[收稿日期]2015-12-30
[作者简介]钟小鑫,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民族学专业2014级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2014年度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高地建设规划项目”。
[中图分类号]D733.7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99(2016)02-0105-07